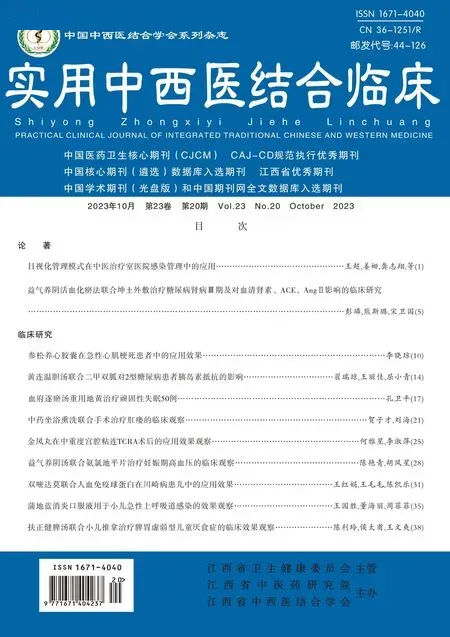積極心理暗示聯合漸進性肌肉放松訓練對食管癌化療患者心理狀態及應對方式的影響
孫起 仲立新 張建東
(河南省南陽市第一人民醫院 南陽 473000)
食管癌是消化道常見的惡性腫瘤,以進行性加重的吞咽困難為主要表現,發病率、病死率較高。我國是世界上食管癌高發地區之一,每年平均病死約15 萬人[1]。早期食管癌患者盡早行手術治療均可獲得較好的預后,但多數患者出診時已發展至晚期,此時化療是治療該病的主要手段[2]。化療通過使用化學治療藥物殺滅癌細胞,可延長食管癌患者生存時間,但同時化療會給其帶來強烈的應激反應,給其身心造成不良影響,易產生不同程度的負性情緒,使應對方式發生改變[3]。相關資料顯示[4],化療的惡性腫瘤患者均伴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和生理應激反應,積極面對行為普遍較低。而積極面對行為較低,可出現退縮性行為,影響化療進程,不利于患者預后。漸進性肌肉放松訓練(PMRT)是一種有效、漸進地使肌肉先緊張再放松的訓練,可調節人體生理、心理的緊張狀態。積極心理暗示是采用含蓄的方式,借助行動、語言等手段,從而達到影響他人心理與行為的方式。本研究旨在探討積極心理暗示聯合漸進性肌肉放松訓練對食管癌化療患者心理狀態及應對方式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倫理批號:20201206XT)。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2021 年1 月至2023 年1 月,醫院收治的90 例食管癌患者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45 例。對照組男30例,女15 例;年齡40~75 歲,平均(56.78±6.03)歲;體質量指數19.5~29.2 kg/m2,平均(23.54±1.30)kg/m2;TNM 分期:Ⅱ期16 例,Ⅲa 期14 例,Ⅲ期15例;病理分型:腺癌17 例,鱗狀細胞癌10 例,小細胞癌18 例;病變部位:胸上段食管29 例,胸下段食管13 例,頸段食管3 例;已婚42 例,未婚3 例。觀察組男32 例,女13 例;年齡41~73 歲,平均(56.84±6.12)歲;體質量指數19.1~29.7 kg/m2,平均(23.62±1.24)kg/m2;TNM 分期:Ⅱ期19 例,Ⅲa 期12 例,Ⅲ期14 例;病理分型:腺癌18 例,鱗狀細胞癌11 例,小細胞癌16 例;病變部位:胸上段食管28 例,胸下段食管11 例,頸段食管6 例;已婚40 例,未婚5 例。兩組一般資料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 入選標準 納入標準:符合食管癌的診斷標準[5],且經食管鏡和活檢確診;患者及家屬知情簽署知情同意書;意識清楚,能正常溝通。排除標準:精神疾病者;聽力不全或視力障礙者;合并其他惡性腫瘤者;預計生存期<6 個月者;嚴重心、肝、腎功能障礙者;認知功能障礙者;依從性差,不能配合完成本研究者。
1.3 干預方法 兩組均行相同的化療方案。對照組采用常規護理,包括健康教育、營養支持、運行干預、心理干預等。觀察組加用積極心理暗示聯合漸進性肌肉放松訓練,具體措施如下:(1)心理暗示。第一,行為暗示。使患者家屬認識到其參與的重要性,獲得其全面支持和配合。使家屬減少對患者的探視,同時護理人員亦減少巡視次數,以使患者相信自己病情好轉。第二,語言暗示。采用安慰誘導性語言向患者傳達一種信息,即食管癌是危害人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天敵”,而化療藥物是“武器”,可消滅“天敵”,且“武器”的效果與心理狀態密切相關,心理狀態好,“武器”才能發揮較好的治療效果,以激發患者自我控制應激反應能力。第三,安慰劑效應。若患者經過短期化療后,病情仍未得到有效的控制,此時可采用“相信”“預期”等暗示患者病情正在逐漸好轉。第四,榜樣暗示。組建微信群,在群體分享化療成功的病例,采用潛移默化的方式緩解患者負性情緒,促進形成積極的應對方式。每日至少采取兩種心理暗示方式,每天至少實施2 次,連續實施3 d。(2)PMRT:將PMRT 的步驟制作成MP3,于化療前1 d 向患者發放,詳細講解并示范16 組肌肉訓練流程。為患者提供安靜的環境,保持25℃左右的室溫,剛開始的連續3 次訓練由護理人員協助進行,待患者掌握后根據音頻后自行訓練。囑患者跟隨MP3 每天14:00~16:30 和晚上19:00~20:30 期間進行訓練,30 min/次。干預過程中采用TD-2A 生物肌電反饋儀監測放松情況,肌電值下降表示放松訓練患者已掌握。兩組均干預至出院。
1.4 觀察指標 (1)心理狀態:于入院時、出院時采用中文版簡明心境量表(POMS-SF)評估,包含緊張焦慮(0~24 分)、疲乏遲鈍(0~20 分)、迷惑混亂(0~20 分)、抑郁沮喪(0~28 分)、憤怒敵意(0~20分)、精力活力(0~24 分)6 個分量表,前5 項為負性量表,評分越高表示患者心理狀態越差;最后1 項為正性量表,評分越高,心理狀態越好。(2)應對方式:于入院時、出院時采用醫學應對問卷(MCMQ)評估,包含回避(7 個條目)、面對(8 個條目)和屈服(5個條目),每個條目計1~4 分,面對維度評分高,且接受、回避評分越低則表示患者應對方式越積極。(3)希望水平和生活質量:于入院時、出院時采用Herth希望量表(HHI)和歐洲癌癥研究與治療組織生命質量測定量表(EORTC QOQ-30)評估,HHI 包含積極行為、對現實和未來積極態度、與他人保持親密習慣3 個維度,共12 個條目,每個條目計1~4 分,總分值12~48 分,評分越高表示患者希望水平越高;EORTC QOQ-30 包含共30 項,總分為30~126 分,生活質量與評分呈正相關。(4)護理滿意度:于出院時采用紐卡斯爾護理服務滿意度量表(NSNS)評估,共19 個條目,采用1~5 級評分法,滿分95 分,包括不滿意(≤56 分)、滿意(57~76 分)和非常滿意(≥77 分),非常滿意+滿意=總滿意。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2.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用()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應對方式評分比較 觀察組出院時的回避、屈服評分均低于對照組,面對評分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1。
表1 兩組應對方式評分比較(分,)

表1 兩組應對方式評分比較(分,)
注:與同組入院時比較,*P<0.05。
?
2.2 兩組心理狀態評分比較 觀察組出院時的緊張焦慮、疲乏遲鈍、迷惑混亂、抑郁沮喪、憤怒敵意評分均低于對照組,精力活力評分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心理狀態評分比較(分,)

表2 兩組心理狀態評分比較(分,)
注:與同組入院時比較,*P<0.05。
?
2.3 兩組希望水平和生活質量比較 觀察組出院時的HHI、EORTC QOQ-30 評分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3。
表3 兩組希望水平和生活質量比較(分,)

表3 兩組希望水平和生活質量比較(分,)
注:與同組入院時比較,*P<0.05。
?
2.4 兩組護理滿意度比較 觀察組護理總滿意度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4 兩組護理滿意度比較[例(%)]
3 討論
食管癌為一項重大的負性生活事件,可對患者心理和生理帶來應激反應,加之化療給機體帶來的毒副作用,會進一步加重患者心理和生理應激反應,進而損傷機體免疫功能,最終影響化療效果[6~7]。抑郁、焦慮、緊張是食管癌化療患者常見的消極心理狀態,患者若長期處于此種狀態而得不到緩解,將影響其化療積極性,出現回避、希望水平低等情況[8~10]。有研究顯示,我國約有20%~40%惡性腫瘤患者存在焦慮、抑郁情緒[11]。臨床常規護理缺乏針對性護理手段,對患者心理狀態、希望水平及應對方式的改善效果并不明顯。
應對方式是個體對環境作出認知性及行為性的努力,食管癌患者大多表現為屈服、回避等消極應對方式,不利于疾病治療,還會增加患者疾病的不確定感[12~13]。希望水平是指機體在行動前自我預期所能達到的目標水平[14]。本研究中,觀察組出院時的緊張焦慮、疲乏遲鈍、迷惑混亂、抑郁沮喪、憤怒敵意評分均低于對照組,精力活力評分高于對照組,回避、屈服評分均低于對照組,面對評分高于對照組,HHI、EORTC QOQ-30 評分及護理滿意度均高于對照組。說明積極心理暗示聯合PMRT 可改善食管癌化療患者心理狀態和應對方式,利于提高希望水平和生活質量,從而使患者滿意。心理學家巴普洛夫認為,暗示可通過一定的假設誘導機體竭盡全力實現這個假設的目標[15]。積極心理暗示通過間接、含蓄的方式可達到緩解患者焦慮、抑郁情緒的目的。本研究采用“預期”“相信”等語言對患者進行心理暗示,使其相信疾病在化療過程中正在往好的方向發展,且行為暗示中通過減少家屬探視和護理人員巡視次數,降低患者敏感度,使其相信疾病正在好轉,利于提高其希望水平。此外,榜樣暗示通過講述食管癌化療成功案例進一步增強患者治療信心,使其積極應對疾病。PMRT 理論基礎認為個體的心情包含“軀體”和“情緒”兩個方面,通過改變“軀體”的反應,“情緒”亦會隨之改變[16~17]。基于上述理論,通過PMRT 訓練,患者有意識地控制自身肌肉活動,可間接松弛情緒,緩解緊張、焦慮、恐懼等負性情緒,穩定心理狀態,直面疾病,積極配合化療,進而提高疾病治療效果,獲得良好的預后,改善患者生活質量[18]。
綜上所述,積極心理暗示配合PMRT 可明顯改善食管癌化療患者心理狀態和應對方式,提高其希望水平和生活質量,且可以獲得較高的護理滿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