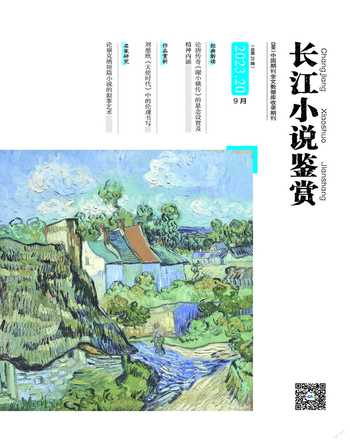擦亮人性之光的送終儀式書寫
孫渝鋒
[摘? 要] 石一楓的作品《漂洋過海來送你》通過溫情書寫向讀者展示了一場普通人的送終儀式。小說以其為原點,空間上橫跨中國、阿爾巴尼亞和美國三個國家,時間上橫跨那豆及其父輩、祖父輩三代人,以國際視野、歷史視野重構送終儀式的想象。《漂洋過海來送你》承接了無巧不成書的寫作模式,小說采用大量的巧合敘事,由此串聯以那豆為中心的擦亮人性之光的送終儀式書寫,體現了作者積極的寫作倫理。
[關鍵詞] 石一楓? 人性之光? 溫情? 巧合
[中圖分類號] 207.4?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20-0088-04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1]這里所說的“送死”,即送終儀式,中國傳統孝文化中送終儀式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五四時期,在“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感召下,“非孝”思潮使中國傳統孝文化遭到了猛烈批判,21世紀以來,送終儀式因人們觀念的變化也趨向簡單。在這個意義上,《漂洋過海來送你》記錄了一場浩大的送終儀式,其不僅是對傳統文化當代意義的重新發掘,更是基于溫情、國際視野和歷史視野等要素構建起的人性之光的表現。
一、送終過程的溫情書寫
承載道德倫理功能的喪葬文化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十分重要,而城市化進程的顯著加快使人們不再那么重視喪葬禮儀。
石一楓的《漂洋過海來送你》則講述了一個因殯儀館錯置了三位老人的骨灰盒,主人公那豆跨越大西洋尋回爺爺骨灰盒的故事。小說的主人公那豆的性格十分執著,作者石一楓在很多作品里都刻畫了“一根筋”型的人物,如《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執著于對道德問題刨根問底;《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的陳金芳執著于成為上層人;《借命而生》里杜湘東執著于追捕許文革以解開自己的心結。如果說《地球之眼》《借命而生》中人物執著的對象是宏觀意義上的社會道德,那么《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的陳金芳、《漂洋過海來送你》里的那豆描寫的則是普通人對自我追求的執著。正因為小說表現的是那豆為爺爺送終的主題,才使作品具備人文關懷的同時也有溫情筆觸。
如果把爺爺那年枝的死作為送終書寫的坐標原點,就不難發現,在爺爺生前和死后,那豆對送終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爺爺活著的時候,每當論及其身后之事如何處理時,那豆總會以“煩躁的疲沓的”語氣向爺爺承諾自己將如何料理周全。這樣的對話里展現的是爺孫二人對死亡的遙遠想象,而當爺爺真的去世了,那豆卻要對醫生們“起范兒”,對參加葬禮的胖矮老頭犯渾。前后的對比不僅體現了那豆在爺爺死后才發現其對爺爺的深厚情感,也構成了石一楓擦亮人性之光的送終書寫的邏輯起點。
小說中的那豆是一位時常“玩嘴”的“鼓樓花臂”,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小混混。而以小混混作為敘述者,“可以更加自然地運用口語,以及令看起來不那么可信的人物顯得真切一些”[2],也可以使讀者看到平凡人身上的人性之光。小說描寫了那年枝、那三刀、馬麗蓮、李固元、田谷多、何大梁、陰晴、陰大夫、黃耶魯等人,幾乎每個人都在送終儀式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且是整個送終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比如,那豆為了找回爺爺的骨灰盒辭去工作,獨自漂洋過海;李固元不僅承認自己因工作的失誤才造成骨灰盒的錯置,并且設計方案,為那豆盜取殯儀館的錄像資料;遠在美國的陰晴聽說爺爺去世的消息,主動與那豆聯系并尋找黃耶魯。
石一楓用質樸的筆調,構建了一個“應然世界”,通過跌宕起伏的情節,勾勒出不同的人對于送終的理解。作者筆下當然不全是正面人物,也有冷漠的人物,表達了作者對社會的反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殯儀館的客服經理,當那豆和父親第一次拿著爺爺的骨灰盒去找客服經理理論時,他們與客服經理的對話是兩種立場和兩套倫理規范的交鋒與博弈。那豆和父親拿不出可以直指殯儀館失誤的確鑿證據,而客服經理則站在殯儀館的立場上,拒絕父子二人所有的要求。到最后,父親那三刀只好說:“我們又不是來講法的,是來講理的。”[3]事情發展的高潮是那豆將“金屬碎片”“戳到了男人的禿頂上”[3],客服經理因此受了傷。最后客服經理請來法律顧問,通過法律手段平息了這場風波。對于客服經理而言,應付死者家屬只是他的工作,是程式化的、不摻雜感情的,正是因為客服經理這類人的冷漠,才襯托了李固元、陰晴等人的溫情。
作者在描述客服經理這樣一種人物時較為客觀,讀者感受不到他對客服經理的批判態度,只是將這樣一個人物描述出來而已。在與其他人形成對比的同時,也滲透著作者的自我反思意識,那豆和客服經理的沖突只是源于兩者立場不同,并無對錯之分。這也是作者在送終書寫中表達出的包容意識。
二、基于國際、歷史視野對送終圖景重構
當今的世界,是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在石一楓精心勾畫的每一個故事圖景中,讀者都可以感受到他在努力去觸摸時代脈搏的誠摯。”[4]小說《漂洋過海來送你》跨越中國、阿爾巴尼亞和美國三大空間場域,將送終儀式放在國際視野中觀照。作者懷著面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宏愿,以回憶的敘述方式將歷史與當下相連,講述了中國人的人性之光。
小說從第一部分的“來自太平洋西”到第二部分的“前往太平洋東”就為讀者呈現了從西到東的邏輯順序以及環繞全球的空間想象。作者在三個國家中分別描寫了故事中的三個主要人物,即那豆、何大梁和黃耶魯。三人將親人或兄弟的送終儀式選在同一個殯儀館,燒爐工李固元因此才有可能將三個骨灰盒錯置。但是作者講述故事并非采取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方式,而是由小故事逐步引出大故事,這體現了作者對文字的組織能力和想象能力。
錯置骨灰盒一事,是那豆發現、李固元證實的,小說因此引出何大梁和黃耶魯二人的故事。何大梁是在阿爾巴尼亞做工的建筑工人,起初他聽到骨灰盒錯置的事件時并不相信,一再向那豆索要證據。何大梁后來相信那豆是因為田谷多的體內曾有一顆螺絲釘,而自己所拿的骨灰盒里沒有。面對何大梁的求證,那豆并沒有“起范兒”,而是耐心地解釋問題,這意味著那豆這一人物的成長。反過來看,何大梁之所以向那豆再三確認,是因為這件事對何大梁也十分重要,這關系到他是否能成功地為他的兄弟田谷多送終。何大梁和田谷多的關系其實與石一楓《借命而生》中的許文革和姚廣斌相似,概括來說,田谷多解救了被騙到緬甸當苦力的何大梁,又帶著何大梁干橋梁焊工,田谷多替何大梁對鋼梁及標語牌進行加固焊接時發生意外,因全身粉碎性骨折而亡。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何大梁的命都是田谷多“借”給他的。因此,何大梁面對那豆時表露出的審慎,是因為害怕遭遇詐騙而表現出的保守和猶疑,也是他為田谷多送終過程中人性之光的反映。
譚雪晴指出:“作家在找尋骨灰的敘事主線之外,又設置了兩條故事線,一條涉及初到美國的年輕移民,另一條則指向在世界各地建造橋梁的外派勞工。”[5]何大梁與黃耶魯就是這兩條故事線的主要人物,這是作者基于國際視野對故事進行的建構。除此之外,作者還通過細節將歷史的經緯聯絡起來,書寫代與代之間的精神傳承。
小說中的李固元和那年枝都是勞模,李固元是省級勞模,而那年枝是街道的勞模,作者用三代人的生活方式呈現不同的時代樣貌。李固元、那年枝的思想受集體主義影響很大,那三刀、馬麗蓮受市場經濟時代影響頗深,到了那豆、陰晴這一代又主張張揚個性,是個性化的時代。石一楓在一篇文章中對代際關系里的“隔輩親”提出疑問:“幾十年來的中國人好像都在反對他們的父輩,但祖輩信奉的東西,是否會以變形的樣貌重現在孫輩身上?”[6]這一想法表現在小說中,即那年枝、李固元身上的集體主義思想是否會重新體現在張揚個性的那豆身上?石一楓是否在對那豆身上的人性之光進行溯源?《漂洋過海來送你》對此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那年枝在抗美援朝時期扭了腰,但他仍堅持工作,導致關節錯位,因此評上了勞模;李固元評上勞模則是因為在汶川地震時,殯儀館派他去清理遺體,他不僅給予逝者極大的尊重,并且幫助幸存者尋找家人下落。作者多次借那豆之口回憶那年枝的過往,包括醬油廠事件、搬缸事件和爬鼓樓看守紗布事件,等等,這一樁樁一幕幕,都使那豆在潛移默化中更加理解、敬佩爺爺,成為他尋找爺爺骨灰的內在動力。石一楓站在胡同口,“看到了市井人家,祖孫兩代之間流淌的精神延傳”[7]。正是基于此,那豆才十分堅持去殯儀館與經理理論,獨自跟蹤李固元以及辭職前往美國,這一切都是為了找到爺爺的骨灰。
石一楓把歷史與當下相連,并將其融匯在國際視野下,既承接了其小說創作的宏大視野,又生成了其小說寫作的世界影響,創作出了兼具國際性、歷史性和時代性的送終書寫。
三、展現人性之光的巧合書寫
《漂洋過海來送你》承接了石一楓無巧不成書的寫作模式,盡管并非通俗文學寫作者,但石一楓的作品兼顧了嚴肅性和通俗性。“石一楓的這部《漂洋過海》也體現了他一貫的寫作追求,即為了顯示自己對所謂純文學的不滿,往往不憚于借助通俗故事的敘事外觀,使得小說時常具有雅俗共賞的獨特氣質。”[8]“對于這部《漂洋過海》,其通俗的敘事外觀則主要體現在對于‘無巧不成書的敘事模式的充分借種”[8]。整部小說借助大量巧合書寫使情節環環相扣,最終爺爺的葬禮得以順利進行。這是作者積極寫作倫理的呈現,也是其借助送終儀式,將人性之光展現于巧合中的寫作方式。
小說的基礎由巧合構建而成。李固元恰好患有“美尼爾綜合征”,又恰好是李固元的發病導致他將那年枝、沈樺和田谷多三人的骨灰盒錯置,而三個骨灰盒中恰好有兩個都有異物。李固元的失誤以及盒中的異物使得整部作品的敘事得以進行。那豆攜帶金屬碎片(子彈片)過機場安檢時被攔下,他因此得到一位中年領導的幫助,這是因為中年領導恰好帶過兵,能認出金屬碎片就是子彈片,這甚至引出了連那年枝和沈樺的關系,他們一個是搬缸工人一個是軍醫,因抗美援朝相識,那豆和黃耶魯又因共同為沈樺掃過墓而相識。
在表現人性之光的時候,巧合發揮著極大作用,它能把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線索交織在一起,進而使小說的敘事圖景變得豐滿和充盈。李固元的發病這一巧合是為了交代三個骨灰盒錯置的原因,但由李固元的病所關聯起來的又不僅是三個骨灰盒,還有那豆、何大梁、黃耶魯這三個個體和那年枝、田谷多以及沈樺背后的三個家庭,中國、阿爾巴尼亞和美國這三個國家。作者把看似互不相關的個人、家庭以及國家通過一場巧合下的送終儀式關聯起來,書寫那豆哪怕漂洋過海也要找到正確的骨灰盒為爺爺送終的故事,這不僅是作者對自己的文字組織架構能力的呈現,也是對自己世界觀中“應然世界”的提煉。
巧合還充當著敘事的潤滑劑,“借助巧合所達成的敘事戲劇性,促使人物性格發展,作品主題深化”[8]。那豆攜帶子彈片過機場安檢時被告知不能通過,按照他以往的性格一定會“起范兒”,然而這次他耐著性子與工作人員溝通,當得到中年領導幫助后,那豆對“他們”(公職人員)的認識也發生了轉變,“他們”在那豆心中不再是抽象、刻板的群體,而變成了“具體的人”。實際上作者在這里借助巧合,展現出那豆的“變”與“不變”。通過找骨灰盒中的一系列磨煉,那豆由一個混混型的“鼓樓花臂”轉變成一個負責任的新青年形象,這是他從北京邁向世界的基礎,那豆性格上的發展合乎作家從講述中國故事轉向寫作世界故事的構想,使作品主題得以深化。
巧合還充當著洗滌劑的功用,它把與主干事件無關的內容加以凈化洗滌,將小說的線索清晰地呈現給讀者。石一楓通過抗美援朝將那年枝和沈樺關聯起來,又通過共同為沈樺掃過墓把那豆和黃耶魯關聯起來,其目的是為讀者釋疑,把故事中的人物關系再一次聚攏。對于巧合的解釋,小說中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事全栓一塊兒了”[3]。其實,正是因為“事全栓一塊兒了”,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人物形象才更加清晰,也更符合人物散發著人性之光的行為邏輯。
從表面上看,巧合僅僅指涉偶然性,實際上,它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結合。“如石一楓所一貫呈現的,《漂洋過海來送你》的最后,所有的人都獲得了人生的教益”[8],正是借助巧合的串聯,石一楓展現了自己堅持追求的“應然世界”,對人的本質做了深入細致地探究,彰顯了人性之光。
四、結語
作為“70”后作家,石一楓對于死亡有著獨特的理解。《漂洋過海來送你》以送終書寫為中心,將國際視野、歷史視野融入作品,通過巧合的方式以溫情的書寫講述普通人的人性之光。
本文從送終角度切入《漂洋過海來送你》,幫助讀者理解石一楓通俗易懂的語言風格下嚴肅的創作姿態,這體現了作家對社會問題的自覺關注、思考與回應以及對生命的價值、意義的理解。
參考文獻
[1] 孟子.孟子[M].武漢:崇文書局,2015.
[2] 石一楓.戀戀北京[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
[3] 石一楓.漂洋過海來送你[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
[4] 侯鰻娟.在現實中浮沉——論石一楓小說中的青年形象[J].新紀實,2021(23).
[5] 譚雪晴.廣闊現實的內在撕裂——從石一楓《漂洋過海來送你》看現實主義文學的困境[J].當代文壇,2022(3).
[6] 石一楓.小說創作中的幾組概念——從《漂洋過海來送你》說開去[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8).
[7] 張鵬禹.石一楓:好故事,一定能夠概括時代[N].中國青年作家報,2022-07-26.
[8] 徐剛.“一楓式幽默”、巧合,以及小說里的道德熱情——關于石一楓《漂洋過海來送你》的閱讀筆記[J].當代文壇,2022(3).
(責任編輯 陸曉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