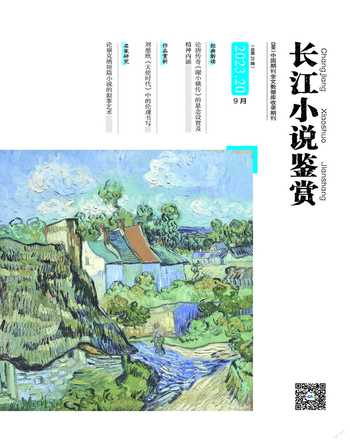論喬葉的鄉土小說創作
王嵐一
[摘? 要] 作為中國當代女作家,喬葉創作的作品類型十分豐富,有婚姻類小說《結婚互助組》、非虛構小說《拆樓記》、社會類小說《認罪書》,還有愛情小說《藏珠記》。《寶水》作為喬葉的新作,以新鄉村寶水村為主要記敘對象,塑造了許多農村女性形象,描寫了寶水村的生活,對故鄉的發展進行了思考。喬葉延續了一直以來的非虛構寫作方式,把人與人之間的真摯感情、青萍治愈自我的過程以及寶水村的振興融合在一起,展示了新鄉土小說的寫作新高度。
[關鍵詞] 《寶水》? 女性? 鄉土小說? 非虛構小說
[中圖分類號] I207.4?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20-0092-05
喬葉的新長篇小說《寶水》是一部鄉村題材的作品,描寫了寶水村的生活。地青萍是一個患有失眠癥的記者,因在城里被嘲笑和父親的去世,她不敢和自己的家鄉福田莊有過多接觸,她怕再看到那些熟悉的人、熟悉的地方,怕因此喚起她內心的傷痛。《寶水》的敘述始于一個關于福田莊的夢:奶奶去世前,有一些想說而無法說出聲的遺言,而青萍的失眠癥正是與這個夢以及她內心的傷痛有關。
作為女作家,喬葉擅長塑造女性角色,將女性的聲音融入小說中,她一直以來都在創作鄉村類型的作品,以村莊為敘述背景來講故事,例如《最慢的是活著》《拆樓記》等。在《寶水》的創作中,喬葉的女性化、鄉土化傾向更加明顯,從前的敘事中,其筆下的女性人物比較單薄,但《寶水》塑造了多元的鄉村女性形象,展現了女性所遭受的不公現象,對青萍來說,福田莊是傷心之地,而寶水村則是治愈之所,書名“寶水”既可以指一個具體的鄉村,也可以虛指鄉村的巨大變化,這是喬葉的創作視角的新變化,也是對自己鄉愁的重拾。具體而言,喬葉在《寶水》中既繼續了自己的女性化、鄉土化的非虛構寫作,又對筆下的人物和鄉土寫作的手法進行了創新,力圖展現最真實的新農村圖景。
一、現實中的女性群像
喬葉的女性化創作擅以女性為主視角講述故事,她站在女性角度描寫女性面對壓迫時的無力,使讀者聽到了許多真實的女性聲音。
《認罪書》中被已婚男人梁知拋棄的金金,懷孕后意圖報復而嫁給梁知的弟弟梁新,既可恨又可憐;因父親被批斗而無奈受辱的梅好,最后在丈夫冷漠的注視下投河自盡;受父母輩恩怨影響的梅梅被迫與愛人梁知分手,當了副市長家里的保姆,最終失去貞潔和孩子。梁家的罪人毀掉了梅好、梅梅兩代女性的一生,而金金以復仇者的身份再次揭開梁家罪惡的秘密,梅好、梅梅的悲慘遭遇得以重見天日,該小說批判了梁家的罪人對女性肆無忌憚的壓迫。
《藏珠記》中的唐珠是唐朝人,14歲的時候父母救了一個波斯人,波斯人為了報恩,給了當時還是小女孩的唐珠一顆珠子,吃掉珠子后的唐珠才知道:“珠有異香長相隨,雨雪沐身保葳蕤,守節長壽失即死,若出體外歸常人。”[1]也就是說,這顆珠子可以讓處女唐珠長生不老、永葆青春,但一旦跟男人交合,她就可能會失去生命。在無窮無盡的歲月里,唐珠都活在對男人的憂慮與好奇中,她也曾想過為男人放棄生命,但結果都是不值得的,直到她遇到了金澤,才恢復了正常的生活。雖然唐珠最后擁有了愛人、孩子,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但她不僅為這種幸福等待了千年,還被歹人奪去了貞潔。喬葉深刻地意識到,女性的幸福是來之不易的,悲劇卻是普遍存在的。
《寶水》中,喬葉繼續沿用女性敘述視角,但又與《認罪書》《藏珠記》中的多角度、多角色敘述不同,從頭至尾都是地青萍一個人的講述,她也一改曾經對女性描寫的單一性、被動性,塑造了多元化的農村女性群像,并直面了農村存在的普遍問題。雖然男女平等的思想已被許多人接受,但寶水村的許多人仍然深受男尊女卑思想的荼毒。喬葉在《寶水》中不避諱地書寫了女性所面臨的問題,其中就有家暴問題。小說中對于家暴問題的描寫主要聚焦在婦女香梅的經歷上,喬葉用簡潔通俗的“那層膜”來概括香梅受害的這一章節,也暗暗點明了香梅被打的主要原因:曾經同別人談過戀愛。香梅的丈夫七成身體有恙,且知曉妻子曾經的經歷,憤怒且無能的男人打心底里認為香梅沒有了“那層膜”,所以經常家暴妻子。青萍和一眾女人勸說香梅離婚或報警,而無知的香梅有自己的想法:“滿村去看,男人打老婆也從沒人報警。都不報,我也就不報。”[2]而且香梅也認為女人應該為孩子默默忍受丈夫的家暴。面對家暴,農村女性不愿意報警,一是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沒有勇氣直面家暴帶來的輿論傷害;二是法律常識的缺失使她們難以想到用法律保護自己。法律意識的缺失是寶水村村民的普遍問題,不僅被家暴的女性不會利用法律保護自己,施以暴行的男性也完全沒有對法律的忌憚。作者借家暴一事,用青萍的視角帶讀者了解寶水村村民普遍的男尊女卑意識,即使是有本事、有作為的村支書大英,回家也要為男人洗手做羹湯;即使秀梅的男人是入贅女婿,婦女主任秀梅仍要伺候丈夫,把葷菜放到男人面前。在男權思想長久的影響下,男女平等在部分農村只是一句口號,現實中仍是男尊女卑的思想占據主導地位。由香梅被家暴一事,青萍聯想到了小時候在福田莊見過許多女性挨打的事,連自己的母親也被打過。青萍回憶起母親因與奶奶有沖突而挨了父親一巴掌,當時作為孩子的自己懵懂無知,多年后,家暴就發生在眼前,青萍再目睹女人被打時,自己已是淚流滿面、憤怒驚懼。青萍為香梅受到家暴而憤怒,也為小時候母親受的一巴掌而哭。
除家暴事件外,寶水村還發生了性侵事件。大英的女兒嬌嬌因被兩個游客性騷擾而抑郁,心理受到極大的創傷,大英為了女兒的名聲也只能閉口不談。留守兒童甜甜被老爺爺猥褻,青萍和支教老師周寧想幫助女孩卻無計可施。青萍發現周寧對性侵事件十分敏感,追問之下,周寧才說起自己曾經也受過侵犯。
讀者不難發現,《寶水》中,一旦提到女性受傷害的問題,就會聯系起另一件類似的事件,香梅挨打和母親挨打,嬌嬌、甜甜的遭遇和周寧的經歷都說明了這一點。人物和事件成對稱,相似的故事發生在不同人身上,更有力地證明了農村存在女性的聲音被遮蔽的情況,部分女性因缺乏知識和勇氣,受的傷害難以被社會大眾看到,喬葉用最真實的筆觸毫不避諱地點明了寶水村女性面對的問題。
面對這些傷害,喬葉并沒有讓她筆下的這些女性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而是用自己的方法反抗。香梅在屢次的家暴中終于對丈夫七成的多疑和專制忍無可忍,一次打軟棗的過程中,香梅趁著七成在陡坡上踩脫腳的功夫將丈夫踹下坡并按在草叢里踢了好幾腳,最終七成被送進醫院。雖然香梅的做法顯示了寶水村的女性對法律的認知不足,以暴制暴也并不是正確的反抗方式,但女性在面對傷害時不再忍氣吞聲,這顯示了某種主體性。而大英的女兒嬌嬌以及留守兒童甜甜所受到的侵害也使得寶水村的村民開始逐漸重視起性教育的問題。談“性”色變的文化傳統使許多女性羞于訴說自己所受的傷害,間接令罪魁禍首逍遙法外,而受害者卻被指指點點。值得慶幸的是,嬌嬌和甜甜沒有受到流言蜚語的傷害,而是得到了大學老師周寧和主人公青萍的幫助。嬌嬌犯病時,村里人默默用自己的方式保護著大英作為母親的脆弱,小女孩甜甜也能勇于說出老爺爺摸她的事情。在大學生周寧的囑咐下,小女孩懂得了老爺爺的行為是犯罪,如果再遇到這樣的事情可以找警察來解決。與此同時,寶水村的村民意識到了性教育的重要性。寶水村作為一個新舊融合過程中的新農村,女性的聲音逐漸得到了尊重和重視,曾經的男權思想糟粕正在被摒棄,作者在小說中直面這些農村現實問題,并讓人看到農村在思想上的進步。
此外,農村經濟也正在快速發展,許多農村女性的命運也因此改變,女性能自主地選擇與誰結婚,能在社會中貢獻自己的力量,作為農村發展的受益者也直接推動了鄉村的進步。小說中的村支書大英是女性干部,她不僅有家庭的壓力,也有工作的壓力,但她也十分強悍,大英作為女村支書,將寶水村的事務打理得井井有條,并且協助村莊發展旅游業,連楊鎮長都夸獎她是懂情明理的老大姐,大英在村莊的一番作為象征了女性的力量。婦女主任秀梅接觸到網絡后,在村里拍短視頻,逢人便提起自己的短視頻賬號,在秀梅的努力下,“寶水有青梅”在互聯網小有名氣,不少游客慕名而來,寶水村的旅游業因此發展迅速。秀梅的成功引得村里的婦女效仿,秀梅作為婦女主任一點不藏著掖著,對她們傾囊相授,鼓勵村里的婦女創立自己的視頻號,呼吁大家積極參與文化生活。《寶水》從不同角度突出了女性力量和女性聲音的重要性,不僅書寫了如今農村女性的群像,也彰顯了女性與農村的共同成長。
二、生生不息的鄉土化寫作
小說《寶水》的敘述主體一直是好友的老家寶水村,有老家的地方一定有鄉愁,鄉愁作為一種文化記憶,是許多文學作品中不可忽視的主題。隨著城市化節奏的加快,年輕人紛紛離開家鄉,鄉村漸漸衰敗,已經離開的人也不愿再回到鄉村。喬葉最早在長篇小說《拆樓記》中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還為這種人創造了一個名詞:“鄉村的叛逃者”[3],文本中“叛逃者”一詞,指的是主人公的閨蜜作為記者,形容主人公這樣生于農村,但離開家鄉后擁有了城市身份的人的統稱,而這些“鄉村叛逃者”也的確不愿再回農村,自然對鄉村的了解欲望大大降低,又何談鄉愁。鄉村主題是現當代文學一直以來的熱門話題,但從“十七年”時期到二十一世紀以后的鄉土小說,作者幾乎都是以知識分子的視角來描述村莊的,這種視角本身就與鄉村生活抽離開來,而《寶水》中的地青萍卻能夠融入鄉村,對鄉村進行事無巨細的記述,喬葉使用這種在場化敘述以及對河南地方性特征的敘述,力圖挽救“失去的鄉愁”,創作出新的鄉土小說。喬葉是一位河南籍作家,寶水村位于河南與山西交界的地方,且《寶水》的敘述語言雖以普通話為主體,但時不時穿插著河南俚語,能夠喚起人們心底的“家鄉煙火氣”。此外,喬葉還在小說中為老家進行了定義:“什么是老家?老家就是這么一個地方,在世的老人在那里生活,等著我們回去。去世的老人在那里安息,等著我們回去。”[2]文中的敘述者地青萍本不屬于寶水村,而寶水村因地處太行山區,優越的地理條件和擅長做生意的晉商使得這個小村莊發展成為旅游觀光地。青萍與寶水村的緣分起源于困擾自己許久的失眠癥,機緣巧合下,青萍在鄉下聞到了混合著麥香的牛糞味,常人都會掩鼻離開,而青萍卻被這牛糞的臭味吸引,白天不由自主地在牛糞地旁打轉,夜晚伴隨著牛糞氣息輕松入睡。青萍回到城市后認定自己不是被牛糞味所吸引,而是被牛糞地背后的鄉村氣息所吸引,因此便跟隨好友老原來到寶水村生活,見證了寶水村的發展過程。寶水村可以作為小說的一個空間主角,地青萍是寶水村的探查者和闖入者,身臨其境地記錄著寶水村的諸事,以撫慰自己內心的傷痛,引出自己對農村老家的鄉愁。
《寶水》采用了平行的敘事結構,分為“冬-春、春-夏、夏-秋、秋-冬”四章,這也對應了一年四季。寶水村位于河南、山西交界處,氣候四季分明,喬葉以春、夏、秋、冬為框,補充進與時節相對應的農俗內容,比如“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軟棗”[2],而在正月的冬天,村民則會去挖茵陳,因為“正月茵陳二月蒿,三月四月當柴燒”[2]。地青萍又回憶起福田村的農俗,她曾經在家鄉秋麥(秋麥的“秋”為動詞,意為收獲)、吃碾饌,青萍逐漸被寶水村治愈,回憶起自己在老家福田村度過的快樂時光,表達對家鄉的思念,寄托了心底的鄉愁。她可以熟練使用方言,也從側面突出了青萍對故鄉的鄉愁,寶水村、福田莊都有方言俚語,青萍對寶水村的各種方言土話十分熟悉,“大樣”是傲慢的意思,“不戧準”是不一定的意思,還有“乖不楚楚”“機不靈靈”等,青萍因能熟練運用這些方言而得到了當地村民的熱情回應。但青萍第一次在城市生活時,因為下意識的一句“怪卓哩”,被同學們嘲笑了很久,這令原本在家說方言的青萍立刻只說普通話了。方言羞恥深深地刻在了同青萍一樣的“叛逃者”心中,對方言的冷漠是失去鄉愁的一個明顯表現。喬葉正是運用這樣的對比來提醒人們拋棄方言羞恥、主動傳承方言、建構新時代具有地域性的鄉村文明,同時喚醒人們的故鄉情。喬葉認為:“寫作(《寶水》)這本書,我特別樸素的一個心愿是對故鄉和我自己的一個交代。”[4]這也正說明喬葉的初心就是希望一些從鄉村走到城市的人,包括作者自己,能在享受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的同時,不要忘記養育自己的老家,要關注故鄉的變化。
喬葉是一位擅長寫鄉村題材小說的作者,許多作品都是以鄉村為背景,例如《最慢的是活著》是以一個農村長大的孩子的眼光寫愛與親情;《拆樓記》寫的是一個鄉村叛逃者介入張莊拆遷所引起一系列現實問題。不過《藏珠記》卻是一個例外,小說創作的靈感來自熱播的影視劇,融合了穿越等奇幻元素,寫了一個跨世紀的浪漫愛情故事,怎么看都與鄉村題材沒有直接關聯,但《藏珠記》中,其實也暗含對故鄉的依戀。主人公唐珠從唐朝活到現在,她換過許多個名字,其中最愛“珠”字,因為唐珠正是千年前那個十三歲少女的真實名字,是父母給她的最初的名字。千年來,唐珠反復在夢中回憶起父母和家鄉的模樣,這是一種對親情和千年前的土地、故鄉的眷戀,唐珠游歷過中國許多地方,但最想念的還是自己最初的那個家,所有的一切都隨時間而改變了,不變的只有唐珠自己和她的名字,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上的鄉愁。
由此看來,喬葉對于故鄉以及鄉愁的認識與思考是一以貫之的,故鄉、鄉愁這些有關鄉村的情感載體一直是喬葉作品的核心,正是這些對鄉愁的思考構成了喬葉的鄉土寫作,只不過《寶水》能夠利用在場化敘述將鄉村設置為敘述主角,直面鄉村問題。《寶水》不僅繼承了喬葉鄉土小說創作的傳統,還能夠推陳出新,取材于寶水村這個小村莊的變與不變,延續鄉村的描寫的同時,加以突出鄉村生活的新舊變化,引發讀者的思考。取材者微,所見者大,喬葉用自己的所思所想使得地方性的鄉村題材作品更加細膩、扎實,更具有現代氣息,吸引更多人關注農村的發展,重拾“失去的鄉愁”。
三、“非虛構”的藝術手法
一方面,與喬葉以往的創作不同,《寶水》中有兩條不同的時間線,青萍敘述寶水村故事的同時,插敘了她對福田莊故鄉的回憶,采用了雙線并行的鏡像式結構。青萍目睹寶水村的香梅被家暴,回憶起福田莊的閨女、媳婦都被打過;寶水村的九奶使青萍想起自己的奶奶,也正是九奶的出現彌補了青萍對奶奶的遺憾;跛腳的光輝叔像極了青萍同樣跛腳的叔叔;寶水村的農俗節日也會讓青萍聯想起少時在家鄉參與過的農事。寶水村的一事一人都像鏡子一樣折射出老家福田莊的一點一滴,寶水村治愈了青萍在福田莊老家所受的傷痛,使她重新思考家鄉的意義,原本的福田莊“叛逃者”地青萍去往了鏡子的另一面——寶水村。
另一方面,喬葉在小說中延續自己一直以來的“非虛構寫作”傳統,在作品中喬葉永遠不忘回歸現實,走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拆樓記》是喬葉首部長篇非虛構寫作作品,通過在小說中加入了建筑的繪圖、實拍的圖片、寫過的作文以及上級部門在當時發布的通告等,以及敘述者對自己和姐姐親歷拆遷事件全過程的記錄,體現了強烈的現實主義風格。《藏珠記》的靈感來自電視劇,女主唐珠生于千年前的唐朝,但作者并沒有用那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風格來書寫作品。唐珠實際上只是一個普通人,除了不會生病、不會死亡外,沒有任何特異功能,她同樣會感到饑餓和疼痛,在其千年的生命中,還要時刻提醒自己遠離男人,她活得也很有壓力。
非虛構寫作的藝術手法貫穿著喬葉的創作,新作《寶水》是她的又一部非虛構作品,與《拆樓記》的社會現實,《藏珠記》的大膽想象、跨世紀的時空對話不同,《寶水》通過書寫新鄉村的生活來回望曾經的家鄉,呈現了現代鄉村的巨變。《寶水》展示了具象的現實生活,充滿了中國鄉村的樸實感。喬葉通過對四季作物的介紹描寫了農村最普通、最真實的生產生活,是農村人對于中國最傳統的四季農耕的認知,為城市讀者填補了地方農業知識的空白,還回應了當下熱門的“三農”問題。《寶水》緊隨時代的變化,在作品中展示現實生活。
喬葉曾總結過自己的小說創作經驗:一是讓傳奇的故事具有日常性;二是讓日常性的生活具有一點傳奇性[5]。她非常關注現實問題,把自己所知道的問題用文字表達出來,這也成就了喬葉一直以來的創作風格,在對非虛構寫作的堅持中,勇于突破敘事的時空限制、大膽想象新農村的巨變,用自己最真實的經驗創作出《寶水》這部緊跟時代、展現新農村巨變的小說,為許多淡忘了鄉村生活的城市人注入對新農村的向往。
四、結語
讀者在《寶水》中見證了鄉村正在發生的變化,小說展現了當下的農村全景圖。在寶水村里新與舊交織,一方面,喬葉直面了農村家長為了打工忽視留守兒童的關愛教育和男尊女卑思想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展現了農村里有了通過網絡發展旅游產業等新氣象,是鄉村現實最具象的描寫。在語言上,喬葉用質樸且充滿地方特色的語言建構其鄉土化的特征。喬葉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寫進《寶水》中,河南地方土語頻頻出現,各種典故、農俗也都被喬葉詳細地寫了出來,獨具地方性。在敘事上,喬葉聚焦于對鄉村審美空間及現實變化的描寫,致力于非虛構寫作,介紹了不少野菜、野花的食用辦法與成熟季節等知識,這是對農村空間之美的現實描寫,同時又能表現出農村的快速現代化進程,還反映了農村切實存在的問題,比如法律意識淡漠的問題。她還表達了對鄉村女性的心靈、情感的關切,提醒女性要增強保護自我的能力,從而獲得更多的自由空間。喬葉的作品《寶水》使更多人重新關注農村的發展問題、關注農村悄然發生的新變化,展示了鄉土小說寫作的新高度。
參考文獻
[1] 喬葉.藏珠記[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2] 喬葉.寶水[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
[3] 喬葉.拆樓記[M].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12.
[4] 李婧璇.專家研討長篇小說《寶水》為鄉村振興留下有力的文學記錄[N].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3-03-08..
[5] 江磊,喬葉.非虛構寫作在努力拓寬文學創作的邊界——喬葉訪談錄[J].寫作,2020(1).
[6] 張天宇.“風景”的發現與新時代鄉村美學的建構——讀喬葉《寶水》[J].當代作家評論,2023(3).
(特約編輯 劉夢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