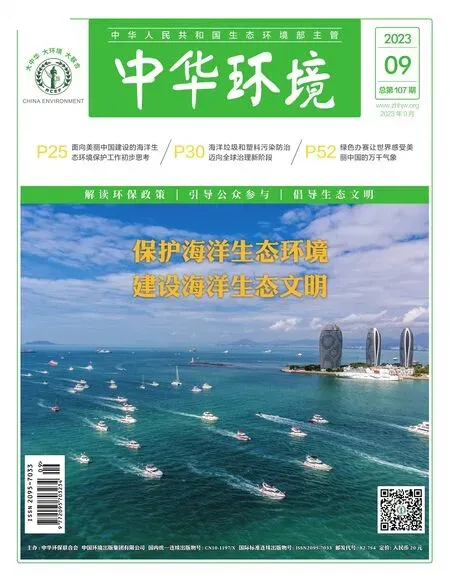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防治邁向全球治理新階段
文|楊越 陳玲 薛瀾
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防治一直是國際海洋環保領域熱議的話題。大量的現實觀察和科學證據表明,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引發的視覺污染、生物纏繞、漁業減產、航行安全、生物體積聚等問題,正在嚴重威脅著全球海洋生態系統的健康以及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國際社會就該問題的關注逐漸從呼吁倡議階段轉向實質性管控階段,但已有治理策略和行動呈現出機制約束力弱、場景協調性差、主體合力不足、措施無序化碎片化等總體特征。面對有別于陸源污染的治理需求,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治理的困境亟待破局,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治理框架呼之欲出,全球治理體系加速重構,“塑料條約”的達成也將標志著該問題正式邁向全球治理的嶄新階段。我國作為較早認識到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危害,并參與和引導全球治理的國家之一,如何為促成條約的順利達成貢獻中國方案,如何通過完善政策體系、開展有效行動、分享最佳實踐以響應未來的國際履約需求,成為當下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治理體系建設的焦點問題。
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治理的進程
國際上針對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防治問題大致經歷了意識覺醒、行動呼吁和全球治理三個階段。
意識覺醒階段:科學認識加深,治理需求不斷萌芽
自20世紀70年代就不斷有研究發現海洋中存在大量的塑料碎片,并預測隨著塑料生產量的快速增加,越來越多的塑料垃圾將進入海洋并危害海洋生態系統健康。以1995年海洋廢棄物被正式納入《華盛頓宣言》為標志,該問題開始逐漸引起全球各界的關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分別在2003年牽頭發起“海洋垃圾全球倡議”、在2012年發布《海洋垃圾全球伙伴協議》,鼓勵圍繞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的源匯分析、通量估算、遷移機制、對生態系統及人類健康的風險評估等問題展開科學研究和監測論證。自此,人類對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危害的認識不斷加深,從而激起了針對海洋垃圾及塑料污染的治理需求,這一時期被認為是意識覺醒的階段。
行動呼吁階段:全球框架初現,治理成效有待提升
以2014年第一屆聯合國環境大會首次通過“海洋塑料廢棄物和微塑料決議”為起點,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防治問題開始進入行動呼吁階段。該時期以聯合國環境大會連續四屆通過五項有關海洋垃圾的決議為代表,不斷呼吁各國應在海洋塑料管理方面采取預防性措施。世界范圍內也開始涌現出大量有關消減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的行動實踐,并逐步形成了覆蓋全球、區域、國家三層機制,聚焦陸源輸入、濱海旅游、船舶運輸和海上養殖捕撈四大場景,包含國際組織、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及公眾五類主體的治理體系,全球范圍內針對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的治理框架雛形基本形成。由于該時期尚未形成針對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單獨規制且就履行義務對締約國具有強制約束力的治理機制,無法針對治理措施的實施情況進行督促和監督,治理成效稍顯不足。
全球治理階段:談判道阻且長,治理目標趨向收斂
實際上,在第二階段就開始有多個國際組織和國家開始深入研究、呼吁采取行動共同應對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問題,將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防治問題逐漸推向全球治理的層面,包括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G20海洋垃圾行動計劃”、聯合國環境大會內羅畢倡議發起的“清潔海洋行動”等,呼吁盡早形成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全球治理框架。直到2022年2月召開的第五屆聯合國環境大會第二階段會議,上述努力才取得了歷史性的進展,大會通過了關于《結束塑料污染:爭取制定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的決議,標志著塑料污染問題正式邁入全球治理階段。與此同時,“塑料條約”政府間談判(INC)也就此啟動,目前INC已于2022年11月和2023年5月分別召開兩次會議,并于2023年9月發布《塑料公約零草案》,該草案旨在為即將在11月召開的INC-3提供指導和支持,具體實施細則有待進一步磋商。從艱難的談判過程就可以看出,盡管要想兼顧各締約國的利益訴求順利達成共識道阻且長,但只要各締約國能夠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義面前堅持開放合作的態度,求同存異,全球塑料污染治理的目標終將不斷收斂達成一致。
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治理的難點
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帶來有別于陸源污染的治理困境,因而有必要在治理體系的設計上創新思路,才能有效開展污染治理。
入海渠道豐富、管控環節復雜,需治理場景的覆蓋協同
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的入海渠道十分豐富,除了通過地表徑流和岸灘潮汐等將陸源塑料垃圾排入海中以外,亦可通過海上作業、船舶航行、養殖捕撈等渠道入海,從而導致需要治理的場景更為復雜。國際上普遍認可的治理措施多集中在塑料制品加工、消費和處置場景,很多國家缺少向塑料原材料生產環節以及塑料廢棄物的循環再利用環節的延伸,針對入海攔截、岸灘清理及海上打撈等場景的治理措施目前仍處于探索階段,尚未將入海塑料納入現有回收再循環產業鏈,沒有實現真正的“全生命周期管控”。因此,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治理的第一個難點在于治理措施能否覆蓋全部管控場景并實現場景間的協同。
遷移路徑復雜、責任分擔不清,需治理主體的合力協作
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遷移路徑復雜,塑料垃圾一旦入海,可形成漂浮、懸浮以及沉降的立體化污染,浸泡、裂解、附著、沉降等物理生物過程又使這種立體化分布具有動態隨機性,增加了清理難度和技術成本。且海洋的連通性加之低溫、季風、潮汐及洋流等因素更是造成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遷移路徑復雜,無疑增加了就責任分擔問題達成一致的難度。因此,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治理的第二個難點在于如何讓更多的治理主體參與進來,形成多元協作的合力。
損害代際顯現、治理動力不足,需治理機制的長效激勵
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危害的代際性特征容易導致治理動力不足。海洋中的垃圾會造成生物纏繞、漁業減產等危害,塑料及微塑料污染極易被海洋生物攝取并隨食物鏈富集傳遞,對生物體的存活率、生長發育、行為活動、生殖狀況、基因表達等方面造成影響。但生物體富集需要一個過程,隨食物鏈傳遞到人類體內的過程和機理漫長而復雜,代際性的影響特征較為明顯,這導致人類為此而付諸行動的內生動力嚴重不足,制約了污染治理參與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以及治理行動的長期有效性。此外,受到海水長期浸泡的塑料性能將大幅下降,導致循環再利用的成本過高,使得原本就微小的利潤空間進一步被擠壓,企業參與回收和漁民主動打撈的積極性也會受到嚴重制約。因此,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治理的第三個難點在于如何確保治理機制設計的長期有效。
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治理的應對策略
作為較早認識到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危害,參與并引導全球治理的國家之一,我國始終高度重視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治理問題,并在科學論證、污染監測、制度建設、實踐探索等方面積極行動。隨著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治理邁向新的階段,一方面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快推進國內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治理體系的建設,通過完善政策體系、開展有效行動,降低海洋生態系統破壞造成的經濟和生態損失,引導泛塑料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逐步形成海洋塑料垃圾及微塑料污染的長效治理機制;另一方面需要我們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全球治理的進程中去,通過聯合研究、分享最佳實踐,聯合響應國際履約需求,始終秉持開放合作的態度,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踐行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大國責任與擔當。
完善塑料全生命周期的廢物管理過程
“從源到匯”實現廢物的資源化再生,將城鄉廢物管理過程延伸至岸灘及近海,組織海上清潔隊,并將其納入城市環衛系統;原有“廢物的管段預防”向塑料原材料生產環節以及塑料廢棄物的循環再利用環節延伸,從原材料生產階段的生物替代、制造階段的綠色設計、可持續的消費方式、采用集中回收的方式進行廢物管理、恢復循環再利用等方面著手,提升塑料產品的可重復利用率,減少塑料廢棄物的產生。同時,改進廢棄物處置管理過程,增加廢物循環再利用,解決塑料垃圾入海前的積聚問題。
建立陸海統籌的塑料污染綜合防治體系
設立跨部門的協調委員會或專家委員會,重點放在行動的落實和各部門協調上,不同于先前的基于部門的管理,提供一個跨部門的機制來促進整個計劃和單個部門政策的協調,從而提升決策效率以及資源配置效率。打破單純以行政區域檢測結果作為考核指標的弊端,逐步形成以流域、海域或城市生態群為中心的陸海統籌的塑料污染綜合防治體系。
探索多元參與的海洋生態環境治理模式
要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在落實企業生產責任延伸制的同時,打通可再生及循環利用塑料產業鏈,拓寬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的資金來源,引入PPP模式提高塑料垃圾的回收和資源化利用率,探索企業參與海洋環境治理獲得稅收減免、綠色行為認證、納入企業綠色信用評級、可抵消減排量制度的可行性。
深化國際合作引領塑料污染全球治理進程
將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防治作為推動全球海洋治理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的重要內容,更加積極地參與和引領相關公約的談判,主動設計新的國際合作研究和實踐項目,以良好的實際行動體現中國在全球生態環境保護中的表率作用。此外,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將協同推進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防治作為重要議題,設計和推動若干重要合作項目落地,適時推動我國主導的區域合作機制形成,提升整個區域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議事能力和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