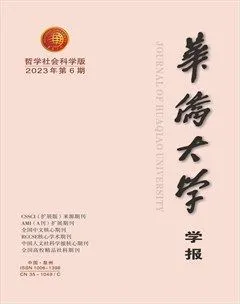美好生活的個體建構:赫勒日常生活理論的當代旨趣
摘 要:美好生活作為唯物史觀的應然理想,深植于日常生活的現實土壤之中。日常生活的拜物教特征導致了人的“自我異化”面貌,個體“自我異化”實質在于資本剝削人們生產的勞動異化,勞動異化導向消費領域,社會層面的符號拜物教就此出現。數字化時代,個體生活面臨著平臺技術與資本剝削共謀的數字規訓。從勞動異化到數字拜物教,個體“自我異化”的加速反映了日常生活的沉淪現狀也預示了推進其變革的可能。東歐馬克思主義者赫勒曾提出了變革拜物教的“激進需要”主張,認為個體需要的滿足是實現美好生活的基本前提,要從個體之維深化自為領域的日常生活變革,實現自在領域的美好生活建構。有鑒于激進需要的日常生活批判,新時代美好生活應從“人本生活”“藝術再創造”“審美體驗”幾方面實現對資本主義舊生活的超越,進一步彰顯唯物史觀“社會—生活—人”的理論視野。
關鍵詞:日常生活批判;異化勞動;資本規訓;激進需要;個體美好生活
作者簡介:張誠,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E-mail:2572499165@qq.com;浙江 杭州 31005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現代性的批判和重構:馬克思與懷特海的比較及中國意義”(19FKSB055)
中圖分類號:B82;C91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398(2023)06-0051-11
“美好生活”是人類社會孜孜以求的目標。在古代封建社會和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美好生活只能是絕大多數群眾的幻想與奢望。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人們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成為了人們最迫切的渴望。美好生活不是空中樓閣,而是建基于日常生活土壤之上。日常生活涉及人存在的方方面面,如我們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的吃、穿、用、休閑等。實現美好生活意味著要對人們的日常生活進行整體變革。
日常生活批判是對現代性背景下人的生存面貌的反思與回應。近代以來,隨著現代性秩序的確立,資本以一種“非神圣形象”取代了中世紀宗教社會塑造的上帝“神圣形象”,并全面接管了人們的生產生活,對個體日常存在的反思成為哲學家們關注的焦點。從19世紀馬克思對生產領域中工人勞動異化的人道主義批判開始,到20世紀鮑德里亞關于消費社會的情景主義解讀,再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對社會物化的病理分析,及其學生赫勒在二戰后從事的日常生活人道化、激進需要與激進民主等批判理論研究。近年來西方又涌現出了韓炳哲“倦怠社會”等理論,著力刻畫出數字化時代個體生存的困境圖景。西方學者對于日常生活圖景的探討,描繪了現代性背景下個體生活樣式的演變,這為當代美好生活實踐提供了歷史性的借鑒與時代性的啟發。
一 日常生活中個體“自我異化”面貌
早在19世紀馬克思就提出,對資本主義的現實批判在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頁。)。之后的列斐伏爾也強調,“日常生活批判完全是圍繞著異化理論建立的”([法]亨利·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葉齊茂、倪曉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2頁。)。自人類社會進入工業文明,隨著現代性統治秩序的確立,大眾在日常生活中承受著資本家剝削其勞役的勞動異化。在生活環境異化的背景下,人們被迫從事非自愿的生產活動,為資本家制造出更多數量的商品。商品的激增刺激了大眾消費活動的興盛,勞動異化開始向著消費領域蔓延,出現了大眾符號消費、奢侈享樂等社會風氣。如今資本剝削又具備了數字化肌體,大眾在數字消費中表現出低俗化娛樂化的審美取向,多重異化的相互疊加構成了日常生活中個體“自我異化”的形象。
(一)實質:資本剝削工人生產的勞動異化
勞動確證了人的本質,表現為人類對象化的生產活動。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通過考察人類歷史發展的前提條件,指出“原初的歷史關系”表現在生活資料的生產。生活的來源即生產,“第一個歷史活動”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生活的主體是從事物質生產的“現實的人”,人的需要首先表現為物質生存的需要,“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頁。),并會在此基礎上產生新的需要。“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頁。),人通過勞動生產出各種物質資料來滿足多樣化的生存需要。
而在19世紀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確證人本質的自由勞動異變為雇傭勞動,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得以延續的條件。通過考察工人在艱苦的生產條件下被資本家持續壓榨的勞動景象,馬克思揭示了存在于商品生產背后的資本主義占有本質。工人在生產中,既要創造出遠超于資本家支付的工資價格以外的超額價值,又要為資本家謀取私利而持續從事生產。在資本家的安排下,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緊密結合,原屬于個人支配的勞動被轉移到物的商品屬性上,商品成為了監督和奴役工人生產的主人,“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6頁。)。
資本壟斷下勞動者與勞動產品相異化,雇傭勞動使得工人的生產表現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并上升為統治工人生命的主宰。工人從事勞動本是為了獲取維持生命所需的生產資料,但卻被資本家強占。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是資本剝削工人勞動的秘密所在,“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已經作為他人的財產而和勞動力的所有者相分離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頁。),為了維持生存,工人不得不出售勞動力為資本家生產而服務,勞動被異變為資本增殖的工具。即死勞動支配了活勞動,物統治了人。
物對人的統治越強,人在生產中感受到的就越是精神高壓與肉體痛楚,“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棚舍(《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8頁。)。一旦肉體的強制消失,“人們就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9頁。)。在資本家眼中,工人被當做“僅僅有最必要的肉體需要的牲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5頁。)。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看似“仇視”奢侈的資本家們實際上卻享受著“需要的精致化和滿足需要的資料的精致化”(《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25頁。)。資本家憑借著對工人勞動的剝削,過上了精致富足的奢侈生活,更暴露出資本為追求財富積累而無止境剝削工人的丑惡本性。
勞動異化直接的惡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出現,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工人的命運體現了社會發展的寫照,“物化就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現實”(俞吾金:《馬克思對現代性的診斷及其啟示》,《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第9頁。)。商品結構成為了社會生活的統治法則,商品的價值本是來源于勞動者的生產勞動,但是由于商品的物化面紗掩蓋與遮蔽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導致了人們對商品神秘性的反向崇拜。“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頁。),這種拜物教來自于雇傭勞動對人“自我異化”的物性奴役。
(二)外象:異化勞動導向符號消費癥候
資本剝削勞動目的是為賣出更多的商品從而獲得超額的貨幣量,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潛在地擁有兌換一切商品的魔力,并且被世人視作新的“上帝”來崇拜。“貨幣拜物教的謎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謎,只不過變得明顯了,耀眼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13頁。)馬克思將商品向貨幣的轉化稱為是“驚險的跳躍”,商品一旦沒有及時出售掉就會被“摔碎”。只有完成了“驚險的跳躍”,整個生產過程才得以完成,社會再生產才可以接續開展。由此,如何激發大眾的消費欲望從而加速完成商品向貨幣的跳躍,成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新課題。
鮑德里亞在借鑒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基礎上,將19世紀生產領域工人的原子化境遇延伸至20世紀消費生活的語境,揭示了消費社會中龐大的符號景觀對人的需要的蠱惑。他認為,當代社會生產的統治地位已經被消費活動所取代,“生產主人公的傳奇已到處讓位給消費主人公”([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0頁。)。在生產社會中,人的現實關系被商品所掩蓋與替換。而到了消費社會,人的現實性只存在于符號的編碼體系中。消費異化成為了日常生活新的特點,當代人被抽象的符號編碼所統治。
個體的欲望成為資本新的生產對象。昂貴商品不再是資本家的專屬,普羅大眾也可以享用到除必要生活資料以外的新式商品。在資本建構的消費話語中,擁有同類的商品已經不再區分出人與人之間階層身份的差異,奢侈品以一種階層區分的證明成為了消費的新寵。奢侈品作為超出了人們生活必需的商品種類,具有遠高于自身使用價值的高額價值量,這種價值量源于資本所構建的商品符號。奢侈品等商品本身并不是生活必需的,但資本操縱的符號話語卻在牽引著每個人的欲望:我們需要它,只要擁有了奢侈品所蘊含的符號價值,我們的生活就會得到極大的改善。
符號消費成為商品生產的新意象,“被消費的東西,永遠不是物品,而是關系本身”([法]讓·鮑德里亞:《物體系》,林志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4頁。),消費指向的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物質商品,而是符號的象征邏輯。被消費的不再只是物品,更是符號所指的意象,商品變成了符號的游戲,意象消費延伸到社會文化全方位,將所有的實在之物都變為可消費的對象。“人們從來不消費物的本身——人們總是把物(從廣義的角度)用來當作能夠突出你的符號”([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第41頁。),消費不再是對某一具體物品的需要,而是對差異性的需求,符號價值的象征意義主宰了社會生產。
符號的消費景觀源于資本對商品拜物教的圖像化改造,“拜物教所揭示的并不是對于實體的迷戀,而是對于符碼的迷戀。”([法]讓·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夏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06頁。)通過對人的欲望的把控,資本以圖像形式將商品的物質特性轉變為生動的圖騰象征。作為當代社會的拜物教肌體,符號景觀展現了類似于遠古時期宗教圖騰對個人精神世界的強力掌控,并幻化為無數美輪美奐的精致商品。超市貨架上琳瑯滿目的罐頭食品、服裝、點心,街道上光芒四射的櫥窗,商家舉辦的各種購物節等等,鮑德里亞筆下的這些20世紀的符號景觀,在今天依舊盛興。在令人眼花繚亂的符號世界中, 人的欲望被解構后再予以圖像化的重構,并鑄造了一個個消解了生命本真樣態又超越真實生活的抽象世界。
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商品流通過程中,只有商品進入消費環節并實現“驚險的跳躍”,生產的總體過程才算完成,新的社會生產也得以接續展開。因此消費是生產的歸宿,也是新的生產的開始。由實物生產指向符碼消費,在此過程中商品本身也呈現出“去真實”趨勢。資本以符號消費的方式實現了貨幣量的龐大增殖,構筑起眾多的不屬于任何實在主體、而是僅依靠文化概念建構、存在于人們頭腦觀念中的形形色色景觀。
(三)新貌:異化勞動換顏為數字拜物規訓
由商品生產到貨幣增殖,資本拜物教的表現形式愈發潛匿。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科技的興起,如今的商品生產具備了數字化肌體,數字勞動應運而生。在數字生產中個體勞動被虛擬化,并使勞動產品對象化為非實物的“數字商品”。數字商品的出現,也使得資本增殖表現出“數字拜物教”新形式,即通過量化與神圣化數字商品的價值,創造出遠超于其使用價值的交換價值,從而形成了“數字拜物教”的消費崇拜。
數字技術催生出多重類型的數字勞動,呈現出隱蔽性的新型剝削,表現為個體在數字平臺上無償提供的“自愿勞動”、群體在數字媒體監視下被迫的“全景敞視勞動”(福柯在“環形監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全景敞視主義”概念。環形監獄(panopticon)由哲學家邊沁于1785年提出,這是一種適用于任何組織的建筑構想。在此類圓形建筑中,角落里的囚徒的言行無時無刻不被居于中央塔臺的掌權者所監視。福柯則認為現代社會是“監視社會”,“懲罰”與“規訓”構成了社會權力機制的編織模式。監視社會施加給每個個體的不再是肉體的摧殘,而是更加隱秘的精神控制。)等多樣形態。個體生產不再簡單地表現為繁重的體力勞作,人們“主動”地成為平臺所驅使的“數字勞工”,在線上平臺從事著數據制造與內容加工。數字平臺上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緊密結合,用戶在平臺上留下的大量的消費數據都為資本無償占有,數字成為資本生產的原材料;而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信息技術在為傳統產業賦能的同時,以數字形式構筑起監視個體勞動的“全景敞視”平臺,客戶在線體驗的一系列活動,如視頻聊天、網上購物、圖片剪輯、影像娛樂等數字休閑活動皆被后臺的資本家所監視。監視場所由工廠車間轉至線上媒體,監視范圍由公共生產轉向私人生活,監視對象由勞動工人轉為全體社會成員,造成了技術監視在日常生活中的無處不在和無所不至。
數字商品的生產呈現為平臺化的圖像體驗,經由圖片的擬像化處理,商品的符號內涵被以更加直觀和感性的方式傳遞給消費者。人們零距離地與手機屏幕上的主播們進行情感的互動,通過線上平臺的點贊、發言、刷禮物等方式來尋覓個體存在的意義。自媒體的盛行,使公開的網絡空間內充斥著各種炫個人“精致感”的旅行照、居家照、婚戀照、工作照的眼球商品,在美圖生產與消費中實現了“產消合一”。通過購買各種奇異另類的網紅產品,人人都以精致圖像來點綴自身“完美”人設,而時下流行的擺拍、美圖、種草等分享方式也為個體“精致生活”創造了身份認同的機會,花樣繁多的“炫”“曬”“秀”都是數字社會的異化圖景。
平臺上用戶看似多樣化的審美體驗,實際上卻是資本以“休閑”與“愉悅”的虛假標簽,投擲出消費誘餌以吸引用戶主動參與的事實勞動。這種數字化審美活動將人們的休閑體驗演變為平臺場域中的數據生產,使人的勞動更直接地服務于資本增殖的欲求。“當我們在臉書上展示自我,也因此把自身變成了商品”([德]韓炳哲:《倦怠社會》,王一力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第102頁。),這只能帶來日常生活中人的類本質的異化。
“生命變成了商品,導致了儀式和慶典的消失”(
[德]韓炳哲:《倦怠社會》,第102頁。
)。數字時代人的異化樣態,呈現出從真實生活感受向虛擬感官刺激的全面蛻化。在新技術加持下,資本與數字平臺合謀打造出了逼真的虛擬世界,包括對媒介自身的圖像影訊、媒介與人之間的訊息傳播、人際間的思維交流等內容的全面虛擬,人們更多地沉迷于親手締造的數字圖景。由此,真實世界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虛擬的符號構成了日漸膨脹的圖像世界,形成了一個比真實更“真實”的數字世代。數字消費給大眾勾勒了一個“審美”的烏托邦,隨之而來的是群體低俗化、碎片化的審美趣味。這是一種毀滅性的數字拜物教,體現了個體由內而發的生命異化。
二 激進需要:赫勒論日常生活異化的解蔽
從肉體勞役到精神規訓,從商品生產到數字增殖,資本對人的剝削愈發地隱蔽。正如韓炳哲所說,在審美泛化的當下,剝削不再以生命剝奪的強制性面貌出現,而是偽裝為自由自在、自我實現的新顏。在新式消費主義話術的蠱惑下,人們心甘情愿地剝削自我,主動地從事看似溫和的工作勞役。這是一種彌散于個體日常活動中的生存窘境,顯然也就需要一種微觀的批判方式。
對日常生活的微觀批判,要透過紛繁復雜的表象洞察其拜物教本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現實生活中工人不僅受到自身創造出的商品、貨幣乃至資本等物質資料的支配,更受由頭腦中生成的“顛倒的觀念”,即拜物教意識的制約。基于對拜物教的深刻反省,東歐馬克思主義學者提出了人道主義的實踐方案。特別是布達佩斯學派的阿格妮絲·赫勒,她在繼承導師盧卡奇的物化思想基礎上,主張以揚棄異化的思路來變革個體感性的生活世界,通過人的需要的革命來重建這個弊病叢生的日常生活。
(一)自在領域的異化:日常生活的拜物教診斷
赫勒對日常生活的考察,創造性地借鑒了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和盧卡奇的物化思想。在馬克思生活的19世紀,“個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動”(《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頁。)的日常生活被“一切感覺的單純異化即擁有的感覺所代替”(《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0頁。)。資本主義私有制將人的生活下降到動物需要的程度,甚至不如動物,工人墮落為無感覺無需要的存在。無產階級的普遍貧困,成為19世紀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生動寫照;而盧卡奇在面對著20世紀西方社會工具化的現實時,也提出了總體性革命的解決方案,他寄希望于工人階級革命意識的覺醒,以此來擺脫商品拜物教的物化糾纏,通過個人精神拯救來實現人類的解放。
有別于馬克思和盧卡奇的宏觀革命立場,赫勒審視了總體性視域下個體的生存面貌,將目光轉向微觀場域中的個體存在。在她看來,只有實現了個體的自我解放才可能走向人類解放的終極目標。在個體實現著自由自覺的類本質的生命過程中,每個人都具有著選擇生活方式與塑造需要結構的權利。
赫勒以馬克思的“類本質”和盧卡奇“對象化”概念為范式,從機理上勘定了個體日常生活的結構形式。作為類本質存在的個體,其對象化活動可以分為“自在的類本質對象化”“自為的類本質對象化”和“自在自為的類本質對象化”三大領域。其中自在的對象化領域,也就是日常生活是其所說的領域。自在領域的生活構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礎,在此中群體的重復性思維(實踐)占據著主導地位,會自發地抵制任何秩序規則的變遷。而以科學、哲學、藝術等為內涵的自為生活領域,展現了日常生活的高級層次,“表達人性在既定時代所達到的自由程度”([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5頁。),體現著個體生命的形上價值與自由追求。
19世紀馬克思筆下的商品、貨幣乃至資本等不同性質的拜物教景觀,在赫勒這里被概括為個人自在領域的生活異化癥候。對拜物教的克服,要在資本邏輯批判基礎上立足于生活世界內部異化加劇的情況,實現生活秩序的重建。赫勒強調,“日常生活絕不是非真實的,它具有引導性”([澳]倫德爾編:《美學與現代性:阿格妮絲·赫勒論文選》,傅其林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12頁。)。日常生活從總體上來看是一種互動的、引導的存在,作為生活主體的人們“可以把某些為更高的對象化所產生的價值引入他或她同‘自在的'對象化的關系之中”([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第254頁。)。日常生活的變革,就是要不斷地克服自在領域的拜物教現象,將異化的舊生活轉型為新的生活形態,引導自為領域的、創造性的日常生活融入自在層次,實現個體的解放。
日常生活異化的背景是碎片化的現代性狀況,自工業社會以來,現代性的生產邏輯深度地殖民了世俗大眾的日常生活,個體被拋入到這個全面異化的生活環境中。在赫勒看來,“每個人都降生于‘自在的’類本質對象化的結構之中”([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第246頁。),雖然人人生來就要面對這種“被拋入”境遇,但生存處境的偶然性并不是日常生活異化的根源。異化源自現代性機制下資本的生產邏輯對于個人生活領域的入侵,并且不斷激化了日常生活“自在”與“自為”領域的嚴重分化甚至對立。由此,對日常生活的批判兼具著雙重意義:一是揭露資本邏輯等強權勢力對人的本能的壓抑和個體創造性的束縛;二是通過批判自在領域日常生活的異化現象,推動日常生活擺脫自在層面的沉淪,轉向自為層面的美好生活,從而不斷地改造與重塑現實生活。
(二)激進需要的出場:日常生活的微觀批判
在現代性背景下,個人的需要完全淹沒在日常生活的拜物教中。如何變革日常生活,成為赫勒反思現代性狀況、重建美好生活的理論基點。在《日常生活》一書中,她試圖從人的需要的感性層面探索日常生活變革的微觀途徑。日常生活是每個人生存所依賴的感性場域,個人只有首先實現自身的生產,才能再生產社會。在這種意義上,赫勒把日常生活定義為“個體的再生產”([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第3頁。)。
基于對個體再生產的考察,赫勒探討了現實物質生產這一相對不變的部分,即“人類條件”。這是我們每時每刻感知的、習以為常的現實,它決定了日常生活中拜物教思維的盛行,拜物教將現存的事物作為給定的習俗來加以接受,卻從不探究事物的本源及發展。因此日常生活是缺少激情的,它的壓抑性使得人的需要得不到根本滿足,從而導致了諸多的異化問題。
生活的實然與應然、感性與理性、現實與目標之間的差距使赫勒無比關注日常生活的重建路徑。她依據馬克思“徹底的革命只能是徹底需要的革命”(《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頁。)論斷,提出了“激進需要”的革命主張。激進需要意指的不是某種具體的需要類型,而是特指產生于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卻又無法在現實中被滿足的需要范疇,即“出現在一個以依附與統領關系為基礎的社會中、但在這樣的社會中不能被滿足的需要”([匈]阿格妮絲·赫勒:《激進哲學》,趙司空、孫建茵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5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親手締造出激進需要,“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不僅產生異化,而且產生異化的意識,換句話說,產生激進的需要”(Agnes Heller, 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76,P.94.)。赫勒認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已解釋了激進需要的成因,資本主義生產下無產階級看似意外地成為勞動力。這帶來了一種“無產者個人無法擺脫,并且任何社會組織也無法掌控的勞動形式”(Agnes Heller, 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76,P.90.),由此激化了“工人的自由個性和強加于他們的生活條件之間的矛盾”(Agnes Heller, 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76,P.94.)。而她后來在《后現代政治狀況》一書中,將激進需要引申到對風險社會的政治考察中,現代性癥候表現為“令人不滿意的社會”([匈]阿格妮絲·赫勒、費倫茨·費赫爾:《后現代政治情況》,王海洋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7頁。)等多重價值沖突,它既呈現為人的生存需要的匱乏樣態,同時也孕育著個體渴望變革的激進需要的豐富形式。
作為革命意識的激進需要如何轉變為現實的實踐,對此還要尋找到政治行動的代言人,即那些具備著激進意識的革命主體,“是那些能夠實現激進哲學理念的人,最終馬克思在工人階級中找到了他們”(Agnes Heller, 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76,P.89.)。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們無時無刻不在渴望著變革物化的日常生活,“工人階級實際上希望解放自己,他們的需要事實上是激進需要”([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第246頁。)。但現實中他們卻沒有可以實現或滿足激進需要的條件,工人的需要被減少到微不足道的程度,這也構成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動力,“超越資本主義的不是激進需要的存在,而是它們的滿足”(Agnes Heller, 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76,P.77.)。
(三)激進需要的實現:日常生活異化的破解
立足于日常生活批判視角,赫勒嘗試著構建一種變革現存秩序的規范性理論,即闡述激進需要的激進哲學。赫勒強調激進需要是多元的,只有超越了現實的生活境遇,人的需要才能得到充分的滿足。以激進需要為宗旨的激進哲學,目的正是變革這個無法滿足多樣化需要的現存社會,并重建一個尊重和實現各種需要的新型社會。激進哲學的出發點就是承認需要的多元性,并且對人們如何更好地生活的現實問題予以解答,為人類生存提供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赫勒認為現代性的分配機制導致人始終處于匱乏的生存狀態。個體被外界強加以各種非自愿的“需要”,人的需要被強制性地展現在社會舞臺上,赫勒稱這些虛假的需要為“需求”。但即便如此,在物化的世俗生活中個體仍然要保持著變革現實的積極訴求。這種訴求就是“自覺的需要”,其代表著源于人內心的、不以損害他人為代價的價值取向。“自覺的需要”是個體激進需要的現實展現,是破除社會拜物教對個人統治的基本條件。
激進需要的實現以個體生存面貌為價值指向。“價值的評判標準是人具有‘豐富的需要’,需要異化等同于這種豐富性的異化。因此,有豐富需要的人是一種有意識的哲學建構。”(Agnes Heller, 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76,P.44.)基于需要價值論的立場,赫勒將人的需要分為量的需要與質的需要。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量化的需要占據了主導,人們“在量的需要的世界中茫然不知所措,因而自發地尋找一種量的需要在其中不再占主導地位的生存模式”([匈]安德拉什·赫格居什、阿格妮絲·赫勒、瑪利亞·馬爾庫什、米哈伊·瓦伊達:《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布達佩斯學派論文集》,文長春、王靜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0頁。)。量化的需要和退化為量的純粹生存需要,成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發展的趨勢([匈]安德拉什·赫格居什、阿格妮絲·赫勒、瑪利亞·馬爾庫什、米哈伊·瓦伊達:《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布達佩斯學派論文集》,文長春、王靜譯,第65頁。)。而共產主義所追求的,恰恰是對人的質的需要的擴展、并對人的量的需要進行壓制的社會體系。對需要的選擇就是對生活方式的選擇,當質的自覺的需要被充分滿足之后,才能夠擺脫將他人視作滿足自身利益的功利關系,實現令人滿意的社會建設。
激進需要的實現依托于日常生活的意義重建。日常生活中個體存在表現為以自我為中心的特性,“特性是異化的日常生活的主體”([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第14頁。)。將人們從特性的狀態中解放出來,需重新挖掘個性中真善美元素的倫理精神,即實現認知指向的真、道德轉向的善以及行動取向的美。通過價值共同體的建設來實現個體道德的倫理規范,從而將日常生活改造成“為我們的存在”。“為我們存在”體現了有意義的生活建設,其中囊括了人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和沖突,這使得我們的生活成為一種開放且包容的前景([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第257頁。)。有意義的生活是一種包含著你我他全體成員在內的共同體,“有意義生活中的指導規范總是有意義生活可一般化,從長遠看,可拓寬到整個人類”([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第258頁。)。在有意義的生活中,人們能夠在追求和改造著自身生活的同時“對他人有用”,這樣就契合了“為我們而存在”的人道化目標。
關于日常生活的微觀分析,揭示了宏大的社會敘事下個體彌散化的生存景象。在《日常生活》序言中,赫勒寫道,對日常生活的分析“為一種新的哲學框架的勾畫開辟出新的途徑”([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英文版序言第1頁。)。她認為哲學研究不應局限于抽象的理論思辨或是宏觀的政治問題,應該重視對生活世界的文化改造。赫勒倡導的是“揚棄日常生活的自在化和異化特征”([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中譯者序言第12頁。),變革目的在于“創造一個異化在其中成為過去的社會”(鄭莉、王靜主編:《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譯文集(布達佩斯學派卷)》,哈爾濱:哈爾濱工程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1頁。),應該助推那些基于生存方式“總體的革命”,這樣才能使每個人“都有機會過上有意義生活”(鄭莉、王靜主編:《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譯文集(布達佩斯學派卷)》,第11頁。)。而這一切的實現,必須落實于對個體需要的改造上。
三 從自在到自為:激進需要的美好生活指向
赫勒日常生活理論的獨特之處,在于對個體生命價值的尊重以及生活需要的考量。赫勒一直將個體的生存狀況作為其哲學理論的基點, “激進哲學的前提就是承認需要的多元性。”([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中譯者序言第17頁。)她認為哲學表達了“人們想要給規范創建一個世界的最基本的激進需要”,從而使“世界成為人類的家園”([匈]阿格妮絲·赫勒:《激進哲學》,趙司空、孫建茵譯,中譯者序言第5頁。),而肩負起激進運動使命的正是現實的個人。
赫勒關于激進需要的日常生活批判,為當代美好生活建設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個體“自在的”對象化日常生活,是人類活動的基礎范圍,但其并不能涵蓋人類生活的全貌。赫勒指出,在基礎性的日常生活之上,還存在“自為”領域的非日常生活,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非日常生活,“它們都為生活提供意義”([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中譯者序言第5頁。)。在理論層面,美好生活屬于自為領域的生活形態,只有對日常生活進行秩序重建,人類社會才能通達至美好生活的至善境界。在實踐層面,“滿足人們‘自在性’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時,把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自為性’生活需要提到日程,這樣才能更加體現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王雅林:《生活范疇及其社會建構意義》,《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第6頁。)
(一)從“赤裸生命”回歸“人本生活”
當代資本主義生產已全面轉向數字時代,信息技術成為資本權力統治的新指揮棒。在全景式數字監控下,個體生存面貌不再呈現為物質層面的匱乏,而是更為隱蔽的“生命赤裸”。以數字技術為媒介的商品生產實現了個體“生命數字化”改造,生命的生物特征在數字平臺上被轉碼為圖像、語音、文字等虛擬符號。數字經濟衍生的平臺娛樂、數碼記錄、時間檢測等全景監控手段,加深了赤裸生命的符碼化程度,個體生命活動被規訓為空洞抽象的數據虛體。赫勒認為,技術的發展使得“人類所有的能力都與創造它們的人們逐漸疏離,類的本質以權威、統治和限制的形式反對著個體的存在”(鄭莉、王靜主編:《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譯文集(布達佩斯學派卷)》,第11頁。),而激進需要旨在實現的是“個體與類在脫離異化的過程中重新統一”([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中譯者序言第17頁。)的理性烏托邦,在那里每個人的需要“不僅是完全理性的,同時也是人類的表達”(鄭莉、王靜主編:《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譯文集(布達佩斯學派卷)》,第12頁。)。
從激進需要的角度審視當下,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開啟的正是一條跨越資本物化陷阱的康莊大道。大眾所盼望的既不是資本無序擴張的“金本位”生活,也不是世俗意義上“房子車子票子”的“幣本位”生活,而是人人“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頁。)的“民本位”生活。黨在領導人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充分考量和尊重個體的生存與發展需要,不斷滿足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8頁。)更高質量的生活所需,將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作為各項工作開展的依據。
(二)從“符號拜物教”轉向“藝術再創造”
在如今這個數字異化、奢侈消費、勞動剝削疊加的異化世界中,日常生活的自在領域陷入被資本深度干涉與遮蔽的沉淪狀態。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符號以榨取每個人的精力與金錢為宗旨,將個體置于消費主義的欲望溝壑中。在赫勒看來,日常生活批判就是對圍繞著我們而存在的各種符號形式及其意義的省思,諸如對日常生活的重復、規則、經濟、情景性等自在特征的考察,為的是實現“為我們而存在”的自為生活。而自在的日常生活和自為的美好生活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形態鴻溝,消除鴻溝除了要依靠積極的實踐行動之外,更要具備著引導實踐的形上追求,如此才能以彌賽亞式的個體救贖完成對社會異化的消餌。
實現“為我們”的自為目標,要將屬于“自為”層面的藝術美學滲透進自在的日常生活中。盧卡奇認為我們要想重拾自身類本質的存在,必須喚起一種新的自在生命特性。赫勒則提出,“藝術是人類的自我意識,藝術品總是‘自為的’類本質的承擔者”([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譯,第103頁。)。藝術作為主體追尋自由的精神生產活動,它可以喚醒個體此在的沉淪,使人們擺脫自發的受動面貌。生活的意義在于個體主動地投身于創造性的活動,比如從事符合自身需要的生產勞動:種花、書畫、閱讀等等,而不是進行沖動上頭的買買買狂歡,這無疑更可提升生命的幸福感。
(三)從“情感消費”升華“審美體驗”
在階級社會中資本家將“審美”獨占為自己才能享受的對象,這是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丑陋生活。對人類審美情感的剝奪是資本剝削的一大原罪,在19世紀人與人“交往時表現純粹人類感情的可能性,已經被我們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階級對立和階級統治為基礎的社會破壞得差不多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9頁。)。在當代,商品生產迎來了戲劇性的變化,資本家由過去對工人情感的無情剝奪轉為對大眾審美認知的魅力蠱惑。從感知太少到感知過多,精神內耗成為當代消費體驗的重要特征。
資本生產主導下的情感消費只能招致個體異化程度的加深,真正的審美活動應是建立在個人生活感受、生命體驗基礎上的。正如赫勒所言,雖然每個人從降生始就被拋入偶然的日常生活,但是伴隨著偶然性而來的生活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個人主動創造和變革的對象。個人要不斷地進行有意識的生活互動,能動地滿足自身的自覺需要,這樣一來“即使我們不能滿足我們所有的需要,我們也能對我們的生活滿意”([匈]阿格妮絲·赫勒、費倫茨·費赫爾:《后現代政治情況》,第34—35頁。)。美好不是物質享受的代名詞,美好生活的實現要注重從精神層面引導。要將原本被資本家獨占的審美需要納入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培育起屬于大眾“審美生活”的消費理念與行為方式,在功利性的世俗生活中實現個人感情的審美超越。
(四)從日常生活批判到美好生活實踐
赫勒將“激進需要”理論貫穿于其政治哲學研究視野中,她認為現代性背景下個體生活表現為“主體性匱乏”與“主體性剩余”的矛盾張力。如果匱乏與剩余之間完全平衡,“那么生命就有意義”(鄭莉、王靜主編:《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譯文集(布達佩斯學派卷)》,第32頁。)。“如果在一個或兩個方面都存在著‘承認的匱乏’”(鄭莉、王靜主編:《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譯文集(布達佩斯學派卷)》,第32頁。),這種匱乏就可以被主題化,生命也會被賦予意義。阿蘭·梅吉爾( Allan Megill) 也認為,“馬克思人類需求的概念有雙重意義: 一方面,需求是一種缺乏,而另一方面,需求是一種機會、一種可能性。”(丁立群:《馬克思: 實踐、匱乏與革命—與 A.梅吉爾的對話》,《世界哲學》2018年第5期,第24頁。)以人的需要考察日常生活,既是對個體生命狀態的生動寫實,同時更指向了美好生活實現的可能性方向。
從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共時態理論視野,回歸到當代中國美好生活建設。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錨定目標。從現實來看,美好生活是處于進行時、不斷前進著的生活實踐,人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頁。),隨著我國社會全面小康目標的實現,人民普遍過上了物質豐足的生活,社會發展向著實現“精神富有”的共同富裕新目標邁進;從理論來看,美好生活是一個內涵逐步豐富、地位切實提高、體系日益充實的科學理論(付文軍:《“美好生活”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審視》,《學習與實踐》2020年第4期,第18—19頁。)。自黨的十八大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來,美好生活的內涵不斷拓展,黨的十九大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明確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表現,黨的二十大上又進一步提出了“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JP4]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01版。)。美好生活的現實實踐,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布局從理論到實踐、從目標到現實、從政黨到人民的逐層展開,彰顯著唯物史觀“社會—生活—人”的理論視野。
馬克思主義強調,意識任何時候都是被意識到的存在,而人的存在便是他們的現實生活。伴隨著個體基本需要的充分滿足,對新的生活內容、美的生活體驗、好的生活方式的審美需要成為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新要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已成為中國語境下社會治理的新課題,如果說共同富裕的“富”還是在強調物質的富饒,那么“裕”則體現了精神富足。美好生活是旨在實現“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JP4]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01版。)的協同生活,是充分考量“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JP4]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01版。)的美滿生活,是努力謀求“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JP4]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01版。)的富足生活,其最終指向的是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至善境界。在無數個人為之奮斗的日常實踐中,美好生活正在不斷轉變為人人參與的生活現實。
The Individual Construction of a Good Life:
The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of Heller’s Theory of Daily Life
ZHANG Cheng
Abstract: As a natural ideal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good life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the reality of our daily lif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tishism of daily life have led to the people’s “self-alienation”. The essence of individual “self-alienation”lies in the labor alienation of capital exploitation of people’s production. The labor alienation ha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symbolic fetishism in the field of consumption and society. In the digital era, individual life is facing the digital discipline of collusion between platform technology and capital exploitation. From labor alienation to digital fetishism, the acceleration of individual “self-alienation” reflects the sinking status of daily life and also indicates the possibility of promoting its reform. Agnes Heller, a Marxist in Eastern Europe, once put forward an idea of “radical needs”to change the reality of fetishism, believing that the satisfaction of individual needs is the basic prerequisite for achieving a good life, an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daily life in the realm of individual self-improvement to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a good life in the realm of freedom.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radical needs in daily life, a good life in the new era should transcend the old capitalist lifestyle from “humanistic life”, “artistic recreation”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theoretical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society-life-man”.
Keywords: criticism of daily life; alienated labor; capital discipline; radical needs; a good life for individuals
【責任編輯:龔桂明】
收稿日期:2023-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