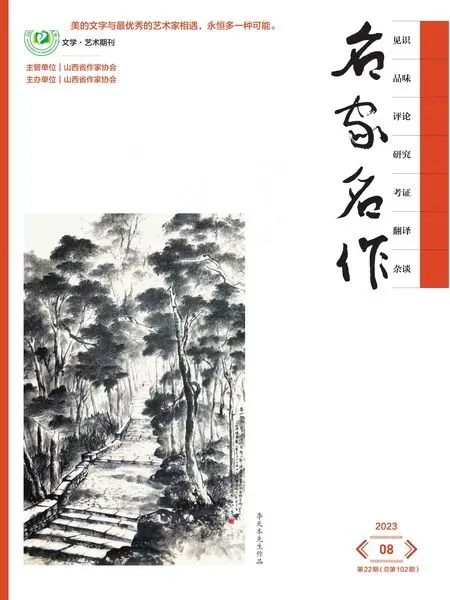李贄及《李氏焚書》淺談
趙宇航
一、李贄與《李氏焚書》
(一)李贄生平概況
李贄(1527—1602),原名載資,字宏甫,號卓吾,又號禿翁、龍湖叟、溫陵居士、百泉居士等,著有《李溫陵集》《藏書》《續藏書》《李氏焚書》《續焚書》等,福建泉州晉江人。李贄出身于教師家庭,因而喜讀書究學問。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福建鄉試中舉人。入仕后歷教諭、國子監博士、知府等二十余年。五十歲官云南姚安知府后棄官為僧,客居于湖北麻城。此間多在湖北黃安、麻城講學,晚年則來往于兩京之地。
李贄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曾師事泰州學派的學者王襞,后繼承其思想成為泰州學派一代宗師。在文學方面,李贄提出“童心說”,主張創作要“絕假還真”,抒發己見。在詩文寫作方面,亦主張“真心”,反對當時風行的“攀古”文風,對晚明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他還同情百姓疾苦,主張個性自由,批判重農抑商的傳統,倡導功利的價值與作用,符合晚明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需求。
(二)《李氏焚書》創作時間及主要內容
大約于明萬歷十六年(1588年),李贄時年62歲,開始編纂此書。關于李贄的生辰,據《卓吾論略》可推論李贄當出生于明嘉靖六年丁亥(1527年)十月二十六日。《李氏焚書序文》言:“然余年六十四矣,倘一入人之心,則知我者或庶幾乎!”由此可以得出,《焚書》的著成時間應為萬歷十八年(1590年)。
《李氏焚書》共六卷:卷一、卷二、卷三為書答;卷四為雜述,卷五為雜述、觀音問、豫約、寒燈小話;卷六為讀史。《李氏焚書》收錄了李贄生前的所思所感,是人們研究李贄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著作。
二、《李氏焚書》的刊刻、版本與真偽
(一)《李氏焚書》刊刻過程
前面說到《李氏焚書》雖被統治者多次禁毀,卻是屢焚屢刻。據目前可查閱到的資料,《李氏焚書》先后共刊刻了四次。隨之,《李氏焚書》的內容也變得越來越充實。
而關于《李氏焚書》的內容,李贄早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承諭《李氏藏書》,僅抄錄一通,專人呈覽。年來有書三種,……更有一種,專與朋輩往來談佛乘者,名曰《李氏焚書》,大抵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恐覽者或生怪憾,故名曰《李氏焚書》,言其當焚而棄之也。見在者百有余紙,陸續則不可知,今姑未暇錄上。”可見李贄不僅對自己的創作有著清晰的認知,也早已明了這樣的抱負必會給他帶來災禍。但恰恰相反,從這封與友人的信中,并未品讀到李贄對即將到來的災難的惶恐與退縮之意,而是透露著李贄面對這部即將出世的作品無以言表的激動與自豪之情。
兩年后,萬歷十八年(1600年)四月,李贄得償所愿,《李氏焚書》在明末被第一次刊刻并公之于世,在當時僅二卷41篇,分別為“書答”與“老苦”;隨著時間的推移,李贄將更多創作納入《李氏焚書》一書中,并在萬歷二十年(1602年)四月完成了第二次刊刻,與第一次刊刻相比直接增加了兩卷,分別為書答一卷21篇、雜述一卷22篇,合成為四卷;第三次刊刻時間為萬歷二十八(1610年)年,不僅增加了新的內容,還重新進行了整理和歸納,老苦、書答兩卷合為一卷,又增補了雜述一卷38篇,其他卷又新加入了大大小小30篇,構成了四卷四冊;第四次刊刻是在李贄死后,后人又將整理的讀史與詩匯收入李氏焚書中,此為《李氏焚書》的四次刊刻。
(二)《李氏焚書》版本概況
今天,人們常見的《李氏焚書》版本大體分為三類:第一類為明代顧大韶所校的《李溫陵集》二十卷中所包含的十三卷《焚書》;第二類為單行本《卓吾先生李氏焚書》;第三類為北京中華書局在1961年和1974年所出版的《焚書》。
1.明代顧大韶所校二十卷《李溫陵集》中所包含的十三卷《焚書》
在今天的學者看來,顧大韶似乎是一位鮮少被提及的人物,但顧大韶在明末并不是默默無聞的。如明季文壇領袖錢謙益,既是顧大韶的同鄉,又在學術旨趣上與他有諸多相同之處。而此版本被稱之為最接近底本文獻的版本,其他兩種版本的真實性皆不及《李溫陵集》本。
2.單行本《卓吾先生李氏焚書》
單行本《卓吾先生李氏焚書》是顧大韶校《李溫陵集》本的謄抄、刪節本,不僅有較多的抄寫錯誤,還刪去了部分章節,如書答部分就被刪去了11篇,雜述部分也同樣被刪去了11篇,讀史部分則是被刪去了104篇。由于該版本錯誤和刪減較多,故研究價值較低,此本《焚書》的各種版本中,除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校本有陳證圣序一篇外,多無序文。
3.《焚書》中華書局本(1961年和1974年)
中華書局本是將《李溫陵集》本與《李氏焚書》本糅合而成。此本譯者為中國李贄研究學會會長張建業先生,張建業先生曾主編了《李贄學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李贄文集》等作品,專著有《李贄評傳》。可以說,中華書局本《焚書》更適合學者閱讀與學習。
(三)《李氏焚書》真偽問題
《李氏焚書》的真偽問題主要分為兩點:一為贗文問題,二為原本的篇章問題。
就《李氏焚書》的真偽方面來說,明末距當今并不是十分久遠,但因《李氏焚書》被焚毀次數較多,難免有贗文出現,而《李氏焚書》的真偽問題是人們研究李贄時重點關注的問題,且《李氏焚書》的主題與內涵難免讓有心之人想要借李贄之筆發表自己的觀念,但又因李贄特殊的人格,使想要仿造之人難以模仿李贄深層的精神內核,又因《李氏焚書》的內容以書信問答為主,不是一方可以單純進行模仿偽造的。
三、《李氏焚書》體例與內容
研究《李氏焚書》體例無疑對挖掘李贄的深層思想有著重要作用,但《李氏焚書》被重復刊印次數較多,在目前可見的版本中,時間較早的有明末的朱墨套印本。本文以該版本為例進行研究,該版本共計六冊,金鑲玉裝,九行十九字,朱筆眉批行五字,白口無魚尾,四周單邊,上方記書名。
(一)序文與批注
明末朱墨套印本的《李氏焚書》組織形式與其他版本大同小異,不同之處在于開篇既為澹園竑為該書所作的序文,文章中亦有澹園竑所作的批點。澹園竑名為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又號漪園,人稱澹園先生、漪園先生、焦太史,著有《澹園集》《澹園續集》《玉堂叢話》等。焦竑為何會為李贄作序并進行批注呢?這不僅由于焦竑與李贄有著深厚的友誼,更因為二人之間酷似的人生經歷。1570年秋,李贄到南京任職,焦竑與其結為知己,來往密切。焦竑對李贄十分敬仰。1581年,李贄不再于云南姚安任職,轉而在湖北的黃安定居,焦竑在此期間曾贈詩“夜郎三載見班春,又向黃州學隱淪。說法終憐長者子,隨緣一見宰縣身。門非陳孟時投轄,鄉接康成不買鄰。苦欲移家難自遂,何時同作灌園人”以表對李贄的欽佩與贊賞。1597年,焦竑受到項應祥、曹大成誣陷,爭辯無果后,被貶為福寧州同知。這讓身為狀元的他倍受挫折。于是在第二年春天,與李贄共同返回南京,到福建上任。1599年,60歲的他對官場已經心灰意冷,轉身退出了官場。是年,他為李贄作《藏書序》。1602年,李贄受誣陷被捕入獄后身死獄中。焦竑悲痛萬分,難以釋懷,作《追薦疏》悼之。可以說,二人為官的生涯皆離不開彼此的陪伴,即使是到了人生之路的末尾也共同感受著官場的險惡與理想的幻滅。
而無論是在焦竑為《李氏焚書》所作的序文中還是批注上,都透露著其對李贄的認同、敬佩與贊賞。從《李氏焚書序》中的“宏甫快口直腸,目空一世,憤激過甚,不顧人有忤者。然猶慮人必忤,而托言于焚,亦可悲矣!”就可以看出,焦竑對李贄雖然表面態度是批判和哀嘆,實則十分欣賞和惋惜。這點從批注上亦可發現,如卷三《李中溪先生告文》中,焦竑評李贄“自負如是”,但又補上了“自信如是”這樣的評價。當然更多的是對李贄的直接贊揚,如《童心說》中,焦竑贊李贄能“借童心二字,發許大塊言”,在很多篇章的批注中,更是用了“透悟”“明凈”這樣的詞語對李贄進行評價。可以說焦竑與李贄不僅是摯友,更是難得的知己。
(二)卷目篇數與分卷內容
該版本《李氏焚書》共六卷,卷一、卷二、卷三為“書答”,其中卷一共十五篇,卷二共二十九篇,卷三共十九篇,卷四、卷五為“雜述”,共計三十八篇,卷六為“讀史”,為四十一篇。就分類來說,尚且存在不合理的現象,如在第六卷中《養生論》應歸為第四、五卷的“雜述”中更合理一些。另一方面,該版本較早,故每卷篇數均少于其他版本篇數。就前三卷“書答”內容來看,卷一十五篇分別與其他版本相比,缺少了《答鄧石陽》《又答石陽太守 》等幾篇。又如卷二共二十九篇,分別為《答鄧明府》《復周柳塘》《又與楊鳳里》等,該卷篇數亦少于其他版本,如《復麻城人書》《與河南吳中丞書》《復澹然大士》《復李漸老書》等篇皆不在內,卷三亦是如此。
從前三卷的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到李贄的交游經歷是很豐富的。如他在《會期小啟》中寫道:“故重會期,是重道也,是重友也。”對李贄而言,重友就是重道。即便是把交友當作自己人生信條之一的他,在死時也是極其孤獨的。李贄在晚年稱自己為“老苦”之人,老而苦于無友也,這對“以友朋為性命”的他何嘗不是最大的痛苦呢?焦竑評李贄被誣入獄后,“相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在李贄命懸一線之時,被他視為摯友的人無一人伸出援手,這其中也包括寫出這句話的焦竑在內。從李贄死后焦竑的種種行動來看,這句話是否也透露出焦竑的幾分愧疚呢?我們不得而知,但事實如何也顯得不再重要,李贄在死時終究是孤獨的。
卷四、卷五的“雜述”對李贄思想的體現更為直截了當。如《童心說》《四海》《八物》《五死篇》《高潔說》都從不同角度折射出李贄獨特的思想光輝。李贄在《高潔說》中將“高”與“潔”分別進行闡釋并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喜好“高潔”,又以“高潔”自詡,終難免有傲慢不恭、不能降低身價之嫌。但即便這樣也無法動搖李贄對“高潔”的熱衷與追求。哪怕他明知自己終被人們視為異端,也不懼怕牢獄之災與殺身之禍。
最后一卷為“讀史”,而“讀史”的目的也是借史來闡釋自己的觀點,如他對關羽的欽佩與贊賞而作的五言律詩《謁關圣祠》:“交契得如君,香煙可斷云。既歸第一義,寧復昔三分?金石有時敝,關張孰不聞!我心無所似,只是敬將軍。”李贄羨慕關羽、張飛之間比金石還堅韌的可貴友誼,也深嘆自己難如關羽一般,只能表達自己對關羽的敬佩。同樣的,五言律詩《觀鑄關圣提刀躍馬像》“英雄再出世,烈烈有暉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十方。居然圍白馬,猶欲斬顏良。豈料人千載,又得見關王”也是如此,李贄在打開關公提刀躍馬的畫卷時,頓時感覺英雄再現于世,甚至有一剎那,李贄竟看到了從畫卷散發出陣陣刺眼的光芒。“讀史”一卷可謂是顯露著李贄獨特的人生追求與理想境界。
總之,從《李氏焚書》的體例與內容來看,我們不僅可以探究出李贄的生平經歷與交游情況,還能深深挖掘出李贄散落在各處的思想碎片,也為我們還原出了一位最真實、最客觀的李贄。
四、結語
《李氏焚書》并不是李贄簡單的一部作品集,可以說《李氏焚書》從內容到書名無不散發著李贄獨特的人格魅力。也許,在李贄為《李氏焚書》命名的那一刻,他所看到的不僅是《李氏焚書》被屢次焚毀的下場,亦在冥冥中看到了自己被捕入獄、孤獨離世的身影。但他并沒有因此選擇退縮,這又何嘗不是“亦余心之所善心雖九死其猶未悔”呢?正如李贄所提出的“童心說”一樣,只有不違背本心,才能成就屬于自己真實的、獨一無二的一生。 而《李氏焚書》所帶來的沖擊也并沒有被短暫地限制在了晚明,《李氏焚書》所蘊含的個性解放與啟蒙思想對后世仍有研究價值與可取之處。如五四時期的中國,李贄的思想就成為反封建的先驅與利刃。此外,在對《李氏焚書》的研究中,通過書影中種種碎片化的呈現,也讓時隔百年的我們看到了一位更鮮活、更立體的晚明思想家與文學家,他雖是那個封建的晚明社會中被排擠的異端,卻永遠獲得了思想上的解放與靈魂上的自由。李贄的思想對現代人仍有警示作用,而《李氏焚書》也是值得人們反復研究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