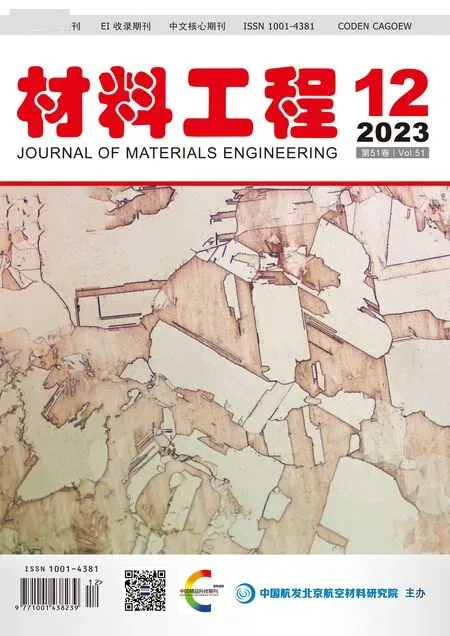β 鍛TC17 鈦合金大塊α 相研究
鄧雨亭,李四清,王 旭
(1 中國航發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先進鈦合金航空科技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95;2 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先進鈦合金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95)
TC17 鈦合金是一種設計使用溫度約為427 ℃的高強、高韌和高淬透性的富β 穩定元素的α-β 型鈦合金,名義成分為Ti-5Al-2Sn-2Zr-4Mo-4Cr(質量分數/%),被廣泛用于制造航空發動機風扇和壓氣機盤類件[1-7]。TC17 鈦合金的盤類鍛件制備工藝在國內經30 余年的探索研究,通常采用β 鍛工藝獲得網籃組織[8-9],其特點為原始β 晶界上的α 相不同程度地被破碎,晶粒內針狀α 相交錯分布,編織成網籃狀,此類組織斷裂韌度優異,具有高持久強度和抗蠕變性能[10]。伴隨新一代航空發動機風扇和壓氣機盤級數減少、轉速增加、高溫段前移、結構整體化的發展趨勢[11-12],β 鍛TC17 鈦合金盤類鍛件尺寸不斷增大,導致大尺寸鍛件的顯微組織中經常出現異常的大塊α 相。國內多數β 鍛TC17 鈦合金鍛件規范參照英國羅羅公司制定的β鍛Ti6246 鈦合金企業標準,雖然規定了組織中聚集大塊α 相的不合格圖譜,但目前對大塊α 相的形成機理及其對力學性能的影響尚不清楚。
吳英彥[13]對TC11 鈦合金的研究發現,微區成分偏析易引起α 相富集,導致大塊α 相的形成,并遺傳到鍛件中。王曉晨等[14]對β 鍛TC21 鈦合金的研究指出,大尺寸長條塊狀α 相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元素的不均勻擴散-內吸附引起成分偏析,同時在高溫變形過程中晶界處α 相再結晶球化聚集長大。趙彥蕾等[15]研究表明TC21 鈦合金中大塊α 相的〈1120〉方向平行于β相〈111〉方向,并認為大塊α 相會對斷裂韌度造成不利影響。綜上可知,成分偏析和晶體取向可能是形成大塊α 相的主要原因。由于TC17 鈦合金的成分與TC11,TC21 存在較大差異,目前對TC17 鍛件顯微組織中不同類型的大塊α 相研究較少。為此,本工作對β 鍛TC17 鈦合金中大塊α 相微區成分、織構類型以及三維形貌進行了表征,并分析了大塊α 相的形成原因。
1 實驗材料與方法
實驗材料為β 相區熱模鍛成型的TC17 鈦合金鍛件,化學成分如表1 所示,金相法測得相變點為900 ℃。β 鍛火次坯料的加熱溫度為930 ℃,變形量約為50%。應變速率約為0.01 s-1,鍛后快速風冷,之后進行固溶+時效熱處理,熱處理制度為800 ℃/4 h,水淬(WQ)+630 ℃/8 h,空冷(AC)。在鍛件縱剖面切取樣品,采用Leica DMI 3000M 型臥式金相顯微鏡(OM)和JSM 7900F 型掃描電子顯微鏡(SEM)攜帶Hikar’i XP(EBSD)探頭對顯微組織與微織構進行觀察,采用LEAP-5000XR 局部電極三維原子探針(3DAP)對組織中的元素分布進行了分析。OM 和SEM 樣品首先經過砂紙粗磨、精磨和機械拋光后,顯微組織試樣采用Kroll 腐蝕液(5%HF+10%HNO3+85%H2O,體積分數)進行腐蝕,微織構分析試樣采用電解拋光(電解拋光液體積分數為5%高氯酸、35%正丁醇和60%甲醇)進行制備。微織構分析測試掃描步長為0.5 μm,利用OIM 軟件進行數據掃描采集和處理。三維原子探針的針尖試樣采用FEI HeliosG4FX 等離子聚焦離子束系統在顯微組織樣品上制備而成,具體參數:樣品溫度25~100 K;離子收集率50%;激光能量1~1000 pJ;空間分辨率0.1 nm;環形視場>150 nm;最高脈沖頻率500 kHz;最大數據采集速率4×106ion/min。

表1 TC17 鈦合金的化學成分(質量分數/%)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TC17 titanium alloy(mass fraction/%)
2 實驗結果與分析
2.1 大塊α 相的光學顯微組織
圖1(a)為β 鍛TC17 鈦合金鍛件正常的顯微組織,可以看出,β 晶粒內部針狀α 相明顯,其長寬比大于10∶1,且尺寸小于晶界α 相。但在顯微組織的觀察過程中發現了異常的大塊α 相,大致可分為以下四類:(1)團聚在粗大晶界α 相附近的塊狀α 相(圖1(b));(2)呈點絮狀彌散分布在同一原始β 晶粒內部的塊狀α相,如圖1(b)中箭頭所示;(3)貫穿整個動態再結晶晶粒內部的塊狀α 相,其尺寸取決于再結晶晶粒尺寸(圖1(c));(4)同一晶粒內部相對粗化的長條α 片層,其長寬比大于相鄰的針狀α 相(圖1(d))。研究指出,圖1(b)中塊狀α 相形貌與觀察面的方向有關,當粗大片層狀α 長軸方向與觀察平面垂直時表現為塊狀,而與觀察面平行或一定角度的平面上表現為長條狀[16-17]。曾衛東等[18]認為TC11 鈦合金β 鍛后采用空冷甚至爐冷均會伴有大塊α 相。本工作進一步對β 鍛TC17 鈦合金的粗大α 相進行了三維原子探針分析和微織構表征,構建粗大α 相的形態并分析其與正常針狀α 相形態差異的可能原因。

圖1 β 鍛TC17 鈦合金鍛件的顯微組織(a)正常組織;(b)晶內團聚或絮狀大塊α 相;(c)貫穿再結晶晶粒的大塊α 相;(d)同一晶粒內相對粗化的長條α 相Fig.1 Microstructure of β forging TC17 titanium alloy(a)idea microstructure;(b)agglomerate or cotton-blocky α inside the grain;(c)blocky α through the entire grain;(d)relatively coarsened lamella α within the same grain
2.2 大塊α 相的三維原子探針分析
圖2(a-1),(b-1),(c-1)分別為晶界附近的大塊α相、呈點絮狀分布在β 晶粒內部的大塊α 相和正常的針狀α 相等三種形貌α 相的SEM 圖。采用聚焦離子束技術分別制備了用于三維原子探針的針尖試樣,如圖2(a-2),(b-2),(c-2)所示。圖3(a)~(c)分別為三種形貌的α 相中Al,Sn,Zr,Mo,Cr,O 原子的三維空間分布圖。可以看出,三種不同形貌α 相制備的針尖中強α 穩定元素Al 和O,β 穩定元素Mo 和Cr,中性元素Sn 和Zr 均沿Z軸有規律性地貧富分布,其中Al,O,Sn 和Zr元素的分布與Mo 和Cr 元素的分布基本呈負相關。樣品均經過β 相區加熱(930 ℃)鍛造和兩相區固溶+時效處理,相轉變過程中發生了合金元素的再分配,且從分布規律可以判定元素貧富偏聚界面即為片層α 相和β 基體相的相界面,富α 穩定元素區域為α 相,富β 穩定元素區域為β 基體相。由圖3(a)可推測晶界附近的大塊α 相呈短粗狀,且基本與顯微組織觀察面的法線方向平行。同理,由圖3(b),(c)可推測晶粒內部α 相均呈長桿狀,桿長度約為5~40 μm,桿基本與顯微組織觀察面的法線成30°角,晶粒內部呈點絮狀的大塊α 相與正常形態針狀α 相可能為相同三維形態的α 相,只是在進行二維平面截切后觀察時所表現出的不同形貌。

圖2 不同形態α 相的顯微組織SEM 圖(1)及針尖試樣和取樣部位(2)(a)晶界α 相附近的大塊α 相;(b)點絮狀大塊α 相;(c)針狀α 相Fig.2 SEM images of microstructure(1),APT specimens and location(2) of different α platelets(a)blocky α nearby grain boundary α phase;(b)cotton-blocky α phase;(c)acicular α phase

圖3 不同形態α 相合金元素在三維空間中的分布(a)晶界α 相附近的大塊α 相;(b)點絮狀大塊α 相;(c)針狀α 相Fig.3 3DAP measured distributions of alloy elements in different α platelets(a)blocky α nearby grain boundary α phase;(b)cotton-blocky α phase;(c)acicular α phase
為進一步了解α 和β 相界面處各種合金元素的分布與成分變化,選取Mo 元素原子分數的等濃度面附近區域進行進一步分析。圖4(a)~(c)分別為三種形貌的α 相等濃度面附近區域主合金元素分布曲線。Al元素在α 和β 相均有較大的固溶度,晶界附近大塊α相、點絮狀大塊α 相和針狀α 相的Al 原子分數平均值分別為9.68%,10.70%和10.54%,但在β 基體中顯著下降到4.70%,4.57%和4.64%。Sn 元素在α 相中原子分數平均值分別為1.03%,1.08%和1.07%,而在β 基體中下降到0.59%,0.52%和0.62%。α 穩定元素O 總含量偏低,在α 和β 相內均有一定的固溶度,α 相中原子分數平均值分別為0.56%,0.58% 和0.52%,而在β 基體中下降到0.25%,0.29% 和0.32%。中性元素Zr 在β 相中的固溶度略高于α 相,α相中原子分數平均值分別為1.24%,1.42% 和1.17%,在β 基體中上升至1.59%,2.16%和1.92%;β 穩定元素Mo 在α 相中固溶度低,原子分數平均值僅為0.38%,0.34% 和0.27%,在β 基體中上升至4.64%,4.69%和4.44%;β 穩定元素Cr 在α 相中原子分數平均值分別為0.43%,0.49%和0.42%,在β 基體中上升至10.25%,9.82%和9.96%。整體而言,β鍛TC17 鈦合金鍛件三種形態的α 相中主合金元素分布無明顯差異,合金成分差異不是形成大塊α 相的原因。

圖4 等濃度面附近區域主合金元素分布圖和相比例分布圖(a)晶界α 相附近的大塊α 相;(b)點絮狀大塊α 相;(c)針狀α 相Fig.4 Distribution map of main alloy elements in isoconcentration plane and distribution map of phase proportion(a)blocky α nearby grain boundary α phase;(b)cotton-blocky α phase;(c)acicular α phase
2.3 大塊α 相和對應β 基體的取向分析
圖5 為整個再結晶晶粒內的α 相和晶粒內部相對粗大的長條α 片層的取向分布圖。由圖5(a)可知,正常形態下原始β 晶粒沿變形方向被拉長,晶粒尺寸大于500 μm,晶界被破碎,晶界附近的α 片層(αWGB)取向類型多樣,析出的晶內針狀α 相無明顯擇優取向。而β鍛變形過程中由于大變形量或大應變速率易形成細小再結晶晶粒[19-21],晶粒尺寸僅為20~100 μm,再結晶的晶界相對平直,晶內α 相取向類型單一。Salib 等[22]研究TC17 鈦合金β 相區加熱后800~830 ℃等溫析出時發現,魏氏體組織中每個原始β 晶界上α 相平均取向類型為1.8~1.9,而αWGB的平均取樣類型為2.8~4.4。因此,本研究認為每個再結晶晶粒相當于一個未變形或輕微變形的晶粒,由于晶粒尺寸細小,晶內α 相基本為同一取向的αWGB,鍛后冷卻速度較慢的情況下相互吞并長大,最終形成貫穿整個晶粒的塊狀α 相。由圖5(b)可知,晶粒內部同時存在針狀的α 相和相對粗大的長條α 片層,α 相取向是決定α 相粗細的主要因素,當α 相〈0001〉∥鍛造方向時α 相呈針狀,而當α 相〈10-1 0〉∥鍛造方向時相對粗大。圖5(c)為晶界α 相和晶界附近α 相的取向分布圖。可以看出,晶界上由大量取向一致的α 相組成,因此,可以推測圖1(b)觀察到的大塊α 相實際上是由破碎程度低且相鄰晶粒取向差小的α 相形成。

圖5 α 相取向分布圖(a)再結晶晶粒;(b)晶內粗大α 片;(c)再結晶晶粒晶界α 和αWGB相Fig.5 IPF maps of α phase(a)recrystallized grains;(b)coarse α lamellae inside grain;(c)grain boundary α and αWGB phase of recrystallized grain
圖6 為晶界α 相附近和晶內呈點絮狀分布的大塊α相以及對應β 基體相的取向分布圖。由圖6(a)可知,熱機械加工后β 晶粒沿金屬流動方向拉長,可以觀察到不同晶粒之間β 基體相取向存在差異,但是同一晶粒內的β 基體取向基本相同。大部分晶粒內部的β 相形成了較強的絲織構(即〈001〉∥鍛造方向),反之,部分變形量較小的晶粒絲織構則較弱。由圖6(b)可知,形成較強絲織構的晶粒內部α 相均呈針狀,無明顯的擇優取向,而變形量較低的晶粒在晶界附近和內部形成了大塊α 相,其取向類型基本為〈11-2 0〉或〈10-1 0〉∥鍛造方向。將晶界α 相和晶界附近αWGB的取向分布圖單獨提取(圖6(c)),低變形量部分晶界雖然不平直、呈破碎狀,但是取向類型單一且長度達到200 μm,其效果相當于一個較大尺寸的再結晶晶粒,導致大塊α 相的形成。因此可以推斷,若原始β 晶粒中存在取向單一的晶界α相,就有可能在晶界附近和晶粒內部形成大塊α 相。

圖6 晶界附近大塊α 相和β 相取向分布圖 (a)β 相;(b)α 相;(c)晶界α 和αWGB相Fig.6 IPF maps of blocky α and β phases nearby grain boundary (a)β phase;(b)α phase;(c)grain boundary α and αWGB phase
3 結論
(1)β 鍛TC17 鈦合金鍛件顯微組織中原始β 晶粒內部存在四種異常形態的α 相:晶界附近的塊狀α 相、呈點絮狀分布于原始β 晶粒內部的塊狀α 相、貫穿整個動態再結晶晶粒內部的塊狀α 相以及晶粒內部粗大的長條α 片。
(2)三維原子探針分析顯示,晶界α 相附近的大塊α 相呈短粗狀,晶粒內部的α 相呈長桿狀,成分差異不是形成異常形態α 相的主要原因。
(3)β 鍛過程中形成的細小再結晶晶粒容易轉化為取向一致的α 片層,形成貫穿整個晶粒的塊狀α 相;變形量較低的晶粒也存在取向單一的晶界α 相,會導致在晶界附近和晶粒內部形成大塊α 相。正常組織中晶內α 相呈針狀,針狀α 相取向雜亂,當α 相的〈10-1 0〉∥鍛造方向時相對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