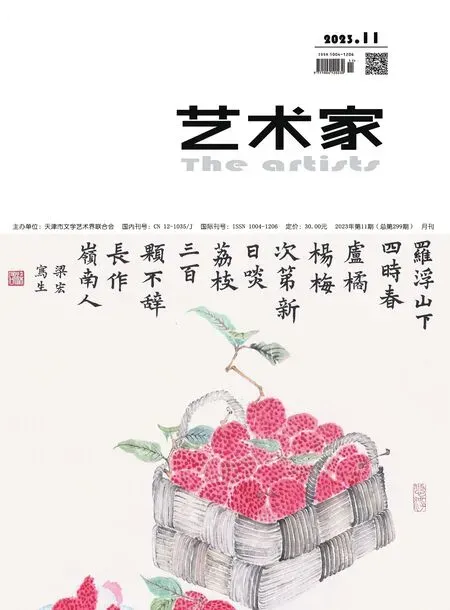二王書法與《老子》哲學思想(下篇)
□李 永
(接上篇)
三、無為無不為的心法
《老子》三十七章有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不欲之靜,天下將自正。”四十八章有云:“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無為”是“體”,是道,是自然,是無目的,是減法,只有無為才能入道、得道;“無不為”是“用”,是目的,也是人為,是加法,只有得道才能無所不為,才能“取天下”。
“無為無不為”是《老子》哲學的核心思想,后被運用于藝術領域,成為藝術創作的心法指導思想。康德講審美之道,即“無目的的合目的性”,與此有相似性。康德云:“美是一個對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在它不具有一個目的的表象而在對象身上被知覺時。”鄧曉芒先生闡釋:“最純粹的美應該是不帶任何目的,到自然界里面欣賞一片風景,就不帶任何目的,但藝術美從創造出來就帶有目的……所以,藝術創作是有目的的活動,包含技巧和熟練的因素。當然它是基于無目的,用審美的眼光來看,它是基于那種鑒賞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它表達出來必須顯得好像是沒有目的,所以它能夠表達美,也能夠被人欣賞。”“無目的”相當于“無為”,“合目的性”相當于“無不為”。中西哲學再次交匯,卻凸顯出老子“無為無不為”的審美價值。
王羲之《比日帖》云:“比日尋省卿文集,雖不能悉周遍,尋玩以為佳者,名固不虛。序述高士,所傳小有異同。見卿一一問……暇日無為,想不忘之。”帖中“尋玩”屬于審美的“無目的”,“暇日無為”是現實中的“無為”,“佳者”與“想不忘之”卻是目的。此帖似為《老子》“無為無不為”的現實寫照。
王羲之諸篇書論均在不同程度上蘊含“無為無不為”的創作思想。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后》有曰:“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后作字。”“凝神靜思”屬“無為”,而“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則是“無不為”的妙用。
前文所引王羲之《書論》又云:“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學無及之。大抵書須存思,余覽李斯等論筆勢,及鐘繇書,骨甚是不輕,恐子孫不記,故敘而論之……每作一字,須用數種意……為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之書,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其中“夫書者,玄妙之伎也”,即書載玄妙之道。“大抵書須存思”如同道教上清派“存思法”。“每作一字,須用數種意,為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之書,須字字意別”則是“無不為”的具體展現。
王羲之《用筆賦》亦云:“秦、漢、魏至今,隸書其惟鐘繇,草有黃綺、張芝,至于用筆神妙,不可得而詳悉也……馳鳳門而獸據,浮碧水而龍驤。滴秋露而垂玉,搖春條而不長……其若自然;包羅羽客,……信能經天緯地,毗助王猷,耽之玩之,功積山丘。吁蹉秀逸,萬代嘉休,顯允哲人,于今鮮儔。共六合而俱永,與兩曜而同流;郁高峰兮偃蓋,如萬歲兮千秋。”其中“用筆神妙”,屬于書道范疇,入無為之境,“其若自然”,即如“獸據、龍驤、秋露、春條”,自然而然,如此能“經天緯地,毗助王猷”“六合俱永,萬歲千秋”,展現書道“無不為”的境界。其《記白云先生書訣》又曰:“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寶齊貴,萬古能名。陽氣明則華壁立,陰氣大則風神生。把筆抵鋒,肇乎本性。力圓則潤,勢疾則澀;緊則勁,險則峻;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遠;望之惟逸,發之惟靜。敬茲發也,書妙盡矣。”其中“望之惟逸,發之惟靜”,屬于“無為”,“達乎道”,能生混元之炁,從而華壁風神,內盈外虛,似七寶之貴,垂萬古之名,又“無不為”也。
“無為”和“無不為”作為創作心法可追溯到蔡邕的《筆論》,其曰:“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若迫于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矣。”其中“散”者,閑散,消遣也,也即無為也。“任情恣性”即放松、寬松性情,使之不“迫于事”。“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入定調息也。在定靜中,即“沉密”,能有所安得,即得“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即同“無不為”,因而“縱橫有可象”矣。
晉代的書論也蘊含這一創作心法。如成公綏《隸書體》的“存載道德,紀綱萬事”,道是無為,德即“紀綱萬事”,無不為矣。衛恒《四體書勢》所謂“寫彼鳥跡,以定文章;幾微要妙,臨事從宜”。“寫彼鳥跡”是模仿自然,“無為”,至于“幾微要妙,臨事從宜”,則“無不為”;索靖《草書勢》中的“守道兼權,觸類生變”,“守道”屬“無為”,“兼權,觸類生變”則屬“無不為”;衛鑠《筆陣圖》中的“然心存委曲,每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心存委曲”即守書道,書道之體屬“無為”,而“每為一字,各象其形”則是“無不為”也。
王羲之“無為無不為”創作心法是吸收了前人成果,也滲透到后世唐代書論中。如虞世南《契妙》曰:
“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于妙……然則字雖有質,跡本無為,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主。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必在澄心運思至微妙之間,神應思徹。又同鼓瑟綸音,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道,則書契於無為,茍涉浮華,終懵于斯理也。”
此論繼承了王羲之書論思想,“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屬于上清派“存思法”,入定無為,因“字雖有質,跡本無為”,而且心悟至道,“書契於無為”,如此“必資神遇”至微妙之間。至于“又同鼓瑟綸音,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則屬“無不為”佳境焉。
孫過庭《書譜》有云:“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自然者,“無為”也,如初月眾星也,若“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則進入“無不為”境界矣。
張懷瓘《書議》又云:“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托以散郁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量其力。是以無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劍之鋒芒。肅然危然,方知草之微妙也。”其中“無為而用,同自然之功”則“無不為”,“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托以散郁結之懷”以及“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劍之鋒芒”則展現了草書神奇微妙的變化,得心契之意而忘言。
二王書法創作也體現著“無為無不為”意蘊。唐宋元明清幾代書論均有評述。唐孫過庭《書譜》有謂“《黃庭經》則怡懌虛無”。《黃庭經》為上清派內丹修煉經典,蘊含虛無之道,王羲之創作此卷小楷也入虛無“無為”之境,故有虞世南《勸學篇》所謂“故羲之于山陰寫《黃庭經》感三臺神降”的感應,真乃“無不為”的神妙者。
宋代沈作喆《論書》云:“唐李嗣真論右軍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像;《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女順孫之像;《逍遙篇》《孤雁賦》跡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像;《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像,皆見義于成字。予謂以意求之耳,當其下筆時,未必作意為之也,亦想見其梗概云爾。”此論評述右軍創作楷書諸篇時“未必作意為之”,即想見其無意為之,故楷書諸篇呈現“忠臣烈士”“孝女順孫”“拔俗抱素”“矜莊嚴肅”諸像,氣象豐富多彩,契合各自的書寫內容,產生“無不為”的書寫效果。
右軍《蘭亭序》創作也入“無為”之境。宋代李之儀《姑溪居士論書》有云:“世傳《蘭亭》,縱橫運用,皆非人意所到,故于右軍書中為第一。然而能至此者,特心手兩忘,初未嘗經意。是以僚之丸,秋之于奕,輪扁斫輪,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以力致也。自非出于一時乘興,淋漓醉笑間亦不復能爾。”右軍《蘭亭》心手兩忘,也有“無為”之志,故能神遇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明學者孫鑛《書畫跋跋·又宋拓蘭亭帖》亦云:“《蘭亭敘》結體全近今元常、世將等,古法至此一大變。其妙處惟在字字飛動,若不甚經意,然亦不全無意。其體是真行,總只若屬草者然,然筆法內擫,結構最緊密,雖佚蕩不拘,而筆筆力到,點畫間無一聊且意,所謂‘周旋中禮,從心不逾矩’。”此跋獨標《蘭亭序》筆意玄妙,難得在于有意無意之間,即“無為有為”之間,故“從心不逾矩”矣。
元書畫家郝經《移諸生論書法書》亦云:“楷草之法,晉人所尚,然至右軍將軍羲之,則造其極。羲之正直,有識鑒,風度高遠。觀其遺殷浩及道子諸人書,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江左高人勝士,鮮能及之,故其書法韻勝遒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風絕跡,邈不可及,為古今第一。”此論言及王羲之“遺殷浩及道子諸人書”楷草諸帖,似“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呈現“無為”之志,故“韻勝遒婉,出奇入神”,又入“無不為”妙境焉。
解縉《春雨雜述》又曰:“此鐘、王之法所以為盡善盡美也。且其遺跡偶然之作,枯燥重濕,濃淡相間,益不經意肆筆為之,適符天巧,奇妙出焉。此不可以強為,亦不可以強學,惟日日臨名書,無恡紙筆,工夫精熟,久乃自然。”鈡、王遺跡偶然之作(大王《上虞帖》如圖1),“不經意肆筆為之”,屬無意,如蘇東坡云“書初無意于佳乃佳爾”,而有“無為無不為”之效。“奇妙出焉”,如項穆《書法雅言·神化》所云“字雖有象,妙出無為”也。

圖1 《上虞帖》唐摹本 上海博物館藏
王獻之行草諸帖也是無意為之。劉熙載《藝概·書概》有曰:“歐陽《集古錄》跋王獻之《法帖》云:‘所謂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敘暌離、通訊問、施于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余興,淋漓揮灑,或妍或丑,百態橫生,使人驟見驚絕,守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王獻之諸多行草書帖如《鴨頭丸帖》、《十二月帖》、《不謂帖》(如圖2)、《鵝還帖》、《愿馀帖》、《適應帖》、《奉對帖》、《鄱陽書帖》、《阮新婦帖》、《患膿帖》等,“初非用意”,即“無意無為”,而揮灑淋漓,“意態無窮盡”,則“無不為”矣。

圖2 《不謂帖》
綜上所述,本文從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書法創作的布白、用筆、心法三個層次論述其蘊含《老子》道論相反相成的哲學思想,體現了天師道徒對老子道家哲學的消化吸收及靈活運用的藝術修為。道家哲學不但成為中國書法的指導思想,而且也體現了中國藝術精神與藝術之道,形成了中國藝術哲學體系。它不僅是中國文明的寶貴財富,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