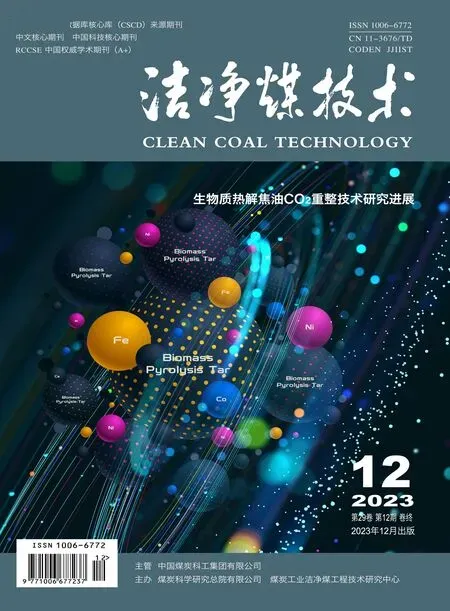Ce對CoMnOx催化劑協(xié)同CO/NH3脫硝性能
張興宇,劉倩倩,糜淑琪,韓運斌,玄承博,耿文廣,孫榮峰,王魯元
(齊魯工業(yè)大學(山東省科學院) 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部,山東 濟南 250353)
0 引 言
隨著我國污染物排放標準不斷提高,燒結煙氣因溫度低、污染物含量高等原因成為NOx脫除領域的難點,因此,環(huán)境保護部相繼制定了更嚴格的NOx排放標準,持續(xù)推進我國生態(tài)文明建設[1]。傳統(tǒng)的NH3-SCR脫硝工藝是針對燃煤電站煙氣處理開發(fā)的高效脫硝技術,需在300~400 ℃將NH3噴入煙氣中,并在催化劑作用下將NOx轉化為無毒N2。但由于工藝所需溫度較高,而燒結煙氣屬于低溫煙氣,溫度僅110~150 ℃,在此溫度下脫硝催化劑活性較低,難以實現(xiàn)NOx減排的目的。而將燒結煙氣預先加熱至催化劑反應溫度范圍,需耗費大量燃料,導致脫硝工藝運行成本增加,因此為降低加熱成本,實際脫硝過程中會噴入過量還原劑,以期降低反應溫度,但過量噴氨導致氨逃逸到大氣中又會引發(fā)嚴重的霧霾問題[2],加上燒結煙氣中殘存的CO無序排放也會加劇溫室效應。因此如何低成本協(xié)同脫除燒結煙氣中CO、NOx和NH3,成為研究熱點。
筆者課題組前期研究發(fā)現(xiàn)CO同樣具有還原性,可作為NOx的還原劑。如用CO代替部分NH3,既可消除CO和NOx,又可降低NH3使用量,具有較強應用前景,但該技術的難點在于在常規(guī)催化劑的作用下,煙氣中O2對CO還原NOx存在干擾,使CO直接被O2氧化為CO2,失去對NOx的還原作用。
為克服O2的干擾,近年來研究人員致力于開發(fā)以過渡金屬為主的多種金屬復合催化體系[3-5],對催化劑進行了一定修飾,以期通過提高活性組分的分散度,提高活性成分的協(xié)同作用,改善催化劑選擇性差的問題,并得到性能較好的CO-SCR催化劑,如Co和Mn作為助劑可明顯促進Cu/Al2O3的低溫CO-SCR活性[6],而將Ni、Co、Mn加入 MOFs材料制備催化劑,可顯著促進CO-SCR反應活性[7]。在前期研究基礎上,優(yōu)選Co、Mn、Ce等金屬成分,通過XRD、TEM、Raman、H2-TPR、XPS等手段對催化劑物化性質(zhì)進行表征,并研究CO對NH3-SCR脫硝活性的影響,該研究對于CO協(xié)同NH3脫硝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 催化劑制備與表征
1.1 催化劑制備
所用催化劑采用共沉淀法制備,用去離子水將Co(NO3)2·6H2O、Mn(NO3)2·4H2O、Ce(NO3)3·6H2O混合配置為物質(zhì)的量濃度2.0 mol/L的金屬鹽溶液,制備催化劑中選擇物質(zhì)的量濃度4.0 mol/L的NaOH作為沉淀劑。首先在反應器皿中加入200 mL 2.0 mol/L氨水作為反應底液,隨后將混合后的金屬鹽溶液在反應器皿中進行反應,混合后充分攪拌,溶液水浴加熱升至指定溫度,加入NaOH溶液調(diào)節(jié)混合液pH穩(wěn)定于10,并使用磁力攪拌器進行二次攪拌1 h,靜置陳化2 h后,抽濾,再次用去離子水洗滌,將洗滌后的固體樣品置于馬弗爐,在450 ℃煅燒4 h,煅燒完成后,將催化劑原料研磨、壓片,并篩分催化劑顆粒粒徑為0.250~0.425 mm。其中催化劑Mn∶Co物質(zhì)的量比為1∶1,Mn∶Ce物質(zhì)的量比為1.00∶0.75~2.00,并以Ce物質(zhì)的量比作為標記區(qū)分,分別記為CMC0.75、CMC1、CMC1.25、CMC1.5、CMC1.75、CMC2。
1.2 催化劑表征
采用D/MAX-2600型XRD儀分析催化劑晶體結構和相組成,XRD數(shù)據(jù)采集范圍為10°~80°;通過TEM和HRTEM(FEI Tecnai F20)測量樣品微觀結構和晶格條紋;使用Thermo DXR2X光譜儀(激發(fā)波長514.5 nm)在50~3 400 cm-1收集樣品的拉曼光譜。使用連續(xù)流量計獲得催化劑的H2-TPR曲線。通過NH3-TPD研究吸附物和催化劑之間的結合,并使用熱電偶測試和控制溫度,以獲得關于催化表面活性中心、表面反應等信息。每次測量前,將催化劑在200 ℃氦氣流中吹掃1 h;然后將溫度降至約30 ℃。將樣品由50 ℃加熱至950 ℃(10 ℃/min)。XPS數(shù)據(jù)通過使用C1s(284.8 eV)作為標準結合能校正,用Al-K-α源槍和SEMERFLY 250XI掃描獲得。
1.3 催化劑性能測試
催化劑的脫硝評價試驗在自制反應裝置中進行(圖1),催化劑樣品置于微型反應器內(nèi)。配制的模擬煙氣組成為NO、NH3、O2,N2為平衡載氣,各氣體流量由質(zhì)量流量計控制,煙氣總流量為500 mL/min,空速30 000 h-1,原料氣及反應后尾氣中NOx濃度變化采用德國MRU MGA6型煙氣分析儀在線分析。催化樣品活性測試以NOx(NO和NO2)轉化率作為基準。NOx轉化率η(NOx)和CO氧化率η(CO)計算公式為

圖1 自制模擬煙氣脫硝裝置Fig.1 Simulated flue gas de-NOx device
(1)
(2)
式中,C0(NOx)、C0(CO)分別為初始時刻的NOx和CO體積分數(shù);Ci(NOx)、Ci(CO)分別為不同溫度下的NOx和CO體積分數(shù)。
2 表征結果
2.1 XRD分析
CMC系列催化劑的XRD圖譜如圖2所示,所有樣品均未觀察到歸屬于MnOx物種的衍射峰,說明MnOx物種主要以無定形的形態(tài)高度分散在催化劑表面[8]。CMC系列催化劑可觀察到在19.05°、31.24°、36.75°、44.80°、59.20°、65.10°處歸屬于Co3O4的衍射峰[9-10],以及在28.50°、31.24°、47.50°處歸屬于CeO2的衍射峰[11-12]。Ce物質(zhì)的量比由0.75增至1.75時,屬于CeO2峰強度明顯增強,同時半峰寬增加,其中位于31.20°處的Co3O4衍射峰逐漸被CeO2(111)處的峰覆蓋。

圖2 不同催化劑的XRD譜圖Fig.2 XRD patterns of different catalysts
利用Scherer公式(D=0.89λ/(βcosθ),D為晶粒大小,β為實測樣品衍射峰半高寬度,θ為布拉格衍射角,λ為X射線波長),計算樣品晶粒尺寸,結果表明Ce物質(zhì)的量比由0.75增至1.75時,Co3O4的晶粒尺寸分別為13.7、12.0、11.3和10.6 nm,顯然隨Ce物質(zhì)的量比增加,Co3O4晶粒尺寸減小,證明Ce摻雜對Co3O4中晶粒的生長有抑制作用。同時,在所有催化劑中,并未發(fā)現(xiàn)Co3O4和CeO2衍射峰角度明顯偏移,表明Co3O4和CeO2晶格結構沒有很大的改變或破損,仍保持原有晶格結構。
2.2 Raman分析
CMC系列催化劑的Raman譜圖如圖3所示。盡管在XRD譜圖中未檢測到Mn物種的特征峰,但在Raman譜圖中605 cm-1處檢測到歸屬于MnO2的特征峰[13]。所有催化劑在440 cm-1處存在歸屬于CeO2螢石結構的F2g震動峰,該峰由純CeO2位于460 cm-1的振動峰發(fā)生紅移導致,且隨Ce物質(zhì)的量比增加,振動峰強度增強,這表明Ce與Mn和Co金屬晶格相互摻雜,導致晶格畸變,影響了[Ce-O8]振動單元的對稱拉伸模式的極化率,導致與單晶相CeO2中對稱拉伸模式的極化率發(fā)生改變。位于173和235 cm-1處突出的弱帶歸屬于催化劑表面氧空位,其中主帶與肩帶面積比反映了氧空位濃度。CO與NO在樣品表面反應被認為是空位氧參與的氧化還原反應,樣品CMC1.25、CMC1.5在該波段有明顯突出的寬峰,表明其有更多的缺陷結構,并形成了大量氧空位。

圖3 不同催化劑的Raman譜圖Fig.3 Raman patterns of different catalysts
2.3 TEM分析
CMC0.75、CMC1.25、CMC1.5、CMC2四種典型催化劑的TEM圖像如圖4所示。在前3種催化劑表面上可觀察到明顯的周期性晶格條紋[14],其中占據(jù)較大的區(qū)域的晶格條紋間距為0.31 nm,這與CeO2晶格的(111)面的晶格間距相符[15],表明CeO2由于其晶胞較大,組成催化劑的骨架[16],這也說明催化劑的晶格結構與CeO2相似,部分區(qū)域的晶格條紋間距0.28 nm,對應的Co3O4的(220)晶面[17],并未觀察到Mn物種的晶格條紋,表明Mn物種在催化劑表面較分散,這與XRD表征結果相同。隨Ce物質(zhì)的量比增至2,催化劑表面的晶格條紋不再明顯,表明過多的CeO2覆蓋催化劑表面結構,且過剩的CeO2出現(xiàn)團聚現(xiàn)象。

圖4 典型催化劑的TEM圖譜Fig.4 TEM spectrum of typical catalysts
2.4 XPS分析
CMC催化劑O的XPS圖譜如圖5所示,經(jīng)過擬合后,XPS峰可分為3個小峰,分別是位于529 eV附近的晶格氧Oα(與金屬陽離子結合的晶格氧)、530 eV附近的空位氧Oβ(氧在晶格作為M-O-M,在催化反應中可能失去O,形成M-□-M)和531~532 eV附近的表面氧Oγ(來自氧污染、—OH、—CO3和吸附的O2等)[14]。XPS光譜計算的氧物質(zhì)組成見表1,CMC0.75催化劑表面含有最豐富的晶格氧Oα,其相對含量(Oα相對含量計算方式為Oα/(Oα+Oβ+Oγ))為72.3%,其表面空位氧Oβ相對含量為16.4%,而CMC1.25催化劑表面晶格氧相對含量僅9.8%,空位氧相對含量高達85.3%;CMC1和CMC2催化劑具有最多的表面氧,其他濃度的Ce催化劑也表現(xiàn)出氧種類之間較大的濃度差異。不同含量的Ce與Co、Mn金屬氧化物之間相互作用對催化劑表面氧濃度有較大影響,影響催化劑催化性能。

表1 XPS光譜計算的氧物質(zhì)組成Table 1 Oxygen composition calculated by XPS spectrum

圖5 不同催化劑的XPS分峰圖譜Fig.5 XPS peak separation maps of different catalysts
2.5 H2-TPR
CMC系列催化劑H2-TPR曲線如圖6所示,整個TPR曲線可分為3個區(qū)域:100~250、250~500、500~900 ℃,分別對應屬于Mn4+、Co3+及CeO2和晶格氧的還原[13,15,18]。隨Ce物質(zhì)的量比增加,歸屬于Co3+的寬還原峰中心明顯向低溫移動,表明CeO2的摻雜導致混合氧化物電荷不平衡和晶格畸變,促進了活性氧的產(chǎn)生,使其更易被還原。特別地,CMC1.25、CMC1.5催化劑在200 ℃左右出現(xiàn)還原峰,這可能與表面活性氧和部分Mn的還原作用有關。Ce物質(zhì)的量比大于1.5時,樣品在310 ℃附近向高溫移動,峰強度隨Ce摻雜量的增加而增加,這是由于Ce離子在催化劑固溶界面上過剩,這一部分Ce因其與Mn、Co相互作用較弱,從而消耗了更多H2。

圖6 不同催化劑的H2-TPR譜圖Fig.6 H2-TPR profiles of different catalysts
3 催化劑脫硝性能
3.1 CO-SCR催化活性
CO體積分數(shù)1 000×10-6、NOx體積分數(shù)500×10-6時,CMC系列催化劑的CO-SCR活性如圖7所示。CMC0.75催化劑的NOx轉化率在起始溫度100 ℃時為18%,并隨溫度升高而增加,在175 ℃時達到峰值44%,繼續(xù)升高溫度其轉化率反而下降;CMC1.25、CMC1.5和CMC1.75催化劑在整個溫度區(qū)間均表現(xiàn)出較低的NOx轉化率;CMC2催化劑在整個溫度區(qū)間具有最佳的催化活性,在起始溫度100 ℃時為17%,隨溫度升高而增加,特別是溫度高于175 ℃時,轉化率增速加大,225 ℃時NOx完全轉化。同時,不同催化劑的CO氧化率也表現(xiàn)出較大差異,不同催化劑在溫度低于175 ℃時,其CO氧化率差異較大,而溫度高于175 ℃時,CO氧化率均較高,除了CMC2催化劑CO氧化率僅98%外,其余催化劑的CO氧化率幾乎達100%。與前期文獻研究相比[19],CMC系列催化劑在CO-SCR反應中表現(xiàn)出較好的抗O2氧化性能,特別是CMC0.75催化劑,在150~175 ℃低溫下其抗氧抑制性能最佳,而高溫下CMC2催化劑抗氧抑制性能最佳,這可能與表面負載的Ce較多有關,低溫下Ce負載量小,Co和Mn摻雜到Ce中,相對濃度高,表面O豐富,可自由流動,導致電子轉移快,而高溫下,Ce表面的O流動加快,CMC2催化劑表現(xiàn)出最佳的抗氧抑制性能。

圖7 CO-SCR反應中不同催化劑的催化活性Fig.7 Catalytic activity of different catalysts in CO-SCR reaction
3.2 NH3-SCR催化活性
NH3體積分數(shù)600×10-6、NOx體積分數(shù)500×10-6時,CMC系列催化劑的NH3-SCR脫硝活性如圖8所示,CMC0.75催化劑在100 ℃時NOx轉化率達84%,繼續(xù)升高溫度,NOx轉化率增長緩慢,125~175 ℃達100%,繼續(xù)升高溫度,NOx轉化率反而下降;CMC1.25催化劑呈現(xiàn)類似趨勢,但其NOx轉化效率相比CMC0.75催化劑更高,100~200 ℃下NOx幾乎完全轉化。在此溫度區(qū)間除CMC1.5催化劑外,其余催化劑隨溫度升高,NOx轉化率均先升高后下降,且175 ℃是NOx轉換效率由升高到下降的關鍵溫度點,需要注意,除CMC0.75和CMC1.25催化劑外,其余催化劑在整個溫度區(qū)間NOx轉化率較低。

圖8 NH3-SCR反應中不同催化劑的催化活性Fig.8 Catalytic activity of different catalysts in NH3-SCR reaction
CMC1.25催化劑在100~175 ℃轉化率隨溫度升高而升高,超過175 ℃時開始下降,但降幅不大;CMC2催化劑的脫硝效率先下降后上升,這是由于只有NH3脫硝的環(huán)境下,125 ℃相較催化劑適宜反應溫度較低,此時發(fā)生NH3-SCR反應較少,其他副反應進行過程中導致NOx濃度較初始時刻出現(xiàn)濃度下降現(xiàn)象,125~225 ℃,隨溫度升高,CMC2催化劑脫硝效率略增加,可從側面佐證該論證。
3.3 CO/NH3協(xié)同催化活性
CO體積分數(shù)700×10-6、NH3體積分數(shù)300×10-6、NOx體積分數(shù)500×10-6時,CMC系列催化劑的CO/NH3協(xié)同脫硝活性如圖9所示,CMC0.75催化劑在100~225 ℃內(nèi)NOx轉化率呈整體下降,但在125 ℃時脫硝效率高達98%,且溫度低于200 ℃時最低值也達到了75%,而其他催化劑在100~200 ℃內(nèi)NOx轉化率整體較低,最高也僅有81%。其中CMC1.5催化劑在175和200 ℃時具有與CMC0.75催化劑差異較小的NOx轉化率,而在225 ℃時,CMC1和CMC1.25催化劑表現(xiàn)出較好的NOx轉化率,其轉化率高于70%。此反應中,CO氧化率與CO-SCR脫硝反應中存在較大差異,全部催化劑在溫度低于125 ℃時CO氧化率均較低,最大值僅在10%左右,隨溫度升高,CMC0.75、CMC1.5和CMC1.75催化劑CO氧化率快速上升,并在225 ℃時達到100% CO氧化,而CMC1.25和CMC2催化劑CO氧化率則隨溫度增加上升較緩慢,特別是CMC2催化劑,CO氧化率在225 ℃時為最大值,僅為18%。

圖9 CO/NH3協(xié)同反應中不同催化劑的催化活性Fig.9 Catalytic activity of different catalysts in CO/NH3 synergistic reaction
4 機理分析
4.1 Ce物質(zhì)的量比對催化劑結構的影響
由于Ce晶胞尺寸較大,CeO2晶胞成為催化劑的主框架結構,且隨CMC催化劑中Ce物質(zhì)的量比增加,催化劑結構變化較大。首先Ce物質(zhì)的量比增加抑制了Co3O4中晶粒生長,導致Co3O4的晶粒尺寸由13.7 nm逐漸減少至10.6 nm,同時Mn物種較好分散在催化劑表面,且Co3O4和CeO2仍保持原有晶格結構;其次仍有部分Co或Mn原子與Ce原子相互摻雜,導致金屬晶格畸變,催化劑表面形成缺陷結構,并生成大量氧空位;最后,Ce物質(zhì)的量比較大時,CMC催化劑無法容納較多CeO2,導致CeO2覆蓋催化劑表面結構,且過剩的CeO2在催化劑表面出現(xiàn)團聚現(xiàn)象,阻礙了Mn和Co物種參與催化反應。
4.2 Ce物質(zhì)的量比對催化劑性能的影響
CMC系列催化劑表現(xiàn)出一定的抗氧抑制能力。Ce物質(zhì)的量比較低時,低溫下CO-SCR反應活性較好,而隨Ce物質(zhì)的量比增加,過多的Ce會覆蓋Co和Mn物種,導致其難以參與反應,影響反應過程中電子轉移,使催化劑抗氧抑制能力下降;隨溫度升高,表面氧在催化劑表面流動加快,促進反應進行,此時含Ce較多的CMC2催化劑表現(xiàn)出最佳的抗氧抑制性能。
由于催化劑表面含有較多酸性位,CMC0.75和CMC1.25催化劑表現(xiàn)出較好的NH3-SCR脫硝活性,但CO-SCR反應與NH3-SCR反應遵循不同的反應機理,CO-SCR以E-R機理為主[20],即吸附態(tài)的NO物種與氣態(tài)CO分子直接反應生成N2和CO2,而參與NH3-SCR主要遵循L-H機理[21],NH3與NO分子首先在催化劑表面吸附,進而吸附態(tài)的NO與NH3物種反應生成N2和H2O,因此當CO協(xié)同NH3脫硝時,相比NH3-SCR反應,催化劑的活性整體下降,而對于CMC0.75催化劑,在相對較低溫度下,其協(xié)同脫硝效率仍較高,這可能是由于催化劑含有的Co、Mn和Ce金屬氧化物具有極高的氧化能力,不僅可促使CO氧化為CO2,還可促使NOx轉化為其他含氮物質(zhì),因此合理控制不同金屬間的比例與分布,可以提高催化劑表面氧化能力,增強表面氧流動,從而有效增強協(xié)同催化活性。
5 結 論
1)催化劑中Ce物質(zhì)的量比增加抑制了Co3O4中晶粒生長,導致Co3O4和CeO2在保持原有晶格結構的同時,部分Co或Mn原子與Ce原子發(fā)生相互摻雜,導致金屬晶格畸變,促使催化劑表面形成缺陷結構,并生成大量氧空位,同時Ce物質(zhì)的量比較大時,導致CeO2覆蓋催化劑表面結構,且過剩的CeO2在催化劑表面出現(xiàn)團聚現(xiàn)象,阻礙Mn和Co物種參與催化反應。
2)Co-Mn-Ce催化劑表現(xiàn)出一定的抗氧抑制能力,特別是Ce物質(zhì)的量比較低時,低溫下CO-SCR反應活性較好,而隨著Ce物質(zhì)的量比增加,催化劑抗氧抑制能力下降;同時隨溫度升高,表面氧在催化劑表面流動加快,促進反應進行,此時含Ce較多的CMC2催化劑表現(xiàn)出最佳的抗氧抑制性能。
3)CO降低了NH3-SCR脫硝活性,但對于CMC0.75催化劑,在相對較低溫度下,其協(xié)同脫硝效率仍較高,這可能是由于催化劑含有的Co、Mn和Ce金屬氧化物具有極高的氧化能力,因此合理控制不同金屬間的比例與分布,可提高催化劑表面氧化能力,增強表面氧流動,從而有效增強協(xié)同催化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