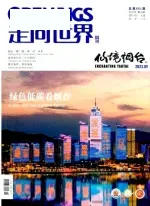蘇軾與濟南似被前緣注
張智輝

“應似飛鴻踏雪泥”,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蘇軾以六十六歲人生謝幕。“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人間絕版”的蘇軾,冥冥中緣結濟南,且留下諸多詩文佳話。《濟南通史宋金元卷》記載:“到神宗熙寧時,蘇轍出任齊州掌書記,蘇軾則知密州,并兩次經過濟南。”
宋熙寧十年(1077)二月初一這天,位于濟南王舍人莊的張掞(字文裕)故宅格外熱鬧,大文豪蘇軾來到府上拜謁,寫下《張文裕挽詞》:“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空推德業余。每見便聞曹植句,至今傳寶魏華書。濟南名士新凋喪,劍外生祠已潔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喬木鄭公廬。”并留下了“讀書堂”墨寶。
張掞,齊州歷城人,進士出身,是北宋時期歷事三朝的重臣。此時,張掞已故三年。“讀書堂”三字,既是對張氏一門重德行精學問的贊許,也飽含著對故友后人的殷切期望。蘇軾文章書法名傾朝野,能得到他的題字,是一件難得的事,張掞后人珍而寶之,不久后即刻石為碑。有文史專家推測,張家此時當有一讀書學習的堂所,蘇軾故而題此三字。
金元文學家元好問見過此碑,他在《濟南行記》中記載:“繡江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后來,該碑不知何故被埋入地下。明萬歷初年,村民在修房挖宅基的時候復將其挖出,后被運往歷城縣學文廟。
該碑后亡佚。我們現在能看到的“讀書堂 ”三字,是不知拓于何時的拓片。
千年文豪題字王舍人,人們不禁要問——你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
史料可考,此時正值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春,蘇軾卸任密州(山東諸城)太守,轉徙徐州,路經濟南。
蘇軾任職密州緣起兄弟之情。蘇轍在《超然臺記敘》中寫道:“子瞻(蘇軾字子瞻)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轍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
1073年,蘇轍“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自請而來,任齊州(濟南)掌書記。為了離蘇轍更近一點,蘇軾“拋棄”了湖山秀麗的杭州,于1074年底來到密州任職。但是到了密州,兄弟二人卻仍然不能相見。
丙辰(1076年)中秋,蘇軾和蘇轍已經離別6年之久了。“每逢佳節倍思親”,面對一輪明月,蘇軾寫下了千古第一中秋詞“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兼懷子由”。
懷著重逢的祈愿,蘇軾首次來到濟南。
老城墻外,馬蹄嗒嗒,雪地泥濘。蘇軾遠遠望見了三個侄兒恭立雪中,翹首企盼伯父的到來。“憶過濟南春未動,三子出迎殘雪里。我時移守古河東,酒肉淋漓渾舍喜。”多年后,他回憶當年赴濟場景,字里行間盡是滿滿的喜悅和感動。
圓缺皆是緣。蘇軾這次濟南行,有遺憾也有驚喜。蘇轍恰好進京述職不在濟南,少了一次文壇兄弟“雙星會”。時任齊州知州的李常(字公擇,北宋著名詩人黃庭堅的舅父),是蘇軾故友。在此期間,李常陪蘇軾賞檻泉(趵突泉)、游龍山,即景賦詩,互為唱和,行程滿滿。
檻泉有緣,蘇子大駕光臨。蘇軾在李常等人的陪同下游覽檻泉,觀賞了檻泉旁的梅花,并“寫枯木一枝于檻泉亭之壁”(見《濟南金石志》卷四)。
對這“枯木一枝”的解讀,眾說紛紜。有“題字說”,還有“畫畫說”。原記載在《禹城縣志》中,后收入乾隆《歷城縣志》的說法是:北宋時檻泉位于寺丞劉詔家庭院內。熙寧十年蘇軾游檻泉在墻壁上寫下“枯木一枝”四字,后來劉詔讓人刻石。此石刻后來輾轉到了禹城文廟中,因前來求字或摩拓的人太多,當地官吏怕得罪人,索性把刻石扔進井中,碎為數塊。再后來,有人撈出碎石比著筆跡制成木版,可字跡卻失去神韻。
“更憶檻泉亭,插花云髻重。蕭然臥灊麓,愁聽春禽哢。”對這次客居濟南期間的檻泉之游,蘇軾印象極深,并追憶與李常詩文往來之趣:“忽見早梅花,不飲但孤諷。詩成獨寄我,字字愈頭痛。”
“濟南春好雪初晴,才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還作陽關斷腸聲。”此行,蘇軾還在好友的陪同下策馬暢游龍山(章丘),欣然寫下《答李公擇》。雪后初霽,春光正好,心情豁然開朗。“馬足輕”應脫胎于王維“雪盡馬蹄輕”,與“雪初晴”相照應,即景即事,借物寫人。后兩句溫馨中有戲謔,以“請客對主”的巧妙技法,道出與老友的惜別離,情趣盎然。
蘇軾回憶抵達濟南時的窘態,“敝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自笑餐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宦游到處身如寄,農事何時手自親。剩作新詩與君和,莫因風雨廢鳴晨。”(《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裹著破氈,騎著瘦馬,忍不住想起了在北海渴飲雪、饑吞氈的蘇武前輩。他慨嘆宦海沉浮,與老友互訴衷腸。
“夜擁笙歌霅水濱,回頭樂事總成塵。今年送汝作太守,到處逢君是主人。聚散細思都是夢,身名漸覺兩非親。相從繼燭何須問,蝙蝠飛時日正晨。”往事不堪回首,聚散皆是夢。
透過這珍貴的詩文,可以略略感受946年前濟南那個空氣里都彌漫著詩意的春天。名滿天下的蘇軾,所到之處皆詩意。
蘇軾首次來濟,盤桓一月有余,緣分再續已是10年之后。
元豐八年(1085)六月,蘇軾奉旨知登州(治所在今蓬萊市)軍州事,再次踏上了齊魯大地,并于十月十五抵達登州任所。誰知朝廷政局多變,改革派與保守派輪番上臺,受其影響,任命朝令夕改。僅在5天之后,蘇軾又接到了要他進京擔任禮部員外郎的任命。
于是,他只好于當年11月初匆匆地離開了登州,趕赴汴京(即今河南開封)。機緣巧合,在赴京途中,蘇軾第二次來到了濟南。
這次仍為過客,行色匆匆,但有備而來,不顧旅途疲憊,馬不停蹄,城西拜佛,城東訪友,興致勃勃。
12月路經長清縣時,吸引了眾多“蘇粉”追捧。長清縣真相院(位于長清老城區西北隅)住持法泰是其中一位,他誠邀蘇軾到真相寺一敘。當蘇軾得知法泰所建十三層磚塔(名全陽塔,今已不存)未有葬物,便想將蘇轍所藏的釋迦舍利捐獻出來,為已過世的父母祈求“冥福”。法泰聽后當然是求之不得,只是當時蘇軾急急趕赴京師上任,并未留一物。
這位法泰是個行動派,第2年就赴京師找蘇軾拜請舍利,并請蘇軾撰寫塔銘。出于對佛的虔誠和對父母的敬重,蘇軾一改往日的隨意灑脫,鄭重其事地寫下了《齊州長清縣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敘)》,然后又贈法泰“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眾人,以具棺槨”。元祐二年(1087),法泰又將東坡書跡刻勒于石。
該刻石于1965年在全陽塔地宮中出土,現被長清區博物館珍藏。從保存的碑刻看,書刻精湛,用筆豐腴跌宕,結體天真爛漫,字字神完氣足,如珠似璣,堪為蘇軾書中逸品。
法泰去世后,真相院的繼任住持文海于宣和三年(1121)也據東坡書跡刻石一塊,這塊刻石現亦存于長清區博物館。只是由于歷代摩拓過多,其形神俱遜于法泰刻石。因有復刻,故市場所見拓片有兩種。
蘇軾此行再到章丘龍山鎮看望時任龍山監鎮的宋寶國。這位宋寶國頗受王安石器重,當時宋寶國把王安石所書的一卷《華嚴經解》給蘇軾看,并請蘇軾為之作跋。蘇軾因此作了《跋王氏華嚴經解》一文。
蘇軾緣結濟南,有師生緣亦有“同事緣”。《宋史》和《濟南通史宋金元卷》記載: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蘇軾”。“蘇門后四學士”之一李格非為章丘明水鎮人。雙方建立了密切的師生之誼,元豐六年(1083),蘇軾被貶謫到黃州時,李格非前往拜訪,蘇軾驚喜交加,大為感動。這李格非即是李清照的父親。
蘇軾在任密州太守時,章丘人劉庭式也在此任職。二人配合默契關系甚洽,蘇軾曾寫《書劉庭式事》贊頌劉庭式中進士后不棄盲女與之白頭偕老,這一經典愛情故事被傳為美談。
蘇軾問劉庭式:“哀生于愛,愛生于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劉庭式回答說:“只是因為我知道死去的是我的結發妻子而已,她有目是我的妻子,無目也是我的妻子啊!如果我因她容貌俊美才生愛戀之意,因對她有愛戀之意才生哀痛之情,那么隨著她逐漸變得年老色衰,我對她的愛戀之意就會越來越少,她死后也就不會有哀痛之情了。如果那樣的話,那些站在大街上揮舞衣袖、用眼神挑逗男人、賣弄風流的女人,豈不是都可以娶作妻室了嗎?”蘇軾聽了劉庭式的這番話后,至為感動。
蘇軾一生如雷似風,少年及第,名動朝野,烏臺詩案,大難不死,仕途蹭蹬,宦海游歷“黃州惠州儋州”。其實又何止于此,還有“密州徐州齊州”。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這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彌留之際,仍不忘與好友互懟“西方不無,著力即差。”
蘇子之于濟南,何曾是過客,仿佛有一根紅線相牽,折折疊疊,有緣有分。
Su Shi at age of 66 during the Emperor Huizong’s region in 1101. Su Shi, whose poetic achievement was unparalleled in the circle, had a much-told story of developing a liking for Jinan.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Su Shi visited Jinan twice when he took up the post of chief of Mi Prefecture. To some extent, Su Shi had a predestined relationship with Jin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