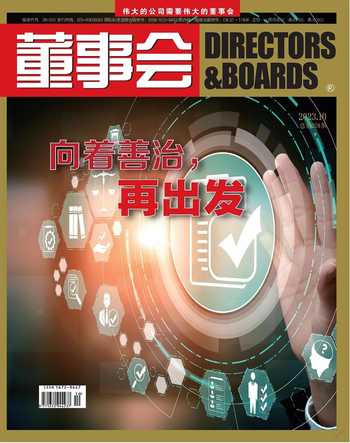“燒錢”的新經濟企業如何設計治理制度
鄭志剛
燒錢的新經濟企業公司治理制度設計的核心邏輯,是在創新鼓勵和權益保護二者之間尋求平衡,不再是簡單的“防火、防盜、防經理人”
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將由信息技術及其應用產生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等新型經濟形態概括為“新經濟”,其最早出現在1996年12月出版的美國《商業周刊》上。新經濟企業已逐漸成為全球后疫情時代經濟復蘇和增長的新引擎。
“好的虧損”挑戰治理制度設計
為了搶占賽道,不同于傳統企業,一些新經濟企業尤其是平臺經濟,往往選擇看上去難以想象的“當期收益無法覆蓋成本”的“燒錢”模式。如果把傳統企業始終較為穩定的現金流分布描述為“蜈蚣狀”(見圖1),對于短期內大量籌資流入與投資流出、現金流呈現出交錯態勢的新經濟企業,我們更愿意將其描述為“蜘蛛狀”現金流分布(見圖2)。
這種以犧牲前期利潤為代價,尋求市場快速擴張與業務模式加速成熟的“燒錢”行為自然離不開外部融資,尤其是權益融資的支持。新經濟企業“蜘蛛狀”現金流分布決定了必須選擇同樣特殊的權益融資結構來匹配。
我們以蔚來汽車為例,這家新能源汽車企業從成立到上市不到4年的時間內,完成了總融資金額過22億美元的7輪融資,引入包括高瓴資本、紅杉中國在內的27家知名風險投資機構,“燒錢”程度遠超傳統工業企業。盡管營業利潤的巨額虧損使其進入“2020年中概股虧損排名前五”,但公司上市后營業總收入與總市值的雙料超額增長表現亮眼。相比于短期“壞的盈利”,“燒錢”致力于培育和創造市場的“好的虧損”似乎成為新經濟企業創業早期必經的戰略選擇。
以中概股為例,其中的新經濟企業IPO前融資超過4輪的,占比超過40%(見表1)。
我們關心的問題是,一家新經濟企業如何說服外部投資者為其“燒錢”的行為埋單呢?換句話說,“燒錢”的新經濟企業應該如何設計治理制度?具體而言,對于創業團隊,在被迫進行外部權益融資引入大量股東后,如何保持對“燒錢”業務模式持續的主導權?對外部投資者而言,如何在公司治理制度設計上建立發揮影響力的路徑與機制,以確保自己對以犧牲前期利潤為代價的“燒錢”新經濟企業的投資是安全的?
可以說,“燒錢”的新經濟企業如何設計治理制度,向公司治理理論和實踐提出了新的挑戰。
雙重股權結構與創始人兼任CEO
對于具有典型“燒錢”行為的新經濟企業,為了獲得外部融資支持,創業團隊股權稀釋似乎不可避免。那么,這些在引入外部資金支持過程中股權可能稀釋的創業團隊,如何保持對業務模式創新的主導、在認為還需要“燒錢”的時候能夠繼續“燒錢”呢?
在傳統控制權安排強調“同股同權”和“一股一票”原則下,創業團隊股權稀釋將有業務模式創新主導權旁落的風險。我們的研究發現,兼具外部融資實現與加強公司控制功能的發行雙重甚至多重股權結構股票,形成投票權配置權重向創業團隊傾斜的“同股不同權”構架,成為眾多“燒錢”新經濟企業的理想選擇。
仍以蔚來汽車為例。公司上市時,創始人李斌作為第一大股東僅持股14.5%,與持股12.9%的第二大股東騰訊相比,持股比例僅相差1.6%。2018年9月在美國紐交所上市的蔚來汽車選擇同時發行ABC三類股票。創始團隊持有的C類股票一股有8份投票權,騰訊持有的B類股票一股有4份投票權,其他股東持有的A類股票一股僅有1份投票權。通過投票權配置權重向創業團隊傾斜的“同股不同權”構架,出資額占14.5%的創始人李斌通過持有C類股票獲得了48.3%的投票權,而出資額相差1.6%的騰訊卻只獲得了21.5%的投票權。由此,“同股不同權”構架幫助蔚來汽車創始人實現了有限資金投入下對企業的實際控制。蔚來汽車也成為繼Snap之后全球同時發行ABC三類股票的為數不多的公司之一。
除了形成投票權配置權重向創始人傾斜的“同股不同權”構架,我們的研究同時發現,為了確保業務模式主導權,在燒錢的新經濟企業中,創業團隊成員甚至創始人本人選擇兼任公司董事長或CEO。例如,蔚來汽車創始人李斌、京東創始人劉強東、拼多多創始人黃崢等,均選擇在上市時兼任公司董事長及CEO。
通過上述兩方面的公司治理制度設計,董事會中的董事和管理團隊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被股東雇用的“打工仔”,而是和股東一樣,成為當家作主的“主人”。這對其人力資本投資的持續激勵自然不言而喻。
我和我的團隊基于中概股的大樣本經驗研究表明,采用雙重股權結構上市、創始人兼任公司董事長及CEO的新經濟企業,在研發投入上持續增加,長期績效表現良好。上述結果的出現,很大程度源于股東內部不同類型、股東之間的深度專業化分工,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其中,一部分股東(創業團隊)專注業務模式創新,另一部分股東則專注風險分擔。而深度專業化分工必然帶來效率的提升。
董事安排限制條款保護外部投資者權益
在公司治理理論上,我們把反映出資比例進而能夠為作出錯誤決策承擔責任的能力稱為“現金流權”,而把反映對重大事項的影響力進而集中的投票權稱為“控制權”。在前述投票權配置權重傾斜和創始人兼任董事長或CEO的制度安排下,現金流權與控制權出現了“分離”。我們看到,投票權配置權重向創業團隊傾斜固然保證了其對業務模式創新主導權,但潛在的問題是,在現金流權與控制權“分離”下,這些投票權集中的創業團隊的權利與責任不對稱,因而道德風險的發生可能性增加。那么,如何在投票權配置權重傾斜下,讓外部投資者的權益得到有效保護呢?
創始人兼任董事長或CEO的情形下,在董事會中爭取更多董事席位,確保在董事會中的話語權,進而獲得知情的通道和權益保護的路徑,對于保護外部投資者權益變得至關重要。我們的研究表明,越來越多的新經濟企業通過簽署股東協議,以書面形式對創業團隊和其他大股東有權委派的董事數量作出明確規定。IPO前進行過6輪融資,采用雙重股權結構,且由聯合創始人唐巖兼任董事長和CEO,在NASDAQ上市的摯文集團(陌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按照主要股東達成的股權協議,在9名董事會成員中,發行后持股20.4%的阿里巴巴可以指定2名董事,持股17.7%的Matrix?Partners指定2名董事,持股5%的Sequoia?Funds和Rich?Moon分別指定1名董事,持股26.3%的聯合創始人唐巖“只能”指定剩余的3名董事。
我們的研究發現,在投票權配置權重傾斜的新經濟企業中,簽署具有董事安排限制條款的股東協議的可能性更大。而這提高了新經濟企業的資產利用效率,降低了代理沖突,成為控制權傾斜背景下外部投資者權益有效保護的制度安排。
在創新鼓勵和權益保護之間尋求平衡
圍繞存在“燒錢”行為的新經濟企業的公司治理制度設計,我們有以下政策建議:
其一,在互聯網時代外部投資者與創業團隊圍繞業務模式、創新信息不對稱加劇的現實背景下,對于用于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燒錢”行為不是簡單排斥,而是通過新經濟企業的公司治理制度設計加以必要引導,使其停留在“合理”范圍內。
其二,盡管投票權配置權重向創業團隊適度傾斜的“同股不同權”構架,看起來權利與責任不匹配,但我們更要看到其鼓勵業務模式創新的一面,應采取更加包容鼓勵的態度。
其三,對于投票權配置權重傾斜下創業團隊的道德風險傾向,主要股東應通過簽署具有董事安排限制條款的股東協議,提高股東在董事會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加強對投資者權益的保護。
其四,“燒錢”的新經濟企業公司治理制度設計的核心邏輯,是在創新鼓勵和權益保護二者之間尋求平衡,不再是簡單的“防火、防盜、防經理人”。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學教授,金天對本文的寫作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