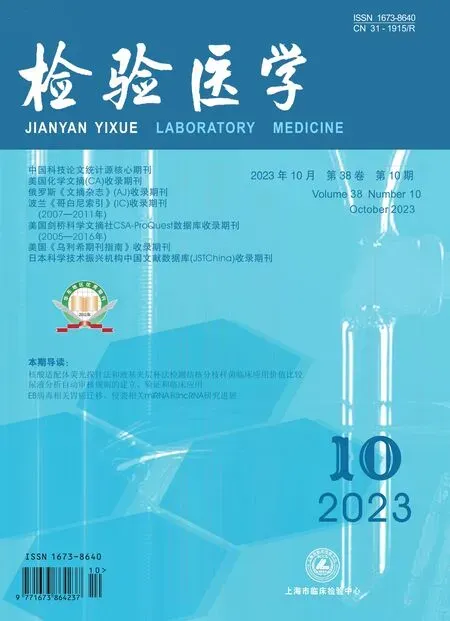EB病毒相關胃癌遷移、侵襲相關miRNA和lncRNA研究進展
郭 霜 劉紅莉 李 婭
[西安市人民醫院(西安市第四醫院),陜西 西安 710000]
主題詞:非編碼RNA;遷移;侵襲;EB病毒;胃癌
胃癌是消化系統常見的惡性腫瘤,據估計,全球每年新增病例超過100萬[1]。由于胃癌早期無癥狀,患者被確診時常處于晚期。侵襲和轉移是影響胃癌患者生存率的主要因素。以往主要依據組織學形態和細胞生物學特性進行胃癌病理分型。2014年,美國癌癥基因組圖譜研究計劃(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提出了新的胃癌分子分型[2],將胃癌腫瘤類型分為 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陽性、微衛星不穩定型、基因組穩定型和染色體不穩定型[3]。EBV感染是胃癌的主要病因之一,EB病毒相關胃癌(Epstein-Barr virus-associated gastric cancer,EBVaGC)約占所有胃癌的1.3%~30.9%[4]。EBV主要以潛伏復制和溶出復制2種形式感染細胞。初次感染通過口腔途徑形成終生攜帶病毒的狀態稱為潛伏感染[5]。這種潛伏期的建立對于維持病毒在受感染細胞中的終身持久性至關重要,而病毒維持持久性感染與EBV核抗原、潛伏膜蛋白、BamHⅠ A右向開放閱讀框(BamHⅠ A rightward openreading frame,BARF)和病毒編碼的多種非編碼RNA(non-coding RNA,ncRNA)有關。ncRNA可調節基因表達,是一種重要的表觀遺傳調控機制[6]。微小RNA(microRNA,miRNA)是由19~25個核苷酸組成的小RNA,可直接與mRNA的3'-非翻譯區(untranslated region,UTR)結合,抑制其翻譯。EBV編碼的miRNA通過表觀遺傳調節細胞周期進展、遷移、凋亡分子的表達,促進病毒復制和EBV相關腫瘤的發生、發展。長鏈非編碼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是指長度超過200個核苷酸且不具有蛋白質編碼能力的RNA,在一系列生物過程中具有重要功能。lncRNA可調節多種基因的表達,介導多種細胞通路,影響細胞穩態,影響腫瘤的發生、發展。一些宿主lncRNA對EBV感染具有調節作用,EBV編碼的lncRNA也在腫瘤的發展中發揮調節作用[7]。
EBV ncRNA可以通過抑制病毒基因和宿主細胞基因的表達抑制免疫細胞的活化和細胞毒性,進而抑制病毒抗原的表達和提呈,實現長期潛伏、免疫逃逸,促進宿主細胞永生和腫瘤發展[8]。本文重點闡述與遷移、侵襲表型相關的EBV和宿主編碼的miRNA、lncRNA,以及其他EBV編碼的ncRNA,如環狀RNA(circular RNA,circRNA)、EB病毒編碼的小RNA(Epstein-Barr virus-encoded RNA,EBER)在EBVaGC中的表達、功能和相互作用。
1 EBV相關的miRNA
EBV是第一個被發現自身編碼miRNA的病毒。在EBV基因組的2個區域:BamHⅠ片段H右向開放閱讀框(BamHⅠ fragment H rightward open-reading frame,BHRF)區域和BamHⅠA右向轉錄本(BamHⅠ A region rightward transcript,BART)區域中鑒定出25個EBV miRNA前體(圖1)[9]。其中22個EBV miRNA前體位于miR-BART內含子區域的2個集群中,其余3個miRNA前體出現在BHRF位點,這些前體能夠產生4種成熟的病毒miRNA。盡管已有研究證明BHRF1 miRNA可抑制受感染B細胞的凋亡[10],但目前尚未見文獻報道BHRF1 miRNA在胃癌中的表達。因此,對于EBV自身編碼的miRNA,目前主要研究其在EBVaGC中的表達和相關功能表型。

圖1 EBV編碼的ncRNA示意圖[9]
1.1 EBV編碼的miRNA
EBV編碼的miRNA通過表觀遺傳調控細胞遷移、侵襲、上皮-間質轉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凋亡等功能,在支持病毒復制和EBVaGC的發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miR-BART8-3p通過直接結合E3泛素蛋白連接酶--環脂蛋白38(ring finger protein 38,RNF38),并激活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和細胞外調節蛋白激酶1/2(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ERK1/2信號通路來促進腫瘤細胞的遷移、侵襲[11]。miR-BART10-3p直接靶向腫瘤抑制因子--dickkopf Wnt信號通路抑制因子(dickkopf WNT signaling pathway inhibitor 1,DKK1)的3'-UTR,并下調其表達,從而促進EBVaGC細胞的增殖和遷移[12]。有研究發現,miR-BART10-3p和miR-BART22通過靶向APC和DKK1激活Wnt信號通路,而APC和DKK1在促進EBVaGC轉移中發揮重要作用[13]。miR-BART4-5p能直接結合磷酸酶和張力蛋白同源物(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PTEN),并促進細胞侵襲和遷移。此外,miR-BART1的2個分支(-3p和-5p)在體外均能與PTEN直接結合,并激活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又稱Akt)、Akt/局部黏著斑激酶(focal adhesion kinase,FAK)/p130和Shc/絲裂原活化蛋白(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通路,從而誘導miR-BART-4-5p在腫瘤轉移中的附加效應[14]。高表達的miR-BART17-5p[15]和miR-BART22[16]抑制了腫瘤抑制因子kruppel樣因子2(kruppel-like factor 2,KLF2)的表達,該過程能增加細胞的運動和非貼壁性生長,促進EBVaGC的轉移。miR-BART2-5p和miR-BART11-5p通過靶向結合和抑制RB和p21的表達促進EBVaGC細胞增殖、遷移,抑制凋亡[17]。miR-BART11還會加速腫瘤的侵襲和轉移,影響患者的生存和預后[18]。miR-BART3-3p直接靶向抑制腫瘤抑制基因,導致p53的下游靶點p21下調;另外,miR-BART3-3p通過改變衰老相關分泌表型因子(senescence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SASP)和腫瘤中自然殺傷細胞、巨噬細胞的浸潤,抑制裸鼠胃癌細胞的衰老。miR-BART3-5p靶向抑制腫瘤因子DICE1促進癌細胞的生長和轉移[19]。miRBART5-5p直接靶向活化信號轉導和轉錄激活因子3蛋白抑制劑(protein inhibitor of activated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PIAS3),并通過miR-BART5/PIAS3/pSTAT3/程序性死亡受體-配體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軸促進PD-L1的表達,增強腫瘤細胞抗凋亡、增殖、侵襲、遷移和免疫逃逸,使胃癌患者臨床預后惡化,因此miRBART5-5p可能適用于PD-1/PD-L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治療[20]。
1.1.1 miR-BART參與EMT過程
SAITOH等[21]發現,部分EBV調控宿主惡性表型進展是通過參與EMT過程發揮作用的,揭示了EMT不僅是腫瘤侵襲、轉移發生的第一步,還是侵襲性和轉移性癌細胞擴散的根源。上皮型鈣黏蛋白(epithelial cadherin,E-Cad)是細胞間黏附的關鍵蛋白。受突變和表觀遺傳因素(如啟動子區域高甲基化)的影響,E-Cad在大多數腫瘤中表達下調,形成了建立和維持細胞與細胞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構。miRNA和lncRNA等非編碼轉錄物是腫瘤發生中控制基因表達、表觀遺傳的關鍵成分,能通過直接結合靶基因或受多種基因轉錄調控因素的影響,參與E-Cad功能的調節,不僅影響著腫瘤細胞的增殖和轉移,還影響著EMT[22]。
在EBV相關上皮腫瘤中,EBV編碼的miRBART9-5p和miR-BART9-3p會通過2條途徑參與EMT:1)miR-BART9與宿主hsa-miR-200a和hsa-miR-141的種子序列高度同源,且hsa-miR-200a和hsa-miR-141已被證實能夠抑制EBVaGC的EMT表型,因此有學者推測miR-BART9可能與宿主hsa-miR-200a和hsa-miR-141競爭結合靶標位點,從而促進腫瘤進展[23];2)miR-BART9-5p和miR-BART9-3p都能直接與編碼E-Cad的基因CDH1的3'-UTR結合,并下調其轉錄,且可能會沿著miR-200/E盒結合鋅指蛋白(zinc finger E-box-binding homeobox protein 1,ZEB1)/E-Cad軸引起反饋調控,進而下調宿主hsa-miR-200a的表達,影響EBVaGC細胞的增殖和侵襲能力[24]。miR-BART10-3p可以通過靶向BTRC抑制β-catenin和Snail的泛素化,從而調控許多EMT分子,如下調E-Cad、ZO-1和Claudin-1,上調ZEB1和神經型鈣黏蛋白(neural cadherin,N-Cad)[25]。miR-BART1-5p通過調控E-Cad、β-catenin和PTEN促進腫瘤細胞EMT過程[14]。有研究發現,miR-BART7能促進EMT關鍵分子Snail和β-catenin的高表達[26]。SONG等[27]發現,miR-BART11能下調Foxp1轉錄因子,通過直接影響胃腫瘤細胞或間接影響腫瘤微環境促進EMT。
1.1.2 miRNA-BART參與細胞凋亡過程
有研究發現,miR-BART15在EBVaGC中高表達,且miR-BART15能通過抑制凋亡抑制蛋白BRUCE的翻譯,并靶向抑制抗凋亡基因TAX1BP、NLRP3的表達,誘導凋亡[28]。miRBART1-3p能通過與失能同源物2(disabled homolog 2,DAB2)靶向結合,抑制胃癌細胞凋亡,促進細胞遷移。DAB2在多種癌癥類型中被認為是一種腫瘤抑制因子。從機制上來說,miR-BART1-3p/DAB2軸可能是通過調控DAB2的各種信號通路促進胃癌細胞周期進程、遷移和凋亡[29]。miR-BART5-3p在鼻咽癌和胃癌中上調,并促進癌細胞的生長,其可直接與p53編碼基因的3'-UTR結合,下調細胞周期依賴激酶抑制因子1A(cyclin-dependent kinase inhibitor 1A,CDKN1A)、BAX和FAS的表達[30],加速細胞周期進程,抑制細胞凋亡。也有學者觀察到miRBART5-5p可促進p53的降解[31]。此外,miRBART5-5p在EBV感染的胃上皮細胞中過表達,并靶向p53上調凋亡調控因子(p53 up-regulated modulator of apoptosis,PUMA),使其表達下調,該過程可抑制細胞凋亡,有助于細胞存活[32]。miR-BART4-5p在EBVaGC中能抑制BCL2家族成員促凋亡蛋白BH3相互作用結構域死亡激動劑(BH3-interacting domain death agonist,Bid)的表達[33]。miR-BART20-5p通過靶向BAD促進細胞增殖,抑制凋亡[34]。EBV miR-BART6-3p可通過lncRNA LOC553103/STMN1信號軸阻斷細胞周期G0/G1的進程,抑制腫瘤細胞增殖,促進凋亡。EBV miR-BART6-3p和miR-BART15是為數不多的2個能誘導癌細胞凋亡的病毒miRNA。有研究指出,miR-BART6-3p可靶向細胞基因并發揮其“抗癌”活性,可能主要是有助于病毒逃避宿主免疫系統監視,使其實現長期潛伏感染[35]。從這個意義上講,EBV編碼的基因不僅具有癌基因功能,還具有抑癌基因功能。
1.2 宿主編碼的miRNA
EBV感染可以調控宿主編碼的miRNA。MARQUITZ等[36]發現,在EBVaGC中宿主編碼的miR-34a低表達,該miRNA的表達降低是受到病毒蛋白EBNA1的抑制。所有EBV感染細胞都表達EBNA1,其是建立和維持EBV潛伏感染的必要基因。有研究發現,miR-34a表達降低會促使NADPH氧化酶2表達上調,在提高活性氧表達的同時,增強細胞的活力[37]。TREECE等[38]研究了EBV陽性和EBV陰性腫瘤中miRNA的表達,結果顯示,EBVaGC患者hsa-miR-21、hsa-miR-155和miR-196b表達與EBV陰性腫瘤患者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 25),他們使用NormFinder算法將這3種宿主miRNA確定為“歸一化因子”,表明這3種宿主miRNA與EBVaGC的疾病狀態有關;他們還發現,與未感染EBV的胃癌患者相比,EBVaGC患者癌組織和血漿hsa-miR-21表達均上調,hsa-miR-155和miR-196b在癌組織中表達上調,血漿中表達下調,這可能提示用某些血漿miRNA來判斷腫瘤來源是不準確的。有研究者探索了miR-196b的功能,發現其能下調促凋亡基因FAS的表達,抑制凋亡,增強腫瘤細胞的轉移能力,FAS的過表達能夠逆轉miR-196b介導的表型[39]。miR-21和hsa-miR-155均與細胞凋亡有關,其中miR-21可與FasL(外源性凋亡通路的成員)的3'-UTR結合,抑制凋亡[40]。miR-155在轉錄上調控Fas相關死亡域蛋白(Fas-associating protein with death domain,FADD)和半胱氨酸天冬氨酸特異性蛋白酶3(cysteinyl aspartate-specific protease 3,Caspase-3),而Caspase-3是作用于不同凋亡途徑以執行細胞死亡的關鍵效應蛋白酶之一。有研究結果顯示,miR-155可通過與Caspase-3的靶向結合來抑制細胞凋亡[41]。在與EMT過程相關的miRNA中,病毒編碼的BARF0、EBNA1和LMP2A可導致胃癌中前體pri-miR-200下調,進而下調成熟miR-200家族成員ZEB1、ZEB2和E-Cad,并進一步導致EBVaGC侵襲、轉移[42]。由此可見,EBV感染可調節宿主miRNA表達,有助于被感染的細胞逃避宿主的免疫反應,有利于病毒慢性感染和增強細胞活力,但具體作用機制有待進一步闡明。
2 EBV相關的lncRNA
EBV中編碼lncRNA的基因有2個,1個位于BamHⅠ H左向開放閱讀框1(BamHⅠ H leftward open reading frame 1,BHLF1)區域,另1個位于BART區域,BART區域的轉錄由一組高表達和選擇性剪接的轉錄本組成,這些轉錄本中包含多個開放閱讀框基因(BARF0、A73、RPMS1)。BART lncRNA位于EBV感染細胞的細胞核內,是EBVaGC最豐富的病毒聚腺苷化RNA。然而,這些開放閱讀框翻譯的蛋白質尚未見報道。近期多項研究結果表明,EBV BART lncRNA可通過表觀遺傳調控和染色質重塑影響宿主基因的表達,且在調控腫瘤細胞侵襲、遷移、增殖、免疫逃逸和血管生成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43]。
2.1 EBV編碼的lncRNA
有研究結果顯示,在胃癌AGS細胞系中轉染全長BART lncRNA可導致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血管內皮生長因子A(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VEGFA)]、未折疊蛋白反應(SLC7A11、ATF5)、凋亡(RNF144B)、細胞黏附和遷移(RASIP1、CDH11、VEGFA、ITGA6)相關的基因顯著下調[42]。此外,BART lncRNA可調節氧化還原酶活性、炎癥和免疫相關基因的表達。BHLF是一種在潛伏期開始時表達的溶環基因,長度為1 980個核苷酸,可編碼lncRNA[44]。以往研究發現,BHLF1只在病毒復制周期中通過在轉錄位點形成RNA-DNA雜交而發揮作用[45]。而YETMING等[46]發現,BHLF1在潛伏期也可轉錄,且能轉錄成lncRNA,促進病毒潛伏,遺憾的是,BHLFlncRNA在腫瘤發生中的具體作用還不清楚。值得一提的是,BHLF在募集RNA結合蛋白到EBV誘導的核結構中發揮結構和支架作用,因此,BHLF1 lncRNA可能有助于病毒復制[47]。
2.2 宿主編碼的lncRNA
EBV除了自身可編碼lncRNA影響宿主基因表達外,還能用自身基因實現對宿主lncRNA的調控。目前報道最多的是lncRNA SNHG8。有研究結果顯示,EBV陽性胃癌細胞lncRNA SNHG8表達顯著高于正常胃黏膜細胞或EBV陰性胃癌組織(P<0.01)[48]。EBVaGC中lncRNA SNHG8表達與TNM分期顯著相關,可影響多個胃癌特異性通路和EBV的靶基因[49]。與正常胃組織相比,lncRNA SNHG8在胃癌中的表達上調了14倍,通過對EBV基因組數據的篩選和富集分析,發現lncRNA SNHG8與EBV基因BHLF1、BHLF3和BNLF2a54顯著相關,并且lncRNA SNHG8通過與上述EBV基因相互作用影響多條胃癌特異性通路,并調控TRPM7、TRIM28、EIF4A2、RPL18A、PLD3和NAP1L1表達[49]。另外,有研究發現,BHRF1能夠促進lncRNA SNHG8表達,且lncRNA SNHG8能夠吸收miR-512-5p并上調三重基序蛋白(tripartite motif,TRIM)28和一系列效應物,如BCL-2、CCND1、PCNA、CDH1、CDH2、Snail和VIM,說明lncRNA SNHG8能通過miR-512-5p/TRIM28軸發揮作用,進而促進EBVaGC的發生和侵襲[50]。下調lncRNA SNHG8的表達可抑制EBVaGC細胞在體內外的增殖和集落形成,阻斷細胞周期,并促進細胞凋亡[51]。還有研究結果顯示,宿主lncRNA MALAT1在EBVaGC中高表達,且lncRNA MALAT1被認為是miR-124的海綿,并通過下調下游靶基因E-Cad,上調N-Cad,參與EMT的調控[52]。
以上研究結果揭示了EBVaGC中宿主編碼的lncRNA受EBV自身基因的調控,使研究者對參與EBVaGC的ncRNA有了一些認識,但其具體機制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2.3 EBV相關miRNA和lncRNA之間的作用
因lncRNA的長度遠長于miRNA,從而提供了吸附和結合大量miRNA的可能性,因此miRNA與lncRNA的相互作用主要以競爭內源性RNA(competing endogenous RNA,ceRNA)機制為主,這也緩沖和削弱了miRNA對其靶mRNA的直接調控,這種相互作用被稱為ceRNA網絡[53]。目前,對于EBV感染相關的ceRNA網絡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基于生物信息學分析。有研究者利用GEO數據庫對EBVaGC進行了數據挖掘,建立了ceRNA網絡,主要的ncRNA包括5個miRNA(hsa-miR-4446-3p、hsa-miR-5787、hsa-miR-1915-3p、hsa-miR-335-3p和hsa-miR-6877-3p)和2個lncRNA(RP5-1039K5.19和TP73-AS1),其中hsa-miR-335-3p可抑制胃癌細胞的增殖、遷移和侵襲,其他4個miRNA參與了乳腺癌、酒精性肝細胞肝癌和結直腸癌中糖代謝和耐藥的調控途徑[54-56]。以往研究發現,lncRNA TP73-AS1在肝細胞肝癌、膀胱癌、乳腺癌、骨肉瘤、宮頸癌、胃癌等人類多系統腫瘤中異常表達,并可調節這些腫瘤的發生、發展,因此被認為是人類腫瘤的潛在生物標志物和治療靶點[57]。lncRNA RP5-1039K5.19的功能和作用尚未見文獻報道,但已發現其在不同的ceRNA調控網絡中存在結合的靶基因,如GDF5、CXCL10、PTGER3、SMAD5等,其中GDF5和CXCL10表達在EBVaGC患者癌組織與癌旁組織中存在顯著差異(P=0.047),這可能與EBVaGC基因調控機制不同有關[58]。有研究表明,HOX基因家族與腫瘤的發生有關,其中HOTAIR是一種位于HOXC位點的lncRNA,是胃癌的致癌因子;lncRNA HOTAIR可作為hsa-miR-331-3p的ceRNA,增強Erbb-b2受體酪氨酸激酶2的表達,促進胃癌細胞的增殖和侵襲[59]。lncRNA MALAT1作為hsa-miR-23b-3p的海綿,可減弱miR-23b-3p對自噬相關蛋白12的抑制作用,誘導化療耐藥[60]。這種相互作用不只局限于宿主lncRNA-miRNA之間,有學者還提出了“病毒和宿主競爭性RNA”的假說[61],并且有學者報道了“病毒和宿主競爭性RNA”這種相互作用存在于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C virus,HCV)、人乳頭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感染的宿主體內[62-63]。這種作用網絡在EBVaGC中同樣有跡可尋。有研究證實,lncRNA LOC553103在EBV感染的鼻咽癌和胃癌患者中異常表達,可促進腫瘤細胞侵襲、遷移、增殖和調節細胞周期。生物信息學分析、人類全基因組微陣列篩選和雙熒光素酶實驗結果表明,宿主lncRNA LOC553103是EBV miR-BART6-3p的直接靶點,miR-BART6-3p的表達可顯著抑制lncRNA LOC553103介導的腫瘤細胞遷移和侵襲,并可調節EMT相關分子E-Cad、Snail、N-Cad的表達水平,還可以通過破壞應力纖維的完整性來防止細胞假足的形成,同時顯著降低淋巴結轉移的風險[64]。目前,關于這一點的研究還相對較少,有學者采用ViRBase v2.0檔案預測了EBV編碼的miRBART與人類lncRNA之間的相互作用[9],并采用先導分析方法對EBV編碼的miR-BARTs構建了一個網絡,該網絡包括了在凋亡和EMT通路中被驗證的人類靶標,見圖2。

圖2 EBV編碼的miR-BART和宿主lncRNA之間的相互作用[9]
3 與EBV相關的其他ncRNA
3.1 circRNA
circRNA是一類共價閉合的RNA環,由于沒有5'或3'多聚A尾,因此不受RNase降解的影響。circRNA的功能主要有:1)作為miRNA海綿競爭性地抑制其相應的線性mRNA;2)順式調控轉錄或RNA剪接調控發揮其功能。此外,circRNA也起著“mRNA陷阱”的作用。在反向剪接過程中,circRNA可能會隔離翻譯起始位點,阻止某些可翻譯的正常線性轉錄本的表達,從而降低某些蛋白質的表達水平。
UNGERLEIDER等[65]在起源于B細胞系統的腫瘤和上皮來源腫瘤中鑒定出EBV基因組編碼的circRNA,證實EBV致癌基因RPMS1/BART和LMP2A編碼的相關circRNA與胃癌遷移、侵襲等不良預后相關。EBV circBART在所有EBV相關腫瘤的潛伏期表達[66]。有研究發現,EBV circLMP2A在SNU-4th細胞中大量表達,并主要定位在細胞質中[67]。TRIM59是TRIM家族的新成員,在腫瘤細胞增殖、凋亡、侵襲、遷移過程中起重要的作用。在胃癌中,TRIM59通過泛素化和降解p53蛋白來促進胃癌的發生,而circLMP2A作為miR-3908的海綿,能通過TRIM59/p53通路維持EBVaGC干細胞表型,因此EBV circLMP2A與EBVaGC患者的轉移和不良預后密切相關[68]。有研究結果顯示,EBV circLMP2A的高表達與EBVaGC中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和缺氧誘導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 alpha,HIF-1α)、VEGFA蛋白表達密切相關(P=0.006),其具體作用機制是EBV circLMP2A在缺氧條件下通過KH型剪接調節蛋白(KH-type splicing regulatory protein,KHSRP)/VHL/HIF-1α/VEGFA軸促進血管生成。在EBVaGC癌組織樣本中,EBV circRPMS1與遠隔轉移和不良預后相關。EBV circRPMS1通過將Sam68招募到METTL3啟動子來誘導METTL3表達,從而促進EBVaGC的進展[69]。因此,EBV circRPMS1、Sam68和METTL3可能是EBVaGC的治療靶點。目前,有關EBV circRNA在EBVaGC中的功能報道較少,因此對于circRNA的認識依舊不足。
3.2 EBER
IWAKIRI等[70]發現,在EBVaGC和鼻咽癌患者EBV潛伏感染期間,表達最多的ncRNA是EBV轉錄本EBER1和EBER2,其長度分別為167和172 nt。EBER1和EBER2的轉錄效率幾乎相同,EBER1的半衰期較長,因此其含量遠高于EBER2。EBER1和EBER2一級序列的同源性僅為54%,但二級結構具有明顯的相似性,并且EBER與RNA依賴蛋白激酶(protein kinase double-stranded RNA-dependent,PKR)密切相關。有學者發現,EBER在EBVaGC中普遍高表達,通過原位雜交技術在組織中檢測EBER表達量能夠作為診斷EBVaGC患者EBV是否處于潛伏感染的金標準[71]。此外,在EBVaGC中,高表達的EBER可以誘導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IGF-1)上調,IGF-1作為一種自分泌生長因子,能夠促進胃癌細胞增殖[72]。EBER還通過Toll樣受體3(Toll-like receptor-3,TRL3)及其下游信號分子腫瘤壞死因子α招募巨噬細胞,從而引發炎癥反應,促進腫瘤微環境的建立[73]。
4 小結與展望
近年來,隨著基因芯片、新一代測序技術的不斷完善,圍繞EBV編碼的miRNA、宿主miRNA和相關lncRNA、circRNA在病毒感染和腫瘤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等相關研究得到了快速發展,ncRNA因為參與了多種重要機制過程的調控逐漸成為研究熱點。本文介紹了EBV lncRNA、miRNA(特別是miR-BART)、circRNA、EBER和宿主編碼的相關ncRNA。研究發現,miR-BART在EBVaGC細胞中高表達,我們總結整理文獻發現了19種miR-BART與胃癌細胞遷移、侵襲、凋亡或EMT相關(表1)。另外,本文還介紹了宿主和病毒ncRNA之間相互作用的新型調控網絡,這種相互作用關系網極為復雜,因此對EBV胃癌中相關的lncRNAmiRNA相互作用機制的認識仍然不夠充分。目前,關于EBV編碼lncRNA作用的研究相對較少,學者們對EBV與circRNA之間的關系認識有限,尚有許多未研究的領域需要探索。總體來說,EBV相關ncRNA在病毒感染和腫瘤中發揮著關鍵作用,近年來的研究為EBV的致癌機制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為發現胃癌的生物標志物和治療靶點開辟了更多的可能性。

表1 胃癌惡性表型相關的EBV ncRNA與宿主ncR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