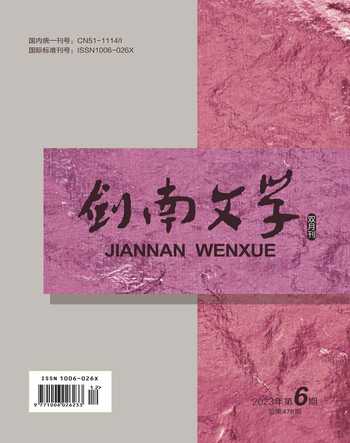奔跑的光棍
陳敏,1984年5月出生,四川蓬溪人,四川省作協(xié)會(huì)員,蓬溪縣作家協(xié)會(huì)主席。2000年開(kāi)始發(fā)表作品,先后在《中國(guó)農(nóng)村金融》《男生女生》《中華文學(xué)》《劍南文學(xué)》《川中文學(xué)》《文化遂寧》等刊物發(fā)表小說(shuō)、散文等數(shù)十萬(wàn)字。出版有中短篇小說(shuō)集《木魚的春天》。
木魚姓胥,至于名字,木魚寫不來(lái),別人也沒(méi)有叫過(guò)。
無(wú)所謂。這名字就像錢財(cái),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倒是可有可無(wú)的。比起名字,他更在乎自己的心跳,呼吸。因?yàn)榛钪湍茔裤揭环輥?lái)之不易的愛(ài)情,晚上,會(huì)做同一個(gè)美夢(mèng)。
(一)
木魚憧憬著一個(gè)春天。
到那個(gè)時(shí)候,油菜花競(jìng)相開(kāi)放,耀眼的金黃會(huì)刺得他雙眼隱隱作痛。他便不得不把眼睛瞇成一條線,貓一樣地思考。比如,油菜花下那成群的螞蟻會(huì)不會(huì)趁他不注意啃食他渾濁的眼球,讓他在一瞬間看到黑暗提前來(lái)臨;又比如,這個(gè)春天過(guò)了,會(huì)不會(huì)有人也隨著那些美好一并去了,用明媚的春光掩蓋悲傷。
木魚日漸老了,雖不聰明,卻也懂了許多。過(guò)去的幾十年,每一年都是那么的平淡、煎熬,他像一塊普通的石頭,在一鍋潲水中反反復(fù)復(fù)地烹煮,早就沉積了一身濃重的貌似歲月的味道。
對(duì)于已經(jīng)活了五十六歲的木魚來(lái)說(shuō),四就是五十六后面的零頭,像小數(shù)點(diǎn)后面的數(shù)一樣,幾乎可以忽略。而時(shí)光仿佛就是被這些零頭飛逝而去的,比如木魚的記憶、他的青春沖動(dòng),抑或他的所有。坐在時(shí)光飛船中殘忍穿梭的是歲月,也是木魚日漸稀薄的信心和耐心,以及那具他已無(wú)法準(zhǔn)確掌控的殘敗軀體,他緩慢跳動(dòng)的心臟,像一臺(tái)陳舊的機(jī)器茍且運(yùn)轉(zhuǎn),并早已銹跡斑斑。不過(guò),他很滿足,滿足每一個(gè)冬天的離去,每一個(gè)春天的來(lái)臨,每一叢油菜花散發(fā)著濃郁的香;他也不介意每一只蝴蝶、蜜蜂驚擾他的生活。按照爹臨死前的預(yù)言和顧慮,自己能活到五十六本就是個(gè)奇跡,他倔強(qiáng)地多活這么些日子,算是賺了。盡管,在這些日子里,自己活得好像不怎么像個(gè)人。
木魚一直等待著六十歲的到來(lái)。
到那個(gè)時(shí)候,他一定會(huì)去找賈德栓。在去找他之前,他一定要去老街上的李寡婦抄手?jǐn)偵铣园虢锍郑嘁ㄒ簧桌苯罚壬隙膳菥疲対庥舻木莆逗屠弊映浞执碳げ嘏陋?dú)幾十年的五臟六腑,出上一身的汗,繼而摒棄掉自己的膽怯和懦弱。
對(duì)的,二兩就夠了,多了,他也不知道會(huì)不會(huì)醉。不是因?yàn)樗屏啃。撬麖膩?lái)就沒(méi)有喝過(guò)二兩以上的酒。
借酒壯膽找賈德栓,是有正事說(shuō)。
這是他剛進(jìn)五十就決定的。他猶記得那年天旱,整個(gè)冬天都沒(méi)有下雨,炎熱早早地就來(lái)了。油菜花像那些瘦小貧困沒(méi)有吃飽的鄉(xiāng)下女孩,土里土氣地站在貧瘠的土地里,三三兩兩地開(kāi)著花,在成群蜜蜂和小偷一樣的風(fēng)的肆意騷擾下,東倒西歪。高低不平的鄉(xiāng)村路上,暗紅色的灰塵肆意襲擊路人的鼻腔和瞳孔,驚擾著他們清貧的生活。
父親死的那一天,木魚正在自家地里賣力地?fù)]舞著沉重的鋤頭。汗水悄悄打濕他滿是塵土的衣衫,留下各式各樣的痕跡,像歲月的記憶一樣布滿每一個(gè)角落,并寄生蟲一般地繁殖和肆虐。他摸著手中的鋤頭,鋤把的光滑讓他很是受用,女人們擦了護(hù)膚品的皮膚也未必有這么滑吧。所以他總是在干活的時(shí)候享受來(lái)自手感的臆想,后來(lái),他甚至猜測(cè)這把鋤頭是不是父親故意留下的。父親清貧一生,除了一間漏雨的稻草屋,鋤頭似乎是唯一留給他們?nèi)值艿呢?cái)產(chǎn)。
估計(jì)父親到死都沒(méi)弄明白,自己為什么生了三個(gè)兒子,卻沒(méi)能得到一個(gè)像樣的葬禮,沒(méi)有棺材、靈堂、花,甚至沒(méi)有一點(diǎn)眼淚和悲傷。自己大半輩子都過(guò)著和仨兒子一樣的光棍生活,這是對(duì)他那段簡(jiǎn)短卻失敗的婚姻直接打臉,這份屈辱估計(jì)也會(huì)作為陪葬品,一并被他帶到另一個(gè)世界去。
埋葬父親,木魚使用的就是這把父親遺留下來(lái)的鋤頭。他在后山一個(gè)隱蔽的地方,刨了一個(gè)坑,一個(gè)足以裝下骨瘦如柴的父親的坑。坑被填滿的那一刻,木魚覺(jué)得自己空落落的,仿佛好些屬于自己的東西也被一并填了進(jìn)去。卸空了壓力的他又忽然感到了輕松。那種輕松每每在洗過(guò)澡后才能體會(huì)到,但木魚早已記不起上一回洗澡是在什么時(shí)候了。
在他掩埋父親的時(shí)候,兩個(gè)哥哥就那么靜靜地看著,聾子顯得淡定沉著。他看著木魚一鋤又一鋤地?fù)]舞鋤頭砸進(jìn)干土里,感覺(jué)像掄著一把斧頭不斷砍進(jìn)父親的尸體。在木魚把僵硬的尸體推進(jìn)深坑的時(shí)候,他才匆忙地提起土撮箕,把要來(lái)的石灰胡亂地撒到死去父親的身上,最后撒到臉上的時(shí)候,他竟然對(duì)著父親蒼白的臉淡淡地笑了。
瞎子自始至終沒(méi)有動(dòng),像一個(gè)坐鎮(zhèn)指揮的將軍,他雙手杵著一根柏樹做成的拐杖,仿佛杵著一把日式軍刀。他側(cè)著耳朵,仔細(xì)聽(tīng)著木魚把鋤頭砸進(jìn)土里,聽(tīng)風(fēng)經(jīng)過(guò)卷起暗紅的灰塵,聽(tīng)樹梢上烏鴉喳喳的胡亂言語(yǔ)。他忽然覺(jué)得那群該死的畜生大約是在嘲笑他們,特別是嘲笑在一邊不為所動(dòng)的他,所以他在黑暗中重重?fù)]了一下拐杖,大聲地咒罵:
“畜生,該死的!”
木魚看了大哥一眼,自始至終沒(méi)有叫他過(guò)來(lái)幫忙。瞎子是真瞎的,萬(wàn)一他不小心掉進(jìn)足夠深的坑里,木魚也不知道自己會(huì)不會(huì)還有力氣拉他起來(lái)。至于聾子,撒完石灰,欣慰之后,又雙手捧土,慢慢與父親瘦骨嶙峋的臉作了訣別。
(二)
幺爸胥尚貴回來(lái)了。
他是父親唯一的兄弟,也是木魚唯一的親戚。他回來(lái)的時(shí)候,木魚刨開(kāi)的深坑已經(jīng)填平,凸起一個(gè)土堆,仿佛就是父親占用的那一部分土的空間,被擠到了地面上。
“你們幾個(gè)傻兒,狗東西,硬是幾個(gè)傻兒!”
幺爸搖著頭憤憤而去,瘸腿讓他的背影一高一低。
在木魚心里,幺爸的地位遠(yuǎn)遠(yuǎn)高于父親,有時(shí)候,木魚甚至荒誕地希望自己的父親就是幺爸。父親雖然結(jié)過(guò)婚,有一個(gè)人丁興旺的家,卻遠(yuǎn)遠(yuǎn)比不得胥尚貴現(xiàn)在光棍一個(gè)。特別是當(dāng)他從鎮(zhèn)上回來(lái),左手提溜著一塊兩三斤重的槽頭肉,右手拎一壺兩斤多重的泡酒,腳下一深一淺,酒卻一點(diǎn)未灑的時(shí)候。三兄弟像一群羽翼豐滿的老鳥,沉浸在更老的鳥兒覓食歸巢的喜悅里。
木魚知道,幺爸這是去鎮(zhèn)上要著錢了,用胥尚貴自己的話說(shuō),國(guó)家的錢,國(guó)家的政策,不要白不要。木魚還知道,幺爸的酒就是在李寡婦抄手?jǐn)偵弦ǖ模莻€(gè)泡酒的味道,是他夢(mèng)中喝過(guò)多少回的。甚至,他還知道,一瘸一拐的幺爸,有幾次在天快擦黑的時(shí)候,敲開(kāi)過(guò)李寡婦家的門,一晚上都沒(méi)有出來(lái)過(guò)。所以有幾次他經(jīng)過(guò)李寡婦攤前的時(shí)候,猶豫要不要進(jìn)去喝一杯開(kāi)水,喊上二兩抄手。李寡婦看在幺爸的面子上,估計(jì)自己不給錢,也是走得脫的。
五十二歲那年,他終于大膽地走了進(jìn)去,像是跨出人生的重要一步那樣,帶著悲壯和決絕。進(jìn)去后,他選擇坐在一個(gè)足以被人忽略的角落,殷切地等待忙碌的李寡婦注意到他。
“嬢嬢……來(lái)碗抄手。”等店里人少了,木魚有些沒(méi)有底氣地說(shuō)。
“耶,胥木魚,今天太陽(yáng)打北邊出來(lái)了嗎?都喊我嬢嬢了哦!”
李寡婦訕笑著,她揮舞著黑色的抹布,一股油膩的味道徑直鉆進(jìn)木魚粗大的鼻孔。這讓木魚懷疑精明的李寡婦其實(shí)早已看穿他,看到了他內(nèi)心深處的想法,他開(kāi)始有些不知所措。
“跟到胥瘸子喊,即便喊個(gè)媽,又爪子嘛!”一邊的食客開(kāi)起了玩笑。
“二娃子,你狗日的少?gòu)埰鹱彀蛠y說(shuō)。”李寡婦的表情略微有些變化。
“嬢嬢,那多放點(diǎn)海椒嘛,我給錢。”木魚摸了摸口袋里不多的幾塊錢,想要堅(jiān)持一下。
“放你媽個(gè)逼的海椒!你吃錘子,你給老娘爬出去。”
李寡婦明顯沒(méi)吃木魚這一套,這種意外是木魚未曾預(yù)料到的,他黑瘦的臉立馬就紅了,像巴掌才落到他的臉上。
木魚最后還是被李寡婦無(wú)情地推了出來(lái)。武力,彰顯著這個(gè)世界女人的潑辣,一個(gè)上了年齡的女人,缺乏雄性關(guān)愛(ài)的女人明顯要更潑辣一些。李寡婦的潑辣,儼然已經(jīng)超過(guò)秋后自然風(fēng)干的辣椒了。
木魚有點(diǎn)不滿李寡婦的薄情寡義,甚至想要去幺爸那里告上一狀,揭露這個(gè)女人的無(wú)情,而且想要強(qiáng)調(diào)幺爸是瞎了眼的。但當(dāng)他冷靜下來(lái),他又發(fā)現(xiàn)自己明顯沒(méi)有膽量去陳述一個(gè)想要吃混食的事實(shí),更怕自己因此影響了幺爸和李寡婦的交往,還被李寡婦拿出來(lái)遍街亂說(shuō),連累胥尚貴的名聲像瘟疫一樣蔓延,臭到四面八方。
木魚忍了,他說(shuō),為了幺爸。
幺爸雖然這輩子沒(méi)有結(jié)婚,但似乎并不缺少女人,雖然女人的質(zhì)量參差不齊,但本質(zhì)上還是女人,對(duì)于一輩子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裸露一半以上女人的木魚來(lái)說(shuō),這樣的成就值得他仰望。
木魚欣慰的是自己的兩位兄長(zhǎng)也一樣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女人裸露的樣子。或者說(shuō)應(yīng)該除開(kāi)瞎子,因?yàn)閷?duì)他而言,即使有女人愿意裸露在他的面前,愿意搔首弄姿,他也看不到。自打他小時(shí)候熏火藥一不小心把火苗扯進(jìn)了眼里,他那雙泛白的眼睛就跟美好的世界斷絕了關(guān)系,而且斷得徹徹底底。在他的黑暗國(guó)度里,除了生存需要,奢侈點(diǎn)的恐怕也只是一些想象中的裸露了。其實(shí)他應(yīng)該慶幸,自己還有一雙敏銳的耳朵沒(méi)有被火苗一并吞噬,不然他狗日的乍一聽(tīng)出是女人說(shuō)話的聲音,就會(huì)像只奸猾的老鼠猥瑣地嘿嘿笑呢?
聾子正好和瞎子相反,他生下來(lái)就是聾的,也不知道怎么學(xué)會(huì)了說(shuō)話,可能是本能,就像某些生理需要一樣。他過(guò)了幾十年純粹安靜的日子,沒(méi)有聽(tīng)見(jiàn)過(guò)別人哪怕一句譏諷、抱怨和謾罵。所以,他是一個(gè)幸運(yùn)的人。在成為五保戶之前,他甚至沒(méi)有進(jìn)過(guò)城,一個(gè)人活在本就狹小的世界里。這也是木魚敢肯定自己的二哥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裸露女人的理由。
胥尚貴在新時(shí)代活得非常愜意,國(guó)家和政府在適當(dāng)?shù)臅r(shí)候推行了適當(dāng)?shù)恼撸@讓胥尚貴一次次容光煥發(fā)。他先后享受了低保金、五保金,還有一點(diǎn)農(nóng)村養(yǎng)老保險(xiǎn),每個(gè)月去當(dāng)?shù)氐男庞蒙纾焊邭鈸P(yáng)得像個(gè)退休工人。他把自己的頭發(fā)向后梳起,露出看上去并不寬闊的額頭。走路的時(shí)候走在馬路的正中央,壓著分道的實(shí)線,一瘸一拐的也是八字步。在木魚的印象里,幺爸總是驕傲地登上進(jìn)城的長(zhǎng)途車,留給他們一個(gè)神秘、羨慕的背影。木魚想,恐怕是幺爸在外面也有家了,一家人都還幸福地活著。
木魚摸著鋤把,光滑的鋤把磨出了主人一輩子勞動(dòng)的痕跡。可以看出他是一個(gè)并不懶惰的人。可是他活得很難。他不知道為什么以自己還算健全硬朗的身體,成不了一個(gè)簡(jiǎn)單或期望稍低的家,不能擁有一份簡(jiǎn)單的愛(ài)情。
不知不覺(jué),瞎子和聾子已經(jīng)暮年,接下來(lái)的下半輩子不知道何時(shí)會(huì)悄悄畫上一個(gè)句號(hào)。然后發(fā)現(xiàn)自己這六十年,是在充分地重復(fù)前二十年的活法,早已衰老結(jié)疤的青春仍然揭露著他們老齡處男的真相。自己的后四十年,注定再?zèng)]有什么新奇的活法。身邊的變化,除了父親的死去,所有的東西一成不變。
木魚也不明白,每次幺爸看見(jiàn)他下地的時(shí)候,鼻子里便噴出一種類似嘲笑的聲音。
“傻兒啊,你就知道挖,挖一輩子鋤頭有什么出息。”
“幺爸,我不種地吃什么啊?我還有兩個(gè)不中用的哥老倌。”木魚在胥尚貴面前老實(shí)回答。
“傻兒啊,現(xiàn)在世道變了,國(guó)家,你得找國(guó)家解決。知道什么叫老有所養(yǎng)么,傻兒啊,你得把困難留給國(guó)家,留給政府,我就不信人家不來(lái)解決!挖挖挖,你挖個(gè)球啊,能挖出金疙瘩嗎?”
胥尚貴留下一句木魚半天沒(méi)有聽(tīng)懂的話,飄然而去。
幺爸就是幺爸,到底是出過(guò)門的。而且,這幾年國(guó)家的救助,讓幺爸有了充足的底氣和自信,就像是找尋到了一個(gè)足夠硬實(shí)的后臺(tái),足有鋼筋水泥那般堅(jiān)硬,以至于連他的背影都格外硬朗了。雖然還是那樣一瘸一拐,搖搖晃晃,但他從沒(méi)有真正摔倒過(guò)。
木魚開(kāi)始許愿,這個(gè)愿望,就是跟幺爸出去一回,看一看村鎮(zhèn)以外的世界,看一看別個(gè)地方的女人是不是和本地的女人一樣。他得抓緊時(shí)間,趁著現(xiàn)在還能看得見(jiàn),聽(tīng)得著。
還有一個(gè)愿望,他得等到六十歲,找賈德栓說(shuō)事情。
這一年,木魚五十歲。
(三)
胥尚貴是唯一敢指著鄉(xiāng)黨委書記鼻子罵的人,其間,他用了很多政策名詞和術(shù)語(yǔ)給干部們上課,也用了自認(rèn)為很明顯的“道理”,質(zhì)疑基層干部所有的工作其實(shí)都飽含貪污和腐敗的嫌疑。他著重強(qiáng)調(diào)了“所有”兩個(gè)字,原因可能是他自己就沒(méi)有充分享受相匹配的待遇。這讓領(lǐng)導(dǎo)們避之不及。對(duì)的,他是唯一可以讓領(lǐng)導(dǎo)遇見(jiàn)他繞著路走的人。
瞎子比聾子大兩歲,比木魚大五歲,木魚不知道為什么那個(gè)該死的媽,囫圇生了一個(gè)瞎子和一個(gè)聾子后,還有勇氣生下他。他憎恨該死的母親生下他后就匆匆地跑了,匆匆得自己都記不住她。而她明顯早已經(jīng)忘記了自己還有三個(gè)不健全的孩子。木魚在咒罵她的同時(shí),也抱怨自己的兩位殘疾兄長(zhǎng)。是他們,改變了他木魚的命運(yùn)。如果沒(méi)有他們,他那該死的媽或許就不會(huì)跑,而他早就該討上一個(gè)將就點(diǎn)的婆娘,生幾個(gè)子女。這個(gè)時(shí)候,兒女怕是都該在外打工掙錢了。
幺爸又回來(lái)了。望著三個(gè)散發(fā)著臭氣的侄子,胥尚貴沒(méi)有進(jìn)屋。三個(gè)大齡侄子就那么排成一排,一個(gè)比一個(gè)瘦弱,他們整齊地呵呵傻笑著,和小時(shí)候一樣。
幺爸牽起瞎子就走。瞎子很配合,步子也邁得大大的,他甚至沒(méi)有帶上珍愛(ài)如生命的拐杖。一瘸一拐的人牽著張開(kāi)手亂揮的人一路上顯得很滑稽,路人都捂著嘴,像在欣賞一幕滑稽劇。但胥瞎子覺(jué)得,自己眼前已經(jīng)不再是黑黢黢的一片,幺爸帶他走的是一條光明大道,從此,他的人生將發(fā)生重大變化。所以他嘗試抓一根救命稻草失敗后,緊緊抓住了幺爸那摸上去很是粗壯的手臂。
胥尚貴帶著瞎子找到賈德栓的時(shí)候,賈德栓正和一個(gè)上了歲數(shù)的婦女開(kāi)著較為低級(jí)的玩笑,而且笑得一臉燦爛。看見(jiàn)胥尚貴來(lái)了,并領(lǐng)來(lái)一個(gè)具有相同氣質(zhì)的瞎子時(shí),賈德栓才一本正經(jīng)地掏出煙來(lái)點(diǎn)上。
賈德栓看了看一臉訕笑的胥瞎子,最后將目光落在一臉嚴(yán)肅的胥尚貴臉上。他心里沒(méi)有底,想著胥尚貴該不要給他出難題,而文化不高的他,顯然是難以解題的。
胥尚貴板起的臉最終還是松弛了下來(lái),畢竟自己有求于人,終究還是應(yīng)該和藹一些。況且,從以往的交道來(lái)看,賈德栓并不像茅坑中的石頭又臭又硬。賈德栓很快就弄清了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記起了上一回跑了空路的一個(gè)瞎子和一個(gè)聾子。他有點(diǎn)慌,今天胥尚貴明顯是興師問(wèn)罪來(lái)了。于是,賈德栓掏出一支煙,小心遞了過(guò)去。
胥尚貴沒(méi)有接他的煙,但他很滿意賈德栓的態(tài)度,他笑著揚(yáng)了揚(yáng)自己手中黝黑的長(zhǎng)長(zhǎng)的煙桿,謝絕了賈德栓的好意。
“賈院長(zhǎng),現(xiàn)在的政策是不是提老有所養(yǎng)?”
“這個(gè),國(guó)家的政策是在向這個(gè)方向傾斜……”賈德栓一邊回應(yīng),一邊揣度胥尚貴的用意。
“你也知道我那短命的哥老倌,丟下幾個(gè)不中用的殘疾娃,我當(dāng)長(zhǎng)輩的,也不能站在一邊看著不是?我這大侄子胥大金,瞎了六十年了,你們?nèi)嗣裾叾疾桓覕n,有時(shí)候慰問(wèn)一下,給點(diǎn)米、給點(diǎn)油、給點(diǎn)穿的、給點(diǎn)錢,你們那點(diǎn)錢,抵得住個(gè)卵,喝茶都不夠。這怎么讓人民老有所養(yǎng)?”
胥尚貴一臉憤慨地點(diǎn)燃火,很快,賈德栓的辦公室就彌漫起一股酸臭和旱煙混合的刺鼻味道。
賈德栓搖搖頭,小心地看著在一邊吧嗒著嘴的胥尚貴。
“胥大爺,國(guó)家雖然強(qiáng)大了,政策好了,但現(xiàn)在還有很多困難,你是見(jiàn)過(guò)世面的,明事理,現(xiàn)在民政壓力大,救助金有限,有些事情還得慢慢來(lái),我們政府幫扶一點(diǎn),你們?cè)僮粤Ω稽c(diǎn),相信會(huì)慢慢變好的。你說(shuō)呢?胥大爺?”
“好,好個(gè)球,那些當(dāng)兵的,戰(zhàn)場(chǎng)都沒(méi)上過(guò),一年好幾千;那些退休工人,一輩子拿工資,老了不上班了,還拿高工資,憑啥?人是平等的。”胥尚貴說(shuō)得一本正經(jīng),被煙嗆得連咳了幾下。他端起賈德栓桌子上的茶,一口氣喝個(gè)精光,再“呸”的一聲,吐出嘴里的茶葉。
“胥大爺,你得找村上把資料申請(qǐng)交上來(lái),你這大侄子是眼睛看不見(jiàn)?”
“你賈院長(zhǎng)未必也瞎了?”
“有意見(jiàn)你提,胥大爺,這回不會(huì)出遠(yuǎn)門吧?”
“出!得出!找上級(jí)反映問(wèn)題嘛,天經(jīng)地義,你們這些吃官家飯的,個(gè)個(gè)都是吸血鬼,沒(méi)有人管,我請(qǐng)鄧大爺來(lái)管,殺光你們這群貪官污吏。”胥尚貴揚(yáng)起光光的額頭,一舉一動(dòng)都似重要領(lǐng)導(dǎo)那樣,仿佛在他的面前,擠滿了貪官污吏。
“胥大爺,你息怒,話不能亂說(shuō),國(guó)家出現(xiàn)個(gè)別腐敗現(xiàn)象,現(xiàn)在都在嚴(yán)打嘛,是正常現(xiàn)象,哪個(gè)社會(huì)沒(méi)有負(fù)面人物哦?沒(méi)有負(fù)面哪里能襯托出正面呢?你這樣說(shuō)有些欠妥,沒(méi)有壞人咱還要警察干啥?沒(méi)有我們這群吃官家飯的,誰(shuí)來(lái)給你們辦事?為人民服務(wù)也需要人嘛!”賈德栓聽(tīng)著有些不舒服,小心地回應(yīng)。
“我懶得跟你這小角色說(shuō),我去找省長(zhǎng)說(shuō),去找書記說(shuō)。自有人來(lái)治你們,全部拖去勞改槍斃。”
胥尚貴拉起瞎子,對(duì)賈德栓不屑一顧,揚(yáng)長(zhǎng)而去。
(四)
有了救助,胥瞎子覺(jué)得自己的人生仿佛改變了,從一個(gè)可憐的無(wú)人問(wèn)津的瞎子,上升到每月有固定收入的瞎子。這種轉(zhuǎn)變的劇烈讓他幾欲把礙事的拐杖丟了,忘了自己還是瞎子的事實(shí)。他的地位一下子高了起來(lái),至少在他兩個(gè)兄弟面前,他開(kāi)始漸漸具備了胥尚貴的氣勢(shì),連說(shuō)話都是一本正經(jīng)的樣子。今非昔比,兩個(gè)兄弟已然成了他胥瞎子的寄生蟲,靠他養(yǎng)活。所以他除了眼睛,整個(gè)面孔都透露出一種嫌棄,滿是驕傲和自大。
兩兄弟都讓著瞎子,因?yàn)樗麄兣孪棺右徊恍⌒木退懒耍戎鹁蜁?huì)一并死去。
后來(lái),聾子也有了五保救助。
這下,木魚一個(gè)人成了吃閑飯的人。活在一個(gè)瞎子和一個(gè)聾子的的鄙視下是非常憋屈的,雖然家里的主食還是他用父親留下的鋤頭一鋤一鋤地從地里刨出,平均到了三個(gè)人的嘴里、胃里,最后變成大便。對(duì),變成了大便,不然兩位兄長(zhǎng)為什么就忘了是他胥木魚一直養(yǎng)活他們到現(xiàn)在呢?
木魚給幺爸說(shuō),幺爸,你也給我辦一個(gè)救助吧,你好事做到底。原來(lái)老大和老二還幫忙做點(diǎn)活路,現(xiàn)在是一點(diǎn)忙都不幫了。
“傻兒啊,你還早呢,你挖鋤頭就是個(gè)錯(cuò)誤,唉,你要是和你大哥二哥一樣就好了。”胥尚貴嘆口氣,這樣回答他。
木魚想不通自己為什么比不上瞎子和聾子了,難道領(lǐng)了救助就看其他人都低了一等?木魚瞬間明白了很多事,明白了為什么在信用社取錢時(shí)五保戶們個(gè)個(gè)聲音洪亮,臉色通紅,強(qiáng)詞奪理,并彌漫著一股酒氣。甚至有一回一個(gè)光棍仗著劣質(zhì)的泡酒給自己壯膽,面露淫邪,公然給信用社的兩個(gè)年輕女職工講下流的笑話。講的時(shí)候,他的酸臭和酒臭在營(yíng)業(yè)大廳肆意彌漫,一群貧窮的老頭們兀自沒(méi)心沒(méi)肺地傻笑,更助長(zhǎng)了他的氣焰,把他襯托得像一部荒誕劇的主角。
直到瞎子被胥尚貴帶上進(jìn)城的客車,木魚才明白幺爸說(shuō)的并不是一句玩笑話。進(jìn)城本是木魚的愿望,沒(méi)想到最先被幺爸帶出去的卻是瞎子。他認(rèn)為即使是聾子也比瞎子更適合帶出去,因?yàn)槊@子的那雙眼睛總會(huì)綠油油放光。回來(lái)的時(shí)候,也更適合給他們講述外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人。
幺爸帶瞎子走的那一天,他們一起去鄉(xiāng)上的信用社取了錢,完了就在李寡婦的攤上,三兄弟一人吃了半斤抄手,激動(dòng)和辣讓幾人一臉通紅,滿頭是汗。
“慢點(diǎn)吃,又沒(méi)有哪個(gè)和你們搶!”
李寡婦嘖嘖地說(shuō),她倒潲水喂豬的時(shí)候也這么說(shuō)那幾頭搶食的豬。
店里面沒(méi)有外人,可李寡婦和胥尚貴自始至終都沒(méi)有表現(xiàn)得親近,甚至連眼神的交流都沒(méi)有,就像兩個(gè)已經(jīng)分手多年的戀人再次碰面,物是人非,尷尬而又陌生。
三人走出來(lái)的時(shí)候,胥尚貴似乎想起了什么,他給他們?cè)谮w老頭的茶鋪攤上買了三杯一塊錢一杯的茶開(kāi)水,讓他們慢慢喝著等他。
瞎子和聾子默默地傻坐著、傻喝著。只有木魚知道,幺爸是辦正事去了。
胥尚貴和瞎子上車的時(shí)候,木魚默默地看著,心生一種想要一起去的沖動(dòng)。他繼續(xù)思考,為什么幺爸選擇了一個(gè)瞎子和他出去闖蕩,而不是相比年輕的自己。
車開(kāi)走了,一個(gè)聾子向一個(gè)瞎子胡亂揮手。
木魚和聾子不知道瞎子到底要去哪里,是不是換一種活法。估計(jì)他回來(lái)后也不見(jiàn)得能敘述這一次出門的際遇,比如新鮮事什么的。指望一個(gè)瞎子給他們講述經(jīng)過(guò)就像一個(gè)瞎子給另外兩個(gè)瞎子講述差不多,瞎子出門像一個(gè)沒(méi)手沒(méi)腳的人游了一回泳,抑或像聾子聽(tīng)了一場(chǎng)美妙的音樂(lè)會(huì)。這讓留在草屋中的另外兩個(gè)人感到痛心并滿嘴埋怨。這么多年對(duì)瞎子的不滿集中在這段時(shí)間爆發(fā)了出來(lái)。
胥木魚抱怨的時(shí)候,聾子似乎能聽(tīng)懂似的不斷點(diǎn)頭,完了反復(fù)重復(fù)一句:
瞎子進(jìn)城,能折騰個(gè)啥子名堂?
瞎子走后來(lái)了一場(chǎng)大雨,大雨打得路邊的樹枝東倒西歪,像要折斷大樹的臂膀,把白楊樹脫成一身赤裸。木魚和聾子在沒(méi)有門的草屋中安靜而木然地坐著,時(shí)不時(shí)地挪動(dòng)位置躲避穿過(guò)屋頂?shù)挠晁抡慈镜缴砩希路鹩晁畷?huì)像硫酸一樣刺激得他們渾身戰(zhàn)栗,然后血肉一片一片掉落,骨頭像貧窮一樣突兀,清晰可見(jiàn),觸目驚心。像胥木魚想要掙脫出現(xiàn)狀而必需付出代價(jià)那樣,充斥著滿滿的危機(jī)和壓抑。
一把雨傘經(jīng)過(guò)的時(shí)候,聾子和木魚都注意到了,傘下是一個(gè)年輕的女學(xué)生,十四五歲,她小心翼翼地應(yīng)付著腳下的泥濘和天上的落雨,單薄的衣衫和短短的頭發(fā)在雨幕下未能全身而退。走到哪里都能看出她是從一場(chǎng)雨中慌忙走來(lái)的,且受了一定程度的驚嚇。
木魚猛然想起,當(dāng)年那個(gè)總是捏著鼻子走過(guò)他面前的小女娃娃已然這么大了,而自己還是停滯不前。除了貧窮,連面上的表情都始終如一,這讓他再也鼓不起勇氣像前幾年那樣,說(shuō)她是點(diǎn)點(diǎn)大的妹仔,講究得很。
木魚認(rèn)得這個(gè)受了驚嚇的女學(xué)生,她是母豬灣莊駝背的老幺女,是和一個(gè)云南女人生的,那個(gè)云南女人最后也像自己那個(gè)該死的母親一樣,悄悄地消失掉了,以至于自己都以為母親從沒(méi)有出現(xiàn)過(guò)。木魚覺(jué)得自己和面前的女學(xué)生有著相似的遭遇,除了他們各自擁有不同的性別。而且,女學(xué)生現(xiàn)在很年輕,像土里鉆出來(lái)的正欲開(kāi)花的油菜苗,翠綠翠綠的。而木魚,正在日漸衰老。
木魚對(duì)著女學(xué)生表達(dá)著善意,他只有傻呵呵地笑。一旁的聾子也笑了。木魚不知道他為什么笑,懷疑他也洞悉了女學(xué)生的遭遇以及木魚心中的秘密,他對(duì)聾子大吼說(shuō):
“笑,你笑個(gè)錘子,你曉得哪樣?你就曉得吃。”
胥聾子還是笑,他的眼神尾隨著女學(xué)生雨幕中扭動(dòng)的單薄的背影,莫名其妙地叨叨說(shuō):
“女學(xué)生,母豬灣的。”
“傻兒,你曉得個(gè)卵。”木魚又罵了一句,他的心里酸溜溜的。
木魚看著女學(xué)生遠(yuǎn)去,忽然覺(jué)得這個(gè)和他有著相同遭遇的女學(xué)生該是和他一樣有著做朋友的打算,因?yàn)閯偛排畬W(xué)生經(jīng)過(guò)他們的時(shí)候,竟然看了他一眼,并淡淡地笑了一下,而對(duì)傻笑著的聾子慌忙躲避。而且,木魚意外發(fā)現(xiàn),她沒(méi)有再高傲地捏著鼻子了。
“或許,下一回見(jiàn)面,我該主動(dòng)打個(gè)招呼。”
然后再和她一起,請(qǐng)她吃一碗抄手,一起詛咒那兩個(gè)不知道現(xiàn)在在哪里的該死的媽。
木魚繼續(xù)挪動(dòng),忽然發(fā)現(xiàn)屋子里已經(jīng)沒(méi)有了躲避的地方,無(wú)數(shù)雨點(diǎn)似從天而降的利箭,釘?shù)玫孛媲Н彴倏住K鼈兛惺潮榈乩某睗竦孛妫坪踹€要把黑暗的屋子變成不見(jiàn)天日的深井,并埋葬掉并不輝煌的過(guò)去。木魚忽然想起,這件父親留下的遺產(chǎn)該修一修了。
說(shuō)做就做,這是胥木魚多年養(yǎng)成的習(xí)慣,他沒(méi)有多余的時(shí)間思考一件事到底該不該做,值不值得。或者說(shuō),他也沒(méi)有能力去深入思考。雨剛停下,屋頂像淋濕的頭,幾十年來(lái)都沒(méi)有打理,彌漫著一種腐臭。木魚便開(kāi)始動(dòng)手了。主材是隨處可見(jiàn)的稻草,這樣的材料幾乎不用花他們一分錢。木梯子也是現(xiàn)成的,雖然有些松動(dòng),但支撐住木魚瘦小的身體足夠了。聾子很默契,他知道木魚想要干什么,所以當(dāng)木魚爬上屋頂時(shí),聾子在下面焦急地看著,并緊緊地扶著木梯。
在屋頂?shù)母杏X(jué)很好,就像站上一座高岡,把所有的景物盡收眼底。木魚站在房頂,父親留下的財(cái)產(chǎn)便全部呈現(xiàn)在他的眼前,他這才發(fā)現(xiàn)父親留下的東西實(shí)在太少了。破舊的房子和焦急張望的聾子讓他生不出一絲的欣慰。他的人生就像站在這個(gè)屋頂一樣顫顫巍巍,每走一步都不知道前方是否是陷阱?自己是不是會(huì)掉下去?掉下去了是不是自己就再也爬不起來(lái)了?爬不起來(lái)是不是就跟著父親去了?所以他站在屋頂上,小心翼翼得有些麻木。一個(gè)麻木在屋頂,一個(gè)麻木在地上,兩張臉的表情,竟然那么相似。
想象中的事情還是發(fā)生了,父親留下的草屋并不堅(jiān)固,像他自己一樣,到最后也沒(méi)有撐起這個(gè)家。瘦小的木魚也沒(méi)能撐起。所以,承載著這個(gè)家的一切,它慢慢地倒了下去,就像孩童們用樹枝石塊搭建的一個(gè)游戲的新房,兒戲一般地垮塌。這時(shí)候,木魚和他的聾子哥哥,像曾經(jīng)面對(duì)父親死去一樣,像面對(duì)母親離去一樣,像面對(duì)著他們自己的命運(yùn)一樣,無(wú)能為力。
倒下去的時(shí)候,木魚發(fā)現(xiàn)自己的手中抓了一把枯敗的稻草碎末。
(五)
當(dāng)晚,木魚枕著那把父親留給他的鋤頭睡了,膝蓋的疼痛沒(méi)有影響木魚的熟睡,睡在別人屋檐下的木魚做了一個(gè)夢(mèng),夢(mèng)見(jiàn)自家的房子完好無(wú)損,一草一木都變成鋼筋水泥一般堅(jiān)硬,再也不怕風(fēng)吹雨打和歲月的侵蝕,母豬灣的女學(xué)生,和她一起坐在李寡婦的攤前,大汗淋漓地吃抄手。
好在聾子的救助金又到了,可是胥尚貴還沒(méi)有回來(lái)。以前都是他操持著的,而對(duì)一輩子沒(méi)有取過(guò)錢或者說(shuō)一輩子沒(méi)有錢取的木魚來(lái)說(shuō),取錢跟女人身體一樣陌生,而且在這個(gè)神圣動(dòng)作面前,木魚覺(jué)得哪怕多伸一下手都等同于非禮女人一樣,讓他全身都能戰(zhàn)栗出一身雞皮疙瘩。垮塌的屋子打壞了他們?yōu)閿?shù)不多的幾個(gè)完好飯碗,一個(gè)破鍋也在變成兩半后成了一堆廢鐵。木魚和聾子在餓了兩天后,連生火的家什也沒(méi)能翻出一件。好在存折是隨身攜帶的,所以兩兄弟顫顫巍巍的,硬著頭皮來(lái)到了信用社。
明亮的大廳里,和聾子一樣年紀(jì)的一群老頭早已排起了長(zhǎng)龍。看來(lái),鈔票氣味濃烈,不然這群老頭為什么總是那么嗅覺(jué)靈敏,還站得整齊而有精神。像等待上臺(tái)領(lǐng)獎(jiǎng)一樣,眼神充滿了期盼、驕傲和滿足。木魚和聾子小心地排到了最后,有著這么多的老頭在他前面墊底,他的神經(jīng)也開(kāi)始松弛下來(lái)。而且,木魚已經(jīng)認(rèn)出那個(gè)經(jīng)常喝醉的瘋子就在前面,這讓木魚有了一點(diǎn)自信。看來(lái),取錢也不是多么高難度的事情,不然一個(gè)人在喝醉了酒且瘋了的情況下,怎么能辦理。而自己,明顯比瘋子強(qiáng)多了。
最終,喝醉酒的瘋子沒(méi)有能取到錢,因?yàn)橘~上已經(jīng)不足十元,這是信用社的女同志耐心告訴他的。木魚不明白這些年輕漂亮的女同志怎么會(huì)那么耐心地給瘋子解釋了一遍又一遍,而這個(gè)瘋子仍然口出不敬并夾雜污穢的詞語(yǔ),最后在幾個(gè)老頭的大聲呵斥下他才讓到一邊,松松垮垮地站著,張冠李戴地講理,喃喃自語(yǔ)地罵人。直到木魚辦完手續(xù)后,他還站在那邊不消停。
木魚在信用社職員的幫助和提示下,順利地拿到了錢。這讓木魚和聾子一陣興奮,并對(duì)兩位工作人員千恩萬(wàn)謝。早先的顧慮在拿到錢之后煙消云散,工作人員的溫和也讓木魚的膽量瞬間提升。木魚在救助金的刺激下忽然變成了一個(gè)充滿能量的人。他忽然明白了幺爸為什么要反對(duì)他挖鋤頭,也終于明白了為什么幺爸會(huì)說(shuō)他傻了。
酒瘋子仍然沒(méi)有離去,似乎確實(shí)是醉了。看見(jiàn)木魚手中的錢,他竟然搖搖晃晃地偏過(guò)來(lái),伸出骨節(jié)凸露的老手,一把就把錢搶了過(guò)去。
這讓聾子和木魚非常意外,仿佛被奪走的不是金錢,而是堅(jiān)守了幾十年的貞操,且是面前這么污穢厭惡的人生生的用手奪去了。木魚遲疑了一下,他竟然在這樣的突發(fā)情況下思考起了他為什么會(huì)被搶,為什么是搶他而不是別人,思考他怎么面對(duì)兩兄弟救命錢被搶后的反應(yīng)。直到聾子撲過(guò)去,拳頭落到瘋子的臉上,木魚才全身充滿了能量,加入到毆打的行動(dòng)中。
木魚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打他,他打瘋子的時(shí)候,感覺(jué)挨打的是自己。
錢終于回到了聾子的手中,他們也停了打瘋子的動(dòng)作,瘋子臉上一片青腫,躺在地上,嘴角流著血繼續(xù)喃喃自語(yǔ)地罵。
起初,所有在場(chǎng)的人都嚇到了,銀行的職員甚至開(kāi)始撥打120急救,當(dāng)他們以為瘋子必將死去,木魚和聾子必將勞改槍斃的時(shí)候,瘋子的鼾聲慢慢響起,這一頓揍似乎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相當(dāng)享受和滿足。
“早就該揍了,這貨在敬老院吃個(gè)雞蛋都還得分大小。自己有錢的時(shí)候幾下花了,沒(méi)有錢就搶別人的,這一頓打是白撿著了。”
“就是,這酒瘋子,有錢還耍小姐呢!”
“白天是流浪,晚上是放浪。”
一群人指指點(diǎn)點(diǎn),麻木地看著躺在一邊熟睡的酒瘋子,像看著一條無(wú)家可歸的野狗即將死去。
木魚忽然發(fā)現(xiàn)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正確的事情,非常有成就感。窩囊了一輩子,似乎今天才見(jiàn)到自己真正的暴脾氣,到底是自己兇一點(diǎn),人家就對(duì)你忌憚一點(diǎn),自己狠一點(diǎn),別人才怕你一點(diǎn)。從今往后,咱得學(xué)幺爸,昂起頭走路,誰(shuí)不服,打他。
在吃抄手的時(shí)候,他甚至覺(jué)得李寡婦老了,而面前狼吞虎咽的聾子,純粹就是一頭餓極了的牲畜。
回去的時(shí)候,聾子跟在他的后面,這讓木魚忽然覺(jué)得聾子才像一條等他養(yǎng)活的狗,且是丟都沒(méi)法丟掉的。木魚覺(jué)得自己有必要凸顯自己當(dāng)家人的身份,不能再將就瞎子和聾子,被一個(gè)瞎子和聾子瞧不起是一件極其侮辱人的事情,這一定會(huì)讓母豬灣的女學(xué)生看不起。
木魚忽然覺(jué)得自己挖鋤頭的確是一件愚蠢的事情。自己這么多年,竟然沒(méi)有察覺(jué)到。
(六)
瞎子回來(lái)了,木魚和聾子誰(shuí)都沒(méi)有去打聽(tīng)他出門的經(jīng)歷,他們知道打聽(tīng)起來(lái)也是無(wú)果的,指望一個(gè)瞎子出去帶回來(lái)所謂的見(jiàn)聞顯然不可信 。而瞎子也沒(méi)有主動(dòng)講起,只是有時(shí)候想起什么的時(shí)候,呵呵地傻笑半天,兀自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像要吃獨(dú)食一般提防兩個(gè)兄弟分享他的經(jīng)歷。他大約是準(zhǔn)備帶著這份財(cái)產(chǎn)作為陪葬隨自己還原在天地之間,抑或準(zhǔn)備作為一份厚禮帶去給自己的老子。
木魚有些不滿瞎子偷偷的笑,這是一種明顯的自私的行為,這也是對(duì)他的一種挑釁或者傷害。屋子垮掉了,瞎子還占據(jù)著他睡覺(jué)的地方,讓他擠在一起的時(shí)候感覺(jué)自己依舊活在瞎子的庇護(hù)下,他本來(lái)打算狠狠地揍一頓瞎子的,但他到底放棄了,還是那句話,要是瞎子死了,五保救助金也一并會(huì)死去的。
這間臨時(shí)棲居的房子是一戶全家外出多年的農(nóng)戶留下的,已經(jīng)有十來(lái)年沒(méi)有住過(guò)活物了,當(dāng)然,老鼠和昆蟲除外。頂上的瓦片已經(jīng)破敗且不知去向,在破敗中難得一見(jiàn)生命的痕跡——那片片翠綠的青苔——彰顯著這間房屋的老舊,墻壁上泥灰斑駁,一把鐵鎖已被銹蝕,卻依然老老實(shí)實(shí)地守護(hù)了多年。院子和階檐上已滿是青草,甚至還有擠在一起的蔬菜,像生活在一群世俗之人中的那些自清者,顯得瘦弱、古怪而又迂腐。那有限的屋檐勉強(qiáng)地為他們遮住了雨,局促得像是一張隨時(shí)準(zhǔn)備被吹破的塑料布。它像死去的父親那樣,小心翼翼地庇護(hù)著下面的三個(gè)男人,蒼白無(wú)力。好在現(xiàn)在不是冬天,木魚三兄弟并不感覺(jué)很冷,可是,木魚還是想念原來(lái)的屋子。
木魚最后還是大膽地把鐵鎖撬了,反正這房子空著也是浪費(fèi),這是木魚給自己的堂皇理由。幾個(gè)兄弟像發(fā)現(xiàn)了寶藏,強(qiáng)盜一般搶占了里面的幾間屋子,即使屋子里也滿是荒敗的情景。因?yàn)殛?yáng)光照得少的緣由,里面的草沒(méi)有外面的茂盛,除了漏雨帶來(lái)的潮濕,屋子還彌漫著一股發(fā)霉和死耗子的味道。木魚竟然在柜子中翻出了棉絮和衣服,衣服已經(jīng)霉?fàn)€,但棉絮給他們帶來(lái)了溫暖。
村子中的人很快知道了他撬了人家的屋子,這明顯是犯法的行為,誰(shuí)都知道他們?nèi)值艿娜魏我粋€(gè)都沒(méi)有權(quán)利去占有別人的屋子,但誰(shuí)都沒(méi)有站出來(lái)指責(zé),事不關(guān)己,人們習(xí)慣了少管閑事。
其實(shí),這間屋子的主人早已在外買了房子,像一個(gè)已婚的男人常年不歸,在外面有了小三,這間老房子便如一個(gè)被冷落好多年的丑陋妻子。而且,這個(gè)被遺忘的妻子在家正無(wú)力地被一個(gè)瞎子、一個(gè)聾子,以及一個(gè)稍稍正常的男人輪流強(qiáng)暴著。他卻并不關(guān)心。留守家里的親戚給他說(shuō)明情況的時(shí)候,他在電話里無(wú)奈地嘆了一口氣,最后不了了之。
被拋棄的房子和被拋棄的三個(gè)人,顯得非常有緣,如果草屋不垮,他們的緣天知道會(huì)從什么時(shí)候開(kāi)始。但三兄弟沒(méi)有一句感謝,木魚覺(jué)得是因?yàn)樽约旱脑颍亲约旱牡匚惶嵘木壒剩屓思也坏貌唤o他屋子住,就像幺爸說(shuō)的,這是應(yīng)該的。
聾子成了家里干活的人,因?yàn)槟爵~已經(jīng)明確認(rèn)識(shí)到自己以前確實(shí)傻了,聾子不像瞎子,他就像一個(gè)青蛙,你得戳一下他才動(dòng)一下的,這樣的人需要?jiǎng)e人指揮才知道該干什么事情。可是,木魚他這輩子吃虧就吃在沒(méi)有指揮過(guò)人,只有被別人指揮的命,要是自己能早日改變的話,木魚認(rèn)為,自己應(yīng)該能成一個(gè)家的。都是聾子和瞎子拖累了他,是他那個(gè)死去的父親拖累了他,是他那個(gè)早就跑了的母親拖累了他。
所以,一次瞎子吃飯的時(shí)候因?yàn)槁耍爵~就莫名憤怒了,他站起來(lái),抓了一把土,撒進(jìn)瞎子的碗里,看瞎子吃進(jìn)去的時(shí)候,露出凄厲的眼神和冰一樣的笑容,嚇得一邊的聾子一陣哆嗦。
存折都由木魚保管,這明顯意味著財(cái)政大權(quán)的獨(dú)攬。所以他覺(jué)得有必要精打細(xì)算并開(kāi)始改變生活,因?yàn)樽约盒枰淖儯查_(kāi)始有能力改變了。他覺(jué)得自己有了房子,有了固定的收入,他還夢(mèng)想著擁有一個(gè)女人,成一個(gè)家。
上街吃抄手已經(jīng)成了木魚趕集的習(xí)慣和動(dòng)力。他不帶聾子也不帶瞎子,所以聾子和瞎子是吃不到的。但他會(huì)在場(chǎng)快散去的時(shí)候,守在屠夫的攤前,買走屠夫本欲留給自家牲口剩下的所有帶著葷腥的東西,就著各種雜菜煮上一大鍋給兩個(gè)哥哥開(kāi)葷。看兩個(gè)人狼吞虎咽的時(shí)候,他感覺(jué)自己像是一個(gè)救世主,美好的生活似乎就是這樣。
(七)
胥尚貴難得地稱贊了木魚,用他的話來(lái)說(shuō),面前的這個(gè)侄子還真正地懂事了很多,這個(gè)“很多”多少是肯定了他成長(zhǎng)的局限,而不是充分懂事了。在他看來(lái),五十多歲的木魚不管怎么成長(zhǎng),都是孩子。
木魚在幺爸的肯定中覺(jué)得自己已然跟上了他的腳步,他將在這條路上繼續(xù)走下去的,他覺(jué)得自己的生活中接踵而來(lái)的應(yīng)該還有女人和地位,那一種走路要走正中的地位。木魚覺(jué)得自己應(yīng)該找一房女人,并和母豬灣的女學(xué)生做朋友。他如果再和女學(xué)生偶遇的話,他會(huì)禮貌地請(qǐng)她一起去河邊坐一下,去李寡婦的攤上吃一碗抄手,不夠的話就再吃一碗。這種際遇是非常不錯(cuò)的,木魚每每想起就一陣傻笑,和瞎子傻笑相似。
胥尚貴大約猜出了木魚的心思,竟然就突然帶回來(lái)一個(gè)女人,一個(gè)比李寡婦年輕的女人。只是,這個(gè)女人有些癡呆,一舉一動(dòng)都能說(shuō)明她是一個(gè)病人,但難得的是,她非常年輕。木魚覺(jué)得她最多只有40歲,或許更加年輕,因?yàn)榘V呆的邋遢把她襯托得明顯比實(shí)際年齡大,而且,這個(gè)傻女人還難得地豐滿。
木魚不知道胥尚貴為什么帶這個(gè)女人回來(lái),也不知道他的那些相好們知道了會(huì)怎么想。這個(gè)傻女人絕對(duì)和幺爸有了不可說(shuō)破的關(guān)系。至少,木魚相信幺爸雖然不是君子,也還是男人。
癡呆女人成了他們棲息之所的新成員,誰(shuí)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因?yàn)樗约阂膊恢馈?wèn)她的時(shí)候,她會(huì)想上好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然后號(hào)啕大哭,像個(gè)孩子一樣,哭上一段時(shí)間后又哈哈大笑說(shuō):
“四月、四月!”
于是她有了“四月”的名字。
“有可能的話,成個(gè)家。”胥尚貴對(duì)三個(gè)兄弟說(shuō),背著手踱步而去。
瞎子低著頭站得一本正經(jīng)。
聾子看著傻女人嘿嘿地傻笑。
木魚看了看幺爸,又看了看四月,想了好一陣都沒(méi)有明白幺爸的意思。
直到那一天聾子追打提著褲子的瞎子的時(shí)候,木魚才明白是瞎子最先領(lǐng)會(huì)幺爸意思的,聾子追打瞎子的舉動(dòng)明顯他也明白了,所以追打瞎子莫不有種嫉妒的意味。可是木魚仍沒(méi)有領(lǐng)會(huì),他不知道為什么幺爸帶回來(lái)的女人,雖然是傻的,幾時(shí)輪到瞎子和聾子爭(zhēng)風(fēng)吃醋了。
一個(gè)聾子追打一個(gè)瞎子,一個(gè)木頭木腦的人詫異地看著。
陰暗潮濕的屋子里,在那張?bào)a臟的床上,赤裸著的豐滿的四月滿足地呵呵傻笑。
聾子打了瞎子,讓瞎子再也不敢輕易接近豐滿的四月,即使他知道自己是兄長(zhǎng),而且手中還有一根拐杖可以作為武器。而聾子在幾次接近四月的時(shí)候,被提防的瞎子聽(tīng)出了動(dòng)靜,掄著拐杖大叫大嚷,最后在木魚的呵斥下提著褲子慌忙逃走。
沒(méi)有料到的是一個(gè)比較熱的晚上,木魚睡熟的時(shí)候,一個(gè)龐大的身軀忽然就壓到了他的身上。木魚剛想尖叫,自己的手便摸到了一片汗?jié)n的后背。木魚一哆嗦,知道了壓著自己的正是四月。因?yàn)橄棺雍兔@子的后背總是突著尖銳的骨節(jié),永遠(yuǎn)不可能這般油膩。木魚不知道這么熱的天氣,這個(gè)女人為什么會(huì)到自己睡的地方,且以一個(gè)奇怪的姿勢(shì)壓在他的身上。他全身局促得像是一個(gè)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脅,甚至腿肚子都開(kāi)始抽筋,疼得他不敢亂動(dòng),直冒汗。四月喝醉一般地喘著粗氣,呵呵地傻笑。她趴在他的身上一動(dòng)不動(dòng),仿佛等待著什么。而明顯嚇著了的木魚,懦弱得像個(gè)未成年的孩子。
這一夜,四月的手在他瘦弱的全身摸來(lái)摸去,可是木魚仍舊一聲不吭,一動(dòng)也不動(dòng),他怕自己驚擾到聽(tīng)力敏銳的瞎子,也怕聾子像打瞎子一樣追著打他,更怕光著上身在一邊摸摸索索傻笑著的女人,翻身奪取他幾十年如一日?qǐng)?jiān)守的貞潔。
第二天一早,木魚匆忙地離開(kāi)在一邊赤裸著打鼾的四月,他甚至沒(méi)有看清四月的皮膚是否白皙,就匆匆地跳到一條河里面,開(kāi)始清洗幾個(gè)月沒(méi)有洗澡散發(fā)著惡臭的軀體,特別是昨晚被四月的手驚擾過(guò)的沉寂了幾十年的襠部。他甚至開(kāi)始懊惱自己的褲襠在女人的手伸進(jìn)去的那一刻,散發(fā)出惡臭。這讓他感到羞恥,深深體會(huì)到了一個(gè)男人的悲哀。他破天荒地把身上的衣服在水中揉出一團(tuán)團(tuán)漫延開(kāi)去的渾濁。惡臭隨著渾濁被稀釋而沖淡,他聞到了水草的腥臭和稻苗的清香,他赤裸地躺在河堤上,讓自己的那一副瘦弱的身軀陪著衣服慢慢晾干,等著火紅的日頭從山頭慢慢升起。
胥尚貴帶著四月走了,他發(fā)現(xiàn)這三個(gè)孩子般的侄子,根本沒(méi)有像自己預(yù)料的那樣,有能力再養(yǎng)活一個(gè)飯量巨大的女人,盡管這個(gè)女人還很年輕。
他們走的時(shí)候,瞎子明顯有些不舍。他東張西望,難得的沒(méi)有杵著他的寶貝拐杖,顯得自己不一樣的精神。可能還自信自己還能像個(gè)健碩的男子還會(huì)活上幾十年。聾子還是那樣呵呵地笑著,連木魚也不知道他和四月睡了沒(méi)有,只知道他的眼睛中充滿了貪婪和欲望,靠在門框上反倒像是沒(méi)有精神。
“安逸,走了,安逸。”聾子說(shuō)。
胥尚貴走到半路又回來(lái)了,帶著木魚一起登上了去縣城的客車,這對(duì)木魚來(lái)說(shuō)是一個(gè)天大的恩寵。自己的人生好事都在57歲后開(kāi)始胡亂地降臨,這讓他沒(méi)有準(zhǔn)備好,而好多東西在他沒(méi)有準(zhǔn)備好的時(shí)候就走了,讓他惋惜又痛心。
“幺爸,那個(gè)……四月呢?”木魚不見(jiàn)了傻女人,小心地問(wèn),畢竟在一起待了那么多天,況且她是他唯一親密接觸過(guò)的女性。在一個(gè)炎熱的夜里光著身子和他睡過(guò),即使木魚什么都沒(méi)有做。
“走了。”胥尚貴瞇縫著眼睛,靠在座椅上不知道是睡著了還是假裝睡著了。
(八)
木魚終于明白了胥尚貴的秘密,他沒(méi)有想到幺爸這么多年,竟然在縣城最大的寺廟門口有了自己的地盤,用胥尚貴的話來(lái)說(shuō),為了這塊地盤,他甚至都去過(guò)一回省里,在侄子面前,他吹噓說(shuō)這一塊地盤是省上劃給他的,甚至連地痞流氓都得服氣。
木魚只知道,在這塊不大的地方,來(lái)往的人們總是絡(luò)繹不絕,他們中有蹣跚如瞎子的老人,也有衣著性感暴露的年輕女人、穿著樸素的和尚、尼姑,甚至蹦蹦跳跳的孩子。更多的是露出一臉饑餓游走乞討的操著各地口音的乞丐。游走的閑人,在過(guò)往的時(shí)候就那么隨手一丟,一個(gè)五毛或是一塊的硬幣把叔侄倆面前的搪瓷缸子砸出“啪”的一聲響。視力下降至零的胥尚貴便又是摸索又是磕頭作揖。
“幺爸,你咋看不見(jiàn)了?你看不見(jiàn)我?guī)湍銚彀桑俊蹦爵~詫異地說(shuō)。
“傻兒啊,你是真傻啊!你沒(méi)有看見(jiàn)我這是在為生計(jì)演戲啊,你要能看見(jiàn),人家誰(shuí)還拿硬幣砸地戲弄你啊?”胥尚貴小聲地給木魚說(shuō)。
木魚忽然覺(jué)得胥尚貴說(shuō)的非常有道理,這一天,他也瞎了一回。
沒(méi)有想到瞎了的這一天竟然收入了接近80塊錢。但胥尚貴沒(méi)有驚喜,在他看來(lái),木魚的激動(dòng)主要來(lái)自從沒(méi)有一天掙過(guò)這么多的錢,并且只需要一動(dòng)也不動(dòng)地聽(tīng)那一聲清脆的響,然后假裝把頭埋在盡量靠近地面的高度。
木魚記得臨近收工(如果可以叫作收工的話)的時(shí)候,一個(gè)五六歲的小女孩拿著一張十元的鈔票小心翼翼地遞到自己的手里。開(kāi)心跑開(kāi)的時(shí)候,那個(gè)小女孩充分體會(huì)了助人為樂(lè)的驕傲和快樂(lè),而自己呢,竟然是一個(gè)完全能看得見(jiàn)的騙子。
木魚想說(shuō)什么,可是看著日漸衰老的幺爸,他不知道從何說(shuō)起。
胥尚貴帶了木魚回到了自己長(zhǎng)期居住的地方,這是幺爸每月花100塊錢租的,盡管簡(jiǎn)陋的屋子不光能頂風(fēng)遮雨,還用木板隔了一個(gè)簡(jiǎn)易的廁所。胥尚貴買回來(lái)一堆對(duì)于木魚來(lái)說(shuō)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也沒(méi)有嘗過(guò)的肉食,外帶一瓶氣味濃烈的泡酒。大約是餓了,木魚這一回竟然吃得相當(dāng)酣暢。他覺(jué)得自己來(lái)到縣城沒(méi)有白來(lái),終于看到了好多從沒(méi)有看過(guò)的東西,比如一到天黑就自己亮起的路燈,比如打著刺耳喇叭堵成一團(tuán)的轎車,比如那些靠著電線桿子抽煙的花枝招展的年輕女人。
木魚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和幺爸把那瓶酒都喝了,看來(lái)幺爸在城里過(guò)的就是這種酒足飯飽的生活,這讓他的生活愜意并充滿現(xiàn)代都市的氣息,能很快地融入老頭們打太極、女人們遛狗、孩子們玩滑輪的生活當(dāng)中。
木魚喝醉了,但他不敢倒下去,他怕,他怕自己這么愜意的生活剛一開(kāi)頭就被自己的睡意搶走了,所以他盡管早就頭腦一片渾濁,卻老是對(duì)胥尚貴說(shuō),兄弟,我沒(méi)有醉。
木魚和幺爸?jǐn)v扶著走到了街上,木魚覺(jué)得眼前很快就閃過(guò)了耀眼的路燈,靠在路燈上的女人們呵呵地笑著,張著猩紅的嘴吐出一口又一口嗆人的煙霧,讓他感覺(jué)頭重腳輕并眼前一片迷糊。幺爸明顯沒(méi)有醉去,至少他還知道緊緊地?cái)v扶著木魚,一高一低地防止他倒在地上沉沉睡去。
木魚迷迷糊糊卻倔強(qiáng)地清醒著,盡管他早就沒(méi)有了力氣。他清醒地記得自己在進(jìn)入一條巷子后,耳邊傳來(lái)了一陣陣的音樂(lè)。悠揚(yáng)的音樂(lè)讓木魚總是想不起這首歌曲的名字,而他總覺(jué)得自己會(huì)跟著依依哦哦地哼唱一截。接下來(lái),木魚眼前的昏黃已經(jīng)變成了曖昧的紅,像雞血涂抹在燈罩上,讓他的眼睛一陣吃力。
他驚奇地發(fā)現(xiàn)一個(gè)豐滿的女人像四月一樣在他面前麻利地褪去了所有的衣褲,像晾曬的一只死去不久被褪毛鹽腌的土雞一樣白皙和勾人食欲。木魚在她靠近他的時(shí)候忽然聞到一股油漆的味道。當(dāng)他在一邊的痰盂中吐了個(gè)痛快后終于看清,面前這張化妝濃烈的臉竟然不是四月。
這個(gè)不是四月的女人比四月大膽多了,她像屠夫一樣很快褪去了木魚所有的衣衫,像準(zhǔn)備把木魚推進(jìn)一鍋歡暢的開(kāi)水中去。接著,木魚的身子開(kāi)始被她的刀一刀一刀地刮去積攢了幾十年的污垢。為了怕他逃走,屠夫騎到了木魚的身上,這讓木魚絕望,抑制了自己逃離的沖動(dòng)。木魚開(kāi)始扭動(dòng),騎在他身上的“屠夫”也跟著扭動(dòng)起來(lái)。她的表情開(kāi)始變得激動(dòng)、刺激而緊張,繼而像是痛苦。木魚笑了,他認(rèn)為自己的抗?fàn)幤鹆俗饔谩K_(kāi)始更劇烈地扭曲,并用手拉拽屠夫身上能拉拽的東西,直到他用一個(gè)撒尿后的激靈結(jié)束扭動(dòng)的時(shí)候,才發(fā)現(xiàn)屠夫結(jié)束了對(duì)他的控制,轉(zhuǎn)身離去。木魚笑了,他勝利了。他一身汗水,一動(dòng)不動(dòng)地享受戰(zhàn)斗帶來(lái)的喜悅。
半小時(shí)后,木魚逐漸清醒,他這才發(fā)現(xiàn)自己一絲不掛地睡在一間昏暗的屋子,這讓他有些驚奇和恐懼,開(kāi)始以為自己進(jìn)入了地獄并很快會(huì)遇到自己死去的父親或者母親。他有些羞愧,胡亂穿上發(fā)餿的衣服。撩開(kāi)鮮紅門簾的時(shí)候,他發(fā)現(xiàn)胥尚貴正坐在外屋的二手沙發(fā)上,一口接著一口地吞吐著歲月的煙圈。
回來(lái)的路上,木魚慢慢清醒,并逐漸恢復(fù)了力氣。他走在胥尚貴的后面,數(shù)著他一正一斜的兩個(gè)腳印,看自己和胥尚貴一長(zhǎng)一短的影子,木魚竟然想起了那個(gè)叫做四月的傻女人。
“怎么樣?感覺(jué)如何?”胥尚貴臨睡前終于問(wèn)了他。
木魚一陣臉紅,他終于明白了剛才發(fā)生的事情。可是,面對(duì)胥尚貴的詢問(wèn),他也不知道從何說(shuō)起。
“不知道,我好像睡著了。”
胥尚貴翻了一個(gè)身,很久之后,他才嘿嘿的暗自笑了。
“傻兒啊,真的是個(gè)傻兒。”
木魚心想,可能,這就是城里人的生活。
(九)
木魚沒(méi)有順利地成為幺爸的搭檔,畢竟他不是正經(jīng)的瞎子,也沒(méi)有充分的演技和應(yīng)變的反應(yīng),還有幾次差一點(diǎn)穿幫,追著遍地亂滾的硬幣強(qiáng)調(diào)一個(gè)瞎子的艱辛,這讓胥尚貴的生意受到了嚴(yán)重的影響。
木魚最終還是回到了家鄉(xiāng),回到他霸占的人家的房屋。瞎子還是那個(gè)瞎子,聾子還是那個(gè)聾子,只是在沒(méi)有他的日子里,聾子幾乎把瞎子餓死,這個(gè)慘淡湊合的家也變得有些陌生。
三兄弟最后均被證明是爛泥扶不上墻,胥尚貴有些失望,開(kāi)始擔(dān)憂自己的手藝后繼無(wú)人。
木魚知道,聾子也已不是處男了,他一看到異性就兩眼放光。有一回在信用社取了錢,木魚第二天發(fā)現(xiàn)少了一百。在木魚發(fā)問(wèn)的時(shí)候,聾子搓著兩只手,不斷地重復(fù)一句話:
“安逸,安逸。”
一邊的胥瞎子兀自猥瑣地笑著。
再見(jiàn)到那個(gè)母豬灣的女學(xué)生,又是一年的春天。年輕的女學(xué)生開(kāi)始讀高三了,她像一朵花,正含苞待放。在花開(kāi)的季節(jié)里,女學(xué)生充分散發(fā)著青春的味道。
木魚很快發(fā)現(xiàn)了女學(xué)生身體發(fā)育的異樣,這讓他感到慌亂和激動(dòng),他很怕女學(xué)生就這樣嫁人,而后再也不經(jīng)過(guò)他的門前。也怕女學(xué)生考上大學(xué),像一只驕傲的鳳凰展翅飛走,只留下一個(gè)背影,讓木魚遺憾未能和她做一回朋友。
“嘿!”
所以木魚大著膽子叫住了她,她表情異樣地回了頭。她看著面前的木魚,露出那種淡淡的微笑。
“你是母豬灣的?你老漢是莊駝背吧?”
“是的,你認(rèn)識(shí)他嗎?”女學(xué)生詫異地看著他。
“嗯,認(rèn)識(shí),那個(gè)……你媽是不是跑了呢?”木魚生硬地說(shuō)。
“要你管?!”女學(xué)生似乎被刺到了痛處,開(kāi)始面露不悅。
“呵呵,我媽也是跑了的,你看,我們都一樣。”木魚說(shuō)。
“哪個(gè)和你一樣哦,神經(jīng)病樣!”女學(xué)生憤憤地說(shuō),飛快轉(zhuǎn)身離去。
木魚憨笑著看她走開(kāi),卻沒(méi)有生氣,他已經(jīng)很滿足自己今天和她交流的過(guò)程,雖然很短暫,短暫得像那晚的一個(gè)激靈。木魚安慰自己說(shuō),這是一個(gè)不錯(cuò)的開(kāi)始,他和她可以做朋友的。
聽(tīng)見(jiàn)女學(xué)生喊救命的時(shí)候,木魚想起了聾子那有些不正常的笑,他咒罵了一聲便沖了出去。當(dāng)發(fā)現(xiàn)那個(gè)正在扒女學(xué)生褲子的人正是聾子的時(shí)候,他說(shuō)不出來(lái)自己有多么氣憤。可看到那么清新純潔的女學(xué)生像四月一樣赤裸著一雙白生生的腿,他竟然有了一絲驚愕和猶豫。但他很快反應(yīng)過(guò)來(lái),用一根桑樹條子,在聾子背上留下一排抓痕一樣的痕跡,趕走了慌慌張張的聾子。
女學(xué)生是幸運(yùn)的,因?yàn)槟爵~這個(gè)老是對(duì)她傻笑著的人救了她。她看到木魚,也認(rèn)出了聾子。剛才掐著她脖子,扒下她褲子的那個(gè)令人惡心的面孔,現(xiàn)在又回來(lái)站在救命恩人后面,傻傻地笑著。
她毫不猶豫地報(bào)了警。
聾子被抓走了,木魚像看著父親死去、母親離去一樣地?zé)o力,任手足無(wú)措的聾子在警車內(nèi)驚慌地看著自己,慢慢消失在路的盡頭。
木魚忽然想起了幺爸。
當(dāng)他進(jìn)城看幺爸,發(fā)現(xiàn)神氣的胥幺爸忽然變得很虛弱,那久尋不見(jiàn)的白發(fā)悄悄地爬上了他的頭。它們不再像往常那樣被朝后面光光地梳起,而是凌亂地披散在額頭上,顯得很是沒(méi)有規(guī)矩。
聽(tīng)見(jiàn)聾子被抓走的消息,幺爸沒(méi)有再表現(xiàn)出憤慨的樣子,只是深深嘆了一口氣,悄悄地摸出旱煙來(lái),沉悶地抽了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這讓一邊等待的木魚感覺(jué)自己和幺爸在這么長(zhǎng)的一段時(shí)間內(nèi)是在等待死去。所以他局促不安。
“二娃啊,可是我害了你啊!”胥尚貴嘶啞地說(shuō)。
木魚發(fā)現(xiàn),堅(jiān)強(qiáng)倔強(qiáng)的幺爸已經(jīng)淚流滿面。
第二天, 幺爸便去找聾子了,可是到了晚上,幺爸還沒(méi)有回來(lái)。
第三天快中午了,幺爸依舊沒(méi)有音訊,他像聾子一樣消失了。比起伴隨聾子離去時(shí)警笛的喧囂,幺爸的離去像一個(gè)小偷,這讓木魚感到一陣莫名的恐慌。木魚在胥尚貴的小床上一夜未眠。
木魚找到縣城那座寺廟門口,他希望那里的人告訴他幺爸就在某一個(gè)角落。可是,讓木魚失望的是那幾個(gè)常年蹲守在那里的老頭早已像幺爸一樣不知去向。一個(gè)賣香蠟紙錢的小販推著板車占據(jù)了胥尚貴的地盤,那個(gè)用胥尚貴的說(shuō)法是拿命換來(lái)的地盤。
“大哥,你見(jiàn)過(guò)胥瘸子嗎?”木魚小心地問(wèn)那個(gè)小販,他本想說(shuō)胥尚貴的名字,但估計(jì)也沒(méi)有人能記住他的名字,他知道,胥瘸子,遠(yuǎn)比他的姓名好記。
“胥瘸子!他還敢來(lái)?!他要是再來(lái),老子非把他的另一條腿也打瘸!”健壯而年輕的小販惡狠狠地說(shuō),手臂上露出一條像是黃鱔又像蛇的紋身。
木魚尷尬地走了,他不敢再多說(shuō)一句話,怕面前的青年不講理地揍他,把他的腿也打瘸掉。有一點(diǎn)他已然明白了,幺爸為什么開(kāi)始日漸憔悴,不光是他已經(jīng)徹底失去了自己的地盤,還有就是,幺爸老了。
人老了,不光會(huì)失去寺廟門口的地盤,他也將失去城里的生活。
木魚走了,他知道再等下去,也不見(jiàn)得幺爸就能馬上回來(lái),而他回來(lái),木魚又是一個(gè)累贅,他不想讓幺爸的頭發(fā)徹底花白,因?yàn)樗撬麄兓钪募耐校麄儾荒軟](méi)有幺爸。
幺爸被賈德栓送回來(lái)了,一個(gè)四四方方的盒子,像一盒不錯(cuò)的糖果,還帶有幾分精致和喜慶。可惜的是胥尚貴那么康健的一百來(lái)斤,竟然在燒透后只剩下不到一小盒子。像他的人生經(jīng)歷,過(guò)眼云煙一般,終究被時(shí)間打磨成為一個(gè)匆匆而過(guò)的名字。
木魚把幺爸的死訊告訴李寡婦時(shí),沒(méi)有想到,她竟當(dāng)著木魚的面嗚嗚地哭了。
幺爸的內(nèi)衣兜內(nèi)還有十張存單,合計(jì)4萬(wàn)多塊錢。這么多錢讓賈德栓都一陣驚愕,就這樣,木魚成為繼承人。
拿到錢,木魚沒(méi)有吝嗇,他請(qǐng)人給幺爸修了一個(gè)結(jié)實(shí)的墓,還刻下了一塊石碑。這樣的待遇跟自己的親生父親有天壤之別,這當(dāng)然用去了不少錢。他把幺爸剩下的錢存在了信用社,以備自己和瞎子死后也可以用這些錢挖一個(gè)像樣的坑,立碑不立碑便無(wú)所謂了。反正自己也不好意思把名字孤獨(dú)地寫上去,讓人認(rèn)出來(lái)這是一個(gè)光棍的墓。
先后失去了聾子和幺爸,天便像塌了一般。木魚肩頭的壓力又加重了,他覺(jué)得自己快扛不住了,隨時(shí)會(huì)像一根承重的老朽竹竿,噼啪散開(kāi),然后爆成一絲一縷。
瞎子到敬老院去了,看得出來(lái)他是高興的。他睡的那張床,就是賈德栓給胥尚貴留的那張。
曾經(jīng)的屋子原本非常擁擠,特別是四月還在的時(shí)候。那時(shí)候幺爸還在,瞎子還在,聾子也還在。現(xiàn)在屋子里依然潮濕雜亂,但已人去室空,木魚一個(gè)人活得空蕩蕩的,老是摸索著父親留給自己的那一把光滑的鋤頭。
木魚開(kāi)始迷惑,到底是父親對(duì),還是幺爸說(shuō)的對(duì)呢?
木魚跳進(jìn)滿是雜草的自留地里尋找答案。他快速揮動(dòng)著鋤頭,除盡身邊思緒一般的雜草,讓新鮮的土地重新露出本來(lái)孕育生命的肌膚,種下新的種子、新的希望,他仿佛看見(jiàn)流過(guò)的汗水,收獲的季節(jié)就在不遠(yuǎn)的地方。
最后的一個(gè)春天來(lái)臨,可木魚似乎不再期待。,他對(duì)自己說(shuō)人活到六十歲,不能就為了一張床吧。何況,自己才六十歲呢。
這一年的油菜花開(kāi)得極其茂盛,色彩厚得幾欲遮蓋春天的氣息。聾子仍然沒(méi)有音訊,女學(xué)生也再?zèng)]有路過(guò),木魚也不再尋找他們,等待他們。
只是,木魚還是會(huì)偶爾想起四月,然后,露出一絲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