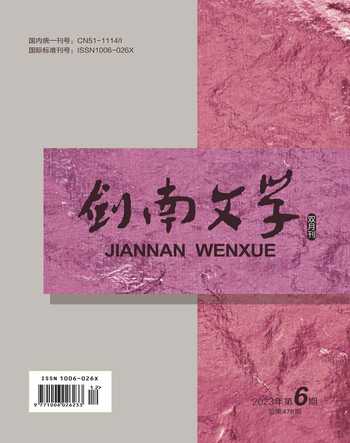以手指月
每到7月,不管大雨小雨,入了伏,涪江總會漲水。渾濁的江水上面漂浮著許多物體,木頭、雞鴨、豬牛,我媽甚至說,以前她還看到過人,但我寧愿相信那只是衣服褲子。空氣中,它們沒有了生命。江水中,它們漂浮著享受著快速奔流的痛快。如果順利,它們將先匯入長江,再流入大海。視野可見的大海盡頭,天地相接,它們實現了與天地精神相往來。
站在桑林村看涪江漲水,絕對是上游又下大雨了。江油。也許還要往上,平武。于是,自然想起了平武的作家,羌人六。
我與羌人六相識已近十年,但因生活、工作、人事、感情、利益等世俗方面皆平行不相交,接觸并不算多。從零星的交流可知,他是一個很純粹、勤奮的寫作者,取得的成果也不俗,是我輩學習的榜樣。
近年來,我一直在關注他的一部有關羌民族長篇小說的情況,因為我正在西北求學,那里曾是古羌民棲息的地方。在酷暑及初秋寂寞時,便拿出一部他兩年前出版的小說集《1997,南瓜消失在風中》閱讀消暑。
現當代及西方小說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最主要是讀不出差別。我看的更多的是文藝理論、歷史典故、讀書隨筆、新聞報道一類。白話文的詩歌、小說自然是當代藝術中影響最大者。其實不管文言、白話,只是創作形式,核心還是文字背后構建的藝術世界。
我認為,羌人六已經營造出了這樣一個藝術世界,猶如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古都西京,莫言的高密東北鄉,羌人六的是平通河上的斷裂帶。他用熟稔的手法敘述對故鄉、民族的眷戀和熱愛。文中出現的人物,他都抱以“理解之同情”,并無居高臨下的批判。也許,他也有恨、有怒,但都不張揚,不靠文字取巧,不靠結構變幻、故事新奇取勝。
不用現成理論套作品,不作藝術高低之評論,也不刻意拔高攀附或貶低炫技,我更喜歡用作品之間的比較,用讀后帶來的美學感受寫評論。當然要聲明的是,以下僅是個人心得,沒有去刻意挖掘作者本身。作品發表、出版后,已卓然獨立,猶如大自然之山水,我不能知道山水之美在何處,也不知道大自然緣何如此創造,但我能夠知道我來欣賞山水時所獲美感為何。此書正如這自然山水,我談的,就是我的角度看出的東西。也是康德《判斷力批判》所謂,無利害而生愉快。
當代小說文體形式,盡管是受西方影響,但作家都是東方思維,因此評論使用“文字優美、結構非凡、立意高遠”等雷同話術,或者亦步亦趨換個方式把作者講過的復述一遍,皆味同嚼蠟。我還是喜歡使用中國傳統美學中的直觀、整體、零星感悟來敘述,評論本身也是一種創作。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講了一個小故事,一宋僧高度評價注莊子的郭象:曾見郭象注莊子,識者云:卻是莊子注郭象。也就是文學作品的形象與理論的抽象,最佳狀態應該是并駕齊驅,互相爭輝。當然,這是我努力的方向,其道尚遠。
此書是一部小說集,由數篇小說構成。讀到《父權色彩》,已近全書尾聲,卻讓我大為感慨,為藍英子命運一哭。一位普通的婦女,喜歡唱歌看書,丈夫只顧賭博,絲毫不能理解,兩人的心也無法共鳴,藍英子頗為痛苦。她只能慢慢移情到小說中,并知道了小說與現實竟然如此相似。藍英子因難產去世,她的小秘密,就珍藏在一個筆記本與一本書中。筆記本里是首歌,毛阿敏的《渴望》。能夠理解藍英子的,是多年后長大成人的女兒。故事發生在一個普通家庭,內蘊著一首生命禮贊、一曲生命挽歌。其實《父權色彩》完全可以倒讀,從后讀到前,倒食甘蔗,漸入佳境。
《1997,南瓜消失在風里》是書名,也是第一篇小說名,開篇敘述斷裂帶風光,看似尋常,卻極有意境,且看這段:
一日將盡,倦鳥歸巢,炊煙自河谷人家的煙囪緩緩升起,爬升的巨擘,很快讓風吹歪了脖子,霧靄一般白茫茫地斜斜地盤旋在山腰。牛的叫聲混合著狗吠,從很遠的地方打架似的攆了過來,貼著男孩水生家石灰刷過的墻根,順著那一遇下雨天便會爬滿蝸牛和鼻涕蟲的墻根,很快地,也被這個季節冰欠欠的涼風吹遠了。
寒假,因我動工收集文同材料,與李寶山博士讀錢鍾書《宋詩選注》文同部分四首詩,其中《晚至村家》是:
高原磽確石徑微,籬巷明滅余殘暉。
舊裾飄風采桑去,白袷卷水秧稻歸。
深葭繞澗牛散臥,積麥滿場雞亂飛。
前溪后谷暝煙起,稚子各出關柴扉。
各位看官請細品,是否意境相似。古詩的翻譯,其實頗為不易,著名學者劉夢溪指出,今譯改變了文體,不宜大力提倡。錢鍾書在《七綴集·林紓的翻譯》一文中寫道:英國人贊美造詣高的翻譯,比為原作的“投胎轉世”,軀體換了一個,而精魂依然故我。于是我們從中外、古今之別來看翻譯、注釋、解讀,就會發現實際上很有可能偏離原意。自從學習哲學以來,在閱讀比較熟悉的《論語》等古籍時,不自覺地帶入哲學視野,特別是考慮到當時著書人的思維情況,便發覺自己曾經對倫理的、藝術的看法,固然不能說錯,但畢竟還不全面,忽略了當時人的精神狀態和思維習慣。
古詩之所以為古詩,正在于它的文體特征,用白話文翻譯,幾乎損失其形式之美。俄國形式主義,同樣重視文學特性,就在于其形式。因此,古詩不好翻譯。羌人六以白話文創作的幾段話,其特性也在于白話這種形式。文同所吟,是宋代鹽亭初秋的畫面,羌人六所寫,是上世紀90年代平武農家小景,讀后感受頗為相近。劉勰說,觀千劍而后識器。兩個作品,一為青釭,一為龍泉。
羌人六的文字中,很少議論文風,說理都似詩歌。如《鐵器時代》中對悲劇的看法,分成幾行,就是一首詩。錢鍾書認為,詩,要么是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含蓄,要么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寄托。我以為,羌人六對于悲劇的描寫,二者皆有:
所有悲劇都長著一顆堅硬無比的腦袋。悲劇沒有嘴,所以它不會把自己說出來;悲劇沒有腿,但總是如影隨形。它苔蘚一樣隱秘地依附在生命的某些角落,直至塵封,或者煙消云散。悲劇的腦袋可能是一段不堪的回憶,可能是一條河的源頭,看似其貌不揚,細細品味,又覺得驚心動魄。悲劇其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隱蔽在它后面的迷惘、愧疚和疼痛,這些都是時間難以消化的苦果,也是生命所不能輕易超越的部分。
總之,這是創作上對悲劇的詩意表達。這令我想到亞里士多德從理論上對悲劇的定義:
悲劇是對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語言,具有各種悅耳之音,分別在劇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動作來表達,而不是采用敘述法,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知道預言也無法改變命運;莫言的《生死疲勞》中,財主西門鬧六次轉世,以動物之眼看盡半個世紀人心之險;電影《土撥鼠之日》無限循環,主角獲得“永生”卻異常痛苦。20世紀世界大戰,藝術家內心之彷徨,畢加索《格爾尼卡》中充滿撕裂的扭曲……悲劇自然是文藝表達中永恒的主題。我通過亞里士多德知道了戲劇中悲劇的定義,通過羌人六的形象描寫則將悲劇概念具象為一幅畫作,一個人形。再將這幅畫代入上述文藝作品,隱約中已能感到悲劇藝術背后的規律。但這規律,非人為定義,而是康德的“無概念而具普遍性”,是無法用語言文字表達而頗得其味的“道與邏各斯”。
《鐵器時代》發生的時間依然為1997年。在80后這一代的意識中,1997是一個特殊的符號,我們第一次親眼見證了國家大事,那就是7月1日凌晨,觀看香港回歸祖國。這一件史冊必載的大事,無論其發生地方或性質,都與身在四川尚且年幼的我們,似乎并無多大關系,但祖國強大帶來的榮譽感、自豪感,是真切產生了的。我正在閱讀《天朝的崩潰》,作者爬梳史料,盡力還原鴉片戰爭前后始末,那正是香港遠離祖國的源頭。以史為鑒,值得深思。《鐵器時代》的故事發生在香港回歸的前夜,主角還在因為家庭重男輕女而備受精神煎熬。這種背景給人一種美學上“殘酷的對照”之感。鐵器時代,不僅是勞動工具的刻畫,還有思維觀念仍然停滯不前的批判。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對各種思想包容度更高了,但這依然是一個漫長的歷程。縱觀人類歷史,數百萬年的改變,每次進化都不是一蹴而就,我們因近百年科技發達而生活得更好,但把幾千年的文明史放在人類史來看,我們的基因不一定會比先人更先進,思維不一定就更先鋒。在重返校園這一個月里,我的導師多次提到列維斯特勞斯的《野性思維》,核心就講的是,人的思維其實并無多大變化。比如對人生、宇宙本質探索的興趣和結晶,我們就遠不如軸心時代的東西方圣人們。從這個角度看,史書不會記載的,報紙不適合報道的,正需要文學、藝術去刻畫。因我《袍哥》《茶館》等微觀史而認識的歷史學教授王笛,就認為文學作品反映的歷史可信度并不低。今天的作家,沒有了儒家文以載道的規范,作品藝術性更強,不是為其他而創作。但人性是不變的,況且我們創作的基石,仍然來自于生活。藝術與人生,浪漫與現實,不是一體兩面,本身就是一面。我們太習慣于是非之分,《維摩詰經》講不二法門,本質就是一樣的。因此,文學就是歷史,不是帝王將相歌頌史,是普羅大眾生活史。
正因有了本書的閱讀,我對羌人六的長篇小說更加期待。一部民族史、民族志,歷史性的、理論性的資料汗牛充棟,涉及人類學、社會學等多學科。要駕馭這些知識,再輔以藝術的方式表達,已不僅是寫作技巧的問題,而涉及作者的眼界、高度。從我的角度看,他已具備。而且,他在三十余歲便甘于坐冷板凳,明明可以有更為豐贍的收入,卻選擇了大量精力專攻這個方向,這是一份使命感和不為物質所轉移的定力。明知終南捷徑卻甘愿走一條更難但卻堅實之路,斷裂帶文學世界的版圖,將再次擴大。
《1997,南瓜消失在風里》出版時,我從羌人六手上購買了兩本,他在其中一本扉頁寫道:與有肝膽人共事,從無字句處讀書。我不知道此句源自何處,但包含了為人做學問兩條方針,不由得想起十多年前讀大學時購買的一本胡適的書,上面寫著他的名言: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做人要在有疑處不疑。慚愧得很,這兩點我都還遠遠做得不好。我很喜歡從無字句處讀書,讀書不拘泥于書,真理往往并不是語言文字就能傳遞的。有文字書不過指月之手,無字書更接近道之本源所在。《楞嚴經》云: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魏晉時代王弼提出的“得意忘象”,張無忌學張三豐太極招術而渾然忘記,這些都講的是不能拘泥于現象而要求背后之本質。
黑格爾說,熟知非真知。中國也有真正被老虎咬的人,才能確切知道老虎厲害的典故。我所言之羌人六,非熟悉之羌人六,亦非真羌人六。
作品作為一個現象已然存在,作者未必然,但既然是藝術,就會允許讀者從各種角度解讀。伽達默爾筆下的“真理”,或許正在于此。以此作結,與有緣讀者共勉之。
【作者簡介】
宋長豐,四川綿陽人。青海民族大學哲學研究生在讀。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綿陽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