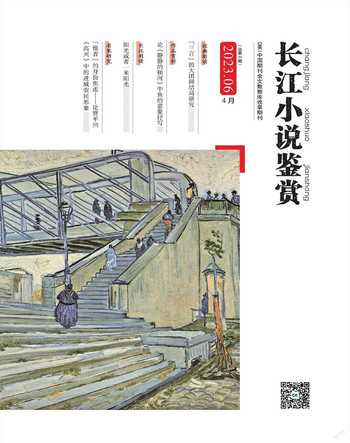“三言”的大團圓結局研究
[摘? 要] 自古以來,“大團圓”結局寄托了人們對人生的美好愿望,作為通俗小說的經典之作,馮夢龍的“三言”結局有明顯的“大團圓”色彩。“三言”根據題材內容可分為世俗情感類、錦繡前程類以及絕地逢生類三種大團圓結局,這三大類型的大團圓結局模式形成原因可以從文學四要素的世界、作者、讀者這三種觀照視角來分析,發現“三言”的大團圓結局不僅傳遞人文溫情、教化世態世風,同時也存在不可規避的局限性色彩。
[關鍵詞] “三言”? 馮夢龍? 大團圓結局? 情節模式
[中圖分類號] I06? ? ? ? ?[文獻標識碼] A
明代,通俗短篇小說蓬勃發展,馮夢龍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成為中國古代通俗短篇小說的一個高峰,拉開古代文壇的新帷幕。筆者注意到“三言”的情節模式有明顯特點,即以大團圓作為結局的小說故事占據一定數量的篇目。
《辭海》解釋為:“大團圓,戲劇名詞,劇本的一種結束方式,表現劇中主人公經過波折而終于獲得的圓滿結局。其他敘述性文學作品也有用大團圓做結束的。”[1]因此,“大團圓”指的是故事主人公歷經萬般艱難險阻、挫折磨難后,在因果報應的推演模式下,獲得一個美好圓滿的結局。據筆者統計,“三言”中符合“大團圓”結局共有76篇,其中《喻世明言》27篇,《警世通言》22篇,《醒世恒言》有27篇。
一、“三言”故事中大團圓結局的類型
“三言”有大量篇目以士人和商人兩大階層作為故事主人公。故本文以故事的題材為“三言”大團圓結局類型的劃分標準,在限定的故事題材中再對主人公身份階層進行分類討論。
1.世俗情感類:美好圓滿
在文學作品中,情感是一個永遠繞不過的主題,馮夢龍的“三言”中不少以情感為題材并以大團圓結尾的故事值得關注,愛情、親情和友情這三類最為常見。
1.1男女情愛之終成眷屬
“三言”約有二分之一的篇目以愛情為題材,并以“郎有情妾有意”而結合或二人破鏡重圓、再續前緣為結尾。
《樂小舍棄生覓偶》中自幼同讀的樂和與順娘,二人互生情愫,但未互訴衷腸,后在生死危難之際實現二人同好的心愿,實現“喜樂和順”的美滿人生。《玉堂春落難逢夫》寫的是官宦公子王景隆和風塵女郎玉堂春的愛情故事,一開始甜蜜幸福,但王景隆的錢財散盡,玉堂春被騙賣,幾經波折,兩人再遇,王景隆幫玉堂春平反冤案,兩人感情依舊,終成眷屬。
商人階層的愛情故事以《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賣油郎獨占花魁》兩篇最著名。《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講述一對恩愛佳偶蔣興哥和王三巧從和愛到離散再團聚的故事,蔣興哥在外行商久不歸家,妻子被誘出軌,奸情敗露兩人離散,最后在“因果報應”的輪回中夫妻重聚,相伴到老。《賣油郎獨占花魁》中賣油郎秦重對青樓女子莘瑤琴一見鐘情,日積月累地存錢只為與她獨處,秦重老實穩重、體貼入微的性格慢慢虜獲美娘的心,后主動嫁與秦重,夫妻二人白頭偕老、幸福一生。
“三言”里男女情愛故事,以士人商人結合、士商與妓女的結合為主,多以戀人終成眷屬、夫妻破鏡重圓為結局。他們以愛之名沖破封建的桎梏,打破門第之別,尋求婚戀自由;以情愛萌芽為始,披荊斬棘,以情愛圓滿為末。
1.2孝悌情深之家庭和睦
在“三言”中,不少以“孝悌”為題材的故事,多是勸誡眾人不可忘“孝悌”,方能家庭和睦、安居樂業。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中,許家三兄弟是踐行孝悌的典范,老大許武勤儉好學,撫養和教育弟弟成人;分家產讓世人看到弟弟“孝廉”之德,最后許氏代代為官,世間流傳“孝悌許家”的佳話。反之,不行孝悌之道,家庭就會雞飛狗跳。《滕大尹鬼斷家私》中,善繼與幼弟善述爭奪家產,倪太守設下錦囊奇策,滕大尹識破啞謎,“鬼斷”家私,巧用屋中機關,占有倪家一半財產。最后,善繼家產敗盡,善述念書成名,一衰一榮,乃善繼不守孝悌之報應。倪太守對孩子的教育方式使得家庭不睦,他放任長子凌辱庶母,自己又暗中關照幼子,若一開始就以孝悌之道教育孩子孝敬雙親、愛護弟兄,就不至于鬧出自家人互相算計、不孝不悌的笑話。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中,呂玉因兒子走失,便轉行行商打聽孩子的下落,他不貪飛來外財,送還拾得重金,意外找回兒子;他懷善去營救落水之人,救起三弟呂珍。呂大以善心去面對不幸,善有善報,夫妻重會、骨血團聚。《張孝基陳留認舅》描寫漢魏時張孝基有義節之事,巨富過善的長子過遷是敗家子,惡跡斑斑,屢教不改,過善臨死前將家產交給女婿張孝基,孝基以務農和經商結合之徑,擴充幾倍家產,且心存義善,主動拯救墮落的過遷,并將家業轉還給舅兄。
文人之家和商人之家的故事體現儒家的孝悌觀念,行孝悌之道與不行孝悌之道所產生的結果天差地別。凡是孝悌情深之家,總能家庭和美、其樂融融;而背棄孝悌之家,常常親人間明爭暗斗、生活一地雞毛。
1.3深情厚誼之生死之交
深情厚誼,即指深厚的情意,珍貴的友誼。“三言”中不少篇幅把主人公交友時講信義、重友情的故事描寫得動人心扉。
自古文人交友,易存“文人相輕”弊病。但在“三言”,有不少文人士子相交情深的故事。《羊角哀舍命全交》中羊角哀與左伯桃同赴楚國取仕,途中遇風雪、缺糧,伯桃留衣糧給羊角哀后死在途中,羊角哀獨自往楚,取仕后尋伯桃尸體改葬,并刎頸自殺,既完成遺愿,又信守情誼。《吳保安棄家贖友》講述吳保安和郭仲翔恩深義重的友情。吳保安感念二人知己情深,不忍好友受難,便傾盡所有、拋家棄子籌足贖款,終救出被困的郭仲翔;郭仲翔千里背負吳保安的尸骨遷葬回其故鄉,撫養幼孤成人,后人修立“雙義祠”追念二人義舉。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中,張劭和范巨卿參加科舉在途中相遇、相識、相知,張劭為范巨卿請大夫治病,日不離身為其煎藥、喂食,后范巨卿被救活、痊愈。二人結拜為兄弟揮淚定下重陽之約,但范巨卿因忙于經商糊口而忘重陽之約,選擇自刎化為鬼魂赴約,而張劭吊祭時,拔劍自刎陪義兄合葬,后漢明帝賜封號與神廟表彰二人信義,名傳后世。
“三言”中的士人之交、士商之交感人肺腑。深情厚誼的情節模式基本為:他們偶然相遇,結成至交,離別之后,彼此重義守信,危難之際愿為朋友伸出援手,甚至以死相報,而結局多為名垂青史或得善報。
2.錦繡前程類:名利雙收
“三言”中有一類關乎金錢和事業的題材可歸納為錦繡前程類,錦繡前程指的是主人公在經濟上從貧窮轉變為富有,社會地位從低賤轉變為高貴,前途美好光明,而士商為這類題材的關鍵人物。
2.1士人之科舉取士與薦拔為官
“三言”塑造文人形象依舊沿襲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軌道[2]。文人士子孜孜不倦地追求這種人生境界,傾其一生以科舉取士與薦拔為官兩種途徑來實現。
《鈍秀才一朝交泰》中家道中落的生員馬德稱被叫“鈍秀才”,他堅持與困境抗爭,有“經解之才,早晚飛黃騰達”[3],歷經磨難后,榜上高中,如愿以償。《老門生三世報恩》中主人公鮮于同“八歲時曾舉神童,十一歲游庠,超增補廩”[3],但直至六十一歲才連中鄉試、省試、會試三元,任臺州知府,后官至巡撫。
《窮馬周遭際賣追媼》講述主人公馬周從一貧如洗的寒門士子到高貴的吏部尚書的發跡過程。他“分明是一條神龍困于泥淖之中,飛騰不得”[3],王媼見馬周氣質非凡及“白馬化龍”的異夢指引,將他推薦給常何,從此平步青云,一生富貴。《趙伯升茶肆遇仁宗》中趙旭博覽群書、滿腹經綸,卻因一字之差不合圣意名落孫山,仁宗皇帝夜間“夢一金甲神人,坐駕太平車一輛,上載著九輪紅日,直至內廷”[3],經解夢官解夢九日為“旭”,就尋找名中有“旭”的人,趙旭得以重任,從此發跡變泰。
馬德稱、鮮于同都以科舉來取功名,從而改變人生軌跡,獲得圓滿的結局;還有部分在“異夢”助力下,貴人相助遇上明主,最后平步青云、飛黃騰達。
2.2商人之積德致富與勤懇發家
《宋小官團圓破氈笠》講述宋金在家道破敗后發跡變泰的故事。宋父因救僧人,積陰德才得子。后宋金被岳父母丟棄在荒島,被人救起后發現寶藏,掙得十全家業,從此發跡變泰。《施潤澤灘闕遇友》的主人公施復也因積陰德發家致富。施復拾金不昧,積陰德,與失主朱恩交友,因朱恩的款待和挽留避免翻船身亡的悲劇。施復知曉“善惡有報”才得以免難,日后愈加行善,家境日益富裕。
《徐老仆義憤成家》講徐家老仆阿寄為向主母展示自己老當益壯,憑借靈活經營的生意手段和勤懇能干的性格為主母掙下大家產的故事。《趙春兒重旺曹家莊》講青樓女子趙春兒靠織麻扶持敗家丈夫重新發家的故事。曹可成靠春兒拿出多年積攢的錢財給他辦文書上任,夫妻最終衣錦還鄉,贖回往日資產,家門重旺。
士人和商人實現錦繡前程的途徑并不一致,在名利雙收的過程中帶有不同身份階層的特色:士人謀官,商人謀財,但殊途同歸,都實現了金錢和地位的轉變。
3.絕地逢生類:柳暗花明
“三言”有一類題材即主人公在許多生死攸關之際能逢兇化吉、化險為夷的絕地逢生,以下是兩種不同身份的主人公在不同的絕境面前絕處逢生的故事。
3.1士人之沉冤得雪
《蘇知縣羅衫再合》中蘇云在赴任途中遭賊人行劫,妻室鄭氏被賊人徐能劫走。鄭氏之子正好被徐能撿回撫養,成人后任監察御史,蘇云夫婦訴狀申冤,經過兩件羅衫的對證,徐繼祖認回親生父母,骨肉團圓,懲處賊人,實現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反轉。《張廷秀逃生救父》講述富商王憲招木工張權長子入贅為婿,但遭到大女兒反對,他們暗中施展陰謀詭計,先陷害張權入獄,后又誣謗張廷秀將其逐出家門,并羞辱玉姐、逼其自殺。張家陷入困境,兄弟四處奔走訴冤,歷盡坎坷磨難,兄弟倆雙雙中舉,昭雪冤獄、懲辦惡人、合家團圓。
3.2商人之劫后余生
《楊八老越國奇逢》中楊八老入贅與后妻生子檗世德,回鄉途中,遭倭寇侵犯,被擄去他國。楊八老的小廝隨童失散后更名王興,發現楊八老被擄,在被審理時發現楊世道是他與前妻所生之子。檗太守聞訊來賀楊家團聚,并得知家母是楊八老的后妻,最后舉家完聚。《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程彪程虎投奔燒炭冶鐵而發跡的汪信之,二人誣告汪信之謀反,汪信之害怕事情禍及全家老小,就主動去官府自首。官衙澄清汪信之被陷害,汪信之在牢中飲毒自殺,其子汪世雄接手家產,家業繁盛。
在“三言”中,士人的絕地逢生多以主人公科舉高中、取得功名為轉折點,以讀書做官的途徑來解決尖銳矛盾沖突,獲得人生境遇的變遷;商人的絕地逢生多是有貴人相助或積累陰德而獲得人生的反轉。在面對生死存亡的威脅之際,總能實現置之死地而后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生命奇遇。
二、“三言”故事中大團圓結局的成因
美國當代文藝學家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一書提出文學四要素的著名觀點,他認為文學作為一種活動,總是由世界、作家、作品、讀者四個要素組成的[4]。“三言”的大團圓結局這一文學現象的形成離不開文學四要素相互作用和相互滲透,關于“三言”故事中大團圓結局的成因,筆者試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1.社會環境因素
“三言”的成書年代大致在明代天啟年間,此時明朝國勢日益衰微,面臨閹黨專政、農民起義、外軍突起等內憂外困。“三言”中對封建官吏形象的抑揚,反映明末社會政治風貌。顧炎武在《日知錄集釋》中提到明末腐敗黑暗的政治現實,“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為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為矣。”[5]可知明末朝廷上下將貪賄習以為常,無所顧忌。“三言”揭露明代官場腐敗丑惡,如《張廷秀逃生救父》中“捕役”楊洪接受他人行賄,為其誣告、殺害好人等。“三言”關注社會現實,以冷嘲反諷表達,但社會現實與理想社會相差甚遠,且當時的文人和市民都不具備改變現實的能力,只能在虛擬的文學世界中以“因果報應”尋求圓滿結局的安慰。
首先是儒家的“中庸之道”。馮夢龍把儒家推崇的中庸之道借用在“三言”的情節敘述上,使故事的矛盾沖突緩解,幫主人公實現圓滿的人生愿望,擁有枯木逢春、始悲終歡的完美結局。這種大團圓結局能給讀者帶來一種審美的愉悅,從而達到倫理教化的目的。
其次是佛教“因果報應”的宿命論。“三言”中幾乎所有的惡人都得到惡報,好人都有圓滿的結局。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蔣興哥惹上官非,是三巧兒向后夫求情才使他免受牢獄之災;與三巧兒偷情的陳商死后,其妻陰差陽錯地嫁給蔣興哥。佛教“因果報應”的宿命論的終極目的是懲惡揚善,給小說故事添上光明結局,勸世人為善遠惡。
再次是道家的隨緣、無為的人生態度。人們認為天地萬物起于沖突,終于和諧,否極泰來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反映在小說中則形成小說特有的情節發展模式,那就是喜——大悲——大喜[5]。在《陳希夷四辭朝命》中陳希夷看破功名利祿,面對加官晉爵,內心也如一潭靜湖,一生不為萬事勞形,只為自己而活,最后羽化成仙。正是看淡現實生活的悲苦,才能尋得超外自足的人生境界。
復雜的社會現實中,在政治上理想和分裂的狀態以及傳統文化觀念的互相影響和滲透下,馮夢龍的“三言”大團圓結局的出現存在必然性,這種情節模式是時代浪潮的產物。
2.作者主觀因素
馮夢龍在青壯年時,像所有讀書人一樣,研讀四書五經,應舉趕考[6],但51歲才取得貢生,任職知縣時已61歲,而65歲就離任回鄉,繼續研究通俗文學。弗洛伊德曾言:“一篇作品就像一場白日夢一樣,是受到抑制的愿望在無意識中得到實現。”[7]“三言”中很多落難士人歷盡磨難、金榜題名后擁有與佳人共結良緣或發跡變泰的美滿結局。從審美心理學的角度看,馮夢龍帶著一種代替性或補償性的心理進行文學創作,雖然在現實中取得功名較晚,但他用小說故事的圓滿來補償現實中的缺失。
馮夢龍在創作思想上深受儒家倫理觀的影響,馮夢龍認為文學應具有教化民眾的功能。“三言”的教化功能多以懲惡揚善模式來實現,如《蘇知縣羅衫再合》中的賊人徐能到晚年也無法磨滅早年的惡行,最終被捕入獄。馮夢龍描寫惡人、惡行來警醒后人,以致正人倫、敦風俗。
其次是馮夢龍的“情教觀”。《情史》序中,他提到“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8]。馮夢龍極其尊崇情,他認為“情”是萬事萬物的根本,是人充滿生機的象征,“情”能教誨民眾、教化世態。“三言”許多篇目都體現他借娛情來療俗的文學思想傾向。從《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興哥和三巧兒兜兜轉轉的情感經歷和《賣油郎獨占花魁》的賣油郎和花魁娘子的雙向選擇來看,馮夢龍注重女性的感受,肯定女性的情欲,但又有禮有節,強調互相信任與互相尊重,營造一種情愛共存的婚姻關系的世俗風氣;從《吳安保棄家贖友》到《羊角哀舍命全交》中,可以看出馮夢龍極力宣揚朋友之間真摯的友誼,贊美忠信守義的高貴品德。
馮夢龍的“三言”創作思想體現“情”與“理”的完美結合,既肯定和贊美“情”,又能“看到濫情必亂,情而縱欲,情而成仇,見利而忘情的害處”[9],在世俗面前很快從“情愛”中清醒,回歸到道德教化的責任中進行說教,保持“情”和“理”的平衡,讓不完滿的完滿、離散的團圓。
3.讀者接受因素
在晚明,士商互動頻繁,士人的審美情趣受到市民趣味影響,士人的文學創作會考慮讀者的消費需求和審美需求。“三言”正是馮夢龍“因賈人之請”[8]而編輯整理,故“三言”的產生帶著一定的商業意識去考慮市場需求,考慮作品的商業利益以及作品的市場銷售情況,而大團圓結局正是呼應市場的需求。對普通讀者來說,閱讀通俗小說是一種娛樂方式,渴望在閱讀中享受到歡樂,體驗到善惡有報的快感,他們就會更想看到大團圓的結局。因此,在特定的社會現實下,作者的主體因素和讀者的接受因素的雙向選擇促使“三言”的大團圓結局的產生。
三、對“三言”故事的大團圓結局的思考
“大團圓”結局這一情節模式,在不同的時代會引起不同的思考。對于“三言”故事的大團圓結局的思考,應該要帶有時代特征,辯證、全面地思考。
1.傳遞人文溫情
馮夢龍關注蒼生,他總把溫情的目光投向社會各階層,在“三言”故事的大團圓結局中能感受到他對現實生活的關懷和人文溫情的一面。
“三言”120篇作品中有二分之一把市井小民設為主人公。隨處可見他們在社會底層各個角落的身影,即使身份地位低賤、自身實力弱小,但“三言”把他們強大的生命力展現得淋漓盡致,極盡描寫他們的言談舉止、七情六欲,并關注他們的物質生活以及精神追求。
“三言”中不少描寫男女情愛的篇目,肯定正當情欲。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因寂寞難耐而出軌的三巧兒,三巧兒深愛丈夫,但因欲望背叛,自責和愧疚中主動救前夫于困境,兩人相見仍情深,后破鏡重圓。《閑云庵阮三嘗冤債》中官宦小姐玉蘭與情郎阮三私通,不顧性命享受一番云雨。在追求婚戀自由時,女性表現得堅決與勇敢。
馮夢龍極盡描摹人情世態,關心廣大民眾,對人追求正常情欲表示寬容與肯定,強調人的感情和價值應受到尊重,對社會道德的不合理之處以及封建禮教殘害人性的本質進行控訴。
2.教化世風世態
深受儒家、佛家思想感化的馮夢龍完美地將因果報應論與教化論結合起來,實現警醒人心的教化目的。
積陰德之人會結善果,如《裴晉公義還原配》中裴晉公出于憐憫之心把歌姬小娥還給她的未婚夫并幫其重得上任官誥,使他既得婚姻又有官職,最后裴令公福壽綿長,子孫世代不絕。但惡人逃不掉惡果,《桂員外窮途懺悔》中桂員外貪財忘義、作惡多端,他的下場不但家破人亡,且轉世為犬、以糞便飽腹。這種因果報應的思想鼓勵世人做好事、積陰德;懼怕惡報,做壞事前會三思而行,起到一種警示世人的作用。
3.存在局限色彩
“三言”順應時代需求而興盛,載道而行遠。“三言”能從出版之時起流傳至今,有其吸引各時代讀者的出彩之處,但也無法忽略大團圓結局情節模式下暴露出的局限性。
從小說文本看,故事人物塑造有類型化的傾向,塑造極端性的絕對良民或絕對惡人。“三言”不僅反映市民思想意識,而且夾雜著命定的思想,在因果報應、懲惡揚善的邏輯影響下,公式化傾向嚴重。
明朝中后期,商品經濟發達,商人地位得以改善,金錢逐漸變成支配社會的力量和衡量個人的重要標準,金錢至上成為當時的社會法則。《臨安里錢婆留發跡》中早年的錢婆留吃酒賭錢,靠打家劫舍獲取錢財,后因貴人相助得以發跡。可見,部分人當時獲得財富并不是靠勤奮或智慧,而是靠上不得臺面的把戲。《宋小官團圓破氈笠》中久病不愈的宋小官被丈人拋棄荒島且另擇有錢佳婿,待宋金在小島冒險發跡再歸,兩人道歉謝罪,為其設盛宴接風洗塵,這凸顯當時厚利薄義的價值觀和扭曲的金錢觀。
“三言”中女性角色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在“三言”大團圓結局中的女性角色,她們有強烈的抗爭意識,為爭取愛情自由、經濟地位、獲得權利做出種種努力,但她們的角色仍受到時代局限,女性在男權社會仍居于附庸地位。《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玉奴花費金錢和精力資助丈夫科考,卻遭丈夫謀害,玉奴在棒打莫稽后,夫妻和好,實現看似圓滿,實際凄涼的結局。在這段感情中,莫稽兩次對玉奴的選擇都是因為利益與金錢,一旦她沒有這些砝碼,她就會被無情拋棄。
人尚且無完人,何況是文學作品。對于“三言”的大團圓結局,應保持理性的態度,不能無限放大進步之處,但也不能過度苛責其局限之處。讓其傳遞的人文溫情繼續溫潤人心,讓積極的教化繼續引領前進方向,而對于局限色彩要正視。
四、結語
馮夢龍的“三言”是我國古代短篇小說的重要財富,在“三言”中可以看到中國古代社會的人間百態。從情感題材的男女之情、孝悌親情、深情厚誼和錦繡前程類題材以及絕處逢生題材出發,看士人和商人這兩大階層的大團圓故事,明確大團圓結局的形成離不開社會現實、作家創作和讀者接受三方面。不可否認大團圓結局傳遞的人文溫情和對世風世態的教化,但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在大團圓結局模式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小說創作趨于公式化、不正當的金錢觀和輕視女性等。應該把“三言”的大團圓結局模式視為一種合理的存在,堅持用辯證、發展的眼光看待它。
參考文獻
[1]? ?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M].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
[2]? ?李雪梅.論三言二拍的中和之美[D].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2006.
[3]? ? 馮夢龍.警世通言[M].北京:中華書局,2009.
[4]? ?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傳統[M].酈稚牛,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5]? ?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十三)[M].欒保群,呂宗力,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6]? ?繆詠禾.馮夢龍和三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美文選[M].張煥民,陳偉奇,譯.北京:知識出版社,1987.
[8]? ? 朱一玄.明清小說資料選編(下冊)[M].朱天吉,校.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
[9]? ? 羅宗強.明代文學思想史[M].北京:中華書局,2013.
[10]? 朱祖延.引用語大辭典(增訂本)[M].武漢:武漢出版社,2010.
[11]? 艾布拉姆斯.批評理論的方向[M]//戴維,洛奇.二十世紀文學批評(上冊).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12]? ?高明.論“三言”愛情小說的“大團圓”結局及其成因[J].牡丹江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4).
[13]?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4]? ?馮夢龍.醒世恒言[M].北京:中華書局,2009.
[15]? ?馮夢龍.喻世明言[M].北京:中華書局,2009.
(責任編輯 李亞云)
作者簡介:何舒平,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