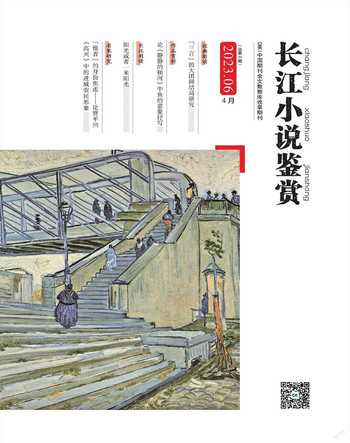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
嚴璐 荊博雯 段俏 王嘉昱
[摘? 要] 艾麗絲·門羅的作品《女孩和女人的生活》展現了20世紀40年代加拿大小鎮的社會風貌及女主人公黛爾的成長歷程。作為集體記憶的一個分支,文化記憶通常以文化符號及文化象征等形式存在,其具有的被建構性在意義賦予與身份認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從文化記憶的視角來看,黛爾對自我身份的認識過程更為明晰。門羅通過記憶與想象的糅合呈現了黛爾的身份認同之旅,揭示出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及社群認知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 文化記憶? 《女孩和女人的生活》? 身份認同
[中圖分類號] I106.4? ? ? [文獻標識碼] A
記憶理論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德國學者揚·阿斯曼和阿萊德·阿斯曼夫婦的文化記憶理論提到,既定的社會框架促成了相應的個體記憶。集體記憶就是一個群體內所有成員分享共同的記憶,而個體的記憶一方面構成了集體記憶的基礎,另一方面又作為這個集體記憶的映像[1]。與此同時,成為文化記憶對象的文本可以為不同時期的人們提供確定身份的立足點和走向未來所需的坐標系[2]。
《女孩和女人的生活》是加拿大著名女性作家艾麗絲·門羅創作的頗具文化記憶印記的作品。在8個相互關聯而又獨立的故事中,門羅聚焦于20世紀4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的諸伯利小鎮,將自身經歷與想象結合,以細膩的筆觸刻畫了主人公黛爾在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碰撞中感悟人生,由青澀的少女成長為成熟的女性藝術家的故事。《女孩和女人的生活》探索了現實和記憶兩者之間的關系,記憶以個人、日常、家庭三種模式復現并重構了現實世界,發揮著勾連現實和精神世界的橋梁作用[3]。此外,小說還著眼于一定地理空間內文化記憶對人文風俗的影響,門羅作品中對加拿大小鎮歷史和風俗的生動刻畫來源于其個人對童年小鎮生活難以割舍的文化記憶[4]。然而從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的矛盾出發,對文學作品的解讀則相對較少。本文以《女孩和女人的生活》中主人公黛爾的“困惑與危機”“探索與反思”“覺醒與認同”的三個成長階段為例,探究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的復雜關系如何推動女性成長、女性意識覺醒并最終獲得身份認同的過程。
一、困惑與危機
記憶是個體成員融入集體并理解自我的重要表達途徑。人們對于過去事件的回憶并不是完全意義上客觀事實的再現,而是受到社會及文化的影響再次建構的過程。揚·阿斯曼指出:“自我的形成是一個由外而內的過程。”[1]記憶的重塑讓個體成員明確自己在集體中的位置,從而鞏固自我身份。黛爾自身成長經歷的回憶與集體記憶相互交織產生沖突,促使她意識到作為女性的身份認同危機,開始重新審視自我與傳統。
黛爾從父權制的集體記憶中獲知了小鎮女性的形象,同時這也成了她身份認同危機的起點。“集體記憶不僅僅是在傳達一種群體共同的認知,也在共享和傳播一種群體的價值觀和情感取向,在特定的互動范圍之內,這些群體認知指引著成員的行為和體驗,并借用情感認同力量來維持和組織群體成員。”[4]個體認同集體記憶的內容,將更容易融入集體;反之,個體將對集體所建立的形象產生懷疑,并將自我放置在集體的邊緣位置。在黛爾生活的小鎮中,埃爾斯佩思姑媽和格雷斯姑媽代表小鎮女性的形象,并擔任集體記憶傳授者的角色。她們忙于家庭瑣事,服從克雷格叔叔的權威,同時也要求黛爾恪守傳統女性的本分。當克雷格叔叔在工作時,姑媽們都壓低聲音說話:“她們不許我到陽臺上去,以免我會走到他窗前干擾了他。”[5]波伏娃指出,在父權制的文化中,“定義和區分女人的參照物是男人,而定義和區分男人的參照物卻不是女人。她是附屬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對立的次要者。他是主體,是絕對,而她則是他者”[6]。相對于克雷格叔叔而言,姑媽們將自己定義為他者,主體和他者的差別導致她們在生活中服從他,在精神上依靠他。當克雷格叔叔去世后,姑媽們找不到繼續生活下去的意義和動力。她們的耳目不再聰明,手腳也逐漸沉重、笨拙起來。“這就是她們沒有男人在身邊,滋養她們欣賞她們的結果,她們離開了她們后天的一切可以自然生長的地方。”[5]在現實的交往中,黛爾認識到傳統女性的處境,無法認同小鎮女性集體的價值觀,試圖將自我與集體區分開來,并渴望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
母親艾迪所講述的個人成長回憶融入了黛爾的個體記憶,彌補了她對父權制下女性抗爭困境認識的空白。艾迪的少時回憶頗具創傷性,她在記憶講述中勾勒出的堅強、獨立、勇敢的知識女性形象深深激勵著黛爾,成為她探尋身份認同的動力源泉。然而,在父權文化根深蒂固的小鎮中,宣揚獨立、堅持“知識女性”的道路面臨重重困難。“女人的悲劇,就是這兩者之間的沖突:總是作為本質確立自我的主體的基本要求與將她構成非本質的處境的要求。”[6]處于兩難境地的女性,要想自由,就必須不斷地解決超越性與內在性的矛盾[7]。在與內在性斗爭、追求超越性的同時,女性容易走進“必須拋棄女性特質才能實現從他者到主體的跨越”的誤區,唯恐因為感性的因素陷入性的誘惑,進而重新回歸內在性的迷惘中。黛爾回憶起母親的告誡:“女性——有知識的女性——不會屈從于性,除非需要。”[5]艾迪將獨立女性置于愛情的對立面,認為愛情與性是阻礙其保持理性、實現超越性的危險因素。然而看到母親兜售百科全書、到學校做演講的宣傳方式并不被小鎮成員所接受,反而遭到排擠,黛爾對此感到迷茫。她渴望知識的同時十分向往愛情,并且希望遵從內心真正的情感,與過去的自我實現融合。在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相匯交融中,黛爾期望突破母親面臨的困境,將個人獨立、自由的成長書寫進小鎮集體的故事中,實現自我身份的認同。
二、探索與反思
集體記憶影響并塑造個體記憶,同時個體與集體成員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個體記憶也會作用于集體記憶,使個體反思集體記憶,建構自我身份。正如揚·阿斯曼所說:“反思是個體認同的形成和發展的必要階段。”[1]記憶的獲得與認同并不是同時發生的,而是有一段過渡時間,在這期間,個體思考記憶之于自我的意義,從而找到真正的自我,確立自我身份。正是在三段感情經歷的“思考空間”中,黛爾對于性、兩性關系、愛情、身份有了更深的認識。
通過與阿爾特·張伯倫的接觸,黛爾獲得了對性的基本認識。黛爾與張伯倫之間的關系最初是基于她對性的幻想與好奇。性是女性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話題,“不管少女以何種方式進入成年期,她的見習期仍然沒有完成。通過緩慢的變化或者突變,她必須經歷性的啟蒙”[6]。張伯倫先生的回應一開始滿足了黛爾對性的期待,“瘋狂的閃念,對體面的表象世界的一次夢幻般的、無情的傲慢入侵”[5]。然而當他開車帶黛爾來到空曠無人的小河邊時,張伯倫展現出的手淫癖好讓黛爾感到錯愕,男性性欲的表演瓦解了黛爾心中對性的美好幻想,同時她也意識到肉體是人無法戰勝的一部分。
之后,黛爾與同齡人杰里·斯多利的交往讓她深刻理解男性對女性思想和身體上的雙重權力控制。米利特在《性政治》一書中認為,“政治”的定義不局限于國家層面的狹義概念,還可以指“一群人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權力結構關系和組合”[8]。父權社會中,男性鞏固自己的控制地位的手段一部分源自對性類別的個性界定劃分。他們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劃分男性為“積極進取、智慧、力量”,而女性為“順從、無知、貞操、無能”[8]。借此,對于女性的貶低構成了男性對女性的控制。與杰里相處期間,黛爾有機會探究自身的潛能,并與杰里交談關于電影、未來等內容。盡管兩人成績同樣優秀,杰里仍然對女性的知識學習具有傳統的偏見:“他坦率地告訴我,我所擁有的是一流的記憶力,對于語言,女性通常具有天賦,而女性邏輯推理相對要弱,幾乎沒有抽象思維的能力。”[5]然而,面對杰里的灌輸,黛爾并沒有輕易相信,仍然保持著自我的判斷,對杰里反而有“一種溫柔、膨脹、專制、荒誕的感覺”[5]。
這段關系中的核心事件發生在杰里的家中。杰里想要見識真正的“裸體女人”,卻對這種行為感到羞恥,實際上也是在他母親的影響下,杰里對于女孩的貞操問題有近乎偏執的認知。杰里對黛爾身體的凝視構成了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控制,在凝視與觸摸中,黛爾成了杰里的欲望客體,她可以被欣賞和掌控,并且不具備個性與自我意識。當他聽到母親回家的聲音時,便將黛爾赤裸地鎖入地下室,并把衣服扔給她。黛爾對杰里的懦弱感到憤怒、憎恨,對自己遭受的不公感到恥辱。她厭惡兩性關系中男性對女性隨心所欲的控制,渴望獲得平等的地位與對待,并在此基礎上反思“愛”的真正要義。
在第三段關系中,黛爾與加內特·弗蘭奇的戀愛讓她明晰了所要追求的女性自我。波伏娃認為:“真正的愛情應當建立在兩個自由人相互承認的基礎上,這樣情人們才能夠感受到自己既是自我又是他者,既不會放棄超越,也不會被弄得不健全,他們將在世界上共同證明價值與目標。”[6]也就是說,愛情應該是兩人共同成長的精神源泉,而不是任何一方借由愛情實施對另一方的壓制,從而迫使對方臣服。黛爾曾萌生與加內特結婚生子的想法,為此,加內特強迫黛爾受洗,想讓她同樣成為浸禮會的教徒。黛爾拼命地掙扎既是為自己的生命斗爭,也是為女性的獨立與自由抗爭,黛爾認為自己不能接受成為男性的附庸,同時也不應該讓愛情屈服于男性的權威。加內特的壓迫就像一面鏡子,黛爾通過將自我意識投射在這面鏡子中,終于看清了真實的自我。她真正意識到,在愛情的漩渦中女性仍需保持一定的理智與獨立性,拋棄個人信仰與思想的愛情已經失去了其作為兩人精神空間的意義。
三、覺醒與認同
記憶對于個體的意識覺醒以及身份認同具有促進作用。“回憶是記憶的動態表現,其所具有的‘力的構建作用,可以作為行動和自我闡釋的發動機產生巨大能量。”[9]黛爾探索女性意義的個人記憶與諸伯利小鎮女性共有的“女性價值應通過男性身份得以實現”的集體記憶逐漸剝離,又相互交織在一起。這種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強烈沖突作為一種無形的作用力,不斷推動黛爾更新和書寫自我意識。“當她成為生產性的、主動的人時,她會重新獲得超越性;她會通過設計具體地去肯定她的主體地位;她會去嘗試認識與她所追求的目標、與她所擁有的金錢和權利相關的責任。”[6]黛爾決心從女性作家的視角尋找自己的意義與價值,這份追求使她獲得“獨立而不邊緣、融入而不屈從”的女性身份認同,探索出一條新女性發展之路。
黛爾在表達自我階段,長期被壓抑的自我意識噴薄而出,完全壓過了集體記憶,使她拋棄現實,沉浸在自我意識形態的輸出當中。在黛爾的小說中,矮胖的網球手馬里恩變為了充滿女性魅力的卡羅琳,在兩性關系中,她是真正的操控者和勝利者。在確定和攝影師平等的戀愛關系后,她決定走進瓦瓦納什河,與愛人共赴黃泉。黛爾腦海中小說的情節與現實中女性的屈從與壓抑、小鎮集體對馬里恩死于未婚先孕的屈辱經歷的構想背道而馳。黛爾試圖將自我意識和集體記憶完全割裂,通過極度渲染女性在兩性關系中的魅力,淡化集體記憶中小鎮女性真正面臨的備受壓迫的困境,卻忽略了現實與記憶、個人與集體之間客觀存在的聯系。
在修正自我的階段,黛爾開始意識到小說中情節與現實情況的裂痕,修正自己的自我意識中過于主觀和情緒化的部分,承認小鎮女性的集體記憶對個體記憶產生的客觀存在的影響。在諸伯利街,她與馬里恩患有精神病的哥哥博比·謝里夫意外相遇,他遞給黛爾檸檬水和自制蛋糕的紳士行為,提醒她注意大學期間飲食的貼心話語,以及整潔的穿著打扮都無法使她將現實生活中這個理智、謙和的男孩與她所創作的瘋瘋癲癲、臟兮兮的霍洛威的形象聯系到一起。于是黛爾從自我幻想中覺醒,意識到寫作應來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而不是脫離生活。她對于小說情節的叩問從“卡羅琳發生了什么事”重新回到了“馬里恩本人發生了什么事”。黛爾嘗試著在小鎮女性庸俗又怯懦的集體記憶與“卡羅琳”般女性灑脫又自由的自我記憶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使其對女性的書寫既不像烏托邦般脫離實際,又不屈從于小鎮女性集體記憶的桎梏。
在重構自我的階段,黛爾實現了對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復雜關系的和諧構建。作為小說家,黛爾從小鎮的“局內人”變為“局外人”,脫離了對小鎮生活極具主觀色彩的描述,而是以客觀的立場,平和冷靜地構建諸伯利街上的人和事,揭露陰暗與美好的每一隅。至此,她完成了從青春懵懂、個人意識萌芽的小女孩到感性與理性并存、對讀者負責的成熟女性藝術家的蛻變。“我想要的是最后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層話語和思想,樹皮和墻壁上的每一道光,每一種氣味、坑洼、痛苦、裂痕、錯覺,靜止地聚攏在一起——燦爛,持久。”[5]黛爾開始在諸伯利街的回憶空間中挖掘創作的元素,在人群與建筑、傷痛與甜蜜中還原出真實而鮮活的小鎮生活,以女性溫柔而又有力的筆觸塑造一個個被男權壓抑而又渴望自我意識覺醒與精神自由的小鎮女性形象。她對寫作歷程的思考與改變,使她重新建立了對小鎮集體的認同,并將自我融入其中,完成了對自我身份的追尋與構建。
四、結語
《女孩和女人的生活》中,黛爾經過童年的懵懂、少年時期的探索,最終通過創作的方式實現了對“我”和“我們”的認同,在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的雙重作用下,蛻變成一名具有獨立、成熟的女性藝術家。門羅借由黛爾的成長歷程表達了自己的對于女性身份的認識,她們既不男性化、排斥男性和婚姻從而淪為邊緣人物,也不完全順從男性從而淪為男權社會的犧牲品,這樣的女性身份在兩性關系中強調調和和平等,獨立而又融入共同體,最終能夠找到心靈的歸屬,實現自我的解放。
參考文獻
[1]? ?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M].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2]? ? 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M].潘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3]? ? 任冰.論艾麗絲·門羅的記憶書寫[J].當代外國文學,2014(4).
[4]? ?李娟.門羅小說中的地域空間、性別體驗與文化記憶——以《公開的秘密》為例析[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3).
[5]? ? 門羅.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M].馬永波,楊于軍,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6]? ?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7]? ?戴雪紅.他者與主體:女性主義的視角[J].南京社會科學,2007(6).
[8]? ?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9]? ?林家帆.“回憶空間”:阿萊達·阿斯曼文化記憶理論研究[D].桂林:廣西師范大學,2020.
(責任編輯 陸曉璇)
作者簡介:嚴? ? 璐,博士,北京工業大學講師,研究方向為文學哲學、20世紀加拿大女性小說。
荊博雯,北京工業大學英語專業本科在讀。
段? ?俏,北京工業大學英語專業本科在讀。
王嘉昱,北京工業大學英語專業本科在讀。
基金項目:2021年度北京工業大學“星火基金”項目“文化記憶視域下共同體書寫研究”(項目編號XH-2021-1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