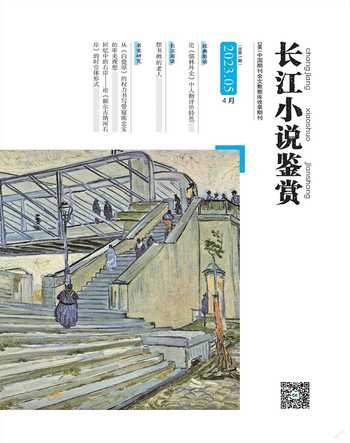《云中記》中原鄉人精神世界的重構和現實價值
[摘? 要] 汶川地震發生十年后,阿來寫下了小說《云中記》,用闊別已久的眼光回望那場災難。自然災害與現代性雙重沖擊下無家可歸的原鄉人,在精神的真空化、存在的疏離化、行為的無能化三個重要方面陷入了精神失衡的狀態,隨著主人公阿巴的返鄉經歷了精神重建的過程。小說中,阿來借地震之口,探討了傳統與現代文明之間的沖突,自然災害與原鄉人的固有生命體驗之間的沖突,表現了對當下人們精神狀態深切的人文關懷,對解決當今困境中人們的精神危機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關鍵詞] 精神困境? 現代性? 返鄉? 重建
[中圖分類號] I06? ? ? ? [文獻標識碼] A
一、精神困境的來源:現代性與天災的雙重沖擊
原鄉人的精神困境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自然災害,二是現代文明。地震是直接因素,以暴力且殘酷的方式摧毀了云中村人固有的家園,致使他們離開家鄉,成為移民村中的“異鄉人”。被迫離鄉的云中村人一方面面對的是家園的消失,另一方面由于不被移民村接受,成了兩個地帶中的邊緣人。現代性則對云中村產生了隱蔽而漸進的沖擊,最顯著的一個特點是以往村民骨子里根深蒂固的苯教發生了動搖,云中村人開始質疑鬼神的存在。科學的進入無疑使傳統的“鬼神”觀念祛魅,但多年封閉生活的云中村人不可能迅速接受現代觀念。由此,原鄉人的精神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中國學者魯樞元在《生態文藝學》中提到,生態危機不僅發生在自然領域和社會領域,同時也發生在精神領域。精神層面的東西是極具價值和意義的,建立在精神本體論上的生態批評也更具有理論穿透力。現代人的精神失衡主要表現在精神的“真空化”、心靈的“拜物化”、生活風格的“齊一化”、存在的“疏離化”和行為的“無能化”五個方面。
1.精神的真空化——信仰缺失下的精神無主
精神的真空化是指“現代人既失去了動物的自信的本能,又失去了文化上的傳統價值尺度,生活失去了意義,生活中普遍感到無聊和絕望”。阿來在成名小說《塵埃落定》中曾說:“西藏的現代性進程中,更準確地說,在我所書寫的那一塊地方——藏區的東北部,罌粟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對當地的經濟政治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與之鄰近的四川的商人、軍閥等確實靠這個東西打開了通往這個地區的大門,找到了介入當地政治與經濟的有效的方式。對于一個封閉的地區來說,鴉片似乎是一個有效的武器。”[1]在《云中記》之前的作品中,阿來描寫了經濟發展等物質化條件對邊地世界的異化,如《山珍三部》中罌粟的種植使當地人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對金錢的狂熱追求導致自然生態遭到不可修復的破壞,也使土司制度走向了瓦解。但《云中記》中,在現代性與天災的雙重沖擊之下,云中村人精神上最大的變化是人們先前心中堅如磐石的信仰開始崩塌,他們開始質疑自己的宗教,也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在這之前,云中村人通過宗教信仰給自己建立了一種內心秩序,擁有一套堅強自洽的秩序觀,可以心平氣和地忍受痛苦和罪惡。地震到來之前,因為通電人們覺得“鬼魂不再現身”,逐漸忘記了祭師的存在;地震發生后,云中村人發現自己在滅頂的天災面前沒有能力自救,并且連續不斷的余震讓他們對信賴已久的山神失望,山神不會顯靈搭救,他們只能作為“被救贖者”等待救贖。小說這樣描寫:“從來沒有見過直升機的云中村人沒有認為是山神顯靈了。連阿巴這個專門侍奉山神的人也沒覺得這是山神顯靈了。”[2]人們曾把信仰藏在山野,土地、牲畜、莊稼、死亡,邊地農人一輩子面對著這些,他們木訥的眼神下飽含著關于最本質的活著的信仰。災難沖擊之下,云中村人意識到宗教信仰不能救命,也不能幫他們重建家園,而科學可以幫他們重建家園,可以治愈他們身體上的痛苦,卻不能撫慰心靈。尤其是得知云中村將再次因未知時間的地震而被毀滅,村民必須搬遷,固有的生活方式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后,云中村人的精神世界備受沖擊,心靈漂泊無主,陷入了真空化的困境。
2.存在的疏離化——三重隔閡下的自我迷失
在魯樞元看來,存在的疏離化主要表現在人與自然的疏離、人與人的疏離、人與自己內心世界的疏離。傳說山神阿吾塔毗憑借武力和神子的智慧,率領部落子民趕走了矮腳人,不再遷徙,選擇在此地定居才有了如今的云中村,所以和大多數藏民一樣,云中村村民一致認為自己是山神阿吾塔毗的子民,受自然神的庇護,他們與自然之間是一種和諧的關系。但時代的發展與自然界中不可預測的災難使人與自然的關系發生了轉變。不像動植物那樣是自然界的存在物,人類依據自己的目的來改變和支配自然,村民與自然之間的需求本質大相徑庭,而在需求中產生的犧牲,疏遠了兩者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地震的發生,在頃刻之間吞噬了數不清的生命,村民們失去了自己的親人、住房、家園……可以說人們生命中一切積極的、向上的力量幾乎全在地震發生的那一刻被瓦解,剩下的只有災難過后無法排遣的軟弱、孤獨與絕望。
地震不僅震動了大地、河流、房屋、生命,還震動了村民的思維與生活方式,他們的內心世界越來越物質化。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也隨著現代性而滋生蔓延,最明顯的一點是村民們不再使用傳統的風俗——“告訴”。“告訴”是嘉絨藏區人們特有的傳統,以口耳相傳的方式來傳遞信息,同樣的敘述也在《機村史詩》中出現過。隨著現代化逐漸影響人們的生活,電取代了火,電燈取代了燭光,電話也慢慢代替了過去淳樸的面對面的談話方式。傳統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發生沖擊時,古老習俗中難以堅守的部分就這么輕松地被剝落。
現代文明沒有進入云中村之前,村民們會依時依節祭拜山神,敬畏和崇拜著自然。他們不懂得地質運動也缺乏科學意識,覺得地震的降臨是天神拋棄了自己,他們內心害怕被自己的神拋棄。而在進入移民村后,科學將神祛魅,“瓦約鄉的其他村寨對‘阿吾塔毗的形象進行了改寫,他不再具有與祖先有關的人類原身和精神力量”[3]。并且通過云丹之口,可以發現當瓦約鄉發展旅游業,成為旅游景點后,村民們原本樸實善良的道德觀念隨著旅游開發的進行,遭受著無法處理的誘惑與沖擊——利欲熏心的村民也開始坐地起價,惡意敲詐游客。小說中祥巴兄弟發跡之后回來修建與整個云中村格調不同的新式樓房,不幸斷腿的央金姑娘再次上山哄騙阿巴是為了配合經紀公司拍宣傳片……人往往信賴能給自己帶來利益的東西,利益能滿足人的欲望,從有形到無形,比如金錢權力、健康長壽、多子多福……嘗到金錢甜頭的村民自然而然從信賴宗教轉變為了信賴“錢教”,從而陷入了唯錢至上的拜物教。
3.行為的無能化——焦慮之下的無奈
魯樞元在《生態文藝學》一書中指出,“現代人的身心承受著無形的、無奈的控制與強迫,個人顯得越來越無能為力,越來越依賴成性,進而引發了內心無端的緊張與焦慮。”《云中記》中多次提到“氣味”,首先是云中村人覺得自己和使用的東西身上“總是帶著特殊的氣味”;接著是村長對阿巴說自己不是云中村人了,因為自己身上失去了云中村的味道。味道是一種抽象的東西,阿來反復強調云中村的味道是怎么樣的,把味道具象化為馬匹、祭師行頭、熏香以及木柴燃燒等具體的味道,氣味引發了鄉愁,但現實里無家可歸的無奈又使云中村人陷入精神焦慮。阿巴多次聞自己身上的味道,并且對別人身上的味道非常敏感,云中村人發覺移民村的原住民稱自己人為“鄉親”,而把云中村人稱為“老鄉”,從而意識到移民村不是自己的家園,他們并未被移民村的原住民接納。
在鄉村自然史與激進的現代文明復雜地纏繞交織中,人類在關注人類與其環境之間在物質能量方面的交流轉換而忽略了人的內在精神因素,忽略生態失衡正在侵蝕人的精神信仰與靈魂空間,正如云中村村長身上具有的失去云中村味道的失落感。民族文化的認同和對精神家園的追求成了阿巴回鄉的內驅動力。不僅如此,云中村人一直過著較為原始的生活,更多地依靠自然法則生活,而移民村現代化的生活方式讓阿巴無所適從,融入移民村意味著改變所有與現代性相悖的習性。小說中有一個細節,阿巴決定回云中村后,用自己所有的錢向云丹買馬,這說明阿巴除了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外沒有其他消費,即使阿巴在移民村生活了三年也沒有適應這里的生活。毫無疑問,生活在移民村的阿巴是痛苦而孤獨的,在故鄉味道的刺激下阿巴毅然踏上了回村之路。回到云中村的阿巴是輕松且自由的,他說:“變成移民村的新村民難,變回云中村的阿巴卻是多么容易啊。”[2]阿巴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祭師,祭師的職責是侍奉神靈和撫慰鬼魂,但是祭師在不相信鬼神的移民村并沒有任何作用,政府封阿巴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阿巴卻沒有搞懂過這個稱號的意義。阿巴覺得空有祭師身份,卻沒有以這個身份為云中村人做過事,他失去了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所以回鄉之路也是阿巴證明自己祭師能力、重塑自我認同感之路。阿巴回云中村撫慰死去的魂靈,撫平了云中村人心頭上對于逝去家人的褶皺,安慰了生者,同樣也實現了自我治愈和療救。
二、原鄉人精神世界的重建
自古以來,“家園”對中國人有著特殊的意義,它不僅指房子、腳下的土地等物質因素,還內涵了人與社會的關系以及靈魂的棲息地。災難侵蝕的不僅是人們的生命財產,更是人們的精神世界。相比之下,房子等基礎設施可以在短時間內憑借足夠的人力物力得以重建,但精神世界的重建是一個漫長且痛苦的過程。即使云中村的村民在移民村有了自己的棲息之地,在政府扶持之下也有了自己謀生的手藝,但他們心中始終牽掛著那些仍在云中村飄蕩著的親人的鬼魂。山崩地裂中意識到自己被山神拋棄了的云中村民們,還是懷揣著希望,想在生與死的鑒別中、在信仰的重構中賦予自己往前的信心。
阿巴與云中村其他村民的不同點一是在于他特殊的祭師身份,阿來小說中經常出現“最后一個”的角色,如《塵埃落定》中最后一個土司家族、《空山》中最后一個巫師,阿巴則是云中村最后一個祭師。阿巴說:“我死不了,我是祭師,我是非物質遺產。”[2]這表明阿巴覺得自己的靈魂未死,信仰仍存。對云中村有著深深執念和急切渴望找尋精神家園歸屬感的阿巴來說,自我身份的強調和認同感是其精神信仰世界尚未崩塌的證明。二是阿巴沒有組成自己的家庭,除了外甥仁欽外,阿巴孤身一人。而外甥已經長大成人,不需要自己的照料,這兩點加上阿巴義無反顧的孤勇,決定了阿巴可以成為回云中村的那個人。同樣,云中村其他村民也把自己對逝去家人和故土的思念寄托給了阿巴。在阿巴準備出發時,村民們用最樸素的歌唱和祈禱送走阿巴,盡管現代化已經讓村民不那么信賴鬼神和苯教,但他們還是選擇用古老的祈禱來送別阿巴,將重建精神家園的美好期望寄予在阿巴身上。作為云中村人的代表和“鄉村最后的守護神”,阿巴帶著村人的期望回到了云中村。阿巴安頓死者的靈魂,就如安頓了震后幸存者們無處寄托的心。
震后多年無人問津的云中村安靜地保留著災難留下的痕跡,阿巴看到了斷墻殘檐,聽到了驚鳥振翅,看到了曾經肥沃的土壤中一季季自生自滅的莊稼,還有哺育了祖祖輩輩卻歷盡苦難的土地。他寂寞的鈴聲回響在空蕩的云中村,阿巴是來回憶和祭奠這些苦難的。再次回歸故鄉的阿巴面對熟悉又荒敗的家園,感到孤獨和痛楚,但也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阿巴不是現代文明的抵御者,但對阿巴來說,科學永遠也無法超越他內心對自然的信仰和敬畏,他在逐漸現代化的移民村無所適從,而荒蕪、原始的云中村讓他感到心安與適然。所以阿巴才能坦然面對廢墟,在廢墟之上修葺房屋、種植莊稼、馴養動物,以一己之力恢復自然的生機。
阿巴回到云中村挨家挨戶撫慰亡靈是整本書中最有力量的一部分,它真實又殘酷,但蘊藏著人性的溫情。阿巴是一個“半吊子”祭師,沒有正式為死者招過魂,對鬼魂是否真正存在一事也將信將疑。但當阿巴回到云中村,將自己擺放在祭師這一身份上,披上祭師行頭的那一刻,厚重的責任感與自我價值裹挾住了他。阿巴看到代表著妹妹的鳶尾花在自己的傾訴下應聲而開,看到不幸遇難的亡靈在自己的召喚下來到眼前,他開始相信這世上有鬼魂的存在。阿巴擊鼓搖鈴,以最原始的宗教儀式悼念逝者,他虔誠地走遍每一戶人家,沒有遺忘最偏遠的角落,把他從移民村帶來表示念想的物件逐一放在廢墟上,他撫慰亡靈、高聲祈禱,然后把谷子用力地拋撒出去,讓死者知道自己仍被家人紀念,讓亡靈不再悲怨,讓活著的人走出悲傷好好生活。
阿巴回云中村的使命是祭祀山神、撫慰亡靈,當所有的使命完成時,阿巴選擇了與終要毀滅的云中村共存亡,他平靜地等待著與云中村一起消失的那一刻。阿巴是勇敢的“逆行者”,也是無家可歸的可憐人。云中村中其他村民都搬遷到了移民村,盡管舍不得家鄉的那片土地,但時間終會讓他們適應一切,擁有新的生活。而阿巴明知回鄉的終點站是死亡,還毅然登上返鄉的列車,說明阿巴覺得自己的肉體與靈魂都屬于云中村,只有回歸云中村,腳踏著熟悉的土地,他才有自己的身份認同感和歸屬感。倘若使命完成后的阿巴回歸移民村,云中村消亡后,作為祭師的阿巴自然再度失去了自己的存在價值,他又會成為孤獨、渾渾噩噩、精神無主的阿巴,對阿巴來說,與云中村在滑坡中一同消失是他人生旅途結束時最好的選擇。
三、《云中記》的現實價值
《云中記》是一部書寫苦難的作品。文學可以記錄苦難,當災難離我們越來越遠,人們對2008年汶川地震的記憶不再清晰,但對于親歷者而言關于傷痛的記憶始終是鮮明的。痛苦曾抵達過的地方,無論經過多久,都可以在親歷者心中纏繞、翻騰。面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種種災難,作為人類最為重要的藝術形式之一,文學不能缺席。
文學可以療愈人心,以文學特有的方式表達對個體創傷的關懷與撫慰。就像阿巴安撫亡靈的作用是讓活著的人好好生活,某個層面上文學的抒發也是為了救贖那些歷經苦難的心靈。阿來在《云中記》的新書發布會上曾說:“我愿意寫出生命所經歷的磨難、罪過、悲苦,但我更愿意寫出經歷過這一切后,人性的溫暖和閃光。”與人為發動的戰爭、動亂等災難不同,天災是一場無妄之災,我們可以找到構成自然災難的種種成因,卻無法站在情感與人性的角度上責怪自然。災難中的幸存者可以遷移,房屋可以重建,而人們靈魂上的東西是持久、永恒的,不是會泄氣的氣球,也不像是打了膨脹劑的任何東西。它沒有時間上的限制,心靈上的創傷最終需要個體的自我療治。《云中記》的抒寫方式是莊重而沉靜的,沒有過多描寫天災發生時的天崩地裂,也沒有高聲控訴地震的無情,“他試圖尋找到一種更好地思考與表達方式,在更廣闊的歷史長河和更深遠地對人類與自然關系的思考中尋找書寫的可能”[4],阿來把鏡頭落在了一個個普通的人物身上,寫出了個人與群體在無妄之災中的掙扎,在生死裂縫中的攀爬抗爭。阿來像是在讓最后一位祭師高聲歌唱安魂曲,哀悼那些在苦難中消逝的生命,撫慰那些災難過去后仍后怕而掙扎的心靈,讓所有人前進的道路都暢通,一切都變得明亮起來。
文學以對災難的回憶和重塑的方式告訴人們不要回避苦難,不要把苦難壓制在溫情之下,要去反思災難,從災難中成長。索洛維約夫曾說:“我請求你們,詩人和作家們,承擔起祭司和先知的使命”,這要求作家和詩人要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每一代人的歷史都是由多重歷史構成的,返身回溯歷史需要有對現在的清醒認知,也需要內心的沉淀與淘洗記憶的勇氣。阿來在自我闡釋中說:“科學時代,神性之光已經黯淡。如果文學執意要歌頌奧德賽式的英雄,自然就要脫離當下流行的審美習慣。近幾十年來,受西方現代派文學和后現代派文學的全面影響,文學充滿了解構與反諷,荒誕、疏離與懷疑成為文學前衛的姿態,我們已經與建構性的文學疏離很久了。”[5]《云中記》建構的一切超出了我們的日常想象,更像是在龐大的歷史進程中截取的一個自然片段,以此來實證一個村莊和最后一位祭師的共同消亡,讓后人在阿巴獻祭式的死亡中思考現代文明與自然的關系、宗教與世俗的波瀾斗爭以及死亡對活著的觀照。
人類的悲歡是相通的。負累之下的人們像是被剝光衣服的玩偶小丑,手足無措,底線、認知、希望一次次被擊穿,面對魔幻又離譜的世界顯得未知而惶惑。作家“不必飽嘗赤貧之艱辛”,但用別人的痛苦來治好精神內耗顯得殘忍而卑鄙,也不該成為作家的書寫方式。相比普通人,作家對外部世界的感知更敏感,更清楚世界上苦難眾多且千差萬別,他們能創作偉大的作品,某種程度上自己也在受苦。所謂痛苦是創作的源泉,并非是拿別人的痛苦滋養自己的靈魂,而是由于自身受苦和有一顆悲憫的良心,能深刻理解和共情他人的痛苦。作家在自己的痛苦、他人的痛苦,凡此種種各不相同的痛苦之間建立起聯系,并把這種聯系通過創作告訴不了解它的人們,從而成為人們精神上的指引。雖然《云中記》書寫的是人類的災難,歷經苦難后的阿巴和云中村最后也平靜而安詳地在那一天逝去,但它仍是一部有溫度的、可以給予受苦受難者精神撫慰的作品。在時代和命運交匯的激流中,我們需要時間來告別悲痛,需要像阿巴一樣的祭師安慰心靈,也需要像阿來一樣的作家去記錄和書寫時代的群體創傷。
參考文獻
[1]? ?何言宏,阿來.現代性視野中的藏地世界[J].當代作家評論,2009(1).
[2]? ? 阿來.云中記[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
[3]? ? 武俊宇.以何為家,何以為家?——論《云中記》的“家園”敘事[J].名作欣賞,2021(29).
[4]? ? 許亞龍.生死之間的靈魂救贖——《余震》和《云中記》的倫理問題[J].阿來研究,2019(2).
[5]? ?阿來. 關于《云中記》,談談語言[J]. 揚子江評論,2019(6).
[6]? ? 孟繁華.一部絕處逢生的杰作[J].當代文壇,2019(5).
[7]? ? ?劉大先.作為記憶、儀式與治療的文學——以阿來《云中記》為中心[J].當代作家評論,2020(3).
[8]? ? 季進.安魂與抒情——讀阿來的《云中記》[J].當代文壇,2020(1).
[9]? ? 鄧昕洋,杜慧春.論阿來小說《云中記》中的家園意識[J].景德鎮學院學報,2020(1).
[10]? ?孫德喜.攀爬在生與死之間——論阿來的長篇小說《云中記》[J].阿來研究,2020(2).
[11]? 孔德歡.災難書寫背后的生命安魂曲——解讀阿來長篇小說《云中記》[J].文化學刊,2020(5).
[12]? 張煜棪.廢墟·凝視·安魂曲:《云中記》的后地震敘事[J].當代文壇,2020(6).
[13]? 吳雪麗.重構藏地鄉村的精神圖譜與歷史記憶——從《空山》到《云中記》的文學啟示[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12).
[14]? ?武俊宇.以何為家,何以為家?——論《云中記》的“家園”敘事[J].名作欣賞,2021(29).
[15]? 賀仲明,呂子涵.災難語境下的文學精神建構——論阿來《云中記》的思想意義[J].阿來研究,2022(1).
[16]? 陳思廣.從故鄉出發,抵達信仰的家園——鄉土小說視野下的《云中記》解讀[J].小說評論,2022(4).
(責任編輯 羅? 芳)
作者簡介:楊丹,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與都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