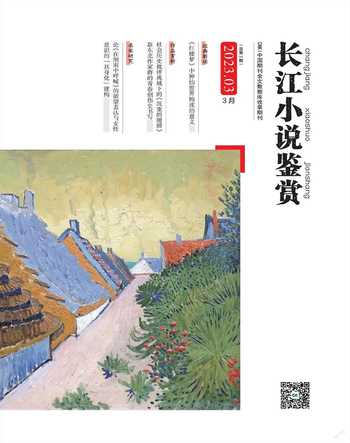“美女之死”主題小說的悲劇因素與生命力感
[摘? 要] 浪漫主義作家愛倫·坡在其廣為人知的以“美女之死”為主題的小說中,將死亡、恐怖與美融于一體,形成了獨特的悲劇因素。作為坡的悲劇性主人公,這些在父權制的重壓之下苦苦掙扎的女性反抗者具有強大的生存意志,強烈地表達了對命運的不服從。她們的反抗精神使“美女之死”不再是凄婉的,而是悲愴的,這在極大程度上喚起了讀者的生存本能,大幅度提升了小說的生命力感。
[關鍵詞] 愛倫·坡? 美女之死? 悲劇因素? 生命力感
[中圖分類號] I107.4? ? ? [文獻標識碼] A
愛倫·坡的小說常常密布著死亡的陰云,其廣為人知的以“美女之死”為主題的小說更是將死亡、恐怖與美融于一體。詭異的死亡往往彌漫著對美的哀悼,死亡的宿命里充斥著不甘的反抗,由此形成了愛倫·坡小說中獨特的悲劇因素。
作為浪漫主義作家的坡志不在展現現實生活中人的悲劇,較之時代變遷、歷史滄桑的大背景,他更關注個體人物內在的小世界。個體的壓抑和精神的苦悶往往是由密閉著的狹小空間來表現的,在坡“美女之死”的主題小說中,女性大多離群索居,幾乎都被囚禁在畫室、古屋、塔樓、城堡之類的狹窄之地。坡架空了社會與歷史的背景,甚至摒除了瑣碎的日常生活的紛擾,他將故事與現實完全隔絕開來,使人物的內在精神不受外部力量的拘束。在坡的時空中,人的內在感受是他關注的焦點,人的靈魂是他藝術舞臺上唯一的演員。
坡對生活在父權制的重壓之下的女性群體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女性的悲慘命運、女性的生存危機、女性的痛苦和壓抑都成為坡關注的對象。“美女之死”的主題小說書寫的不僅是女性的悲劇,更是女性對命運的抗爭。坡在為弱者發聲的同時,也為她們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一、“美女之死”的悲劇性主人公
在坡以“美女之死”為主題的小說中,女性反抗者成為悲劇性主人公。就坡而言,男性擔負不起悲劇的重任。坡塑造的男性形象大多自私涼薄,他們站在女性的對立面,甚至不乏以施暴者的形象出現。《橢圓形畫像》中的畫家通過妻子的付出成全了自己的藝術事業;《艾蕾奧瑙拉》中的戀人背棄諾言,另結新歡;《麗姬婭》中的丈夫繼承了亡妻大量的財產,卻既不知道妻子的姓氏,也不知道她來自何方;《莫蕾拉》和《貝蕾妮絲》中的丈夫更是偏執冷漠、殘忍暴虐,他們或對妻子施加精神上的冷暴力,或粗暴而血腥地將其活埋,致使“美女之死”幾乎成為一個個陰森恐怖的鬼故事。
男性對女性的冷酷無情和男性內心的軟弱自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一想到任何會影響我這脆弱敏感的靈魂的事,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就會渾身發抖……在這種不安的心態下——在這可憐的境地中——我就感到那個時刻遲早會到來,我定會在與恐懼這個可怕幻想的抗爭中失去我的生命和理智。”[1]惴惴不安的施暴者就這樣時時徘徊在精神崩潰的邊緣,惶惶不可終日。于是,坡果斷地將完成悲劇的重任交給了在父權重壓之下苦苦掙扎的女性反抗者。
愛倫·坡將悲劇的英雄形象賦予了女性,特別是反抗中的女性。重壓之下的屈從者令人唏噓,痛苦中的反抗者才給人震撼。“對悲劇來說緊要的不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對待痛苦的方式。”[2]悲劇不需要無怨無悔的順從或逆來順受的退讓,“沒有對災難的反抗,也就沒有悲劇”。 [2]沒有反抗的火花就無法制造沖突,而沒有沖突就無法形成戲劇的張力。因此,引發悲劇的不是“美女之死”,造就悲劇性痛感的是女性對死亡和命運的抗爭。深陷死亡的巨大旋渦,飽受命運的磋磨,坡的女主人公們如復仇女神一般以各自的方式進行反擊。
二、“美女之死”中的兩類反抗者
在以“美女之死”為主題的小說中,具有自主意識的女性反抗者大概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如貝蕾妮絲、瑪德琳、麗姬婭,她們具備強大的生存意志;第二種類型如阿芙羅狄蒂、莫蕾拉,她們鮮明地表達了對命運的不服從。
在第一種類型中,女性的生命受到了嚴重威脅并由此爆發出強烈的反抗意識。偏執的丈夫把貝蕾妮絲送入了墳墓,還極其殘忍地拔掉她的三十二顆牙齒,貝蕾妮絲殊死相搏,最終掙扎著爬出了墳墓。《厄舍府的倒塌》中,瑪德琳在一次病發后被哥哥羅德里克活埋,她歷盡磨難,浴血歸來。垂死的麗姬婭滿懷“一種熱切的企盼”“一種對生命——僅僅對生命——的最強烈的渴望”,一種“強烈得近乎瘋狂的求生欲望——生——只求生”。[1]她病弱的身軀激揚著不屈的生存意志,恰恰驗證了“凡人若無意志薄弱之缺陷,絕不臣服天使,亦不屈從死神”。[3]這些女性在災禍和死亡面前表現出的強大的生存意志和反抗精神賦予了小說悲劇性的效果。
在第二種類型中,女性表達了對命運的不甘心和不服從。《幽會》中的侯爵夫人阿芙羅狄蒂甘愿放棄一切來擺脫命運的枷鎖。在與昔日戀人瞬息之間的見面中,她只匆匆留下了一句話,“日出后一個時辰——我們將相會——就這樣吧”。[1]次日阿芙羅狄蒂服毒殉情,到那寄托著所有夢想的空谷幽地如約赴會。《莫蕾拉》中的丈夫無時無刻不對妻子進行精神摧殘,莫蕾拉在彌留之際控訴愛情的不公并詛咒丈夫的命運,“你的日子會充滿痛苦——那痛苦是最持久的感受,就像柏樹是最不朽的樹木”“你快樂的時光不復,生命中不再有喜悅,不像帕斯圖姆的薔薇能一年盛開兩次”。[4]不管是欣然赴死,還是死而再生,女性對命運的抗爭激蕩著讀者的心魂,并由此生成濃重的悲劇性痛感。
無論是對生命,還是對宿命,這兩類女性都表達了決絕的勇氣和反抗的精神。在死亡的陰影之下,這些無所畏懼的復仇女神爆發出毀滅一切的力量,令人心驚。
三、悲愴的崇高與生命力感
反抗性精神使“美女之死”不再是凄婉的,而是悲愴的。傳統悲劇往往傾向于強調悲劇人物的不平凡,突出英雄品質的高尚和偉大,但坡從未在他的故事中書寫過任何一個英雄的悲劇性傳奇或塑造過某位大人物的悲劇性形象,相反,他將注意力放在了這些默默隱藏在男性背后的女人身上。女性的家庭性注定了她們不可能如傳統悲劇中的帝王將相一般具備社會性或歷史性的影響力。她們太過普通、渺小又卑微,但就是在她們身上,讀者感受到了精神的力量和意志的不朽,并由此激發出內在的崇高性。
愛倫·坡對弱者情感和精神的感性關懷更容易喚起讀者自身的生命力感。傳統的悲劇情節往往蕩氣回腸,坡筆下的故事顯然不屬于此類。作為弱勢群體的女性沒有機會承擔艱巨而偉大的使命,也無須經受艱難險阻的歷史性考驗,她們所要完成的是內在、個體的自我認證。自我意識的復蘇、自我價值的認同和生命尊嚴的恢復是女性生命的本能需求。重病纏身的麗姬婭的生命意志至上論;被活埋的貝蕾妮絲和瑪德琳慘烈的死而復生;金絲籠里的阿芙羅狄蒂對自由和愛情的孤注一擲;被丈夫送入墳墓的莫蕾拉對命運的詛咒……這些女性雖作為弱勢群體,但都將滿足自我作為人生的崇高價值。坡竭盡全力地展示了弱者對自身生命基本需求的渴望,這種悲憫的情懷最能觸動讀者的內心,引發共鳴,從而激發讀者潛在的生命力感。
坡的女主人公拒絕扮演男性強加的角色,拒絕接受命運的安排,她們奮起相搏、堅持到底。這也決定了作為弱者的她們所必經的從生命力受到阻礙到生命力全然噴發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恰恰是悲劇的崇高性得以體現的過程。在《判斷力之批判》中康德提出,崇高之情是間接發生的,要經由從“生命力之暫時抑制而即刻繼之以更有力的生命力之迸發”[5]而產生。坡的女主人公遭受挫折,但她們“在暫時的抑制之后,感到一陣突發的自我的擴張”,[2]由此激發的“生命力感和努力向上的意識”[2]使她們超越了自我的渺小,顛覆了原有的認知,擺脫了命運的枷鎖,沖破了死亡的界限。讀者在這些原本柔弱的女性身上感受到了一種近乎英雄的氣魄,情感也隨之上升到同等的高度,生命力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繼而“打破自己平日的局限,飛向崇高的事物,并在理想中把自己與它等同起來,分享著它的偉大”。[2]
四、悲劇性釋放與生命力感
悲劇性人物所釋放的生命悲情總能給讀者帶來最直觀的感受。坡的悲劇主人公是在父權社會中對男人唯命是從的女人。她們沒有職業、沒有自由、沒有需求、沒有尊嚴,更沒有話語權。她們被孤立、被厭惡、被無視、被傷害,但坡為她們提供了發泄憤怒和痛苦的場所,給她們機會展現她們尖銳的孤獨和刻骨的悲傷。
在坡的故事中,失語的女性有了發聲的機會。緘默無聲的貝蕾妮絲在冰冷的墳墓中發出了“尖利而刺骨的”叫喊,“就像逝去的聲音之魂”刺穿男人的內心。[4]如幽靈一般沉默無語的瑪德琳在猛烈地掙扎后將羅德里克拽倒在地上,發出“一聲低低的呻吟”。[1]從失聲到出聲,哪怕僅僅是一聲大喊、一聲低吟,也終于表達出沉默者內心最深的傷痛。
在坡的故事中,絕望的女性向蒼天斥責人世的不公。莫蕾拉在臨終前聲嘶力竭地控訴丈夫:“啊,多么少!——這就是你對我,莫蕾拉的感情!”[4]奄奄一息的麗姬婭難以抑制心中的悲憤,她質問上帝:“啊,天吶!啊,老天爺吶!——難道這種情況始終不變?——難道這個霸王永遠稱霸不成?難道我們不是上帝您的骨肉?”[3]這些振聾發聵的吶喊源自女性心中被壓抑許久的、難以再遏制的憤恨與不滿,它彰顯了弱者身上潛藏的強大力量,并形成了極具對比的生命反差。
悲劇經驗中強調情感的釋放。在“美女之死”的故事中,女性完成了對壓力的極大釋放和對情感的極度宣泄。伴隨著痛苦的釋放,郁積的情緒也得以緩和,這“不僅意味著消除高強度的緊張,而且也是喚起一種生命力感”。[2]
于是,在坡的故事中,“被死亡”的女性有了生的希望。被丈夫過早埋葬的貝蕾妮絲、被羅德里克活埋的瑪德琳披著帶血的尸衣爬出墳墓,重返人間。在坡的故事中,被丈夫厭棄的女性有了反擊的機會。莫蕾拉死后重生,帶著對丈夫不死不休的折磨回到他身邊。在坡的故事中,受世俗裹挾的女性有了重新選擇的可能。阿芙羅狄蒂被迫嫁給了顯赫的侯爵,壓抑多年的情感在見到舊時戀人的瞬間如火山般爆發,她終將名利付之一炬,甘愿飲下劇毒,也要兌現對戀人許下的諾言,義無反顧地向命運挑戰。
生命力感的提升是多方面的,不僅對于悲劇性主人公,對于讀者也是如此。伴隨著故事中主人公生命悲情的釋放,讀者全方位地感受到一股來自生命深處的強大力量,與此同時,全部激情也被調動到了頂點。
五、恐懼的痛感與生命力感
慘烈的“美女之死”不斷地刺激著讀者產生大量的生命動能。這些女性受難者在死亡邊緣的反抗不僅是對被壓抑的精神和情感的釋放,而且是伴隨著恐怖色彩的生命的動態寫照。“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殘酷與惡意……能給人的生命力以強烈的刺激。”[2]女性的可怕遭遇帶給讀者強烈的刺激,危險性越大,刺激性就越強,而災禍隨之轉化成心理行為,讀者的恐懼感油然而生,恐懼程度越來越高。
“恐懼是一種痛感,痛感在力量上遠比快感強烈,它是一切感情中最強有力的情感。”[6]空前的痛感喚起讀者的生命本能,死的威脅滋生的對生的渴望和命運的桎梏下爆發的不屈的精神在加大悲劇性張力的同時也達成了讀者生命力感的集聚。當恐懼達到極致時,生命力得到最強有力的爆發。在麗姬婭褪去尸衣的那一刻,在復活的瑪德琳破門而入的一瞬間,讀者的恐懼感與生命力感都同時到達了頂峰。
女性的可怕遭遇帶給讀者極端的生命體驗,“它激起恐懼,便使我們感到振奮。它喚起不同尋常的生命力來應付不同尋常的情境”。[2]無論是面對何種生死存亡的逆境,坡的女主人公的生命力都表現了頑強向上的勢頭。她們的生命軌跡表現出極度的相似性:生命力受阻至近乎湮滅-全力抗爭并絕地求生-生命復蘇至生命力迸發。遭遇危險時,她們的生命力受到抑制,讀者的恐懼性痛感隨之上升;而當生命意識覺醒后進行決然反抗之際,她們的生命力不斷昂揚,讀者也隨之得到暢快淋漓的生命感受。不畏恐懼、向死而生,女性在生命的整個過程中所凸顯出的對抗性痛感使讀者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
死亡、恐怖與美是愛倫·坡小說中獨有的特征。坡承認人性中的惡念,也從未否認過人性的弱點,但他一直堅信美的存在,歌頌美的不朽。因此,“美女之死”的悲劇絕不會單一地指向恐怖的死亡終極,女性對命運的抗爭也必然成為這些死亡恐怖小說中最美、最閃亮的所在。而事實上,在“美女之死”的故事中,坡并沒有給出故事的結局。當逝者睜開雙眸、被埋葬者爬出墳墓,坡的故事就戛然而止了。身為作者,坡放棄了對作品的最終掌控權,開放式的結尾卻給予了悲劇性主人公對生命選擇的最大維度,給予了那些被拘禁的靈魂最大的自由。告別過去,不畏將來,無論前方還有多少坎坷曲折,生命和未來都真正掌握在了女性自己手中。個體在經歷了苦難后得以重生,并走向了自由而廣闊的未來。這種豁然開朗的生命境地是坡對女性生命價值的肯定和尊重。
六、結語
愛倫·坡以“美女之死”為主題的小說中,女性所爆發的力量令整個父權社會為之震驚。女性在進行對外的斗爭的同時也實現了內在的超越。在反抗中她們復蘇了麻木的情感,發現了精神的力量,甚至最終超越了死亡,完成了對生命的重建。“美女之死”的故事中所蘊含的獨特的悲劇因素也給讀者帶來了特殊的生命體驗。弱者身上爆發的反抗性精神使崇高感油然而生,悲劇性人物所釋放的生命悲情調動了讀者的生命激情,死亡的恐懼達成了讀者生命力感的集聚。
正如朱光潛所言,“生命的目的則是在活動中得到自我實現”。[2]悲劇性人物必然遭受災難,承擔痛苦,但絕不會在絕望中滅亡,因為“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顆神性的火花,它不允許我們自甘失敗”。[2]不僅故事中的女性受難者,讀者心中的神性也就此被點燃。日常的生活太過狹窄,生命的長度和范圍也極其有限,而“悲劇則能補人生的不足”。[2]悲劇性的苦難并非僅是為了令讀者傷心流淚,悲劇性的反抗才真正使讀者在悲痛中振奮,在抗爭后成長。最終,讀者獲得一種昂揚的生命力感,進而實現內心的充盈、生命力的提升和精神的自由。
參考文獻
[1]? ? 坡.愛倫·坡集:詩歌與故事[M].曹明倫,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2]? ?朱光潛. 悲劇心理學:各種悲劇快感理論的批判研究[M]. 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
[3]? ? 坡.愛倫·坡短篇小說集[M]. 陳良廷,徐汝椿,馬愛農,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 ?坡.摩格街謀殺案[M].張沖,張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5]? ?康德.判斷力之批判[M]. 牟宗三,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8.
[6]? ?劉怡.哥特建筑與英國哥特小說互文性研究:1764—1820[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1.
(責任編輯 陸曉璇)
作者簡介:徐薇,碩士,江蘇第二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
基金項目:本文為2020年度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向死而生——愛倫·坡短篇小說的死亡詩學研究”(項目編號:2020SJA061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