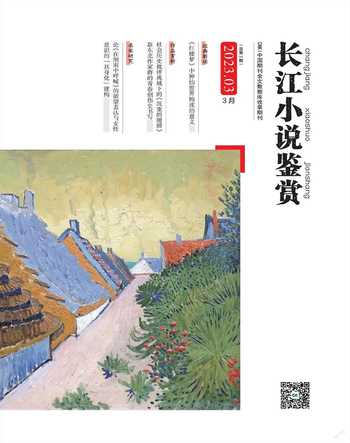論《在細雨中呼喊》的欲望表達與女性意識的“具身化”建構
[摘? 要] 余華在創作中主要通過欲望來刻畫人物,他認為欲望更能凸顯人物的價值。《在細雨中呼喊》中余華以女性人物為依托進行欲望表達,他筆下的女性人物通過對欲望壓制的妥協、變態反應等一系列身體實踐之后逐漸萌生了女性意識。從“具身化”理論層面來看,這些女性的身體行為是女性意識一種默會的表達,而女性意識的覺醒也離不開身體運動實踐,因此女性主體要通過欲望的追求和身體實踐來建構女性意識。
[關鍵詞] 《在細雨中呼喊》? 欲望? 女性意識? 具身化
[中圖分類號] I06? ? ? ? ?[文獻標識碼] A
欲望是小說中的要素之一,但不同作家表達欲望的方式不同,呈現出的形式也大不相同。余華善于以人物為依托進行欲望表達,他認為“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個人的存在價值”[1]。縱觀他在小說中塑造的人物,與其說他在塑造一個個人物的性格,不如說在展現人物身上多方面的欲望。《在細雨中呼喊》是這類作品的代表,作者通過雙重敘述者交替敘述的方式,并通過時間的自由穿梭,在描述三代人的生活經歷和苦澀命運的同時,也展現了欲望在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身上多層面的表達。
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開篇便寫到“我”在黑夜里聽到一個女人哭泣般的呼喊聲,“那個女人的呼喊聲持續了很久,我是那么急切和害怕地期待著另一個聲音的來到,一個出來回答女人的呼喊,能夠平息她哭泣的聲音,可是沒有出現。”[2]黑夜中的呼喊聲正象征著小說中“我”的生母、李秀英、馮玉青等生活在苦難中的女性渴望被傾聽、被拯救的欲望。但是正如平息她們哭泣的聲音始終沒有出現一樣,她們的欲望也在社會的壓迫下變得支離破碎。
女性意識是指女性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和對自我解放的認識與追求[3],從女性主體的角度來說,女性意識可以理解為以女性的眼光審視自我,從女性的立場看待外部世界,進而獲得對自己的社會認同和富于女性色彩的對世界的獨特理解[4]。在書中,我們不僅能體會到女性意識的缺失帶給她們的苦難,也可以窺見她們在特定歷史時代背景下,女性意識散發出的微弱光芒。
一、欲望與壓制
余華筆下的女性人物充滿欲望,但是絕大部分女性的欲望處于被壓制的狀態。小說中的母親、李秀英等女性人物的欲望表達始終處于被壓制的狀態,由于時代以及女性意識的缺失導致的自身局限性,她們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劇性的結局。
1.李秀英的悲劇
作者筆下“我”的養母李秀英不僅在生活中受到丈夫王立強的欺凌,而且在精神上還要忍受丈夫出軌的打擊。在“我”剛來到李秀英家的一段時間,每隔幾天夜晚,“我”都能聽到從李秀英房間傳來的呻吟聲和哀求聲。李秀英為了阻止丈夫的暴行,還苦苦哀求“我”睡到他們二人中間,但是王立強絲毫沒有收斂,甚至毆打來“幫助”李秀英的“我”。王立強不滿虛弱的李秀英,背著她找了個情人,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背叛了李秀英。王立強出軌的這段時間,李秀英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最后傳來了丈夫的死訊,李秀英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丈夫不僅早就出軌,而且在他死前,身上還背負著兩條人命。本就虛弱的她,在經受吃驚、害怕、憂傷等一系列情感沖擊后肆無忌憚地叫喊著,而叫喊是她唯一表達自己悲痛和絕望的方式。這個被壓制的女人,在絕望中逃離了孫蕩,也逃離了一切。
2.“我”的生母的悲劇
“我”的生母似乎只是父親的泄欲和生產、養育子女的工具。母親是傳統社會逆來順受的賢妻良母的典型代表,她一生都在為這個家操勞,為這個家而活,為子女而活,卻從來沒有為自己活過。母親的賢惠、順從、奉獻,并沒有換來父親的絲毫體諒和感恩。父親在得知母親在送飯的路上生產后沒有絲毫的關心,甚至還責怪母親送飯太慢;向“我”講述“我”出生的過程時嘲諷地說“你娘像下蛋一樣把你下出來了”;母親明知父親爬寡婦的床,卻裝作不知道忍氣吞聲甚至“還將一如既往地向他敞開一切”……她的女性道德就是滿足父親的一切要求,為丈夫、為家人鞠躬盡瘁。
魯迅曾說:“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兒性;無妻性。”[5]兩位母親無限度的隱忍正是魯迅所說的“母性”的體現,這反映了當時社會中女性在被奴役被貶低中逐漸喪失了欲望,失去了作為“人”的主體性的現象,也折射出了真正女性意識的喪失,女人失去作為人的最基本的個體欲望的悲劇現實。
二、欲望與變態
女性的欲望長時間處于被壓制的狀態,導致女性的心理出現了變態的反應。余華通過女性變態的心理,揭示了其病態、黑暗的一面。
1.對環境的變態敏感
李秀英對潮濕有著病態的敏感,對陽光也有著病態的渴求。李秀英可以通過手來感受空氣的濕度,她要求“我”每天擦兩次窗戶,保證窗戶的清潔,使陽光能不受污染地照到她的內衣內褲上,從而使她的衣服清爽、干燥。她將她的內衣內褲擺放在一個個小凳子上,使每一件內衣內褲都能充分地接受陽光的照射。文中提道:“她認為,潮濕是風吹來的,是玻璃窗保護了她不受風和塵土的侵擾,維護住了她和陽光美好的關系。”她把自己裝在玻璃當中,企圖用玻璃來阻絕塵埃、病毒等一切骯臟的東西,企圖讓陽光帶走她的病苦,讓陽光去溫暖自己。這種對環境的變態敏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心理遭到長期壓迫后造成的安全感的缺失。
2.對疾病的變態驕傲
李秀英對待自己疾病的態度也是病態的。她總是不停地嘮叨自己這里或是那里不舒服,但這并沒有收獲丈夫的體貼,得到的只有丈夫的聲聲嘆息。孤獨的李秀英只能向“我”訴說她的苦痛,長時間的壓抑使得她將自己的苦痛當作榮耀一般炫耀,甚至當“我”恐懼、吃驚時會引起她對自己疾病的得意和驕傲。她因自己的疾病駭人聽聞而驕傲的狀態也正是她在生活、疾病的壓迫下變態的體現。
3.對統治丈夫的變態欲望
詩人的妻子是這部小說中最為特殊的女性形象,其他的女性或多或少都生活在父權的壓迫和統治下,她們總是處在弱勢地位,是被壓迫者。而詩人的妻子,這個三十多歲的漂亮女子卻截然不同,她對壓迫、摧殘丈夫有著病態的欲望。她具有十分兇狠的性格,經常辱罵、訓斥甚至毆打自己的丈夫,還將她丈夫寫的懺悔書、保證書、檢討書像藝術品一樣掛在墻上展覽,向做客的朋友炫耀。她不僅在肉體上虐待詩人,還在精神上無情地摧殘詩人。她病態地將統治丈夫、壓迫丈夫作為一種榮耀并樂在其中。
4.對死亡的變態認知
國慶樓下陰森的婆婆,對死有著病態的認知,固執地相信陰間世界的存在。她害怕胡同里的黃毛狗,將它視為自己在人世間唯一的敵人,因此每天虔誠地跪在觀音像前,默默懇求菩薩保佑黃毛狗長壽。因為她認為如果黃毛狗先她而死,那么去陰間的路上,就會遇到它,而自己將不得安寧。對死亡的病態認知使她沉浸在孤獨之中,并享受與死人的相處。擺滿了死人照片的屋子能帶給她安全感,她雖然活著,卻迷戀與死人對話。她竭盡全力地保持著原有的生活,像機器一般反復重復。她丈夫在很久之前就去世了,那個男人癡迷于吃螺螄,她認為對丈夫最好的紀念,就是繼承他這唯一的嗜好。她變態般地迷信、變態般地守著舊有的生活習慣,早已沒有對生活的熱愛、對新事物的嘗試,像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行尸走肉。
余華并沒有用過多的筆墨刻畫此類人物形象,僅僅幾句語言描寫、神態描寫,就將那個時代下異化的女性的變態欲望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在為這些病態的女性哀嘆時,也能感受到作者在特定歷史情境中對女性病態心理的精確把握,正如有的學者總結的那樣:“這些女性使我們在疼痛中不得不正視人性中那些惡質因子的現象性存在。”[6]而這些女性身上的惡質因子也正是女性欲望被壓制、女性意識缺失產生的惡果。
三、欲望與覺醒
《在細雨中呼喊》中并非所有女性都對苦難和壓迫逆來順受,有些女性已經沖破了傳統女性“三從四德”的牢籠,有意識地反抗壓迫,為自己的情感生活做主,以至可以努力追求欲望的實現,獲得身心的解放。她們擺脫了“母性”和“女兒性”的束縛,在對欲望的追求中,不自覺地追尋“妻性”,這就是余華欲望表達下覺醒的女性形象。
1.馮玉青的覺醒
女性主體意識是指女性作為自身社會行為和情感的支配者,在客觀世界中形成的對自身地位、社會價值的自覺意識,是指女性能夠以獨立的精神和姿態行走在屬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實現人生價值,而不必成為任何人的附屬品[7]。馮玉青是女性主體意識覺醒者的代表人物。在被王躍進拋棄并當眾羞辱之后,馮玉青展現出了超乎尋常的勇敢和冷靜。她平靜從容地獨自去醫院做檢查,化驗自己是否懷孕。在王躍進的婚禮上,她當眾踩凳子將草繩系在樹枝上,系成要上吊的樣子,然后莊重離去,使得婚禮無法照常進行,也使得旁觀者知曉了王躍進始亂終棄的事實。面對施暴者她沒有忍氣吞聲、一蹶不振,而是用她自己的方式反抗著壓迫。看著混亂的婚禮現場,她釋然了,并對自己的命運產生困惑,這是她覺醒后對自我價值確認的迷茫,也是她女性意識真正覺醒的開端。在聽了賣貨郎講述外面的世界和走南闖北的艱辛之后,她跟著賣貨郎離開了。她就如同易卜生戲劇中出走的娜拉一樣勇敢,這是她追求成為自我的主宰,獲得身心解放、精神獨立邁出的第一步。作者并沒有交代她離開村子后經歷了什么,只是在介紹“我”的朋友魯魯時提到了她,五年的時間她已經從年輕漂亮的少女變成了飽經滄桑的暴躁婦人,一個人帶著五歲的孩子,白天干著又臟又累的洗刷塑料薄膜的工作,晚上干著皮肉生意。她出走后的生活雖然令人心痛,但是不得不承認她思想中已經有一些新特質:有意識的反抗壓迫使她成為自己的主宰,獲得思想解放的同時她也在經濟上達到了獨立自主,雖然其生活還并不如意,但就其方向而言卻成了真正獨立的“人”。
2.寡婦的覺醒
作者同樣也注重發掘女人身體的蓬勃欲望與生命激情,寡婦是在欲望中體現覺醒的形象。這個粗壯的、大嗓門的女人,放縱著自己沉浸在自己皮肉生涯的享樂中。這個欲望蓬勃的女人,在余華的筆下,成了禍害男人的“禍水”。受人尊敬的蘇醫生沒能抵住誘惑落得妻離子散的下場,父親孫廣才為了討寡婦歡心傾家蕩產……寡婦的形象固然可恨,她的欲望表達、實現是建立在破壞他人家庭的基礎上的,但是放浪淫蕩的寡婦身上也具有覺醒者的氣質。她并非“三從四德”的傳統女性,在丈夫死后并沒有依照傳統道德約束自己,而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她身上體現出對自己的欲望勇敢追求的強烈自我意識,沒有屈從于男人閑言碎語的獨立的人格,這些都是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重要體現。在當時的社會,女性一般都處于被壓迫被損害的地位,更何況是無依無靠的寡婦,孤獨寂寞的同時還要承受著冷眼、嘲諷。皮肉生意也許是走投無路的選擇,更多的是不僅在能得到物質滿足的同時,在精神上也能得到滿足。片刻的歡愉和溫情足以溫暖這個可憐的女人,也是她繼續生活下去的微光。所以當父親變賣了家里所有值錢的東西都交到寡婦的手中,當已經老去的寡婦再也沒有對激情的渴望時,慷慨的父親可能是她最好的選擇與歸宿,這一結局不僅體現了作者對寡婦的悲憫與同情,還體現了作者潛意識下對覺醒女性的認同。
魯迅認為:“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兒性的混合。”[5]因此這些女性主體意識的解放更多是在欲望的壓迫中反抗,并以找尋“妻性”作為出路,最終實現女性意識的覺醒。
四、女性意識的具身化建構
具身化(Embodiment)這一概念最早由萊考夫和約翰遜提出,這一概念充分地肯定了身體在認知過程中的作用,作為對傳統身心二元論的反思與批判,具身化一經提出便受到各學科領域的廣泛關注。在《知覺現象學》中梅洛-龐蒂將“具身化”研究引入了關于身體意識的“具身性”現象學這一新的發展方向。梅洛-龐蒂將人的肉身看作一種“現象的身體”,提出用身體表達取代意識表達,強調意識是身體投入的意識。“動作并沒有使我想到憤怒,動作就是憤怒本身。”[8]他認為身體動作本身就傳達著意義,因此身體動作的實踐可以表達著意義,意義也可以通過身體動作得以表達。
《在細雨中呼喊》中女性人物遭受欲望壓制的變態反應和反抗的身體實踐正是女性意識生成的意向性表達,這種表達甚至先于她們的思想意識而通過身體的行為動作表現出來。無論是李秀英、樓下婆婆等人心理上的變態反應行為,還是馮玉青的出走、寡婦的縱欲等肉體上的實踐,這都是她們身體對于欲望的意向性表達,這也是女性意識一種默會的表達。值得注意的是,意識的建構需要意向和身體運動相結合,由此我們可推斷女性意識的建構是一個意向性和身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出走和縱欲的身體實踐是馮玉青和寡婦擺脫“母性”和“女兒性”的束縛,觸及“妻性”的關鍵,因此女性主體要通過欲望的追求和身體實踐來建構女性意識。
五、結語
綜上所述,作品中余華通過女性欲望抒寫,表達了女性欲望被壓制、欲望缺失造成的心理變態以及女性意識的覺醒。從“具身化”理論層面來看,這些深陷苦難的女性一系列的身體行為是她們對于欲望的意向性的表達,也是女性意識一種默會,而女性意識的覺醒也離不開身體運動實踐,因此女性主體要通過欲望的追求和身體實踐來建構女性意識。
參考文獻
[1]? ?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余華隨筆選[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
[2]? ? 余華.在細雨中呼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3]? ?劉釗.女性意識與女性文學批評[J].婦女研究論叢,2004(6).
[4]? ?王小波.再論女性意識與婦女解放[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00(4).
[5]? ? 魯迅.而已集[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9.
[6]? ?林華瑜.暗夜里的蹈冰者——余華小說的女性形象解讀[J].中國文學研究,2001(4).
[7]? ?王曉蕊.淺析余華小說中的女性形象[J].名家名作,2020(5).
[8]? ?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M].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責任編輯 夏? 波)
作者簡介:王麗婷,天水師范學院文學與文化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
基金項目:甘肅省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2021年度一般項目“非遺美育教育在高校的創新與實踐研究”(GS[2021]GHB1761);天水師范學院2022年研究生創新引導項目“文化資源化視角下非物質文化遺產池哥晝的保護與價值實現研究”(TYCX2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