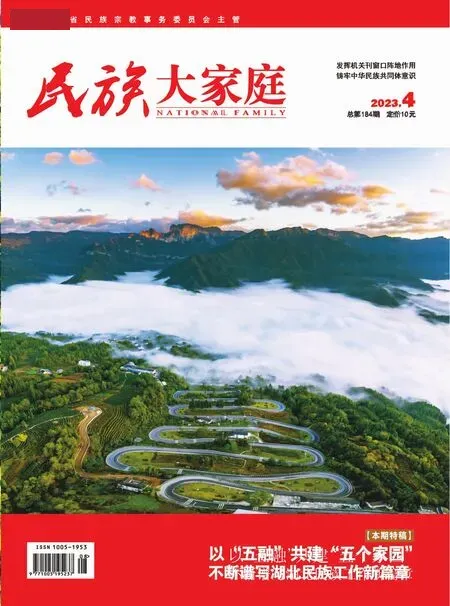容美土司與多民族的交往交流與交融
文/田小玲
跨越元、明、清三個朝代的容美土司(1310—1735 年)自明代伊始,秉承“以詩書為義方”的治司方略和“以詩書嚴課諸男”的家教理念,強化文化自覺,樹立文化自信,追求文化自強,不斷提升自身的文化實力、文化底蘊和文學藝術素養,從而以厚實的文化底氣、開放的胸襟和開明的氣魄,主動與多民族進行接觸,與多民族交往與交流,積極融入中原主流文化圈,融入華夏民族大家庭,不僅成就了一個連續6 代、誕生過10 位文人騷客、綿延近200 年的文學世家,也催生了一個在與中央王朝進行良性互動、與多民族進行友好交往交流與交融方面堪稱典范的土司族群。
以文化自覺尋求與多民族的交往
容美土司的文化自覺肇始于明代正德年間。一代中興司主田世爵倡導“以詩書為義方”的治司方略和“以詩書嚴課諸男”的家教主張,為讓宗室子弟知書識禮,深明大義,便“以詩書嚴課諸男;有不嗜者,叱與犬豕同食同系,以激辱之”,使其子輩“皆知書達理,通達有識”。長子田九霄、次子田九龍文武兼備,相繼成為土司首領;五子田九璋就讀國子監后任錦衣衛指揮;三子、七子、八子也各有所長,“不墜家聲”;六子田九齡博學多才,以詩馳名,有詩文20 卷刊行于世,成為容美土司田氏文學世家的鼻祖;孫子田宗文追慕大詩人屈原,成為田氏文學世家第二代的杰出詩人。自此,“武世家”田氏一族開始蛻變為“文世家”,連續六代詩人輩出,皆性耽書史,以詩名家。
容美田氏一族在踐行“以詩書嚴課諸男”的文化自覺理念,飽讀詩書與潛心詩歌創作的同時,十分重視與多民族進行廣泛接觸與友好交往,以詩會友,唱酬贈答,交游多民族文人士大夫。故此,嚴守升《田氏一家言·序》稱,容美田氏“集異書,產詞人,與天下諸名家唱和”。
容美土司早年與多民族進行交往的主要途徑有進京朝貢、奉調出征、求學拜師、出山訪游等,所涉及的交往對象有文壇翹楚、文學精英、文學同好以及將軍司馬、知府縣令、禪師道長各色人等。其主要交往對象如下。
文官。出于對漢文化與漢語言文學的崇尚,容美土司總會千方百計地尋覓機會,結識結交漢地漢室官員。因為這些官員多為詩人,田氏詩人們期望與他們締結文學情緣,成為文朋詩友。故而,一旦得知有漢地漢室官員升遷、調任或到任,田氏詩人們皆予以祝福,或前往送行,或前往迎接,或投詩唱酬。諸如得知周氏縣令與夷陵地方官殷都欲進京覲見皇上,田宗文即賦詩《華容周明府入覲》《奉送殷夷陵開美入覲》以贈;當聞聽長陽縣令陳氏奉調前往崇陽履職和高君翰前往貴州銅仁赴任,田九齡即賦《送陳長陽調武昌之崇陽》《送新安吳山人君翰之銅仁》,為之送行。即便是漢族漢室官員取道容美周邊地區,田氏詩人們也會尋求與其見上一面。譬如,當劉秉三前往云南主持科典試途經松滋時,田久齡即以《劉秉三民部典試云南過其舊治松滋賦贈十韻》相贈。
容美田氏詩人們還會適時地對仕途失意、遭受貶謫、離職賦閑乃至尋求隱逸的漢地漢室官員予以開導、安慰與接待,對落寞甚至落難者予以同情與慰藉。比如田宗文即有對艾和甫被謫往西寧深表同情的《艾和甫謫西寧有贈》等“為艾和甫賦”之《西寧曲八首》。
武將。容美土司憑借奉調參與抗倭、平叛、治亂等軍事行動,結識了眾多民族將士,并與之建立起友好關系。譬如田世爵、田九霄等在抗倭前線結識了總督胡宗憲。胡宗憲《籌海圖編》稱,容美士兵悍甲諸部;凡戰必捷,人莫敢攖。胡氏曾數次奏請朝廷將容美宣撫司晉升為宣慰司,以嘉獎容美士兵為抗倭立下的戰功。當田九霄所率容美抗倭士兵班師返家時,胡氏曾設宴、題詩為田九霄等餞行。
嘉靖年間抗倭時,田世爵、田九霄父子等與漢族將領伍文定等有過密切交往,并一同受到朝廷的嘉獎。此后,伍氏家族與田氏家族成為世交。明清易代之際,伍氏后裔即前往容美隱居避亂,時任司主田玄、田甘霖等熱情接納。
詩人。容美田氏首代詩人田九齡登臨荊楚詩壇之時,適值明代“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等著名文學流派叱咤文壇之際。由于這些文壇精英的活動陣地多位于荊楚大地,因而田九齡與“后七子”領袖王世貞、吳國倫和“公安派”領袖袁宏道,以及“后五子”之汪道昆、“末五子”之魏允中等結有文學情緣,并存有唱酬贈答之作。
此外,田九齡還與殷都、楊邦憲、周紹稷、孫斯億、王世懋等40 多位詩人有過唱酬寄贈之類的文學交往。田宗文與孫斯億、孫斯傳等荊楚湖湘的詩人文士也有眾多的唱和寄贈之作。
楊邦憲在《田子壽詩集·序》中稱,其“不佞從公車未上時,所日接君家兄弟之雅翰者甚伙”,意即楊氏在尚未中舉之前,與田九齡的兄弟有過交集,結有文學情緣,且雅翰(詩文)往來甚多。
名儒。秉承“以詩書為義方”“以詩書嚴課諸男”的文化自覺理念,一代中興司主田世爵除了親自“課子讀書”外,還“咸聘名儒”教授宗室子弟學習漢文漢語。司主田楚產開辦學宮,“置熟延師”,教授其宗室子弟及民間稚童讀史讀經。自此以后,容美土司一直沿襲“招名流”“聘名儒”教授宗室子弟“習文史”的傳統。
田世爵聘請湖湘名流孫斯億、孫斯傳擔任田九齡、田宗文等宗室子弟的文學啟蒙業師,帶領他們踏入荊楚文學圈。田九齡結識明代文壇領袖王世貞、吳國倫、袁宏道等,全仰仗于孫斯億引薦。
此后,田氏家族與孫氏家族即結為世交,其亦師亦友的文學情緣延續四五代之久。可以說,一代名儒孫斯億及其家族對于容美田氏文學世家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引領與助推作用。
以文化自信尋求與多民族的交流
明代天啟至清代康熙年間,容美田氏文學世家第四代、第五代詩人以空前絕后的壯觀景象登臨詩壇:一是出現了兄弟詩人(即第四代詩人田玄、田圭兩兄弟與第五代詩人田霈霖、田既霖、田甘霖、田商霖四兄弟),壯大了詩人群體,一改前三代詩人單槍匹馬獨立容美詩壇的情形;二是出現了司主詩人(田玄與田霈霖、田既霖、田甘霖父子四人均擔任過司主之職),借助其司主身份進一步擴大了文學交流圈與影響力;三是兩代詩人創作成果突出,人人有詩集刊行于世,將其文學世家之詩歌創作推向了巔峰。容美土司因而更有與多民族進行文化交往與文學交流的底氣與自信。
此間,適逢明清易代之時,藏于武陵深山的容美成為荊楚湖湘文人士子神往之地,眾多明代遺老遺少、紳縉名流紛紛避居容美,使容美宛若世外桃源,群賢畢至,人文輳集。這便為容美土司提供了與多民族人士近距離交往交流的契機,使得容美田氏家族與多民族人士共同棲居于同一片藍天之下、同一方山水之中,形成了和諧相處、平等交流的多民族交融景象。此間,其交流之對象如下。
避居之遺臣。田玄主政容美之時,正值流寇橫行中原、明清易代之際。其時,“雖烽煙四逼,獨容美一區稱為樂土者,比之桃源武陵,良不虛也……時明賢如夷陵文相國、黃太史、松滋伍計步,及歸州、公安士大夫數十輩,挈家聚族而依附于公(田玄)……公(田玄)皆官養,始終無倦”。其遺臣遺老如明太史文安之、嚴守升、黃中漢等為躲避戰亂,皆遁入山林,寄居容美,而田玄、田沛霖父子“皆官養”之。
詩人文安之先為明太史,后系南明首輔。遭遇“甲申之變”時,文安之寄居容美十多年。同為明王朝遺臣遺民的田玄、田霈霖、田既霖、田甘霖父子與文安之,常常以詩酒消愁,慷慨悲歌,抒發懷念故國舊主之情思——“一唱三和皆國愁”,“手疏頻頻計國事”。
故交之后人。嚴守升《容美宣慰使田玄世家》稱,明清鼎革之時,“容美一隅地,如異世江左,人文輳集,避地者咸以為歸;一時明賢如夷陵文相國、黃太史、松滋伍計步,及歸州、公安士大夫數十輩,挈家聚族而依附于公(田玄);館榖不暇給,旁及華陽光澤諸藩,如華容孫中丞等輩”。嚴守升在此提及的華容孫中丞乃田九齡、田宗文的文學業師與文學領路人孫斯億家族中人。孫氏家族的晚生后輩孫谷(1607 年進士)也曾前往容美避亂,受到田玄、田霈霖等的盛情款待。
此間,田玄、田霈霖父子還熱情接納過伍起宗及其家族。早年,伍起宗之先輩伍文定與田世爵、田九霄父子結識于抗倭戰場。后來,伍氏后輩伍騭為感謝田氏家族在明清易代之時收留其父,讓其寄居容美30 年,“父事”(待之如父)田甘霖(田玄之子)30 年。當伍騭老邁時,田甘霖之子田舜年則令其子輩“父事”伍騭,一時傳為佳話。
寄寓之詩人。嚴守升《容美宣慰使田沛霖世家》稱,明清鼎革之時,“各紳縉人士、公子王孫之流避地容美,不可勝數……公(田沛霖)供以館榖……以致客至如歸,殊忘流離之苦”。
嚴守升在其《田信夫詩集·序》中記述明太史文安之、明太史黃中含等詩人寓居容美期間,視容美如梁園,詩酒娛情、樂不思蜀的情形:“丁亂后,南郡避兵,望而投止。鐵庵文太史、中含黃太史籍館谷,暨吾友令宗伯珩、月鹿諸君子,團欒一時,痛飲河朔,分題限韻,仿佛梁園佳事。”
田甘霖《和荊艷史詩·引文》記述了田氏詩人時年與寄寓容美的文安之等詩人“分題賦詩”的情形:“荊州費尚書制艷詩20 題。夷陵文相國、萊陽王暗子每題賦七言八句;囑嚴守升先生和,先生以題有‘荊’字,故作荊人語。予(田甘霖)以己意和其詩。不必屬艷于荊也,聊以消詠日爾。”
以文化自強尋求與多民族的交融
容美土司秉承“以詩書為義方”“以詩書嚴課諸男”的文化自覺理念,在康熙年間基本實現了文化自強,一躍成為南方土司族群中的佼佼者。在政治榮耀方面,司主田舜年破例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見,成為南方土司首領覲見天子的第一人;在經濟實力方面,容美成了楚蜀諸土司中最為富強者,曾受到雍正皇帝的御贊。
田舜年主政容美期間,憑借頗為雄厚的經濟實力、良好的社會秩序、禮賢好客的交游美譽、吟詩賦文與觀戲聽曲的風雅逸趣,以及容美獨特的山光水色,吸引中原大地的“華國鳳麟”、文人雅士、商賈技工紛紛進入山中,云集容美,視容美如“梁園”,樂不思蜀,使容美出現人文薈萃,文風鼎盛,多民族和諧相處、其樂融融的祥和景象。此間,田舜年將容美土司的文化交往與文學交流推向民族交融的歷史高度。
詩賦文化領域呈現的交融。明清易代之后,明太史嚴守升避居容美多年。嚴氏曾為容美田氏存史立傳,撰寫了《容美土司田氏世家》,編修了《容美田氏族譜》,梳理并厘清了容美土司發展壯大的歷史源流以及田氏家族的世系脈絡,記述了執掌容美軍政大權長達400 余年的田氏家族的文韜武略與文治武功。作為詩人,嚴氏還參與編纂田氏世家詩歌總集《田氏一家言》,審讀了《田氏一家言》的全部詩稿,并為《田氏一家言》撰寫序文和評語。嚴氏稱,田氏“詩文冠絕古今,卷帙盈笥,燦然如萬花谷”。
《田氏一家言》問世后,旋即“引來巴楚名士爭相傳閱”。1704 年,江南詩人、劇作家兼旅行家顧彩慕名訪游容美,寫下3 萬余字的《容美紀游》。《容美紀游》對容美土司在詩賦文化方面與多民族交流與交融情形記述頗多,諸如每月初二、十六為容美例行的“詩會日”,“風雨無廢”;每逢詩會日,容美土司“刑政皆輟”,凡司中文人悉數出席;田氏宗室子孫孩童也一并參加,“不能詩者,則課文一首”。顧彩稱,詩會上田舜年“成詩最敏,客皆莫及”。
除了每月的兩次例行詩會外,顧彩、田舜年還以“宴集賦詩”“分韻賦詩”“詩牌集字”“酬答唱和”等形式,邀約寄居容美的詩人們進行詩歌藝術交流。《容美紀游》稱,其“分韻賦詩”形式最受容美詩人們歡迎。
與此同時,田舜年與顧彩常常一邊游覽容美山水風光,一邊尋章覓句、吟詩賦詞,“日以詩相唱酬”;有時在深夜里還“隔山唱和”,由仆人翻山越嶺來回傳遞詩稿。
戲劇文化領域呈現的交融。容美田氏既是文學世家,也是戲劇世家。明代田氏詩人即有描述容美戲劇藝術繁盛情形的詩句:“一劇二劇三四劇,板腔不必循規矩。”及至田舜年、田炳如父子主政時期,容美的戲劇藝術可謂繁榮至極:擁有兩個戲班;“女優皆十七八好女郎,聲色皆佳”;吳腔、楚調、秦腔、巴曲多種聲腔同臺演繹;其演劇水準“即在全楚亦稱上駟”;戲樓、戲廳、戲園、戲臺幾乎遍布全境;“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且演得“旖旎可賞”。
容美土司與多民族在戲劇藝術創作方面進行交流與交融的典型案例是與劇作家顧彩共同排演《桃花扇》《南桃花扇》。《容美紀游》記述表明,在顧彩逗留容美的135 天中,田舜年、田炳如父子與之進行文學藝術交流與戲劇藝術交流的時間將近各占一半;其中,其共同排演昆曲《桃花扇》用了30 天時間,排演巴曲(容美本土曲種)《南桃花扇》用了40 天時間。因為《南桃花扇》屬于新排劇,所以費時較多。從容美土司為《桃花扇》舉行極為隆重(連演三日,為觀眾免費提供餐飲)的公演儀式來看,田舜年、田炳如父子及其戲班與顧彩的合作與交流是極為成功的,也是愉快的,以致顧彩離開容美的前夜,容美戲班演員特地攜酒到其下榻處為之餞行,相擁而泣,難舍難分。
作為劇作家,顧彩千里迢迢訪游容美的動因是,他從孔尚任處得知容美土司戲班搬演過《桃花扇》,期望田舜年幫助他把《南桃花扇》搬上舞臺,了卻他在中原大地無法實現的心愿(當時《桃花扇》遭禁演)。容美之行雖艱辛無比,但田舜年、田炳如父子及其戲班助力顧彩實現了其人生宏愿。故而,顧彩離開容美后,特賦詩《云來莊觀女優演余〈南桃花扇〉新劇》記述了《南桃花扇》成功上演之事,并以《容美紀游》為容美土司記述了他與多民族交往交流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