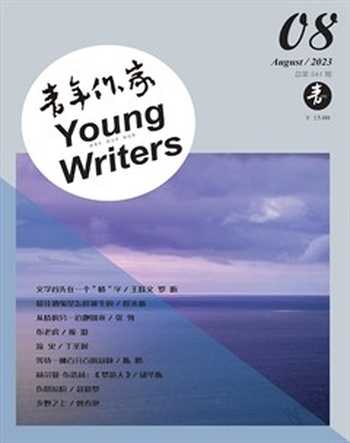井

我是在公交車站邊上碰見他的,那時他正蹲在花壇下,一只手環抱膝蓋,另外一只手垂下來,時不時抽煙。我也想抽,但是把火弄丟了,附近沒商店。我走過去,問他 :“兄弟,有火嗎?”
他抬頭看了我一眼,又四處摸了摸口袋,最后茫然地把手里的香煙遞給我。
“我的火找不見了。”
用他的煙,把我的點著了。為答謝他,我給他遞過去一根,他擺手拒絕。我把煙放進褲兜里,學他一樣,蹲在花壇前,有一口沒一口地吸。
“你是本地的?”他問。
“不是,外地的,從南方過來,剛到北邊。”我說。
“我也不是。”他又問我:“你來干嘛?”
“來看看老婆,她在這里的玩具廠上班。”
“那沒錯了,前面就有一家玩具廠。”他說。
懸著的大石頭,終于放了下來。我是悄悄來北方的,一路坐火車,又倒騰轉了好幾輛公交,才到這鬼地方,碰見他時,天已經黑透。我不知道老婆的具體地點,她從來沒對我說過,只說了一個大概的位置。
過幾天,是她的生日,我特地來,為的是給她一個驚喜。假如能找到她,她一定會很開心,盡管我們已經很久不說話了。
之所以如此,一定是我的問題,我對她的關懷不夠。我想著,要好好給她過個生日,改變我和她的相處模式。我都想好了,也給她買玫瑰花、買禮物。她一直想買一對黃金耳釘,上面是她的生肖圖案,去年沒給她買。來找她前,我挨家金店去看,挑挑選選,咬著后槽牙買上了,現在它正躺在兜里。
“玩具廠在那邊,你還不去?”他側過臉問我,手指著一個方向給我看。
我沒看他指的地方,而是看著他臉上的傷,從淤青判斷,一定是被人打的,像他這樣的年紀,很容易與人打架。
“我老婆晚班,等天亮后再過去。到時,門一開,一兩百個女工涌出來,她們從我身邊走過,把我擠過來擠過去,但是,她剛出現,我就一把抓住她的胳膊。你說,她會感動嗎?”
“沒這種情況,那兒哪里稱得上是玩具廠,就是幾個閑得沒事兒干的老太太搞的作坊。”他嘿嘿一笑。
我也是信口一說,就算真有一兩百個女工,我也不會那樣做。首先我沒有把握能認出她來,那么多人,穿得一模一樣,我不能保證可以一眼看見她。而且,我害怕抓住她時,她太驚慌了,一不留神撞在鐵絲網上。我發現這里的馬路邊上就有鐵絲網,是別人家安的防盜窗,凸出馬路了。
所以現在這樣的情況還不錯,我可以很快認出她,她在老太太中間是很顯眼的。其實也不算好,因為這樣浪漫的程度就衰減了,為了彌補,只有等天亮后,找一家玫瑰花店。買一捧玫瑰,要三十三朵,剛好是她的年紀,雖然她會罵我奢侈,不懂浪漫卻裝浪漫,不過只要她開心,也值了。
“你呢?在這里干嘛?”
在地上蹲了會兒,腿麻,實在受不了,我退回來,坐在花壇邊緣。不遠處是公交車站,有人下,有人上,他們從身邊走過,偶爾回頭看一眼,也不知看的是個什么名堂。
“我等人。”他的煙燒完了,順手把煙蒂彈進垃圾桶里,好利落。
“你等的人要坐公交車來?”
“不是,她是在按摩店上班的,我等她。”他把腦袋埋進兩腿中間。
這下,我對他的印象更不好了。我知道,有一些年輕人不愿意掙錢,叫老婆進按摩店工作。快到下班時間,騎著摩托車,接老婆下班。看他這個樣子,恐怕連一輛摩托車都沒有。這樣的男人挺窩囊的,我猜測他的傷是被客人打的,接老婆途中,看見老婆和別人故作親密,心里不是滋味。雖然他讓老婆這么做,但眼不見心不煩,然而親眼見到,情況就不一樣了。
他跑過去,對他的老婆說陰陽怪氣的話,客人看不下去,揍他一頓,如果不是老婆攔著,他的臉早就被打壞了。
回到家,他沒少罵老婆,毫無顧忌。她委屈巴巴地說:“是你讓我去的。”
對于她的辯解,他充耳不聞,甚至激發了怒火。老婆雖然是為家里掙錢,但他卻接受不了。在街上看到的是一副什么光景?都快吊在別人的脖子上了。
老婆解釋說,這是維護客戶關系,不這樣下次沒人點,沒人點,就掙不到錢。無論她怎么說,他都不聽。老婆對他講:“那么,再也不去了。”當時他點頭首肯,結果沒錢用,又求著老婆去。然后又繼續糾纏,一直沒個盡頭。估摸著,她得到四十多歲,靠化妝術也遮掩不住年齡的痕跡時,才會收手。到時,這個男人恐怕也得離她而去。
想著這些可能的事實,我對他唾棄不止。為了驗證自己說的話,我問他:“你結婚了嗎?”
“結了,前年結的,孩子都一歲多了。”
對,就是這樣,我難免加以蔑視。
“你等的人,是你老婆?”我追問。
他腿也麻了,往后退,坐在花壇上,我的右手邊。他還看了我一眼,故意往下坐了坐,看上去和我一樣高。
“不是,我老婆在南方城市。”
那是我誤會他了,他在等別的女人。看來他的情況和我差不多,和老婆分居兩地,一年也見不到幾次面。在外面,總需要排遣寂寞,我是能夠理解他的。這么想,對他又親近了些,反而還添上愧疚,不該惡意地去揣測他,在心里污蔑他。我掏出煙給他,這下他沒拒絕。不過剛才的火被我們弄滅了,沒法抽。他把煙夾在了耳朵上,他的兩只手垂于雙膝。
“你老婆干嘛的?”
他坦率地回答:“也是在按摩店里工作。”
有風在吹,他掖了下外套。空中楊柳絮飛來飛去,像下雪,路燈照著的地方,看見楊柳絮滾作一團,形成了一個旋渦,這時,他站起來,踩在旋渦里。旋渦碎掉,他又坐在我的邊上。
剛才我對他的歉意消失了,呵!沒什么兩樣。在北方的按摩店和在南方的按摩店,沒什么本質的區別。
“你經常去按摩店嗎?”我問他,我從來沒去過。我不去的原因,是害怕花錢。每次我爸打電話,都是找我要錢,一看到來電顯示,便尤其煩躁,只要有電話,就意味著一個接著一個的麻煩,這些麻煩讓我抓耳撓腮,后悔當人。
我爸要么講小寶的病,小寶又嚴重了。小寶得了肺結核,不是像感冒那樣的小病;要么就講老丈人快不行了,從老丈人摔倒后,一直是一副快死的樣子。有時候我在想,我要是有一個兄弟就好了,他起碼能分擔我一部分壓力。后轉念一想,兄弟未必能幫忙,我認識的不少人家里都有兄弟,最后卻變成了仇人,兩家人拿著棍棒,打成一團。
“我只去過一次。”他看向我,“你如果要去的話,前面有一條巷子,里面全是,有十多家,價格不算貴。”
他指給我看,天太黑,茫茫一指,我沒看見。
“就在玩具廠附近,你可以先去,等天亮了,接你的老婆。兩件事都一起辦了,也挺不錯的。”他補充了一句。
我沒答話,這時風又吹起來了,有點冷。今天晚上去哪里睡,是個問題。夏天隨便找個地方就好,而冬天太冷,凍得慌,像刀子似的割人。
“你要等她多久?”
他說:“我不知道,沒個數,有時候早,有時候晚。不過,都在十二點前。”
“我也沒事,離天亮還早,跟你一塊等吧!”我說。其實我想看看按摩店里的女人是什么樣,應該很漂亮才對,應該比我老婆漂亮。
我和我的老婆是同學,本來她看不上我。那時,她已經跟別的人戀愛了,身邊還有追求者,一個男學生和她的男朋友為了爭奪她而大打出手,還動了刀子,男朋友挨了三刀,傷到了大動脈,送到醫院時,人就已經死了。
她當時的男朋友來歷不小,舅舅是縣里的刑警大隊長,當天就抓到了嫌疑人。嫌疑人殺了人就跑,把將近一米長的刀子藏在花壇底下,人躲在另外一個同學家里。抓住他時,他正光著上半身睡午覺。那時,他睡眼惺忪,還不知道自己殺了人,以為只是給人造成了皮外傷。
我老婆當時在學校出了名,誰都知道因為她死了人,她在學校免不了被人指指點點,承受不住壓力,輟學回家。恰好我學習很差,也從學校里滾蛋了,我和她都去廣東上班,也有了加深溝通的機會。
“隨便。”針對我的提議,他只說了兩個字。
有人過來了,是一個男人,長得很胖,肚子腆著。他走到我們面前,粗聲粗氣問:“哥們兒,有煙嗎?”
“有。”我從盒里抖出來一根,遞給他。
他接上,追著說:“再來一根,我們是兩個人。”
我不樂意了,你們兩個人跟我有什么關系?我沒理他,把煙放回去,先是放進了裝禮物的兜里,又拿出來,換另外一個兜。他等了一會兒,看沒有再給的意思,便悻悻走掉,還回頭瞪了我一眼。果不其然,不知道從哪里冒出來一個人,站在他的邊上,跟他并排走。他們在路燈下站了會兒,又到了公交車站邊上。再看時,人沒了。
“你不給人煙是對的。”那兩個人走開后,他對我講。
我問:“怎么說?”
“這兩個人總在路上找別人要煙。”
兩個人每天都在這條路上要煙,真是不知道是什么來路。
我們又聊了一些別的什么,最后他說:“那天按摩時,我醉了。”
“是嗎?”
“嗯。”他輕描淡寫地點頭。
我說:“喝了多少酒?”
“都說我是喝酒喝醉的,其實不是,我是抽煙抽醉的。那天是小寶生日,他帶我去喝酒,喝完了,一點事沒有,我們坐出租車去按摩店,車沒來之前,抽了煙,抽第一根的時候,就有點不對勁,第二根抽完,想嘔吐,頭暈。”
“你朋友跟我兒子一個名字。”我說。
他好奇地看我:“是嗎?”
我對他說:“我的兒子也叫小寶,你接著講吧!”
“然后我們等到車了,是小寶扶我上的出租車。他把我帶到了按摩店,讓我躺在床上,你知道,就是那種單人床,頭頂有一個洞,讓人把腦袋埋在上面。這個設計是不是針對醉鬼的?下面再設置一個馬桶,可以一邊吐,一邊做按摩,還不會弄臟房間。”
“這我就不清楚了,你還去過一次,我一次都沒去過。”我說。
興許也是讓人呼吸的,不能讓人捂著出不來氣。
“結束后是小寶結的賬。后面我們才知道吃了虧,就不能問出租車司機,司機和他們是一伙兒的,沒有經驗的人就是他們下手的對象。
“小寶問我,你那個還行嗎?我這個很有姿色。我告訴小寶,我這個也不錯。實際上是我瞎說的,我暈乎乎的,看不清人的臉。小寶完事后來找我,我拔了火罐,躺在床上睡著了。”
“聽你這么說,我覺得你們吃虧了。”想想那三千塊錢,我都替他的朋友肉疼,三千塊錢不是小數目,在工地上干小工,得干十天。
“誰知道。”他不想提錢的事兒。
“當時挺煩的,她說她的兒子檢查出了肺結核,她的兒子和我有什么關系?我花了錢,不是來聽她講故事的。她又告訴我,說我長得瘦,臉顯小,一看就知道才二十出頭。
“她告訴我,她還不到二十歲,就嫁了人。她說到這里的時候,我想到了自己,因為我也是十八歲結的婚,在我們老家這算晚婚。我的老婆在南方,說不定我按摩的時候,她正在給別的男人按摩。所以我哭了,當著她的面。”
他又窸窣地摸,最后在屁股后面找到了打火機。他給我點了,但沒抽幾口,我停了下來。
“對不起,剛才彈煙,勁用大了,煙彈滅了。”我打斷他,他把火遞給我,風太大,我背過身去,用手半捂著擋風,點了三次才點燃。
話被攔腰斬斷,續上再也沒那么容易。我們沉默以對,目光看著街道,人越來越少,偶爾有車開過去。一輛公交車從遠處駛過來,泊到近處,下了兩個人,又開走。還是兩個男人,他們站在公交站牌前,偶爾看我們兩眼,不知道他們想干些什么。只看得見兩個人在說話。
大晚上的,我只穿了兩件衣服,里面一件短袖,外面是薄外套,冷得發抖。那兩個人也一定發現了我的異樣,隔得遠遠的,總覺得他們在奚落我,笑話我。
“你怎么了?一直在抖。”身邊的他問。
“想起做過的一個夢,挺古怪的。”我胡亂說。
“什么樣的夢?”
“有一個人在荒郊野外游蕩,一不小心掉進井里,井起碼四五米高,壁面光滑,是水泥做的,根本抓不到,爬也無法爬上去。井里面只有一人多寬,掉下去的那個人,只能在里面轉身,根本沒法活動。”
“然后呢?”
“他焦灼不安,一抬頭,僅能看得見碗大的光斑。他大聲呼救,估計沒人聽得見,知道他的絕望嗎?他用手刨水泥,弄得一身傷,掉下來的時候,說不定小腿骨折了,可他必須在那里站著,沒有辦法換別的姿勢。
“他悲傷地想到,恐怕得死在這里,連死都要站著死,死掉了,也得以一個不舒服的姿勢杵在那里,真他媽憋屈。他決定再喊三聲,三聲之后沒人來救自己,就安安心心等死。第一聲,沒人搭理;第二聲,音量變弱;他喊最后一聲,已然知道結局如何。第三聲喊出去時,他就失望了。但倏地,他發現頭頂上的光被擋住了。
“‘嘿,有人嗎?他抓到了救命稻草,興奮地喊起來。
“‘有人,你怎么了?我剛聽見你在喊。一個人回應他。
“‘我掉進井里了。他抓住了希望。
“‘嗯,我知道了。上面的男人說。
“接著,光又亮起來,井里的人知道,這位好心人走開了,他肯定在想辦法,要么給消防隊打電話,要么在找繩子,總之,馬上會來救他。突然,光斑又消失,他聽見摩擦的聲音,像重物在地面之上挪動,‘轟地一聲,他什么都看不見了。”
我告訴他,井上的那位是個徹底的混蛋,枉顧人的性命,玩起了惡作劇——搬來井蓋后,把井封住,人走了。
他問我:“這個夢真是夠古怪的,被蓋住的那個人就是你吧?”
“哈哈哈,你真猜著了,如果不是我本人的話,對人的心理不會了解得這么清楚。”我贊許地對他說,實際上我依舊對他不屑一顧。
關于惡作劇,我能想起來的,那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支使一個和我一般大的孩子爬柚子樹,他下來時,把腳卡在了柚子樹的分叉里。他被卡得哇哇大哭,我可受不了別人哭,真鬧心,轉頭一個人跑回了家。他的母親見他不回來,跑過來問我,我說了謊話,我告訴他的母親,整個下午我都沒有看見過他。等第二天,他們家人才找到他,他一個人待了一個晚上,面色如紙,身上全是露水。
當時我并不覺得自己犯了錯誤,直到他被情敵用刀砍死后,我才為往日的行為感到后悔,不該那么對他。
那兩個人還沒走,偶爾別過頭看我們。他把耳朵上的煙取下來,放在嘴上,點燃,又拿下,塞進我的嘴里。正好,我很需要,用力吸了一口,讓它進去得更深一些,煙霧從鼻子里出來時,感覺好多了。
又一輛公交車過來,那兩人鉆進去消失了。真不知道今天晚上,他們在搞什么名堂。
他又講起來了。
“她把手指插進我的頭發里,摸我的腦袋,或者捏捏我的背,把手放在背上,說你真瘦,摸著全是骨頭,一點肉都沒有。得多吃飯,有肉,才有力氣。你知道那種感覺嗎?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這種話了,就像陽光曬在稻草上,曬熱了,人剛好躺上去。
“過后,她沒少說話,講她的故鄉。以前他們家境況不錯,爸爸是木工,他們家是最早修紅磚房的,爸爸給別人干活,不小心從樓上摔下來了,然后就不行了。她還有一個妹妹,才十六歲就有不少人上門提親,人不能不讀書,要是不上學,恐怕就得長期陷下去了。
“她也說她的老公,她和她男人經常不見面,一年也就回家見那么幾天。但是不說話,兩個人在一塊兒,什么話也不想說。不是覺得煩,而是沒有感情,生分。這種生分最讓人可怕了,一點意思也沒有。
“她講著講著,我睡著了。是小寶把我叫醒的,那時,頭不暈了。結了賬離開,我也不知道她是誰。”
“后來你怎么知道的?”我問。
“本想著再進去一次,沒那么多錢,普通按摩也得花幾百塊,而且她們最會哄人,會想盡辦法讓你掏錢。所以我只好在外面等她,等她下班。我沒見過她,但知道她長什么樣,是不是聽上去怪怪的?”
“多少有點!”我附和道。
“然后,我等到她了,她沖我善意地笑,我問她,愿不愿意讓我送她回家。我猜,她會害怕,一個男人,等著她,說要送她回家,沒有不害怕的,會擔心是歹徒。但她答應了,她說,她認識我,上次我像個孩子一樣號啕大哭。我醉了,沒看過她的臉,她卻看清楚了我。”
“所以,你每次都送她回家?”我問。
“是,從那天開始后,我每天都送。這不,她讓我在這里等。她住得挺遠的,離這里有好幾公里,平時下班都是騎自行車。但冬天不騎,太冷,還不如走路呢。每次都是由我送她,走路的時間就更長了。送她回去后,我就回廠里。等天亮后,再回去干活兒。雖然很累,但是我很高興。
“在路上,她會跟我講碰見的客人,她引誘客人花更多的錢,通常是撩撥他們,大多數人承受不住。但有的客人就是頑固,都想得到更多,但誰也不想多掏幾個子兒。有一回碰上了一個自稱是導演的男人,他死活不上當,她都快哭著求別人了,但人還是不答應。人還教育她,做服務就好好做服務,別打歪腦筋。
“她還說,希望我發大財,然后每次都點她。不光點她,還給她送禮物,送她生肖樣式的金耳環,她想買,但舍不得。”
我問:“然后呢?”
“她有回問我,如果有錢了,是不是就忘了她?”
“那你怎么回答她的?”我很好奇,不知他會怎么說。
“吶!就告訴她,我根本不會有錢的,這是特別老實的話,我不騙人。她先是很生氣,我不會安慰人,沒有再搭理她,想著哭會兒就好了。過了一陣,她不生氣了。”
聽他講這些,我又想起了做過的那個夢。井里的人,該怎么辦。在瀕死之前,怎樣度過那段時光,估計難挨得很。我想象自己被關在井下,簡直太倒霉了,恐懼感鋪天蓋地而來,遮天蔽日,可是一點辦法都不會有。
不知怎的,我現在愈發不安,關于井的故事始終縈繞在腦子里。我站起來,活動活動筋骨,不讓自己胡思亂想。在黑夜里,我聽見了時間的嘀嗒聲,想離開這里,趕緊走,越快越好。
我給自己找了一個理由:“我得走了,找一個地方住,要不然明天沒精神。”
“都等了這么久,你不再等一下?她馬上就要來了,看見那輛車了嗎?我感覺她跟在車后,車一消失,她自然出現了。”
是的,有一輛車來了,車燈鋪成了兩條光路,又往前延伸,晃到了我們的眼睛。
“等不及了,我先前是騙你的。”
“什么?”他問。
我對他說,關于井的那件事兒,不是夢,是真實發生的事件。來這里的路上,我碰巧從廢墟經過,我聽見有人喊叫,然后跑過去看,有一個人失足掉進井里,井下的人和我說話。
然后,我看到邊上有井蓋,我以為井下的人是讓我幫他把井蓋蓋上,干完這件事,一想到幫助了他人,便莫名地驕傲。然后我拍拍手走了,得去找老婆,在玩具廠附近等她下班回宿舍。剛靈光一閃,才恍然大悟,原來井下的人不是讓我蓋井蓋,而是讓我救他,我得回去看看,看這個井下的人是不是還活著。
他瞪大了眼睛,根本沒有想到情況如此復雜,看得出來,他也為那個井下的人而擔心。
和他打完招呼,我便走了。走之前,手一掏又一揮,把兜里的盒子扔向了他,他眼力不錯,濃濃黑夜卻看得清楚,手力也不錯,身子一歪,接住了。我想,當他把禮物送給按摩女郎時,她一定會很高興。他沒跟我道謝,也可能道謝過,但風太大,我沒聽見!
【作者簡介】廠刀,1995年生于重慶奉節, 2022年開始發表小說,有小說見于《江南》《青年文學》《長城》《安徽文學》《福建文學》《西部》《湖南文學》等刊;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