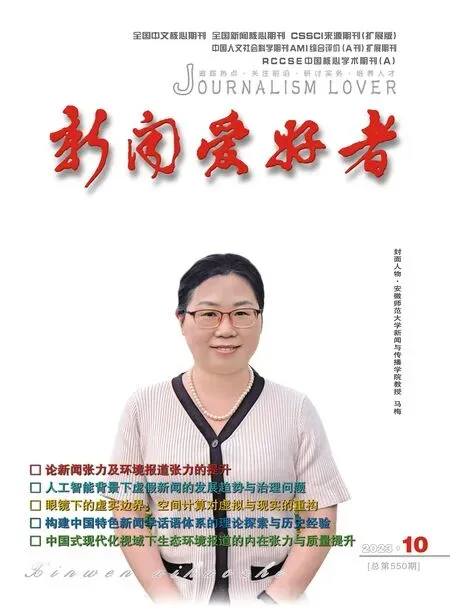眼鏡下的虛實邊界:空間計算對虛擬與現實的重構
□郭全中 黃澤晶
普通的眼鏡對人的意義與耳機、手機等不同。后兩者通常給人傳遞新的信息,例如人用手機搜尋信息、用耳機接聽信息等,而眼鏡通常具有過濾信息、美化信息、明確信息的特點。對于需要用眼鏡矯正視力的人來說,眼鏡是生活的必需品,只要開始接觸信息,就需要穿戴。進入智能傳播時代,穿戴式設備的更新換代層出不窮,眼鏡也成為穿戴式設備更新的重點。蘋果Vision Pro一經推出,在科技領域、技術領域、傳播領域都有劇烈反響,并且褒貶不一。但透過穿戴式眼鏡設備的次次創新,以及透過其背后空間計算的技術底色,我們可從很多方面進行思考。
在視覺傳播領域,VR、AR等技術主要通過感官仿真,將用戶從現實帶入虛擬。源于信息技術革新浪潮的VR技術受到可穿戴設備信息可視化等技術的共同作用,是一種創建場景和體驗的仿真系統。在這樣的系統當中,眼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視覺觀感效果的不斷探索過程當中,眼鏡文化逐漸興起。而佩戴了穿戴式眼鏡之后,信息與人眼之間便多了一重中介,這一中介的效果對真實世界是否為完全鏡像的映照,這里真實與虛擬的邊界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
一、認識論:虛實邊界的再討論
關于真實的討論一直是新聞傳播學科的 “元問題”。[1]當人不再是傳播的主體,而以新技術為依托,以非人類實體融入實踐,真實與虛擬的界限變得愈加模糊。行業的“液態化”、技術的“智能化”和人的“媒介化”等新特征,使真實的評價體系更加多元,使得真實可觸性更強,同時也模糊了真實與虛擬、理性與感性的邊界。邊界的模糊會帶來原有規律的變動,人對外界的認知會因為規律的變動而在短時間內被遮蔽,同時也會動搖人本身對原有媒介過濾后的真實的信賴。眼鏡式虛擬現實工具的不斷發展,不僅改變了人與技術的關系、人與媒介的互動方式,也反映了真實問題因技術因素的輻射而顯示出的新的哲思。
(一)融媒環境下關于真實性的討論
在對真實的多重認知中,主要存在三種真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真實”、經過媒介過濾和加工的 “擬態環境”和經過了人的主觀意志加工的“主觀真實”。[2]真實可以被再現,但再現是否等價,受制于中介條件。個體對真實世界的認知難以脫離媒介對于社會的建構和展示,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沒有一種媒介不帶有本身的立場而一直保持中立。
同時,人依靠視覺對客觀世界獲得主觀認知,視覺是人最直觀的感受世界的方式,也是最具備真實性和說服力的感官。照片將動態固定,使真實變得可控;影像將世界鏡面呈現,使真實突破時空的限制;直播技術的使用,使得真實變得即時。但無論哪一種真實,都難以觸及,因此還是帶有一定的距離。甚至直播過程中,也可以因為AI技術的使用而變得可操縱,變得不真實。而類似于蘋果Vision pro一類的頭戴式眼鏡設備的使用,使得真實既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也變得即時又可觸。
(二)新技術語境下的真實性與真實感
真實是人提出的概念,雖然真實客觀存在,但如何評判真實仍然由人作出判斷。在傳統的新聞敘事中,真實性需要判斷,真實感卻可以塑造[3]。而AR、VR等技術運用到報道或敘事當中來時,是在真實性的基礎上增強了真實感;元宇宙技術是在真實的世界中創造了一個虛擬的世界,而在虛擬的空間中讓人感受到真實。因此,這里的真實感并非是真實的加強,而是真實的塑造。
空間計算則融合了上述兩種情況。從蘋果頭顯的使用效果來看,空間計算讓真實的世界更“便捷”,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增強了肉眼對細節觀察的精度;二是通過手眼結合的肢體動作,達到脫離設備而僅靠動作完成指令的效果。此時,空間計算不僅增強了真實,還塑造了新的真實。從報道到觀看,到體驗,再到沉浸,這是新技術發展下對于真實世界展現的方式,空間計算技術所帶來的知覺的真實性突破,也沖擊著越來越模糊的虛實邊界。
(三)頭顯設備下真實感的逆轉
在新聞報道中,新聞真實被視作某種系統,一種將局部和整體視為統一運轉的系統。[4]關于局部真實和整體真實,一直多有討論。空間計算與元宇宙的區別就在于模糊了人對整體真實與局部真實的感知。在元宇宙技術背景下,虛擬的空間是被真實地標記的,相當于創造了另一個平行世界;而在戴上頭顯設備后,用戶進入了眼鏡建構的真實世界,這一真實對于用戶的視野來說是整體,但對于真實客觀世界來說只是局部。
對于整體和局部的模糊可能會造成對真實評價的逆轉。這里我們討論兩種可能性:一種是脫離眼鏡后,用戶進入整體真實的環境中,可能出現對于真實世界的不適應性。因為在頭顯設備中,用戶享受了更為便捷的“真實世界”形態;另一種是對客觀真實世界的局部更為敏銳,這也意味著當下一次用戶進入頭顯世界中時,甚至覺得頭顯設備中的世界即使使用了高清顯示屏,仍然覺得“失真”。因此,以空間計算為技術核心的頭顯設備究竟打破了虛實邊界,還是讓虛實邊界更為明晰,需要分情況討論。
二、方法論:媒介呈現影響虛實邊界
真實性始終是虛實邊界的元命題,而這一邊界的模糊與明晰和認知、技術、情感分割不開。眼鏡式穿戴設備不斷研發運用體現了人對真實性的追求中視覺感官的重要程度;空間計算賦予了視覺文化下對真實的追求,而與此同時,我們并不能忽視此種情況下,媒介呈現本身的立場給人的情感帶來的影響。同時,眼鏡式設備也并非只關注視覺這個單一感官,多感官的調動帶來的沉浸效果亦值得我們關注。
(一)眼鏡式穿戴設備帶來的虛實革命
賽博格來源于20世紀60年代,它強調的是一種人和機器共生耦合的新生命體。或者說,賽博格是一種后人類的象征,人機共生逐漸成為人們與賽博格的不斷深化發展中不斷提到的概念。[5]隨著智能化設備的不斷發展,設備成為某種器官既是隱喻,也是現實。而智能眼鏡作為最典型的視覺感官類別的穿戴式設備,進入到賽博格實踐當中有其必然邏輯和文化需求。
現實客體相對于認識主體之間的空間關系、形態觸覺都是真實的存在,而主體會基于生理特性對客體進行觀察和視覺成像感知。對視覺真實的追求和探索促進了眼鏡文化的興起,眼鏡的可穿戴特征也賦予了穿戴者對本身身體和形象的賦權。[6]眼鏡矯正了穿戴者對真實的認知,而眼鏡技術對視覺的干預也愈加明顯。從VR眼鏡到空間計算技術下蘋果頭顯設備的演變中,穿戴者進入眼鏡后的世界并產生真實性認知的時間不斷縮短,人機一體有了具體的寫照。人性化趨勢是媒介演進的原因,空間計算技術下,頭顯設備中的世界逐漸符合人的功能性需求,而充分結合人的生理活動,通過眼珠的轉動判斷行為的點位,進一步實現媒介與穿戴者的合一效果。上文我們曾提到,元宇宙、VR眼鏡創造了一個新的視覺體驗場域,這是一個虛擬仿真的世界,但空間計算技術則是以真實世界打底,對真實世界進行拍照后,再在真實的照片圖層上進行數字操作。
此外,人對于真實性的認知往往建立在使用肉眼不疲勞的情況下,而一般的VR眼鏡佩戴后給人帶來的疲勞感和不適感通常會破壞這種真實體驗。不過,據一些用戶調研情況來看,在Vision Pro眼鏡佩戴后不適感比普通VR眼鏡要低很多,產生疲勞感的時間也更長。因此,適應眼鏡時間短、久戴不適感低抑或是Vision Pro更具真實感的原因之一。
從另一個角度看,戴上智能眼鏡后,與人共生的智能設備能夠對人所處的空間進行改造,讓人獲得全新的一種身體存在于智能空間和現實空間的新的存在方式,這種方式更類似于半在場或者半缺席。那是因為,人的肉眼在眼鏡式頭顯設備建構的世界中在場,肉眼的變動會影響設備中視覺呈現的效果;同時,手勢脫離于設備的視覺范圍,但也是控制眼鏡內視覺效果的行為工具之一。人在虛擬空間和現實空間的“一半”狀態,可能會影響人在人際交流中改變以往交流中的邊界,以自己的身體適應眼鏡下的媒介邏輯而影響交往行為。此時,賽博格的身體得以凸顯。在眼鏡式穿戴設備的使用場景下,身體在場的可能性更加豐富,賽博格化的身體進一步嵌入交互過程中,甚至重塑穿戴者的身體體驗與真實認知。
(二)空間計算技術中交互方式的類人性
空間計算不是一個新詞,但是蘋果此次的頭顯設備發布將其帶入大眾視野,并將其定義為一個時代。在人與機器的交互過程中,機器保有真實物體與空間的信息,并以此作為參照進行操控,這是空間計算技術的核心。很多人說,Vision Pro是一款VR、AR眼鏡,但事實上,在這款設備的發布會中,蘋果公司仿佛刻意規避了這種說法,而尤其強調空間計算技術的賦能。
在元宇宙的設想中,空間的概念是被強化的,其中,數字孿生就是一種典型的元宇宙空間與現實空間的關系。[7]但是在空間計算的技術效果中,空間的邊界是弱化的,并非我們不再強調空間的概念,而是側重點發生了偏移,而逐漸往更為柔和的統一方向發展。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不討論尋常的VR眼鏡,而選擇以空間計算技術為核心的設備作為我們的討論對象。
在這款頭戴式眼鏡設備的交互方式中,避免使用筆和鍵盤,代之以手指觸控是其核心。Vision Pro沒有選擇筆和鍵盤這類的普通交互方式,抑或是現代各種VR/AR/MR的觸控手柄,一方面來自其企業的獨特交互體驗信仰,另一方面來自強大的軟硬件整合實力。
在Vision Pro中定義了空間計算的用戶體驗:眼睛注視的地方就是光標,光標作為導航;雙手的各種動作實現功能,雙手完成操作,自然又簡單。而語音完成信息傳遞,通過音頻存儲的方式輸入指令,強大的屏幕完成在整個視野空間的各種三維渲染,完成最后的信息輸出,返回到人眼中來。這一設備的操作工具沒有使用人類發明的某種手柄或者鍵盤,而是通過人類的“手、眼、語音”組合交互,確實完成了絕大多數和周圍自然界的交互。這樣的 “第一性原理”交互簡單自然,而為了實現這樣的類人性交互體驗定義,Vision Pro眼鏡上堆砌了12組攝像頭、2塊4K Micro OLED顯示屏、5個傳感器、6個麥克風以及M2+R1實時計算芯片等——這些硬件都為設備的類人性賦能。
無論是否戴上設備,人類對設備的指令和對人腦進行指令的行為都逐漸類似,操縱機器的行為與身體指令的行為逐漸趨于同步。就像一開始觸屏手機面世,人類逐漸適應了不通過鍵盤操作手機,而直接用手指操縱屏幕,后來,手機就像變成了人的一個器官;當我們對眼鏡式設備發出指令,只需要眼動和手勢,或許這一設備在完成其佩戴舒適度的革新后,亦會成為我們的某種器官,而這種情況下,我們將更加難以分辨肉眼下的真實與客觀的真實。
(三)空間音頻技術的沉浸式體驗
老式的穿戴式設備之所以給人的沉浸感沒有那么強,是因為這類穿戴式設備往往都只重點關注了某一種感官,例如只關注了聽覺或者視覺或者嗅覺,而沒有做到幾種感官融為一體。而Vision Pro搭載了目前最為先進的空間音頻系統,讓用戶更加如身臨其境,在穿戴式眼鏡設備當中還在位于眼鏡與頭戴部分之間增加了揚聲器。空間音頻系統通過獨特的定向傳聲技術,將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讓使用者更有沉浸感。同時,穿戴式眼鏡設備還會分析周圍的聲學特性,以便在進行對話式音頻交流時,達到更為逼真的效果。甚至可以做到人的頭像在哪兒,聲源就在哪兒的真實效果。先進的空間音頻技術是極強沉浸感的核心,聲音猶如從四面八方涌來,而不是單一從某一個角度傳來。同視覺一樣,聽覺同樣可以給人一種空間的縱深感。
空間音頻技術可以根據每個人的生理結構不同定制不同的空間音頻效果,使用3D技術,使得聲音幾乎來自于聽眾周圍的任何地方。而要達到高強的沉浸體驗效果,就是360度地將聲音格式處理為電影式的沉浸式體驗,也可以理解為,在這一穿戴式設備的技術體驗當中,超越電影的真實是其最終的追求。
從技術上講,音頻工程師采用定向音頻過濾器和調整每只耳朵傳遞的頻率,以創造聲源來自不同點位的效果。與傳統的環繞聲不同,空間音頻在混合效果當中添加了一個垂直的部分,也就是相比于全景聲的包裹感,空間音頻技術還強調了人與聲源的距離感。在原始的全景聲技術下,人的移動并不影響對聲音的體驗,但是在空間技術的效果中,人一運動,聲音也在運動,聲源的點位與人的距離會帶來聲音效果的不同。頭戴式的眼鏡不僅完成了視覺上的沉浸式體驗,還完成了聽覺上的沉浸式體驗。其雙重感官的組合效果,比單一增強某一種感官帶來的沉浸感更強。由此,在這些可能會破壞真實感的細節中,空間計算技術下的頭戴式眼鏡設備都做得更為精細,這也實現了一定程度上虛擬與現實的模糊。
三、主體論:用戶對虛實的體驗與建構
談論虛擬與現實的邊界問題,不能單單只討論媒介如何呈現這種邊界的模糊,因為最終對于虛實邊界的界定是由用戶產生的。只有人的體驗構成了虛擬與現實的彌合,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在場感和同理心。一種真實或更為真實甚至超越真實的體驗,需要人作為主體的確認。
(一)空間計算激發用戶的“心流”體驗
當心流體驗產生的時候,人可以無意識地過濾掉外界的干擾因素,而只對我們眼前的世界產生反饋,或者是人本身的心理目標產生反饋,從而獲得一種極高的滿足感。[8]空間計算技術,在用戶這一層體驗上的感受仍然是“沉浸”兩個字。沉浸其實是一種精神狀態,它的意思是作為用戶高度地專注于自己所信賴的世界當中。而心流體驗指的是心靈體驗達到的最佳狀態,也就是我們在做某件事時是一種忘我的狀態。
在穿戴式眼鏡設備中,例如VR眼鏡設備給人帶來的沉浸體驗,其實沉浸于自己某一項感官得到加強的感受,又或者是高度沉浸于一個新的被創造的空間當中;而空間計算技術下的沉浸體驗指的是高度地沉浸于自己所能看見的真實世界,而這真實世界又加上了眼鏡式穿戴設備所給予人體的各種功能。因此,這里的心流體驗是更為沉浸的。
原始的穿戴式設備當中,心流體驗指的是與現實世界暫時發生隔絕的沉浸,而現在視覺作為人最直接的認知來源,被運用在了空間計算技術下的穿戴設備當中,這里我們不是把認知新的世界當成某項游戲,或者是亟待完成的任務,而是我們生活的日常。因此,空間計算下的心流體驗不是要進入某一個新設計的角色,而是以本身用戶所處的角色進入到一個更美好的真實世界,而這一心流體驗的過程需要的緩沖時間或許只有佩戴設備的時間。在心流體驗的理想狀態下,這種用戶的“忘我”狀態或許會真正忘記虛擬與現實的區別,而消解邊界的概念。
(二)人機關系的演變對邊界的彌合
列斐伏爾在空間生產理論中指出,空間是社會的產物,并且提出了空間的三元辯證法。他將空間結構區分為空間實踐、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對應著空間的物理精神社會的三個維度。[9]空間實踐隸屬于感知層面,是作用于有關物質性空間的人類行為和空間創造。空間再現是對于空間的組織化環節處于支配地位,具有構想性、概念性和主觀性,是指在原始空間基礎上的空間想象。
在穿戴式眼鏡設備中,經過技術處理后的畫面空間是由人的主觀意識所賦予的,因為這類設備可以通過捕捉人眼的移動而判斷人的意識。在這一真實場景的空間,用戶基于場景限制性的空間實踐與擬真,共同構成了再現空間。人腦海中的空間由主觀建構而成,包含濃厚的主觀意識形態和空間秩序,而眼鏡下的再現空間是一種包容與超越的狀態,即在再現的作用下,人通過相關意象和象征而直接生活出來的空間,是對物理空間進行直接的空間實踐。
1.邊界在人機互塑中消解
穿戴式眼鏡給予了身體的在場和意識的在場以及事件發生的在場同時發生的可能,由此帶來的技術具身會產生諸多問題,尤其在當今的智能傳播環境下,AI虛擬、仿真身體、腦機融合、數字永生等,已經成為學術界日益關注的倫理問題。人—技術和世界關系的倫理風險揭示了人機合一這一復合空間對于主體和環境的不確定性的危害。[10]身體是一種自然技術,單從它是有意識的實存來說,它是一種比近現代物質技術更為復雜精妙且具有無限可能性的技術實存,作為一種活的技術,身體與物質技術進行交互,物質技術逐漸內化,嵌入身體,拓寬身體感知世界的方式、渠道和能力,這是穿戴式設備對于身體和沉浸的空間進行的更完美結合的嘗試。
人突破了傳統意義上具有生命的個體,衍生出電子人賽博人化身等多種形式,在穿戴式設備當中,人可以以虛擬的身份投身于現實世界,也在虛擬世界中投射現實身份。因此,在人與機器的互動過程中,虛擬與現實的邊界其實是逐漸消解的。大數據與物聯網將與物體處于同一種信息空間當中,在佩戴了穿戴式眼鏡之后,人的每一次透過穿戴式設備的行為、語言、動作指令都將成為這一機器積累的行為數據。當數據連接網絡,這類數據就會呈現出極強的社交屬性,也就是說,設備可以聯網,行為成為數據,數據反過來讓人使用設備更為便捷,而離不開設備的存在。智能式穿戴設備延展了人的邊界,在人與機器相互賦智的互動過程中,人原本認為的虛擬已然成為真實,真實的世界也離不開虛擬的建構。
2.邊界在人機共生中彌合
在蘋果Vision Pro的視覺界面當中,人可以看見自己每天的量化數據,也可以透過眼鏡看見實際經過眼前的人。眼鏡對現實世界進行拍照,再傳遞到穿戴式設備當中。人看到的是美化后的現實世界。因此,穿戴式設備給予人的信息更像是UGC+AIGC的結果。AIGC的應用者擴展到了普通人,人可以通過各種AIGC的工具參與不同的智能化內容創作,也可以大大擴展穿戴式設備在日常生活當中的應用場景。這不僅僅是人機協同,因為眼鏡的穿戴式和必備性,人機協同向人機融合進一步延伸。
當人戴上穿戴式眼鏡的設備之后,人類是否對于機器能夠產生足夠的信任,人類又是否能夠分得清楚虛實邊界。人際關系在穿戴式設備的進一步發展當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賽博格化的身體是人機融合的重要形式,這種身體正在變成新的媒介。當人戴上穿戴式的眼鏡設備之后,人和機器融為一體,而由此帶來的典型結果就是人的數據化生存,人被演進全方位“數據化”,人的身體也因此被映射為虛擬的實體或者被拆解的數字化元件。在眼鏡這樣的穿戴式設備的世界當中,量化自身成為一種更加可行的方式存在。在人與眼鏡充分相融時,人需要與機器實現自我對話、自我審視,而這個過程并不完全從人的神經系統當中或者哲學角度發生,而是獨立于人的身體之外,與人的機器混為一體。可穿戴式設備的眼鏡或者傳感器等帶來的自我量化認知,正是量化自我的一種方式。量化自我對人產生的規訓可能來自于機器本身,也可能來自于人與機器的互動。
對于穿戴式設備最為理想的結果就是人機交互的共生狀態,其實技術可供性并非是技術的一種特征,也并非單單是技術使用的結果,而是提供了這種可能性。這使得人在使用穿戴式設備的時候并不會思考這一設備會給我們帶來什么。這里強調的是我們與穿戴式設備之間的關系并不需要外顯,而是似乎它本身就存在于我們的身體當中。這種認知是無意識的,也是穿戴式設備較為理想的表現形態。這就是為什么蘋果的Vision Pro盡量避開外化于人體的手柄,而是盡可能追求類人化的操作可能性。
媒介是人的延伸,真實地體現在了人機共存的情景當中。當穿戴式設備離開了人體,人們才會驚覺其存在。由此,人從適應眼鏡到忘記眼鏡的存在,其實是對眼鏡下的世界真實性的逐漸信賴的過程。當人相信這樣的世界就是真實,虛擬便只有在取下穿戴式設備的那一刻才又顯現。
3.虛實混融形成的情感依戀問題
人們越是沉浸于虛擬帶來的體驗,越容易產生對于現實生活的抗拒,進而可能會產生強烈的技術依賴性。在蘋果Vision Pro帶來狂歡和媒介期待的同時,我們不能放松對“成癮”的警惕。人們利用Vision Pro等設備,可以滿足自己在現實空間中無法實現的構想。在這段對于未來的美好憧憬的背后,也不難看出其隱藏的“成癮”風險。
在高度仿真的場景敘事引導之下,作為處于場景當中的主體,開始了其在眼鏡下的世界進行一系列拓展性和創造性的各類活動。而面對不管是熟悉還是陌生的眼鏡中的世界,穿戴者首先依照自己原有的認知方式,對于自己所認為的真實世界進行認識。而每一次的行為都會讓用戶更加相信自己所處世界的真實性。
這種沉浸式的體驗帶來的反作用便是對現實生活可能的抗拒。比如說在穿戴式眼鏡設備當中,通過眼球的轉動就可以完成行為的指令,而在脫離了這一設備之后,人可能會產生一系列不適應的感覺,進而產生強烈的技術依賴性。到那時候,戴上穿戴式設備才是人最期待的狀態,取下穿戴式設備就像失去了認知世界的“眼鏡”,對真實客觀世界模糊不清。從這個意義上說,用戶極有可能因為長時間的穿戴眼鏡而排斥真實的世界。用戶會只強調視聽感官的刺激,而不強調思考的深度,也就是不再具有反觀性思想,而是只剩下了應激性的思維。在這種情況下,在人為制造的虛擬認同當中,用戶極易被遮蔽,對于主體認知的敏感性也在逐漸削弱,亦容易迷失對自我的認知。如果用戶發現自己無法在真實世界當中認識自己,就會沉溺于眼鏡設備的世界認識自己。在這樣的情感依戀下,可能就會帶來關于空間計算技術背景下的一系列新倫理問題。
四、結語
在新媒體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我們不斷反思如何表現真實性的問題。而在本文的描述當中,我們盡量不把空間計算或者頭戴式的眼鏡設備,比如Vision Pro與VR、AR、MR進行等同,這是因為空間計算技術發展時間短,也經常被人們與元宇宙混為一談,但其本質還是存在區別的。類似于VR技術和元宇宙技術的核心,就是建構了一個新的虛擬世界,而讓用戶進入到這一虛擬世界,從而產生沉浸式的體驗。但是空間計算是對現實世界進行拍照模擬反饋,再對現實世界進行建構、重塑、融合,從而達到現實世界更為精細的效果。也正因如此,空間計算技術帶來的虛實邊界的變化才更為隱蔽,適應了這類設備的人更加難以分辨出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的區別。
從VR技術興起的那一天,虛實邊界的討論就從未停止,但伴隨著技術進步,信息的傳播形式逐漸變得視覺化,因此,頭戴式眼鏡設備就成為視覺化的載體。空間計算賦予了這樣的設備模糊虛實邊界的功能。而當空間計算技術真正可以達到讓虛擬與現實融為一體的時候,頭戴式眼鏡設備將真正作為人的一種器官而達到一種人機合一的效果。這樣的結果注定是具有雙面性的,一方面我們可以讓真實世界變得更加便捷,比方說我們不用發出語音的指令,僅通過心流指令或者眼球的轉動就能完成一系列技術上的操作,但與此同時,也一定會帶來一些人機合一、人機混融的倫理問題。不過文中我們也討論了另一種可能,當虛擬與真實的邊界越來越模糊,還會出現一些有別于我們推斷的反效果,那就是,人更加珍惜當下的真實世界,也更加注重人與人之間真實的交流與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