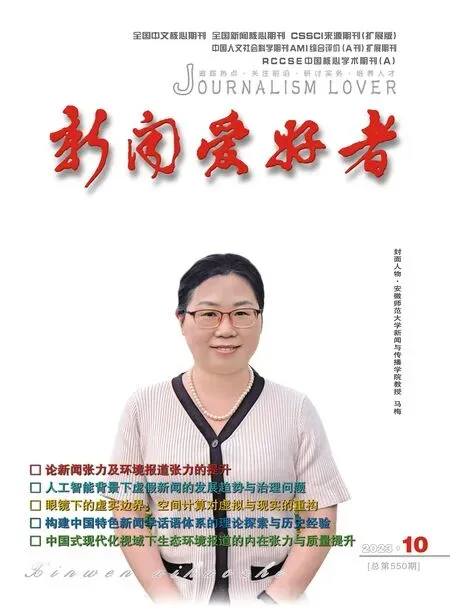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國際傳播:基于文化價值的分析
□谷 玲
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一個“變”字彰顯出了我們所處的這個歷史時期的最大特征,變代表著不確定、不穩定,也代表了挑戰、危機與機遇。對此,習近平總書記給出的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1]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當前,對外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但是展示中華文化優秀基因的國際窗口,亦是提升中國“軟實力”的重要舉措,同時也是崛起中的大國必然要發出的中國好聲音。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含的文化價值
(一)傳承與共生: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
根植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 “和合”思想和“天下”觀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的文化意蘊油然而生。“和合”思想中的“和”,即平和;“不同”,即差異性。《論語》中講道:君子和而不同。《中庸》中講道: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觀念是中華民族獨特的宇宙觀、時空觀、世界觀和政治觀。從《禮記·禮運》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政治抱負,到《大學》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追求,再到王陽明講“破山賊易,破心中賊難”,強調“心能”的修養與不斷強大,通過“知行合一”來歷練內心成就自我“致良知”。儒家思想認為中國人的內心世界是與外界、與他人聯系在一起的,是黏附的。孔子講的“仁”,即仁義道德。“人者,仁也”。中國人的道德追求“融國家于社會人倫之中,納政治于禮俗教化之中”。古代仁人志士不僅有家國情懷,更有天下思想,不僅能夠做到忠于君王、孝敬父母,也甘愿為了追尋理想之光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歷代先賢“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道德情操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擔當,承載著中華文明的獨特品質和鮮明價值,塑造了中華民族以天下為己任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基因。[2]“文明以止,人文也。”用文明的力量使人達到至善,是中國古人倡導的人文精神。古人特別強調修身,修身的同時其實也就是修心,突出了人的使命、價值和意義都是由內而外顯現的。“天人合一”“協和萬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的哲學觀、國際觀、社會觀、道德觀則深度闡明了人類發展前景和世界前途命運。
(二)創造與創新:新時代中華文化的發展要求
中國的傳統政治依靠“家國天下”的傳承精神得以維持。2018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對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第一次進行全面系統的闡釋,他說:“中國人民在長期奮斗中培育、繼承、發展起來的偉大民族精神,為中國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3]深刻詮釋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碼,揭示了中國人的心性特質和內在稟賦,展現了中國人民勤儉節約、吃苦耐勞、堅韌善良、包容寬厚的人文品格和團結一心、同舟共濟、懷抱夢想的集體主義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讓中華文明的影響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來。”[4]“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實施路徑,賦予傳統文化與世界發展愿景和人類未來命運相呼應的時代價值,從中凝煉出體現中國作為大國的責任擔當和歷史使命,為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融合發展提供更多的機遇。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國際傳播面臨的挑戰
(一)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認知標準的不同
在對外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時,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價值觀念、利益關切和思維方式的差異,使得不同國家對此理解和認知標準的不統一,形成了認知態度和關注度存在不同區分。在許多國家中,傳播主體與受眾對象往往能夠形成一定的互動效應,比如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表達的共同價值、人類整體利益等理論提出討論、轉發、引用或者報道等,社會整體呈現的認知程度較強。而在個別國家也存在故意設置傳播障礙、曲解報道內容甚至“貼標簽”的行為,傳播面臨較大的困境。塞繆爾·亨廷頓提出了所謂“文明沖突論”,認為文明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排斥、沖突與競爭。他繼續申明:“我喚起人們對文明沖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于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 ”[5]“現實中,‘我們’ 內部是有差異的,‘我們’與‘他們’之間往往又有很多共性。”[6]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海外傳播必然面對跨文化的客觀差異性,這種差異性的表層顯現出不一致與排他性的區分,但隱性內涵實則包括了尊重、包容與互鑒的融合性前景。
(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認知走向認同的“差距”
從認知走向認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國際傳播的內在要求,包含著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含文化與價值觀的認可、接受與踐行。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聲音”“中國故事”和“中國智慧”逐漸引起世界性的關注,并獲得了國際社會廣泛的認知共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被聯合國頻頻寫入區域合作、人權發展、消除貧困等領域的決議中。中華文化以“有容乃大”“兼濟天下”的胸懷,為解決全球治理困境、新型全球化指明了一條開放、包容、平衡、共贏的道路。然而,西方資本邏輯下形成的“國強必霸”思維定式、追求“個人利益”漠視“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危機、東西方國家在歷史文化和國情方面的差異等因素都會導致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國際認同困境。[7]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還存在著有理講不出、講出傳不開的傳播困境,造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國際認同的提升能力建設尚有一定的差距。
(三)西方國家媒體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存在“過度”解讀現象
歷史證明,19世紀以來以西方國家為主建立起的所謂現代文明已經背離了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確立的政治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則,奉行“強權即公理”叢林法則、優勝劣汰、強權政治等所謂價值觀,積蓄成諸多矛盾問題產生的文化認知根源,已經成為某些西方國家發展的內在掣肘并制約了現代世界的文明發展。出于對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戰略地位不斷上升的擔憂,一些國家和西方媒體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停地抹黑和打壓,利用西方話語霸權對該理念作出曲解、誤讀并抹黑中國的國家形象,不斷消解國際社會已經形成的國際共識,嚴重影響了該理念的國際傳播。基于國家利益訴求,西方媒體不斷加大對“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責任論”等錯誤論調的傳播。[8]
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國際傳播的有效路徑
(一)誰來講:培養話語傳播者做到“以文化人”
在對外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過程中,應當擴大話語傳播主體的范疇。更好地發揮政府官員及官方媒體等意見領袖作用的同時,還應“積極發揮各類國際組織、民間團體、專家學者、華人華僑等話語主體作用”。[9]在對外傳播中,統籌做好官方與民間話語的結合,官方媒體的政治發聲與民間交往的生活發聲形成一套完美的“金話筒”至關重要,兩種方式的融合可以相互促進,大幅度提升國家形象建設的“軟工程”。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海外傳播要打好民間話語這張牌,擅于運用已有的海外力量培養話語傳播者就顯得十分重要。其實,發生在與海外組織、公司以及民眾工作、生活場景之下,具有交互聯系的各類組織、企業以及普通人之間的認知聯系是最有感染力、說服力的。如在海外經營中小企業的華人以及長期在海外生活的人,他們與所在國家的社會、文化每天都發生著深刻的交融與碰撞,他們也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的文化場景感知最為直觀、深刻的人群,他們的發聲會帶給受眾最為強烈的文化感知。
(二)講什么:打造情感共同體做到“以情感人”
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構建,本質上是不同文化的交流,是一種對話關系。增強對話不僅可以加深對本民族的文化認同,增強文化自信,還可以發揮跨文化傳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增強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傳播力和影響力。[10]多種文化的共處,更要強調不同、差異、尊重與包容。真正的文化交流需要做到“感同身受”,唯此,大家才能產生互動和共鳴。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宋代理學家朱熹進一步闡釋為“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體現出儒家文化思想重視、尊重和保障人的權利。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以人類整體利益、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為根本出發點,以全人類共同價值觀為支撐。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傳播要用符合不同民眾的思維習慣、認知表達和語言方式進行情境轉換,做到抽象與具體、宏觀與微觀的有機融合,將理念融入場景、價值融入生活,要針對不同的受眾進行話語的適當轉換和恰當表達,獲取當地社會的共情。通過提煉典型符號,實現符號轉義,構建“視像化”場景,完成圖式借用與語境置換,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個體情境的關聯,以此促進傳播對象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認同與內化。[11]真正的文化認同感,是需要共享的日常生活空間形成的有關身份、情感的歸屬以及化解問題產生的路徑依賴,通過彼此之間長期的博弈、應對挑戰的碰撞中不斷調整適應性策略,逐漸獲得成長的空間、價值的認可。
(三)在哪講:擴展“文化交流”多元傳播渠道
互聯網數字技術的發展形成巨大的影響力和穿透力,沖破了傳統國家之間的物理邊界、改變了社會的交往方式,形成了人人都是“自媒體”的無限傳播空間。圍繞對外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目標,要全力打造“一個主旋律,多重好聲音”的全方位、立體式環繞大合奏。一是不斷做大做強官方媒體,擴大境外發聲渠道和信息發布能力。針對西方媒體不斷利用強勢話語權進行曲解和指責,官方媒體的“正名”和“表態”就顯得十分重要。因此,要在分析海外受眾的情感表達習慣、思維方式等呈現出的接受度和認可度方面加大分析研判力度,注重用海外受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提高傳播的專業化、精準化,不斷提高傳播的廣度和深度。二是擴展多元傳播媒介,注重落地傳播效能。在打造強大的官方話語平臺時,應不斷拓展傳播平臺,充分利用互聯網、國際會議、民間活動等話語平臺,形成傳播的“大合唱”。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海外傳播要充分利用新媒體技術,將觀點以視頻、漫畫或海報等輕松明快的方式表達出來。文化的海外傳播建設往往體現在具體的媒介上,如將“中國風”“中國范兒”“中國劇”“中華美食”“中國功夫”等豐富多樣的文化形式與百姓的日常工作生活形成同構,形成更為現實的中國形象。
(四)怎么講:搭建“文化互鑒”平等對話平臺
一是充分認識到文化價值引領和創新為每一個國家獨立自主的現代化之路提供精神支撐。中國與西方的價值觀并不存在根本沖突,只不過是價值存在、表述方式和關注重點不同而已。經驗證明,只有充分挖掘自身文化的歷史價值和發展潛力,在國家的歷史文化資源中找到具有支撐力的精神價值,才有可能獲得強大的發展內驅力。二是努力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含的文化價值理念融入國際法體系,明確各個國家之間必須確立一些共同認同的規則或原則。通過不斷發掘、尋找并豐富人類社會的共同價值和普遍利益,以此來搭建更多國家、國際組織之間的對話平臺。三是注重推動對話的具體方式。對此,中國古代經典早已給出了答案,說明世界文明的溝通、交流與互鑒并非不可能,只要從人類的生命經驗去做適當的解釋,就能夠順利開展。儒道二家思想共同揭示了中國古典哲學的特質,那就是以生命為中心的宇宙觀和以價值為中心的人生觀。《周易》講求變化之道,目的是通過變化之理讓人活得更有希望,側重“仁愛”。《尚書·洪范》標舉永恒理想,揭示了自然的“正義”,使人可以安身立命。事實證明,只要符合各種文化的基本理念,符合人性,那就都能夠接受。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屬道理一定是相通的,只要找到恰當的溝通方式,就一定可以順利展開。
四、結語
綜上所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國際傳播是人類社會一項長期而艱巨的系統性工程,這期間需要持續挖掘并不斷鍛造適用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內涵,通過多領域、深層次、廣維度的文化交流與合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國際傳播建構文化價值支撐。多年來,中國不斷為促進世界和平繁榮貢獻智慧與方案,始終將促進世界各國團結合作、不同文明交流融合作為最根本的追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基于歷史維度、生命維度、價值維度、實踐維度的考量,闡明了人類命運休戚與共、和合共生的思想,表達了對于構建一個更加和諧、美麗、幸福世界的美好愿望和應有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