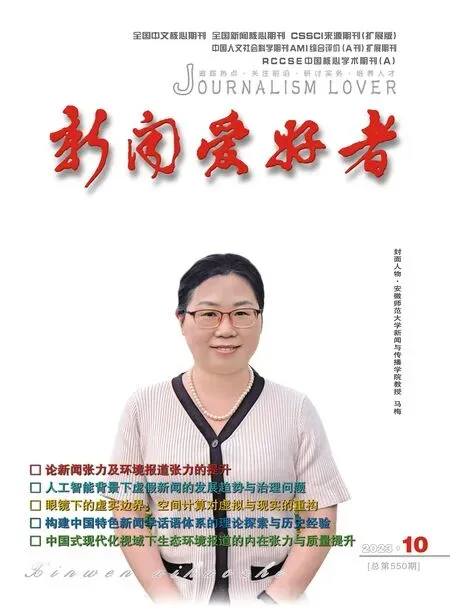人物圖譜、類型拓殖和民族想象:胡金銓電影的共同體意識考索
□李 怡 王雪樺
中國歷史上無數次的風云巨變、生死存亡,使中華民族形成了強悍的共同體意識。文化具有記憶、宣傳功能,是喚起共同體意識的有力武器,華語導演胡金銓(1932—1997),將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改弦更張、民族氣節寄付光影之內,在中國電影制作技法、藝術水平進步和國際傳播方面作出了不朽的貢獻。對胡金銓的重提并非為了重復對其早已有之的舊評,而是為了說明胡金銓的藝術實踐放之今日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將個體觀眾凝聚成為民族共同體的力量。
一、遺失的故鄉:胡氏共同體意識的養成及辯證
弗洛伊德說,那些清醒狀態下似乎已遺忘的兒時經歷,很可能再現于夢中[1]。作為“造夢者”,胡金銓的自身經歷對其創作有深刻影響。
(一)家風傳承:血緣共同體-精神共同體
“共同體”一詞源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認為所有共同體都是為了追求共同意義上的善而建立的,滕尼斯認為共同生活是親密的、隱秘的、排他性的生活。家庭這個組織形式正是建立在親密的私人關系基礎上,以血緣、感情和倫理為紐帶的親密互信的共同生活。共同體成員奉行的統一原則,亞里士多德謂之“共同意義”,放置在家庭中便是“家風”。
胡金銓五歲時開始與胡氏族親在一座四合院中共同生活。胡金銓的祖父胡景桂曾為清末大員,學識淵博、急公好義、懿行佳話①;父親胡源深作為實業家,秉持工業救國的理想;五哥、六哥、五姐出于對國民政府的失望都加入了共產黨。如此優良正直的家風正如滕尼斯規定的精神共同體狀態 “人們朝著一致的方向,在相同的意義上純粹的相互影響、彼此協調”[2],胡氏家族由“血緣共同體”而形成的“精神共同體”氛圍對胡金銓影響至深。1949年解放前夕,胡金銓只身一人來到香港,與內地的至親失去了聯系,留給他的便是胡氏家族精神的影響。
(二)情感升華:家族精神共同體-民族情感共同體
1950年代,胡金銓開始輾轉港臺兩地拍電影,當時港臺兩地剛經歷了長期的殖民統治,根親意識缺失,內地南下移民眾多[3],大量迎合這些觀眾鄉愁想象,披著中華文化符號外衣,有表無里的影片涌現。為此胡金銓以創作文史武俠,嚴格考究史實來糾偏不良現象,《俠女》《忠烈圖》中的道具服裝、場景布置和景深處的字畫都力求符合朝代背景,這種務實求真的態度與胡氏家風一脈相承。
胡家曾是北平長安大戲院的股東,胡金銓從小就對京劇十分熟悉,他影片中臉譜化的人物表現方式、獨特的武術技擊節奏都是受傳統戲曲影響的結果。他的六伯母是佛教徒,胡金銓自小見伯母念經修習②,自然對宗教思想、佛家文化多了一層思考,為其曖昧的中式儒釋道美學埋下了種子。從弗洛伊德的角度來看,這些經歷都成為殘存于胡金銓潛意識中“夢”(電影)的原型。
經年的漂泊使胡金銓渴望找到一個心靈的寄寓地,而常年與親人的“失聯”使他無法找到一個確定的地方作為“故鄉”懷念,只得將自己民族一員的共同身份放大,表達對民族歷史發展和現實處境的關懷。抵抗外族入侵的《忠烈圖》;訴說儒家忠義的《俠女》;抒發離散情懷的《畫皮之陰陽法王》,體現的都不是對某地的緬懷,而是對民族的依戀。
建立起觀眾的情感共同體,認同機制非常重要,[4]通過電影講述中國故事,傳達倫理溫情與文化傳承[5],是構建共同體美學的必由之路。胡金銓將在家庭熏陶中得到的傳統文化知識,運用于寄付尋根情結的電影創作中,激發起中華民族固有的共同體情感,完成了民族情感共同體對家族精神共同體意識的超越。
二、人物圖譜:空間、身體與文化內核
胡金銓的電影中,客棧、朝堂、寺廟和陰陽場景較為突出,并產生了相應的人物,最終指向社會這個虛空的大場域,空間關系與社會關系保持著互生,形成了以空間情景為脈絡的人物關系圖譜。
(一)客棧:俠客/匪徒角色
《大醉俠》《龍門客棧》《喜怒哀樂之怒》《迎春閣之風波》是廣為人知的“客棧四部曲”,客棧往往設置在大漠孤煙、魚龍混雜的江湖深處,人物被自然地分為俠客、匪徒兩個陣營。以儒家義德為參照,這兩類人物對客棧空間有著不同的感知。
儒家道德中,“義”往往與“利”對立,強調為人的道德、良知要大于個人利益。胡氏武俠江湖中,營救友軍、報仇雪恨的忠義之后(如金燕子、朱驥),匡扶正義的江湖游俠(如蕭少镃、范大悲);與那些為禍朝綱的奸臣(如曹少欽、李婉兒)和心狠手辣的山匪賊黨(如索命五虎),前者為公,而后者卻是為了個人私利。胡金銓將對儒家義德觀的強調與空間—人物的感知并置,在俠客的感知中,客棧是一個甘愿舍生取義的壯烈空間,在匪徒的感知中,客棧則是一個阻礙利益實現的詭詐空間。
(二)朝堂:掌權者/弄權者角色
《迎春閣之風波》《忠烈圖》《天下第一》中出現的朝堂場景較多。君與臣是朝堂空間的主要人物關系,君臣關系首先建立在權力的從屬秩序上,可從掌權者和弄權者兩種身份視角加以考察。
影片中君主角色的失敗,多是因為權力濫用導致的掌權者身份缺席。《忠烈圖》中的君主缺位、官員失職,即使俞大猷等人全力抗擊,終究落敗。《天下第一》中的君主偏信讒言,不加約束自身欲望,沒有做到“舉直錯諸枉”、克己復禮、為政以德,最終自食惡果。而對于臣子來說,儒家忠德要求為臣忠、為民忠、為人忠三位一體,電影中弄權者的身份確立是由于儒家忠德的缺失。歐陽年、曹少欽和李察汗等奸臣,欺君弄權、陰險狠毒,為臣不忠君報國,為人不忠厚誠懇,如此,忠德成為判斷臣子身份在場的標志。
(三)寺廟:邪惡者/正義者
胡金銓評價他個人是 “俗念未盡,臨時抱了佛腳”[6],影片中對佛理感悟的表達也融入了世俗倫理層面的是非觀,人物定性的參照物并非信仰身份而是“欲望”。
《空山靈雨》起源于權財欲望的沖突,《山中傳奇》《畫皮之陰陽法王》中的鬼怪都保留著人的欲望。佛教將欲望視為人痛苦的根源之一[7],它的任務是教人從痛苦中解脫,并非維護社會道義。可胡金銓影片中的邪惡欲望持有者們都以一種猙獰的形態被身體消滅了,如樂娘在死后雖面目全非但神態極其不甘,這在佛教層面并不算是真正得到了解脫,而是胡金銓從社會道義出發做的處理。
在中世紀神學統領下,精神救贖必以犧牲身體的方式來達到。欲望使寺廟空間這個超驗性空間中的人物有了身體感知的權利,正如白狐悟到《大乘起信論》的真正法理后剃度出家,以身體上的受戒表現精神上的超脫。人物的身體感知能力便與寺廟空間的超驗性意義產生了互生。
(四)陰陽界:人/鬼角色
胡金銓拍攝的電影似乎總是著力于傳達儒家和佛家思想,道家仿佛被忽略了,但影片中常出現的“鬼”的角色卻離不開道家文化。“鬼”原是佛教宇宙“六凡四圣”中的一凡,[8]佛家中未論及鬼的 “超能力”,道教卻發展出人鬼相克的觀點,“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遂除之之謂人傷鬼也”,在老子看來鬼神能對人產生威懾和傷害。[9]胡金銓影片中鬼的形象顯然借鑒了道家的鬼人觀。
影片中鬼與人能夠共處一個空間,也是在道家鬼人觀影響下以重獲身體感知為基礎的。陰陽法王來到陽界后第一件事便是通過滿足身體感官來確認自己的陽界空間在場。尤楓被困在陰陽界時要靠畫皮遮面度日,被剝奪了身體感知能力,片尾她投胎為王順生的孩子,重獲肉身,身體感知成為她由陰界走向陽界的反映。
以“儒釋道”文化為人物在場的條件,客棧、朝堂、寺廟、陰陽這四類原本只帶有民族文化特征的空洞的能指符號擁有了深厚的所指意涵,由實體空間轉變成可被感受的文化空間。自古以來,儒釋道文化深刻地塑造了中華兒女的思維方式,這種價值選擇中的集體無意識正是扎根于我們內心深處的共同體意識。
三、類型拓殖:民族訴說的變與不變
胡金銓拍攝的電影中,《大醉俠》《龍門客棧》《喜怒哀樂之怒》《俠女》《迎春閣之風波》《忠烈圖》《空山靈雨》《山中傳奇》《天下第一》《大輪回之第一世》《畫皮之陰陽法王》可算作廣義上的武俠電影,《玉堂春》是黃梅調電影,《大地兒女》是革命戰爭影片,《無冕皇后》《終身大事》是現代時裝片,它們涉及中華民族發展的多個節點,是從封建傳統到現代化的民族命運縮影,共同訴說著中華民族向何處去的命題。
(一)殊途同歸:題材選擇的一致性
上述幾種美學風格相差甚遠的電影類型,有著明晰的線索:憂患意識與救亡情結。武俠電影中的“患”是邪惡、朝堂奸佞之患,而“救”,《大醉俠》《龍門客棧》《俠女》是對“忠義”的拯救;《迎春閣》《忠烈圖》是對家國民族危機的拯救;《空山靈雨》《山中傳奇》是對自我精神困境的拯救;《畫皮之陰陽法王》是對處于“中間”的“無根之人”的自救③。
1960年代,在當時大拍娛樂片的邵氏,胡金銓將自己獨立執導的首部作品定為抗日影片 《大地兒女》。《玉堂春》不同于同時期的黃梅調電影注重對纏綿的愛情故事的表現,而將造成蘇三悲劇的社會原因道出,使影片有了一定的反思意味。《無冕皇后》體現了對“文化大革命”的時代反思。胡金銓對臺灣的廣告夸大和環境污染嚴重印象很深④,便以此為主題拍攝了《終身大事》,反映經濟起飛下“四小龍”之一臺灣的行業發展亂象,這些都體現出他對古今社會弊疾敏銳的洞察力。
(二)以小現大:時涉古今的憂患意識
胡金銓對古今社會憂患意識的表現,皆是從小人物入手,無論是顧省齋、何云青,還是客棧老板、伙計,都是時代裹挾下的小人物。他們在歷史浪潮的裹挾中,無法掌握命運的主動權,不得不被動地做出抉擇,這正是歷史憂患加至個人的結果。關于《大地兒女》,胡金銓表示“抗日戰爭連那些地方(小都市和農村)也影響到了……在這種情況下,各行各業的人會有什么反應呢?我想寫的正是這種反應”。⑤《終身大事》更是表現個人抉擇在社會急速發展下的無奈。
這種底層關懷與胡金銓的個人經歷影響有關,他幼時隨父母在外漂泊,見慣了戰亂年代的人世百態,后又目睹親人們在混亂時局中各自沉浮,17歲離開故鄉身無分文地開始謀生。事業有了起色后輾轉于港臺之間打拼,晚年定居美國。可以說他本人正如電影中的人物一般,是被卷入時代浪潮的微小個體,反映出了時代的變遷與無奈。
中國文人歷來有著“位卑不敢忘憂國”的傳統,一面對中國文化抱有極大的自豪感和優越感,一面對國家的發展抱有極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10]。對民族文化的守護責任使得胡金銓根本不像一個國際名導一般風光,時常捉襟見肘。他舉債自費送《俠女》前往戛納參展,才有了影片在國際影壇的成功;此后拍攝了十部電影,仍然是入不敷出的境地。[11]未完成的《利瑪竇傳》表現利瑪竇帶西洋技術到中國的過程中,對腐敗官僚主義思想的批判,“萬歷皇帝”這個角色又帶有知人善用、慧眼識珠的光環。這正是胡金銓文人精神的體現,即肯定儒家的政治理想形態,又對現實社會痼疾有著針砭時弊的責任感。
四、從民族想象到共同體意識的詩性語言策略
通過將傳統儒釋道精神具身化為微觀人物,將其拋入不同歷史時期民族命運的困境之中,胡金銓將故事世界勾連為一個帶有相同文化根基,經歷了相同命運變遷的民族整體,并從技術美化和詩意影像表達兩方面激發起觀眾的民族想象。
蘇聯蒙太奇學派對胡金銓產生了很大影響,《俠女》采用了四格鏡頭快速、簡短的剪輯方法來表現“女俠”不凡的身手。⑥該片中月下彈琴的場景,胡金銓用拆去聚光鏡的采光燈和涂滿漿糊的白紙造了一輪明月,⑦還原了李白《月下獨酌》中明月高懸的清冷氛圍。技術雕琢帶來的美化影像是對民族文化符號的理想化展示。
克里斯蒂安·麥茨提出了電影的認同機制:觀眾首先與攝影機產生認同,再與銀幕中的世界產生認同。通過對中國古典詩學的借鑒,胡金銓將中國觀眾的審美習慣融入電影創作當中。
“意境”是古典詩學的重要范疇,既要求實境的景物描寫,又要求虛境的審美想象。胡金銓擅長以“人在畫中游”的臥游形式,實現虛實結合。《山中傳奇》中有一段山水鏡頭和何云青行走鏡頭,這個片段中,觀眾通過攝影機隨著何云青“行走”,對山水風光進行臥游式的觀賞,達到了對山水風光的族地認同,另有一段“在早年間,咱們中國有不少的傳奇故事”的旁白生發了觀眾的文化認同,并給靜謐的湖光山色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產生了看山非山,看水非水的虛情。借鑒自戲曲的武打動作、配樂,富于韻律;建立在“儒釋道”文化基礎上的主體經驗抒發,都符合古典詩學的要求,使觀眾在熟悉的審美習慣當中,認同了故事世界中的民族整體,并在詩意影像中生發出對其的美化想象。
然而,民族與共同體還有些許差別,安德森將民族視為人造物,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而亞里士多德、滕尼斯概念中的共同體都是建立在成員親密互信基礎上的自然狀態。要將兩者等同,便為電影詩學提供了空間。波德維爾提出“電影是如何同各種跨文本規范相關”的問題,電影詩學便是以歷史的語境來同時揭示規范之間的變化與連續。[12]胡金銓電影的詩性氣質正是來自對中國古典詩學的跨媒介式體現。胡金銓個人情感的影像表達通過中國古典詩學的整合,被轉化為全體中華兒女都可以體味到的“我們”之共有情感,實現了胡金銓的“我”之詩性語言到觀眾之“我們”的共有感受之間的流動,觀眾感受到的不僅是浮于表面的文化符號,更是熟悉的詩性傳統和中華美學氣質,產生了關于中華民族文化與命運共同體的心照不宣的“我們感”。
五、結語
胡金銓電影中從人物到意蘊,從外延到內涵而構成的獨特話語表達體系,都是在對中國文化的堅持與探索下得出的,這些積淀著民族精神內核的多元文化形態,是構建當代中國話語體系不可或缺的文化語境與修辭基礎。[13]胡金銓通過人物圖譜、類型拓殖、民族想象三方面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播,賦予了電影經久不衰的藝術價值,成為喚起觀眾共同體情感的藝術力量。
注 釋:
①②③④⑤⑥⑦胡金銓、山田弘一、宇田川幸洋著:《胡金銓武俠電影做法》,厲河、馬宋芝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24頁、第26頁、第216頁、第210頁、第67頁、第119頁、第1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