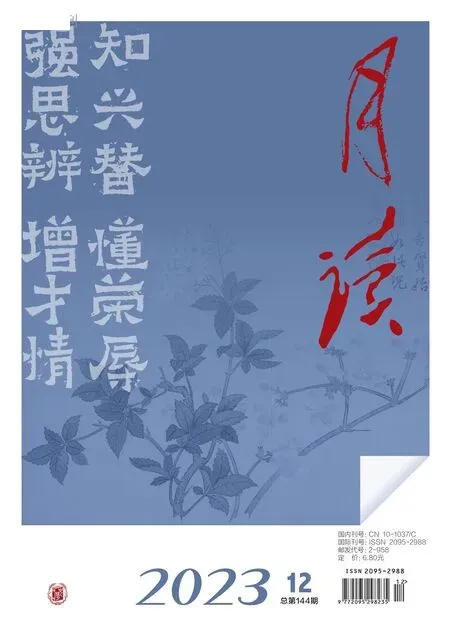憶秦娥
〔唐〕李白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評論】
此詞以寫離殤而發今昔之嘆。其中離殤,非一人之離殤,是眾人之離殤;“秦娥”亦非一人的秦娥,而是眾人各自的秦娥。眾人,亦非同年代的眾人,是很多年里很多“眾人”于灞陵上、簫聲中辭別各自的“秦娥”,自“古道”而去,而就此“音塵絕”。咸陽古道,即漢唐時期由京城往西北從軍、經商的要道。由此推想,“音塵絕”者當是征人或商人。如今回望,那“秦娥”,那“眾人”,皆不見了,唯有漢代陵冢于西風殘照中巋然不動。這就是所謂的光陰荏苒,物是而人非。
讀此詞,人心難免悵惘,覺得那秦娥、那眾人,何嘗是在講秦人,何嘗是在講古人,分明可以由古及今,甚至可以衍至未來。生物一代一代,死物則可相對常在。讀此詞,人也不免發出悵嘆:“西風殘照”,李白今又何在哉?此詞之好,好就好在這里,好在沒有具體人物,沒有具體事件,卻有古今之人可能共生的感嘆。
王國維先生《人間詞話》里說:“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漁家傲》,夏英公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范仲淹的《漁家傲》人盡皆知,自不用說,很有氣格。夏竦的《喜遷鶯》云:“霞散綺,月沉鉤。簾卷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清秋。 瑤階曙。金盤露。鳳髓香和煙霧。三千珠翠擁宸游。水殿按涼州。”此詞描寫真宗時期某個清秋時節華燈初上的宮廷夜宴。據《青箱雜記》講,當時夏竦初授館職,真宗舉夜宴,命人去向他索新詞,夏竦聽聞真宗在“拱宸殿按舞”,遂作此詞奉上。由此可見,此詞是應制之作,作者也并未至現場,是憑空想象之筆。周汝昌先生力推夏竦此詞,謂之“音節很美,鏗鏘有力,字字擲地有聲。”不太懂音律者大概無法完全領略此詞之好。夏竦三言兩語便描繪出的宮廷歌舞之況的確有皇家氣派,他的手筆也的確不凡,不過與李白的《憶秦娥》放在一起讀,似仍顯旖旎小氣。(楊蓉)

盛唐三彩女俑,1959年出土于陜西西安中堡村,現藏陜西歷史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