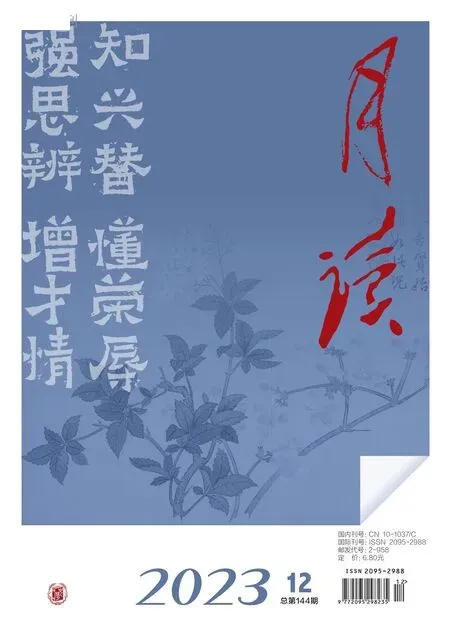讀書人緣何販賣私茶知法犯法?從梅堯臣茶詩說起
◎ 楊多杰

山園茶盛四五月,江南竊販如豺狼。
頑兇少壯冒嶺險,夜行作隊如刀槍。
浮浪書生亦貪利,史笥經箱為盜囊。
津頭吏卒雖捕獲,官司直惜儒衣裳。
卻來城中談孔孟,言語便欲非堯湯。
三日夏雨刺昏墊,五日炎熱譏旱傷。
百端得錢事酒?,屋里餓婦無糇糧。
一身溝壑乃自取,將相賢科何爾當。
—〔宋〕梅堯臣《聞進士販茶》
正如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所說,宋詩真正擺脫唐詩,開始具有自己的氣象,是在北宋建國后半個世紀以后了。第四代皇帝仁宗在位的四十年間,人們才終于意識到,自己已處于完全有別于李唐的新時代。文人漸漸覺得,有必要確立合乎新時代的新詩風。
確立新詩風的中心人物之一,是梅堯臣。
梅堯臣,字圣俞,號宛陵先生,安徽宣城人。他生于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這時北宋建國已將近半個世紀。作為一名文人,梅堯臣在官場一直不得志,年紀很大才入京做了個尚書都官員外郎,所以后人也稱他為“梅都官”。其實這個官職很小。但在梅堯臣的仕途生涯中,這已經算是高光時刻了。
梅堯臣年長歐陽修五歲,二人的交往開始于宋仁宗初年。那時二人還都是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同在洛陽城里作小官。當時梅堯臣已頗有詩名,歐陽修算是他的忠實“粉絲”。隨后的近三十年間,歐陽修的官越當越大,后來做了參知政事;梅堯臣卻一直不得志,只是基層官員而已。二人官位雖然相差懸殊,但歐陽修對梅堯臣的崇拜與尊重卻從未改變。如果查一下二位的集子,可以發現二人之間交換的贈答詩不勝枚舉,歐陽修一直對于梅堯臣贊不絕口。
梅堯臣的詩到底好在哪里,能夠讓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都佩服到五體投地?這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我想關鍵的一點,在于梅堯臣寫作時積極的態度。他絕不滿足效法唐末那些文人,為了瑣事而推敲琢磨浪費時光,而是要在詩作中傾注自己的理想與抱負。他要做到像《詩經》中“大雅”與“小雅”那樣,不但飽含社會意識,而且富于政治批評。
的確,與唐末詩歌相比,梅堯臣的作品呈現出更為開闊的視野。以前很少有人關注的題材,梅堯臣也都細致觀察寫成詩篇。這首《聞進士販茶》,視角就非常獨特。詩里的茶事,不是陽春白雪雅致生活,而是社會熱點世間百態。這首詩諷刺了知識分子的墮落,可視為研究社會史的絕佳資料。
本詩作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這一年梅堯臣五十四歲,為母丁憂,居住在老家宣城。雖然遠離官場,但詩人仍然關心時事新聞。這一年五月的一天,梅堯臣從朋友口中,聽聞了一則怪事—進士販茶。
能考中進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比如梅堯臣才華很高,但早年仍然應試不第,一直考不中進士,最后以恩蔭補官,才得以步入仕途。那么問題來了,進士有直接入仕為官的資格,卻為何要去販茶呢?
這一切,要從宋朝的茶葉貿易講起。在交引茶制下,政府壟斷了茶葉的貨源,切斷了茶葉生產者(即茶園戶)和商人之間的直接貿易聯系。這樣朝廷就會形成茶葉貿易中的壟斷價格,以此獲取巨額利潤;與此同時,由于政府介入商品流通,人為地增加了流通環節,延長了流通過程,帶來了一系列消極后果,其中最嚴重的,便是政府必須付出大筆貿易費用。正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這筆貿易費用肯定會算作成本折入茶價當中。換句話講,最終還是喝茶的人錢包受損。而如果購入私茶,一般是要比官茶便宜得多。私販茶葉,會直接與政府形成競爭。政府要想從茶葉貿易中居間取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一直壟斷茶葉商品的貨源。因此,私販茶葉,在宋代一直是違法行為。
但在利益驅使下,私販茶葉行為屢禁不止,甚至有軍人也加入販私茶的隊伍中。宋太宗時,就已禁止軍人染指茶葉貿易。但開國名將張永德卻罔顧法律,在太原“令親吏販茶規利”。宋仁宗時,御史中丞張方平上疏,指出軍人“趨坑冶以逐末,販茶鹽而冒禁”。
在巨額利益的誘惑下,不光軍人知法犯法,就連進士也參與私販茶葉。換言之,梅堯臣筆下的販茶進士,實際上成了違法亂紀的私茶販子。那么這些販茶的讀書人,到底是利欲熏心,還是另有隱情?我們從正文中來尋找答案吧。
第一部分,自“山園”至“刀槍”句,講的是販茶的猖獗。
對于茶農來說,確實是一年之計在于春。每逢農歷四五月,都是春茶上市的時節。這時候,私茶販子的活動也猖獗起來。那些頑劣的少壯青年,不惜翻山越嶺,到茶山收購佳茗。政府為了打擊私販茶葉,也不得不派出大量緝私官吏。
私販茶葉,說到底是違法行為。所以這些“頑兇少壯”一般還都是晝伏夜出。但是在利益驅動下,他們也不惜武裝販茶。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八月,就曾規定武裝販運私茶者判死刑。所以一旦遇到稽查官吏,販茶隊伍一定會拼死抵抗。在這種茶商面前,政府常常顯得軟弱無力,有時只好采取招降的辦法。宋仁宗年間,“閩人范士舉與其黨數百人盜販私茶,久不能獲”,后來真定府藁城主簿陳昌期靠招安的辦法才解決了問題。陳本人還因此而升官晉職。宋代私販茶葉之猖獗,由此可見一斑。
第二部分,自“浮浪”至“衣裳”句,講的是文人的販茶。
那些浮浪的書生,在利益誘惑下,竟然也私販茶葉。北宋對于販茶,一直嚴厲打擊。雖然自宋太宗開始,一般販茶者已經不必處死了,但是懲罰的力度仍然很大。太平興國年間,對私販茶商的處罰有所減輕,“榷務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五百以下,徒三年;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淳化年間,私販茶葉價值十貫以上,黥面送本州牢城。如果巡防卒私販茶,則加重處罰的力度。
那些文弱書生難道就不怕嚴刑峻法嗎?自然也是怕的。但是讀書人走私,風險會低很多。因為比起那些看起來就很頑兇的亡命徒,書生看起來更有迷惑性。笥,音同四,是竹制的箱子,史笥經箱,代指書箱。他們用書箱裝茶,往往能夠逃避關卡的盤查;即使被抓了個現行,受罰程度也輕得多。宋代尊重讀書人,總要網開一面。正如詩中所說,官員在審判時總會對讀書人減罪處罰。這些浮浪書生,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干脆把“儒衣裳”當作了護身符。
第三部分,自“卻來”至“旱傷”句,講的是文人的墮落。
這些人被釋放之后,仍不思悔改。他們動輒大談孔孟之道,可有時又貶損堯湯這樣的圣君。一邊大談孔孟,一邊貶損堯湯,這些利欲熏心、表里不一之徒,除去夸夸其談,什么也不會做,什么也不肯做。雨天怕淋,晴天怕曬,整天游手好閑,騙吃騙喝。這些人既缺乏勞動者的勤懇樸實,又喪失了讀書人的社會擔當,成為了社會的渣滓。
第四部分,自“百端”至“爾當”句,講的是墮落的下場。
這些人非法牟利,又不免紙醉金迷隨意揮霍,對于家里的老婆孩子卻一概不管,任憑他們挨餓受苦。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真可謂一字不占。他們游走于法律的邊緣,自然也不會有好的結果,最終不免喪身于溝渠,真可說是咎由自取。至于金榜題名封妻蔭子,就更與這些人無緣了。
這首茶詩把一些儒生偽君子的面孔刻寫得入木三分,讀之令人拍手稱快。與此同時,亦足以看出梅堯臣詩歌創作題材廣泛,具有社會責任感。這樣宏大的格局,在晚唐五代的詩歌中是很少見的。
就著梅堯臣的這首茶詩,我們不妨再多討論幾句茶事。茶葉“走私”,不僅減少了政府收購茶葉的貨源,對政府控制茶園戶和茶葉生產也產生了不利影響。更重要的是,私茶占領了市場,堵塞了官府茶葉貿易的流通渠道,從而造成了官府茶葉積滯難銷。但私茶販賣現象為什么屢禁不止?違法者的利欲熏心自然應該口誅筆伐,但更重要的是,宋代官府茶自身的質量實在太差,給了私茶可乘之機:一方面,茶葉貯運時間過長,一旦管理不善,極易腐敗變質。商人為己圖利,自然不敢絲毫懈怠;但是官員辦事,難免玩忽職守。正如宋人所說:“國家榷買茶貨,歲入無窮,堆貯倉庫,充積州部,及乎出賣之際,則大半陳腐。積年之后,又多至焚燒。”在官僚作風盛行的宋代,這種效率低下的情況尤其嚴重。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按收購茶葉數量的多寡對山場官吏加以獎懲,導致了官吏在收購茶葉過程中,片面追求數量而忽視了產品質量。他們經常對茶園戶的摻雜施假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以這樣的態度,怎么可能制出好茶。
其實這一點,宋人已有深刻體會。王安石曾犀利地指出:“而今官場所出,皆粗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官場所出茶葉,因粗惡難食而被私茶所排擠。私茶價格較高,卻仍然深受消費者歡迎。什么原因?答:私茶質量過硬。
按理說官茶有朝廷“背書”,更應該受消費者信賴。但是實際情況,卻是官茶滯銷,私茶暢銷。面對市場的巨大需求,進士都耐不住寂寞,要摻和到私販茶葉的活動中。
由此可見,金獎銀獎,不如愛茶人的褒獎;金杯銀杯,不如愛茶人的口碑。
茶湯好喝,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