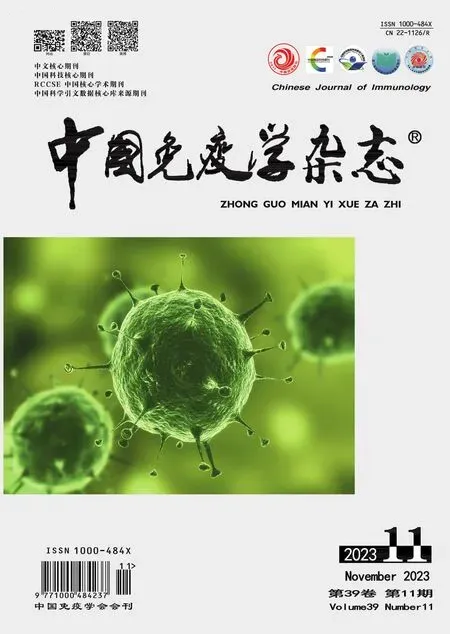腫瘤立體定向消融放療聯合免疫治療的研究進展①
趙 剛 涂甲丁 卜嘉蕊 王然玉 張書涵
(吉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放射生物學重點實驗室,長春 130021)
1 立體定向消融放療的概念
立體定向消融放療(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SABR)又稱體部立體定向放射治療(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SBRT)、立體定向放射外科(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SRS)等[1],本文以下統稱SABR。SABR 是一種有效的大分割、短療程的非侵入性消融治療。SABR 與常規分割放療(每日劑量1.8~2.5 Gy)或大分割放療(每日劑量3~6 Gy,常用于臨終姑息治療)不同,SABR 是在復雜影像引導技術的支持下對腫瘤靶點進行每日可高達8~30 Gy消融劑量的治療,分割次數也大大減少(1~5次)[2-3]。由于其良好的局部控制和耐受性,SABR 目前在許多癌癥的治療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如頭頸部癌癥、非小細胞肺癌、肝癌、胰腺癌和腦瘤[3-4]。
2 SABR與腫瘤免疫的關系
傳統的放射生物學理論主要側重于射線作用于細胞DNA,引起雙鏈斷裂、單鏈斷裂等損傷,最后導致有絲分裂災難和細胞凋亡[5]。現在有大量證據表明,SABR 也具有強大的免疫調節作用,協調了一系列細胞和分子的改變,最終增強了全身抗腫瘤免疫反應。腫瘤細胞通常都進化出了防止細胞死亡被識別為免疫原性的策略,而SABR 恰恰增強了腫瘤的免疫原性,從而誘導腫瘤細胞發生免疫原性細胞死亡(immunogenic cell death,ICD),這種ICD 是通過腫瘤細胞凋亡和壞死的細胞碎片產生的腫瘤相關抗原(tumour-associated antigens,TAAs)大量釋放介導的[6-7]。這些凋亡或壞死的腫瘤細胞也釋放大量的“促炎危險信號”和“損傷相關模式分子(damage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如:熱休克蛋白、高遷移率族蛋白(high-mobility group protein B1,HMGB1)[8-9]。DAMP 和“促炎危險信號分子”通過與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s,DCs)表面Toll 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TLR)結合,增強DCs的抗原遞呈作用,將TAAs 更迅速準確地傳遞給腫瘤特異性細胞毒性T 淋巴細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s,CTL)[10-11]。以HMGB1為例,HMGB1是一種組蛋白-染色質結合蛋白,是一種重要的ICD 標志物,SABR 引起腫瘤細胞發生ICD 后,HMGB1 被大量釋放,釋放出來的HMGB1與DCs表面的TLR4和TLR9結合,進而激活髓樣細胞分化初級反應蛋白(myeloid differentiation primary response protein 88,MyD88)信號通路和NF-κB 信號通路,最后導致DCs成熟、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major histocompatiblity complex,MHC)分子上調、共刺激分子表達上調,所有這些改變都有利于DCs 將腫瘤細胞遞呈至CTL,從而實現對腫瘤細胞的特異性殺滅[12]。SABR 還進一步增強腫瘤細胞的鈣網織蛋白(calreticulin,CRT)移位到腫瘤細胞膜表面,這種細胞膜表面移位的CRT 進一步增強了CTL 對腫瘤的識別和殺傷作用[13]。研究證實,這種CRT 移位是SABR 誘導腫瘤ICD 的重要環節[14]。最后,SABR 還上調正常組織和腫瘤組織表面的MHC-1 表達,從而增加抗原遞呈,促進了CTL 對腫瘤的殺滅作用[15]。以上所有的SABR 作用誘發了機體的抗原特異性、適應性免疫反應,相當于原位疫苗接種的效果,有利于機體免疫系統迅速準確地清除局部腫瘤。
SABR 除了對腫瘤細胞和免疫細胞的直接作用外,還對腫瘤微環境造成影響。通常情況下,腫瘤組織總是處于一種免疫抑制的微環境中,形成這種免疫抑制,甚至“免疫沙漠(immune desert)”狀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某些腫瘤缺乏產生有效抗原遞呈所必需的炎癥介質,導致CTL 無法向腫瘤周圍靠近,腫瘤的脈管系統也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阻止T細胞向腫瘤組織浸潤,而SABR 恰恰逆轉了這種免疫抑制狀態[16]。研究證實SABR 誘導照射局部的炎癥性趨化因子高表達,如:趨化因子10(C-X-C motif chemokine 10,CXCL10)和CXCL6,從而導致CD4 和CD8陽性T淋巴細胞向腫瘤灶聚集[17-18]。SABR也與腫瘤血管相互作用,上調腫瘤局部血管的黏附分子,如血管細胞黏附分子1(vascular cell adhesion protein 1,VCAM-1)和細胞間黏附分子-1(intracellular adhesion protein 1,ICAM-1),這些黏附分子均為促進白細胞局部浸潤的關鍵因子,SABR 還誘導微血管損傷,有利于免疫細胞在腫瘤的局部浸潤[19]。SABR 還對腫瘤微環境中的巨噬細胞產生影響。巨噬細胞分布廣泛,在先天免疫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巨噬細胞可分為不同亞型,通常分為M1 型和M2 型,M1 型屬于促炎型,M2 型屬于抗炎型,M2 型也是腫瘤微環境中誘發免疫抑制的重要因素。研究顯示,SABR 能夠誘導腫瘤微環境中的M2 型巨噬細胞向M1 型轉化,從而解除腫瘤的免疫抑制狀態[20]。綜上,SABR 促進抗腫瘤的CTLs 向腫瘤微環境聚集和浸潤,抑制了腫瘤逃逸作用,增強了局部免疫介導的抗腫瘤作用。
除了這種局部殺滅作用,SABR 對腫瘤還有一種“遠端效應(abscopal effect)”,主要表現為局部照射后遠處非照射野腫瘤的消退[21-23]。目前,廣義遠端效應是指局部放療后,在距照射區一定距離的非照射區產生的全身性效應,包括轉移瘤效應和正常組織損傷兩種形式。前者指腫瘤局部照射后導致遠處腫瘤的消退。在臨床中,肝細胞癌、乳腺癌、甲狀腺癌、淋巴瘤、宮頸癌和黑色素瘤等其他轉移性實體腫瘤類型均可發生遠端效應[24]。但單獨放療引起的遠端效應較為罕見,且大部分遠端效應主要發生在腎細胞癌、黑色素瘤和淋巴瘤等免疫原性腫瘤中[25]。值得一提的是,轉移瘤多在放療后幾個月消退,表明腫瘤消退不是單一事件的結果,而是在一段時間內接受持續不斷的攻擊所致。目前認為這種作用主要是通過免疫介導的不同細胞殺傷機制清除腫瘤的結果[26]。此外,正常組織損傷包括誘導正常組織中的基因不穩定性、細胞死亡和致癌轉化[27]。對正常組織毒性機制的研究表明,免疫反應,尤其是炎癥反應,在電離輻射暴露誘導的早期和晚期副作用中起關鍵作用[28]。
3 與SABR 聯合應用的腫瘤免疫治療的研究進展
單獨應用SABR,其誘導的ICD和遠端效應都很少發生。這是因為腫瘤一般處于一種免疫抑制的微環境中,且腫瘤周圍往往淋巴細胞浸潤不充分,免疫細胞很難發揮作用[29]。這就要求SABR 與一些免疫調節制劑聯合應用,這些免疫調節制劑按照其機制主要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激活抗原遞呈細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s,APCs);第二類是清除T細胞抑制信號[30]。分述如下:
首先是激活APC 的免疫調節制劑。TLRs 激動劑和CD40 單克隆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mAb)屬于這一類調節劑。CD40 mAb 能夠刺激DCs 的抗原遞呈作用和淋巴結轉移,CD40 mAb 已經在一些腫瘤治療的臨床前動物模型和早期臨床試驗中得到應用[31-32]。在一項B 細胞淋巴瘤小鼠實驗中,CD40 mAb 聯合5 Gy 全身照射,收到了良好的抗瘤效果,作者分析這種聯合的效果可能來源于全身照射,誘導腫瘤細胞發生凋亡,并釋放TAAs,同時腫瘤生長速度放緩,而CD40 mAb 的應用使TAAs 更迅速準確地傳遞給CTL,從而發揮CTL 的腫瘤殺傷作用[33]。TLR是一個廣泛表達于造血細胞上的模式識別受體家族,包括APC、單核細胞和B 細胞,TLR 能夠識別DAMPs,觸發先天免疫,并促進適應性免疫的發展。人類TLR 家族有10 個亞型(TLR1~TLR10)[34]。人和鼠的不同DC 細胞亞類表面表達不同的TLRs 亞型[35]。TLRs 激動劑聯合SABR,在臨床前動物模型中收到了良好的抗瘤效果[36-37];更令人鼓舞的是,在B 細胞淋巴瘤患者的臨床研究中,TLRs 激動劑聯合放療,也觀察到了遠端效應[38]。TLRs激動劑的作用是激活TLRs下游的MyD88信號通路,導致轉錄因子NF-κB 入核,從而促進DCs 成熟,上調MHC分子和共刺激分子表達。
其次是清除T 細胞抑制信號類的免疫調節劑。CTLA-4(CTL antigen 4)是表達于T 細胞表面的關鍵抑制類信號分子,能夠與DC 或其他APCs 細胞表面B7 家族的CD80 或CD86 配體結合,從而抑制T 細胞激活[39]。研究顯示,封閉CTLA-4 可增強SABR 的原位疫苗接種效果,有利于CTL 局部清除腫瘤,并增強免疫記憶,防止腫瘤復發[40-41]。放療聯合ipilimumab,一種專用于封閉CTLA-4 的單克隆抗體,已經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上市用于治療轉移性黑色素瘤,收到了良好的療效[42]。程序性死亡受體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是另一類表達于T 細胞表面的關鍵抑制類信號分子。很多腫瘤細胞表面表達PD-1 的配體,包括PDL1 和PD-L2,從而逃避機體的免疫攻擊。美國FDA已經批準多款針對PD-1 或PD-L1、PD-L2 的中和抗體類藥物用于治療各種PD-1 陽性腫瘤,在此不贅述。研究表明,放療后PD-1/PD-L1 表達均上調,這可能是誘發腫瘤放療抵抗的因素之一,因此在放療同時應用PD-1/PD-L1 中和抗體就顯得更有必要[43]。進一步研究顯示,SABR 與PD-1 或PD-L1 中和抗體和CTLA-4 中和抗體聯合應用,其作用優于任何一種或兩種單獨應用的效果,其可能的機制是這三種療法互為補充,發揮了相互促進的協同作用[44]。屬于清除T 細胞抑制信號類的免疫調節劑還包括抗CD137的mAb、抗OX-40的抗體、IL-2、吲哚胺2,3加雙氧酶1(indoleamine 2,3 dioxygenase 1,IDO1)抑制劑和TGF-β 中和抗體等,可喜的是,這些免疫調節劑與放療聯合應用抗腫瘤的試驗都在進行中,其中很多收到了良好的療效[45-53]。
4 尋找最佳的SABR 與免疫治療的組合方式
大量臨床前動物實驗和臨床試驗表明,SABR與免疫調節劑聯合應用前景廣闊。在這兩類免疫調節劑中(激活APC 的免疫調節劑和清除T 細胞抑制信號類的免疫調節劑),激活APC 的免疫調節劑在與SABR 的聯合應用中顯得更為關鍵,因為成熟的APC 可能在腫瘤微環境中發揮有益的多重功效,與SABR 或/和刺激T細胞的藥物發生多重抗腫瘤的協同作用。因此,免疫調節劑與SABR 究竟應該如何聯合應用顯得更為重要。例如:應該先用藥還是先照射,還是給藥的同時給予照射?SABR 后腫瘤釋放TAA和/或DAMP在人體的動力學尚不明確,相關的體內動物實驗和體外細胞實驗表明,SABR 后腫瘤細胞在8 h 內發生死亡,24 h 達到峰值,這種輻射引起的腫瘤細胞死亡會持續至少7 d[54-55]。研究表明,照射18 h 后Ⅰ類MHC 開始增加,這種增加趨勢會持續到照射后的第10 天[56]。激活APC 的免疫調節劑TLR 激動劑和小分子的CD40 激動劑半衰期均較短,48~72 h 內生物活性基本消失[57]。因此,這類藥物的給藥時間需非常精確地計劃,以配合腫瘤抗原釋放的峰值[58]。相對來說,CD40抗體和其他一些大分子類藥物半衰期更長,生物活性持續時間更久,SABR 和給藥時機的配合可以更寬松一些[33]。第二類免疫調節劑即清除T 細胞抑制信號類調節劑,按照其作用機制推測,應該遵循先給藥后照射或給藥和照射同時進行的順序,因為先給藥解除了T 細胞抑制信號,隨后照射誘發的原位疫苗接種效果產生的大量TAA 或DAMP 經APC 遞呈給被激活的T細胞,從而達到殺滅腫瘤的效果。當然,該領域還需要更多更詳實的動物和臨床試驗結果的支持,也需要更客觀的觀測終點指標[30]。另外,SABR 的照射劑量和分割次數也對療效至關重要。研究證實,大劑量照射才能發揮良好的原位疫苗接種效果,7.5~15.0 Gy 劑量范圍內效果最佳。而分兩次照射,每次7.5 Gy,控瘤效果最佳,T 細胞介導的腫瘤殺傷作用最佳,Treg細胞比例最低[59]。當然,這個劑量也不是黃金標準,各組照射劑量和照射次數與用藥的組合都在測試中,針對不同的免疫調節劑,照射劑量和次數也需進行相應調整,以達到最佳的抗瘤效果。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照射劑量和次數與腫瘤的部位、大小、類型、腫瘤周圍正常組織對照射的耐受程度等因素均密切相關。在SABR 治療的納入標準中,患者的轉移灶不能超過5個,而能夠同時進行SABR 治療的部位不能超過3 處。另外,既然SABR 照射的作用是產生原位疫苗接種的效果,那么是否可以出于安全考慮,照射野不必覆蓋整個腫瘤,局部照射是否就能產生同類效果,這一領域還需要深入探索[30]。
5 小結與展望
無論是放療引起機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還是放療與免疫調節劑聯合應用都不是嶄新的概念,相關研究已經在實驗室進行多年。近年來,隨著科學界對T 細胞在抗腫瘤免疫中的深刻認識,特別是免疫檢測點抑制劑和嵌合抗原受體T 細胞免疫療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CAR-T)在臨床應用中取得巨大成功,SABR 與免疫檢測點抑制劑聯合應用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SABR相當于原位疫苗接種,誘發腫瘤釋放大量的TAA 和DAMP,免疫檢測點抑制劑能夠清除T 細胞抑制類信號,從而激活T 細胞更高效地發揮抗腫瘤作用。此外,SABR 與免疫檢測點抑制劑的聯合應用,幾乎都會誘發抗腫瘤的遠端效應,對照射野外的轉移瘤也發揮良好的療效。因此,SABR 與免疫調節劑聯合應用的研究方興未艾。但這種聯合治療也同樣面臨諸多挑戰,例如究竟該如何聯合,如何挑選適應癥,如何準確迅速地評價療效等,這些方面還缺乏國際公認的標準。因此,這方面的基礎和臨床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將有利于早日制定針對不同腫瘤的SARB和免疫治療聯合應用的標準化治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