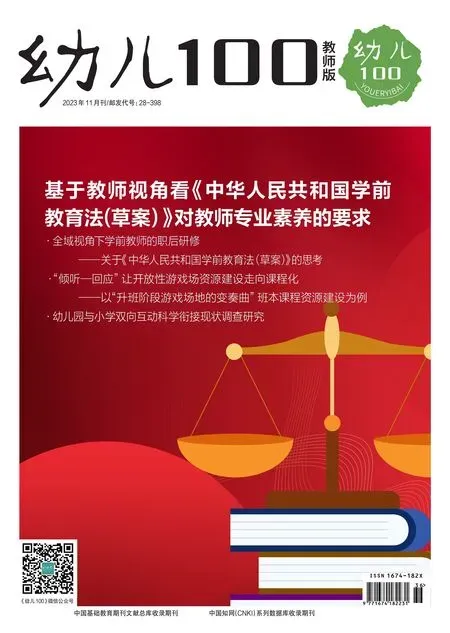繪本里的“壞孩子”:兒童成長中的心理陪伴
文/金雨萱 江蘇省南通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借助繪本中正面人物的榜樣作用,引導兒童形成正確的是非觀,是很多家長、幼教工作者的共識。比如我國情商培養繪本系列中《我不怕失敗》《不哭也能解決問題》等優秀作品都是“正念”兒童行為的典范作品。但生活是面多棱鏡,兒童生來不同,有些兒童因為家庭、社區等復雜環境的影響,性格孤僻、行為怪異;亦或有些兒童天生就很“奇怪”,卻擁有特異的潛能。在常人眼中,他們的行為不可思議,甚至閃光點也被忽視,比如“充沛的生命力”“敏感的內心”,但他們并非品德低下、頑固不化,成人卻片面地把他們定義為“壞孩子”“熊孩子”。不過有些作者,如伯寧罕,開始關注這類少數群體,創作出《愛德華--世界上最恐怖的男孩》《丑狗辛普》這類非常規正面形象,“正視”兒童的不完美,以期讓現實中的“好孩子”了解差異、尊重個體,讓現實中的不完美兒童--“壞孩子”產生皈依感,基于對作品角色的身份認同,感到被看見、被接納,以此愉悅情緒和轉化行為,逐漸形成“正確”的價值觀。
一、承認“壞孩子”:了解“壞因”,靠近“善果”
兒童與兒童,生來不一樣,但都獨一無二、值得尊重。有“好孩子”就會存在“壞孩子”,不過,先別急著給兒童貼標簽。兒童天生就有生本能與死本能,生本能保持種族的繁衍與個體的生存;死本能則派生出攻擊、破壞、戰爭等毀滅行為。生本能讓兒童呈現宜人、積極的面貌;而負面情緒和怪異行為則是死本能在作祟,生、死本能之間相互沖突、轉化和妥協,造就了每一個獨特的兒童。兒童發展就是不斷達到更高水平的平衡,與別人不一樣不是什么錯,可通過不同的路徑選擇成為有價值的人。因此,讓我們靜待成長,重視了解差異化的“壞因”,幫助兒童靠近“善果”。只呈現正面的故事,是對兒童個體差異的不尊,若加入多元化的“壞孩子”角色能讓兒童對自己、對他人有更多認知,有助于兒童積累經驗、明辨是非,后續形成自己的價值判斷,特別是繪本中有某方面不足,甚至殘缺的兒童,不要輕易定義他們,而要真真切切站在他們的立場,了解“壞因”,引導兒童與之共情,充分使用文學作品的育人功用。正如趣味圖像繪本大師賴馬的繪本《我變成一只噴火龍了!》中,阿古力無法及時控制情緒,變成了一只噴火龍,只要一開口,就會有火冒出來,鼻子里的火更是二十四小時噴個不停,無法吃飯,無法刷牙,甚至連鄰居也慘遭他的毒火。在閱讀時,我們很容易給阿古力貼上“壞孩子”的標簽,但阿古力為什么生氣呢?兒童也許會注意到,在故事的開始,阿古力一大早就被蚊子波泰叮了一個包,所以他很生氣。成人的目標導向,可能更注重如何緩解壞情緒,以便在現實中運用,但也需了解壞情緒產生的原因,正視壞情緒,允許兒童合理地抒發壞情緒,這才有利于兒童的心理健康。
二、認識“壞孩子”:辨識“本我”,賦能“超我”
“壞孩子”繪本有利于兒童辨識“本我”。兒童具有吸收性的心智,給兒童創造什么樣的環境,兒童將會運用其驚人的模仿能力從外界汲取能量。在親子共讀《大衛,不可以》時,淘氣的大衛在游戲時差點將魚缸打翻,危險地站在椅子邊緣只為拿到餅干桶,在外面滾了一身泥巴,把家里的地板踩臟,洗澡時把水弄得滿屋子都是,光著身子跑出門外……他的行為讓成人頻頻搖頭,媽媽經常對大衛說:“大衛,不可以!”兒童眼中,繪本中媽媽的“不”和現實中父母的“不”無限重合,兒童產生代入感,理解大衛,引發兒童對自己日常行為的思考。“壞孩子”繪本給兒童提供了看見錯誤的機會,通過他人的故事理解犯錯后果及家長的看法。或許家長已經注意到,《野獸國》的最后,馬克斯和野獸再見,乘船回到了家,餐桌上有熱乎乎的晚飯等待他;《大衛,不可以》中,大衛最后明白自己的錯誤,媽媽沒有再批評他,而是給予大衛溫暖的擁抱。這類繪本讓兒童逐漸意識到,犯錯誤很正常,只要認識到自己的不足,爸爸媽媽會陪伴他一起面對。
“壞孩子”繪本讓兒童發現潛能。榮格認為,不同的我擁有不同的世界,意識的我擁有現實世界,而另一個我,夢想中的我擁有現實世界之外的另一個世界,夢想中的我無時無刻不在與集體無意識對話。兒童的“夢想我”是如此發達,他們認為萬事萬物皆有靈,小世界里充滿了幻想,這些奇思妙想是非理性的、主觀的,以自我為中心。兒童在兩個世界自由地遨游、游戲,即非理性活動,是溝通兩個世界的橋梁。“壞孩子”游戲便是在兒童水平基于夢想而對現實世界的探索,或許,也是未來兒童想象力、創造力的來源。正如漫畫家朱德庸,他小時候設法讓蜘蛛打架,用瓦斯急凍蜜蜂然后剪去它們的尾針,不斷按別人家的門鈴再逃走……后來這些童年的游戲經歷竟成為其漫畫的靈感來源。不僅漫畫如此,創造神話、童話、藝術、游戲都需要有非理性成分的參與。因此,在童年賦予兒童夢想的權利,看見兒童的“壞”,給予兒童“使壞”的機會,這些看似“壞”的活動中可能就藏匿著兒童獨特的天賦。無需害怕兒童總是保持在這一水平,因為成人會給他提供獲得更多高尚、滿足需要的知識和技能,而兒童本人亦有追求更為高級、更為高尚的生活本能。
三、轉變“壞孩子”:平衡“生長”,形成“個性”
兒童的社會化是兒童適應人類社會的必經之路。社會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自然界與社會具有一體性,兒童的個性和社會性發展也有重合部分,兩者并不沖突。因此,在社會化的同時,善待自然給我們留下的野性力量--“動物性”,不斷引導其向個性轉化,這才是題中應有之義,正如,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讓兒童適應眼前的環境,過好當下的生活,滿足其當下的興趣與需要,隨之,兒童便自然生長出應對未來、應對社會的能力。繪本中“壞孩子”主角并非是品德低下、野馬無韁,而是經過精心設計,真實生活中存在的,他們展現出不配合大人的特質,也有自己的小小苦惱,他們“壞而不惡”,這些生動的角色給一些不斷尋求社會認同的家長和孩子喘息的空間。正如《和甘伯伯去游河》,一對兄妹和很多小動物想和甘伯伯一起去游河,甘伯伯給他們提出了一些游船規則,小孩和動物們都滿口答應,但一上船卻又出爾反爾,最后船都翻了……《我是個小孩子,我喜歡假裝聽不見》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小女孩,她總喜歡假裝聽不見,父母叫她起床、刷牙、吃早飯、和客人打招呼……這些她都不愿意做,但是喊她去游樂園,她一下子就蹦起來了,她喜歡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兒童在看這些書的時候一定會產生共鳴,會迫不及待地往下讀:為什么不想聽爸爸媽媽的話?原因和我一樣嗎?在這些繪本里,他們或許尋求到了認同,也許發現自己的行為會給他人造成麻煩,從而愿意改變,這才是兒童社會化的現實途徑--“主動模仿”。
兒童是獨特的存在,體內蘊含著獨特的力量,對兒童抱有一顆敬畏的心,打破“好孩子”準則,承認繪本中的“壞孩子”,給予兒童主動選擇、自由生長的權利。在成人的“正視”差異與“正念”指引下,最終都會創造出應對這個世界的獨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