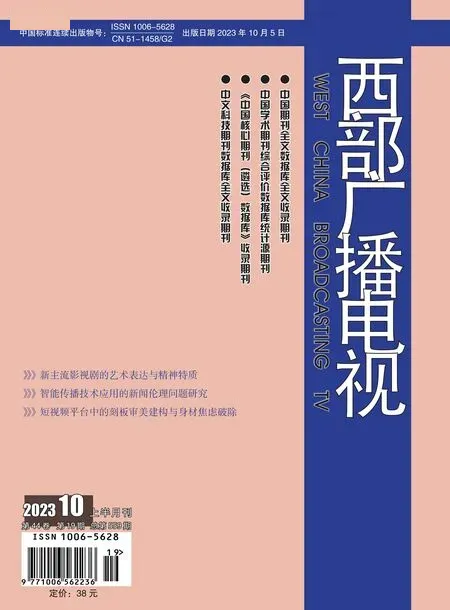“集體記憶”理論視域下《長安三萬里》的敘事研究
張金芳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
“集體記憶”最早由哈布瓦赫在《論集體記憶》中提出,集體記憶是“一個特定社會群體之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1]70。集體記憶往往由群體成員通過特定情境的敘事一致性來實現,并附著在符號和媒介上,使集體記憶得以留存和延續[2]。電影是構建集體記憶的重要方式,通過視覺畫面、聲音配樂、人物對白等形式,不僅可以利用技術手段再現歷史面貌,使集體記憶不斷被喚醒與復活,還可以對大眾的記憶能動地進行改造,減少與當前主流意識形態的分歧,增強民族認同感與凝聚力。電影《長安三萬里》上映僅16天,累計票房已經超過11億。該電影借唐代詩人高適之口,講述了“詩仙”李白從青年到老年跌宕起伏的半生,以及唐朝由盛轉衰過程中一系列重要的史實。
1 符號:激活記憶探索的密鑰
對集體記憶的建構、喚醒和改造,無法在受眾間自發產生,需要以各種符號為線索打開人們探索記憶的通道和路徑,這些符號往往是人們對文化共有的印象。
1.1 器物符號:召喚集體記憶的歷史細節
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器物景觀,電影中通過對這些器物的再現,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與景觀特點,建立起與大眾的認知和記憶相吻合的小世界,避免因為場景構建的錯位導致認知不協調,從而削弱電影構建集體記憶的功能。
《長安三萬里》中復刻了大量考古出土的唐朝文物,玉真公主發簪的花飾原型是唐朝鎏金銀飾中的綬帶形簪、Ⅱ式花飾;玉真公主和岐王欣賞高適的槍舞時,身后的屏風畫還原了唐朝畫家李昭道的《曲江圖》;李白在曲江酒樓飲酒作詩用的酒杯,仿照了鎏金仕女狩獵紋八瓣銀杯;李白朗誦《將進酒》,與朋友把酒言歡時出現的酒碗,是唐朝的鴛鴦蓮瓣紋金碗;李白營救郭子儀時戴的帽子,與唐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彩繪灰陶參軍戲俑戴的帽子極其相似。不同的器物展示了不同時代的風貌。影片中這些高度還原的器物,與人們心中對繁華盛世的想象逐漸重合,激活了人們對中國古代地大物博、文明高度發達的記憶,民族自信心油然而生。
1.2 詩詞符號:構建集體記憶的獨特語言
唐朝詩詞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有著獨特的民族烙印,對于沒有詩詞記憶的人來說,很難感應到相同的文化感召。獨有的詩詞符號作為內部的通用語言,區別了“我們”與“他們”的身份,有利于“自己人”放下偏見與分歧,打破構建集體記憶的壁壘,因共有的文化價值觀而形成有機團結,增強民族向心力。
《長安三萬里》用48首詩歌串起了李白的浮沉身世和大唐命運的跌宕起伏。欲往黃鶴樓上題詩的青年李白,看到崔顥的《黃鶴樓》棄筆而去,展現了他年少輕狂的一面;中年李白與友人縱情詩酒,吟了一首如夢似幻的《將進酒》,縱使豪情壯志也難抵現實的殘酷與世俗的偏見;李白看似放浪形骸,實際上他對朋友用心良苦,比照著高適寫出了“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的豪爽詩句;李白一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展現的是劫后余生的歡娛和包容歲月的胸襟。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詩句被電影重新演繹之后,原本零散的個體記憶被整合成了群體共有的集體記憶,加深了大眾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感。
1.3 儀式符號:強化集體記憶的神圣事件
在建立集體所認可的一整套行為方式和群體之間溝通的途徑時,儀式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傳播過程是各種有意義的符號形態被創造、理解或使用的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3]。因而,這個過程也稱為“分享意義的文化儀式”。電影中往往通過塑造或再現各種儀式來展現社會規則與時代特色,借儀式或程序之下人物的思想和行為表現,讓觀看者受到感召,仿佛與角色同處于一個儀式之中,產生情感共鳴的同時,某種價值觀和集體記憶得到強化。
《長安三萬里》中出現的儀式主要是各種場面熱鬧非凡的宴會,可以說李白的經典詩作大多是在宴會上酒到正酣處的真情流露。宴會也是串起整部影片的重要線索和情節,曲江酒樓的夜宴、岐王府里的晚宴、裴十二家的宴席、李白入道后與友人的慶祝宴等都是比較隆重的儀式。影片中的這些儀式為觀眾帶來了極具視覺沖擊力的盛宴。一方面,浪漫灑脫的詩人群體投射出了唐代文化發展的繁盛;另一方面,在封建等級制的禁錮下,李白等人只能收斂鋒芒,反映出了唐代社會由盛轉衰的文化癥結所在。電影里的儀式成了歷史最精美的包裝,讓記憶中平淡的史實變成了神圣的事件,大眾在頂禮膜拜的同時,探索儀式背后的社會意義,并將其內化為集體記憶。
2 敘事:串聯集體記憶的線
2.1 還原與改寫:“歷史”與“現實”的調和
馬克·費羅指出,“電影是‘人類歷史的代言人’”[4]。電影媒體作為記憶產業的一種,生產各式表征,用以鼓勵我們去思考、感知和認同過去[5]。電影如果要發揮這樣的功能,首先要按真實情況再現過去,提供召喚集體記憶的線索和場景。電影《長安三萬里》中大多數事件、場面是符合歷史記載的,如膘肥體健的馬匹、“身長腿短”的男子、體態豐腴的女子等,都是參照唐俑的造型特點設計出來的,高度重視對歷史細節的還原。
但是,隨著時空的流轉,大眾的集體記憶在漫長的消磨中已經逐漸模糊和消退,是難以通過相對確定的敘事喚起和重構的,再加上影像的敘述者本身也有著不同的個體記憶和情感價值取向,“耦合、想象、轉借是必不可少的”[6]。歷史上沒有明確證據證明,高適曾請求郭子儀對身陷牢獄的李白伸出援助之手,但為了與影片家國情懷的敘事框架相契合,制作團隊設計了高適暗中找郭子儀救李白的情節;歷史上唐朝長安城實行的是“坊市制”,街上一般是沒有商店的,而電影則將長安城打造成了宋朝街市的模樣,以突顯城市的熱鬧繁華。電影對歷史進行的“再呈現”和“再敘事”,不過是在“按‘當下’的需要和尺度在酌情取舍”[7]。哈布瓦赫認為,我們關于過去的概念,是受我們用來解決現在問題的心智意象影響的[1]59。實際上,集體記憶就是基于現在的處境對過去的一種總結與再現。
2.2 奇觀化:藝術化的視覺呈現滋養集體記憶
“影像的奇觀化是指利用電影獨特的聲畫視聽手段,以視覺呈現的方式,極力營造超越日常生活經驗之外的視覺盛宴。”[7]《長安三萬里》運用技術對許多場面進行了“奇觀化”的呈現,影片通過豐富的色彩、精美的構圖、鮮明的東方審美,呈現出了“山頂千門次第開”的錦繡長安、“白云千載空悠悠”的黃鶴樓、“兩岸猿聲啼不住”的三峽奇景,以及梁園、潼關、松州、薊北的風光,都像是精致的工筆畫,這些“場面不再作為敘事發揮功能的附庸,而是成為具有獨立價值的視覺要素”[8]。
其中,最為震撼的情節當屬李白吟誦《將進酒》的部分,李白拉著他的好友乘白鶴騰空起飛,穿過激蕩的江河,飛越璀璨的星河,直登仙宮,汪洋恣肆。此外,電影還運用了古畫、水墨、炭筆等方式體現獨特的東方意境與中國韻味。這些場景結合了靜態和動態的3D動效,借助阿里云的云端運算,實現了電影的高效渲染,將最新的動畫技術和中國美學相結合,呈現出唐代文化恢宏昂揚的氣度與風貌。同時,影片打造了極具想象力的滋養集體記憶的場域,在奇觀的渲染下,大眾加深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
3 集體記憶是對現實的投射
電影并不能與真實的歷史面貌等同,為了增強歷史敘事的流暢性,電影中往往會融入當下的主流意識形態,或多或少都摻雜了想象與虛構的話語。想象性重構的記憶只有加入現代的邏輯,才能被塑造為大眾所認同的集體記憶。導演在將集體記憶和歷史創傷轉換為電影敘事本身的同時,不僅在敘述中重建了過去,還將人物的悲歡離合與現實苦難緊密地聯系在一起[9]。通過對內容進行情感賦能,引起觀者強烈的共鳴,使大眾的情緒和壓力得到釋放。
《長安三萬里》片名中的“三萬里”,隱喻的是同李白、高適等類似的“普通人”與夢想之間遙遠的距離。影片中,李白因為商人的身份,仕途之路坎坷;高適家門落敗,46歲才得到朝廷重用。這樣的遭遇讓現實中的“小鎮做題家”“躺平青年”“佛系青年”也能有所共鳴。雖然現實與理想之間距離遙遠,但“躺平”與“佛系”并不意味著放棄與妥協,而是另一種深層的抵抗。李白與高適都通過對人生真諦的不斷追尋,予以觀眾指引。同時,影片中塑造的李白和高適的“高質量友誼”也是現代人所向往的,為了赴與李白的一年之約,高適如期趕往揚州;因為李白的一句“速來”,高適重新回到長安,盡管李白早已忘了對他的邀請,高適依然理解他、包容他。電影所呈現的古人的社交模式與當代人多線程、并發式的倦怠型社交不同。現代社會中,社交媒體搭建了一個巨大的“圓形監獄”,人們透過他人的目光“圍觀”與“規訓”自己,逐漸失去了人際傳播時代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純粹與真誠。對“高質量友誼”的圍觀,使大眾能“移情”到李白和高適身上,沉浸式地感受知己之情所帶來的精神滿足,感嘆于古人精神境界之高,從而積極主動地接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并將這份記憶轉化為指導現實社交的指南。
4 集體記憶是構建民族文化認同的基石
阿爾都塞提出,意識形態的首要功能就是能夠將個體詢喚為主體[10]。電影通過精彩的呈現使大眾在全神貫注投入的狀態下,認同電影所傳播的價值觀念,主動接受主流意識形態的詢喚,完成“獲得自己是誰的感受”的過程。電影《長安三萬里》中,青年時期的李白與好友多次表達過自己的雄心壯志,通過“你我身當如此盛世,當為大鵬”“大鵬終有直擊云天的一日”“大丈夫當報效國家,建功立業”等話語來喚起觀眾同樣的情緒。在這個過程中,電影就是意識形態實體,觀眾就是被詢喚的個體。觀眾不僅被喚起了對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集體記憶,還產生了強烈的文化認同。
亨廷頓認為,不同民族的人們會用“祖先、宗教、語言、歷史、價值、習俗和體制來界定自己”,并以某種象征物作為標志來表示自己的文化認同[11]。電影《長安三萬里》能喚醒與建構集體記憶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影片中穿插了48首大眾耳熟能詳的古詩詞。古詩詞是中華文化沉淀下來的獨特的結晶,它依托于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和詩人個性化的感情因素,在聲、形、意、文法邏輯上都有獨特的表現。如果沒有中華文化的底蘊和獨特的東方審美,觀眾是難以從文化的層面上產生情感共鳴的。而經歷過義務教育的中國人,自小受到優秀傳統文化與經典國學的熏陶,對著名詩詞已爛熟于心,影片激活了大眾的集體記憶,出現了在片場集體背詩的奇觀,這也是一種彰顯民族身份、表達文化認同的體現。
影片的結尾,高適說“只要書在、詩在,長安就在”,更加深了大眾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書”“詩”和“長安”都是符號,索緒爾將符號看作是“能指”和“所指”的結合,既能引發人們對特定事物的聯想,也能承載其所指代或表述的對象事物的意義[12]。“書”與“詩”指涉的是傳統文化,“長安”指涉的是國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在文化的凝聚下,群體會始終保持著共同體意識,其所處的國家也會一直存續下去。“國家被視為靜止狀態的歷史,歷史被視為運動中的國家。”[13]任何的集體記憶脫離了“國家”與“民族”都是不成立的,只有當某個記憶為擁有同一個民族身份和同一個文化價值體系的群體所共有時,才能稱之為“集體記憶”。為了避免構建集體記憶的話語體系出現缺位或紊亂的情況,電影作為重要的大眾文化載體,必須要承擔起傳播主流意識形態、增強優秀傳統文化影響力、構建集體記憶、強化文化認同的重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