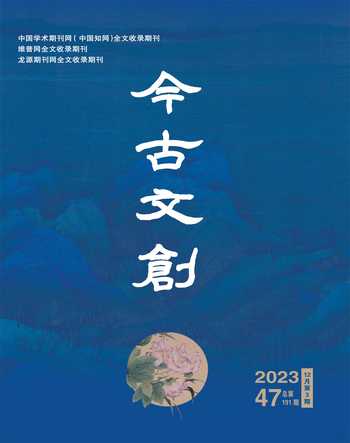莊子的 “ 有用之用 ” 與 “ 無用之用 ”
宋河雨
【摘要】“無用之用”思想是莊子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莊子通過對“有用之物”及“無用之物”的不同命運對比,來說明世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莊子通過轉變固定之用,回歸物自身,及外化內不化,說明了“無用”之“用”的多個方面。“無用”使萬事萬物免于淪為外在的價值工具,從而全生避害,得以實現自身。但同時莊子也看到了絕對的無用之物的危險所在,他最終要達到的是無用而無不用的境界。
【關鍵詞】有用之用;無用之用;無用而無不用
【中圖分類號】B223?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47-008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7.026
戰國時期,周王朝名存實亡,社會上禮崩樂壞,動蕩不安,針對社會上出現的一系列問題,諸子百家著書立說,針砭時弊。儒、墨兩家懷揣著崇高的價值理想,積極地將自己的主張付諸實踐;法家秉承務實的態度,試圖為統治者提供治國之道;而老莊哲學卻顯示出了一種超脫性,莊子的哲學思想更是注重對自由和自我的關懷,帶有一種對內在精神生命的追求。
“無用之用”思想在莊子的哲學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莊子追求理想人格的重要途徑之一,研究“無用之用”對于探尋莊子對生命和外在世界的思考有著重要作用。生活于諸侯混戰、天下大亂的時代,紛繁復雜的社會環境使得莊子不得不思考如何保全自身的問題,在《莊子》文本中,多次提及了“有用之物”與“無用之物”及其不同的命運,莊子試圖通過對“有用之物”和“無用之物”的對比來說明應該如何在充滿利益與紛爭的世間自處,如何達到對更高生命價值的追求。而當人們跳出莊子所處的黑暗社會環境時,以當下社會發展的眼光看待“無用之用”思想,又會發現其中蘊含著不同的思想價值,因此,研究“無用之用”,對于任何時代背景下都是有著重要意義的。
一、有用之害
世間之人多以“有用”作為物的衡量標準,其中“用”即用處、作用。有用之物的用處體現在物可以滿足世人某方面的需求,能為世人所用。莊子多次提到了有用之物,并交代了他們的命運,在莊子看來,有用之物多數因其有用性給自身招致禍患,慘遭遇害且難以全生,如《人間世》中借櫟社樹說出的瓜果之樹:
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①
果樹作為一種有用之樹,它們結出的果實被世人享用,但在果實成熟之后便遭受擊打,大枝被折斷、小枝被扯下。果樹滿足了世人食用方面的需求,但其生長果實的用處被消耗后,便不能享盡天年而落得中途夭折的境地,楸柏桑等樹也遭遇了相似的命運:
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椫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②
像楸、柏、桑這樣的樹木,質地細密,被看作是有用之材,因此難以逃離被做成木樁、屋棟、棺槨等的命運。它們因為自身對世人的有用之處,不能享盡壽命而中途便被斧頭砍去。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③
桂樹因為可以食用而招致砍伐,漆樹因其用處招致刀割,莊子再次說明了材之木雖然可以彰顯它們的有用性,但最終也因其有用性給自身帶來了禍患,而難以全生。
在莊子看來,有用之物如柤梨橘柚、楸柏桑等,因滿足了人們的某種需要,而中途遭受侵害,不能終其天年,對物自身帶來了消耗與傷害。僅僅追求物的“有用”性,是世人對于工具性價值的追求。世人只關注了物的外在價值,以及物對于人的需求的滿足,從而忽視了物自身本質的實現,從物本身保全自我并得以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有用”對物本身而言是一種有害性。
二、無用之用
在莊子看來,無用之物的命運和有用之物的命運截然不同。陳鼓應先生將莊子所說的“無用”稱作是“不被當道者所役用” ④,即“無用”的物對常人來說是沒有使用價值的,盡管無用之物不能滿足世人的具體需求,但正因如此,無用之物得以避害并且保全自身。莊子從多個角度論述了無用之物何以全生,并說明了無用之大用所在。
(一)轉換固定視角
在《逍遙游》中,惠子與莊子對大瓠之用展開了論辯。在惠子看來,如果一個碩大的葫蘆,不能滿足人們盛水、做瓢的需求,那么這個葫蘆便是是無用之物:
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⑤
而莊子與惠子持相反意見,莊子認為,如果不把某物局限于一個特定的功用,那么在世人視角下的無用之物,也是有大用的。他首先以“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為例子,說明了同樣一個藥方,如果轉變使用方法,就能從普通的漂洗絲絮變為大用——受到封賞,這是“所用之異也”。因此在惠子看來無用的葫蘆,也可轉變其用處而彰顯大用: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 ⑥
不能盛水,不能做瓢的大瓠,卻可以縛之于身,浮游于江湖,因此不必憂愁它太大而無所可用。當世人把“用”固定在某一特定的功用時,便會出現“莫知無用之用”的情況。“當某一物被當作某一具體物使用或利用時,此物的其他用途、其他使用價值則無法得到體現,甚至完全遭到了破壞。” ⑦但被稱為無用之物的大瓠沒有陷于某一具體用途而被局限起來,反而因為未能滿足某一具體用途而得以保全自身,因此當人們轉換了看待物的特定角度和特定的功用后,便可以看到該物的廣闊性和豐富性,這便是“無用”的用處所在。
(二)回歸物自身
有用之物之所以有招致禍害的風險,是因為它們滿足了世人的某些需求。能夠滿足世人欲望與需求的便被稱為“有用”,不能被世人利用,不能滿足世人欲望和需求的則被稱為“無用”。但如果我們由物自身出發,使物回歸于物,實現其自我價值,便可以看到“無用”之大用。
惠子認為“樗”是無用之木,在他看來“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途,匠者不顧。” ⑧但莊子反而認為盡管此樹沒能滿足人的需要,對世人來說毫無用處,但是可以將它立于鄉野曠土之上,使其免于斤斧之害,逍遙適性,蔭庇蒼生: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⑨
樗正是拋棄了普遍意義上的功用,回歸自身,自適其性而得以保全自我、實現自我。而南伯子綦所見的大木:
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⑩
此木的枝干不能用作棟梁、棺槨,它沒有迎合世人的需求,而是順其自然生長,因此盡管被稱為不材之木,卻能夠得以全生。而支離疏也因其“無用”能夠享盡天年:
支離疏者,頤隱于臍,肩高于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針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則支離攘臂而游于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
正如“有用”是從世人的角度來看的,樹木或支離疏的“無用”也是對于世人的“無用”而言的,“無用之木”不能用作棟梁、棺槨等,對于世人來說是沒有使用價值的;“無用之人”支離疏因形體殘缺而不能服徭役,對于當時的國家社會而言也是沒有價值的。但正是由于其無用性,“無用之木”得以擺脫了“中道夭”的命運,而實現了自身的完整性;支離疏可以免徭役,甚至能夠領取國家的救濟之糧,養其身,終其天年。樹木和支離疏因其無用性而得自然生長,保全自身,其自我價值得以實現,在這種意義上,“無用”可以看作是一種“有用”。
任何人或物存在于世都應該是逍遙自在的,其存在的意義不應僅以他人現實的功利需要為衡量標準,正如籠中雉一般,“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野雉只有回歸廣闊的天地才能實現自身,而不是依照人的需求圈在籠子中;人和物均應如此,由其自身出發才能使他自然生長,從而實現其真正的價值與意義。
(三)外化而內不化
在《知北游》中,莊子曾借仲尼之口說出:“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古之人能夠做到外化而不化,即外在的行動變化依靠的是內心的寧靜,正是在外化的同時而又保持了心靈的虛靜,不受外在情況的影響,古之人由此達到了內在精神與萬事萬物的相通。
在《人間世》中的櫟社樹,盡管大到可為幾千頭牛遮蔽陰涼,樹干粗百尺,樹高可比山頭,但匠石仍稱其為“不材之木”,他認為此樹“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在匠石看來櫟社樹不能用作舟、棺槨、器物、門戶、柱子等,因此滿足不了世人眼中的有用性與需求,所以是無用之木。但櫟社樹對此進行了反駁: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
櫟樹將自己寄托于“社”這個身份,“社”便是它的托身之處。櫟社樹看到有用之木因其才能而中途夭折,但它有著不同的價值追求,它不愿淪為價值工具,而是尋求“無所可用”,尋求全生以及自我的實現。因此盡管櫟社樹為了不遭到砍伐之害,便在形體上跟隨著外部世界以及社會角色有所改變,并且遭到了不了解它的意圖之人的辱罵,但櫟社樹最終卻以“社”的身份免遭災禍。櫟社樹在外部行為上做到了“與時俱化”,順應了萬事萬物的變化,但內在精神卻能夠與天地往來,其內心仍然保持平靜穩定,保持其本性,實現了外化而內不化,由此保全了生命。
三、無用而無不用
那么“無用”是否是處于社會關系中的人和物的最終追求?莊子多次提到無用之物的處境,與有用之物相比,無用之物似乎更能避害甚至因此終其天年,莊子也因此感嘆“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但在前文中的“無用之用”更多的是使人自身在亂世的狀況下,得以脫身并保全自我,處于混亂的歷史條件下,只有將自己的用處和外在價值適當地隱藏起來,才有可能與黑暗的社會現實相抵抗,在險境中全身而退。
而一旦跳脫出亂世險境,“無用”便可能給人帶來危害:一方面無用之人因其無用而有被淘汰的風險。在社會發展穩定及其不斷進步的過程中,如果只追求做無用之人,其自身價值將難以顯現,同樣會喪失生存的方式條件,從而會被時代發展拋棄;另一方面過度追求無用會使人落入虛無、頹廢的境地。即人們在面對生活中的種種事物時,存在一種不追求不在乎的消極避世態度。這也是后代存在一些聲音批判莊子“無用之用”帶有消極色彩的原因。
莊子同樣也看到了純粹的無用之物的危險所在,在《山木》篇中,莊子和弟子談到了不材之木與不鳴之雁的故事:
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于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
此處與莊子在內篇中提到的有用之物、無用之物有所不同,似乎無論處于哪種狀態都不是絕對安全的,木因不材“無用”而終其天年,不鳴之雁卻因“無用”而慘遭殺害。既然材與不材,“有用”與“無用”都有招致禍患的風險,那么應當如何處世呢?莊子首先提出了處于“材與不材”的中間位置,處于中間位置似乎是妥當的,但他仍認為這種方式不能免于累患。當人或物介于“有用”和“無用”之間時,則很容易在世人需要有用之物時被劃為有用之物,在無用之物遭到拋棄時又被劃為無用之物,所以中間狀態仍是不安全的。
因此莊子認為:“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
萬事萬物均應順應自然之道,不為外物所困,不刻意而為之,沒有贊譽和詆毀,沒有偏滯于一處,而是以“一龍一蛇”“一上一下”的姿態浮游于天地之間,免于淪為外在的價值工具,與時俱化,以和為量,實現精神與心靈的自由。此時的物正是處于上文所說的一種外化而內不化的境界,其外在的形體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并且隨著外部世界發生變化,時顯時隱,時進時退,但其內在仍然保持虛靜澄明,不偏執不被外物使役,由此便可以自由從容地行走于天地萬物之間,最終達到莊子所說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 ?的狀態,實現對內圣外王理想人格的通達。因此莊子最終并不是要人們刻意去追求“無用之物”,而是實現對于“無用之用”的超越,達到“無用而無不用”的境界。萬事萬物都處在不停的變化之中,當人們處于一定的外在社會環境中時,要根據社會角色的需要而與時俱變,通過保持內心的澄凈空虛,不偏執于某一具體之用,達到無所不用、隨機應變的最終目的。
綜上,“無用之用”是莊子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以往對“無用之用”的解讀往往使其帶有一定的消極色彩,認為莊子僅僅是教導人們做“無用”之人,遠離社會紛擾,消極避世。但當我們跳出絕對的“有用”“無用”時,應當看到“無用之用”中蘊含的對于生命本真及精神自由的追求,之于當下社會中處于人生困頓境界的人們有著開解意義,對于人們做出正確的價值選擇也有著一定的引導意義。
如前文所論述,單純地做“有用之人”或“無用之人”在面對日常生活中的情況時都是不夠的。對于當下社會而言,僅做“有用之人”,過分追求外在的工具性價值,只重視名利、利益的獲得,則容易使人迷失方向,無法實現真正的人生價值。而僅做“無用之人”,則存在被社會發展淘汰或者陷入虛無主義的風險。因此要達到如莊子所說的“乘道德而浮游”的狀態,實現對“無用之用”的最終超越,做到無用而又無不用,根據外部世界的需要與時俱化,在社會關系中自適其性、自在自得,使人回歸人自身的存在,尋求生命本身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注釋:
①②③⑤⑥⑧⑨⑩?????????郭慶藩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59頁,第163頁,第171頁,第37頁,第39頁,第41頁,第42頁,第162頁,第166頁,第117頁,第673頁,第158頁,第159頁,第171頁,第592頁,第593頁,第963頁。
④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局2016年版,第128頁。
⑦羅安憲:《 “‘有用之用’‘無用之用’以及‘無用’——莊子對外物態度的分析” 》,《哲學研究》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