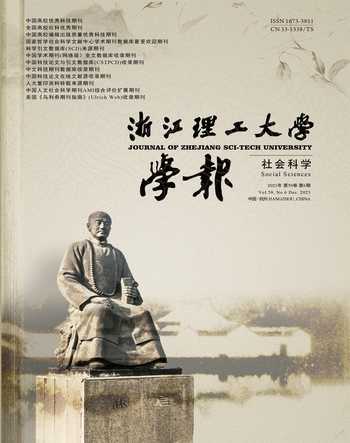土地經營權的信托流轉困境與紓解
胡建 張馳翔
摘要: 土地經營權信托有利于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化與市場化,但尚存在信托公司參與意愿較低、農地用途非農化傾向嚴重和部分地區公權力過度越權等問題。其深層原因在于信托農地產權內容以及歸屬不清。受托人和受益人對信托享有的“所有權”在我國傳統民法立法體系下應當分別定義為所有權以及債權,土地經營權在信托流轉形式中應定義為物權。土地經營權的適格受托人為專業的商事公司,主要權利和義務在于實現土地經營權的資本化運作;受益人應限于農戶,主要權利在于監管信托公司的信托業務。此外,根據“三權分置”的基本原理,也可為其他主體安排適當權能,以促進土地經營權信托的高效流轉。
關鍵詞: 土地經營權;信托流轉;信托財產;雙重所有權;物債二分
中圖分類號: D913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 1673-3851 (2023) 12-0709-09
Difficulties and their relief in trust transfer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ownership" of trust property
HU? Jian, ZHANG? Chixiang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Land management right trust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cale and market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low willingness of trust companies to participate, serious tendency of non-agricultur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and excessive overstepping of public power in some areas. The deeper reas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content and attribu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in trust are unclear. In China′s traditional civil law legislative system, the "ownership" trustees and beneficiaries of the trust enjoy should be defined as ownership and debt, while land management rights in the form of trust transfer should be defined as property rights. The qualified trustee of the land management right shall be a professional commercial company, whose main right and obligation are to realize the capitalization operation of the land management right; the beneficiary should be limited to farmers, whose main right is to supervise the trust business of the trust company.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the three rights", appropriate rights can also be arranged for other subjec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circulation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 trusts.
Key words: land management rights; trust transfer; trust property; dual ownership; the dichotomy between real right and obligation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 2022年12月23日至24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長期以來,農村土地流轉手段較為單一,流轉規模有限,且土地流轉效率偏低。為提高農村土地流轉效率,釋放農業生產活力,國家制定了相關政策,允許土地承包經營權“三權分置”,即將土地經營權分離為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2021年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亦將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予以立法肯定,賦予新設“土地經營權”自由轉讓或抵押的權利。“三權分置”時代的到來為創新農村土地流轉制度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為了因應農村承包土地流轉的現實需要,國內各試點地區不斷涌現出一種土地流轉的新形式——土地經營權信托流轉。其乃委托人在一定期限內將土地經營權委托給受托人,受托人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和保障農民承包權的前提下,按照土地運營的市場化需求,以自己的名義對其進行專業管理和處分,并將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產生的收益分配給受益人的行為[1]。雖然土地經營權信托未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以下簡稱《信托法》)等法律法規所承認,但是作為一種得到改革實踐驗證的全新流轉形式,其日益成為當前農地流轉中的重要選擇[2]。
我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土地碎片化以及大片土地撂荒一直是難以解決的問題。土地經營權信托對于解決上述難題以及提高土地流轉效率而言是極為有益的探索。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也肯定了土地經營權信托的可行性,并認為其乃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能夠充分地適應“三權分置”理論,推進了市場機制和農村土地公有制的契合[3]。然而,近年來,土地經營權信托的運用與推廣遭遇瓶頸。其對實行土地用途管控和維護農民土地權益提出較高的要求;同時受商業利益驅動,其極容易導致農業的非農化和非糧化[4]。當前土地經營權的信托流轉困境是土地經營權的性質認定難題和《信托法》的立法罅漏綜合造成的。一方面,既往的研究未能從信托法理出發,探尋土地經營權的物債屬性以及信托主體的權利配置等具體問題;大多受限于三農視角,并未充分考量信托財產歸屬這一問題在土地流轉制度中的特殊性,信托的金融功能亦未被完全挖掘。另一方面,土地經營權信托不僅是一種土地流轉形式,本質上更是一種信托商行為,其運行的基礎——《信托法》本是英美法系特有的制度。土地信托作為信托法律體系的源起,英美法系國家對其有著極為詳盡的規定,信托財產“雙重所有權”理論更是土地信托實施的根本。而法律移植于域外的我國《信托法》,自頒行二十余年以來,尚未有過任何形式的修訂,細節性操作規定的缺位更讓土地經營權信托的法律適用尤顯尷尬。本文從土地經營權的信托流轉的現實困境出發,結合信托財產“雙重所有權”理論,提出土地經營權信托流轉困境紓解的對策,以期為土地經營權信托制度的完善提供參考。
一、土地經營權的信托流轉困境土地經營權信托在我國已有十余年的改革實踐經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湖南益陽、安徽宿州、江蘇無錫等試點地區的實踐。上述地區的具體操作模式大同小異,主要差異在于信托中受托人不同。根據受托人的種類,可以分為政府主導模式和商業信托模式兩類,而實踐中以前者為主流。相較于其他傳統的土地流轉形式,土地經營權信托引入了信托公司以及農業生產公司對土地進行經營和管理,規模生產優勢較為顯著。但是,隨著農村土地改革實踐步入深水區,阻滯土地經營權信托流轉的各類問題也日益凸顯。
(一)土地經營權的信托流轉困境之表現1.信托公司參與意愿較低
土地經營權信托存在相關主體積極性不高的問題,主要是商業信托公司參與不充分,導致流轉效率低下。盡管當前已經有北京信托、中建投信托和中信信托等商業信托公司參與土地經營權信托流轉,但是更多的商業信托公司對進入這一市場仍持觀望態度,即便開展信托業務較多的中信信托也放緩了擴張的腳步[5]。目前導致信托公司參與動力不足有多方面的原因,具體而言:第一,從信托公司本身出發,大部分信托機構不具備農業經營能力,農業經營主體對農地的經營和管理水平又直接決定了信托收益的大小。同時,農戶的小農意識深厚、戀土情節嚴重,信托公司能簽訂合同的信托農地范圍有限,信托公司對此的預期利益不高。第二,保障機制的缺失也會讓信托公司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農業生產的長周期性決定了土地經營權信托不具備短期獲得大量收益的前景,而且長期的農業生產過程中難免遇到自然災害等問題,減產所帶來的收益風險該如何分擔也是當前土地經營權信托制度設計所欠缺的。第三,信托公司在土地經營權信托中的權利配置不清晰。我國《信托法》并未直接規定受托人對信托財產享有所有權,而農村承包土地也有“三權分置”的背景,如此一來,相關權利人之間的權利配置就顯得極為混亂。我國的土地經營權信托實踐尚缺乏明確且細致的法律規定作為依據,如何合理配置土地經營權信托各方主體的權利義務是激勵商業信托公司進入這一市場的前提,也是促進土地經營權信托流轉的合法性根基。
2.信托農地用途的非農化傾向嚴重
我國土地經營權信托已經出現近十余年,大量實踐印證了其在提高土地流轉效率以及經濟效益方面的優勢,但是長時間以來并未獲得立法上的認可,究其原因可能是其農地非農化、耕地非糧化的經營方式觸碰了農地用途管制的底線。為了追求經濟效益,已經開展的土地經營權信托實踐多將信托農地用于建設農業生態園、發展旅游觀光農業等[6]。在“安徽宿州模式”中,5400畝信托農地被規劃為構建現代農業循環經濟產業示范園[7];在“湖南益陽模式”中,農業經營主體在信托農地上挖塘進行湖藕養殖[8];信托合同直接規定將農地信托用于經濟作物種植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在我國,國家糧食戰略安全和農業生產安全日益受到重視,倘若土地經營權信托的農地用途不受到合理限制,糧食產量必定受到影響,其獲得立法上的承認亦將遙遙無期。
3.部分地區存在公權力越權現象
土地經營權信托本質上應當是土地權利市場化、資本化的運作形式,更是農戶與信托公司之間基于公平、效率原則的自主市場選擇行為[9]。土地經營權信托在實踐萌芽階段恰逢“三權分置”改革初期,農戶、信托公司以及農業生產公司都缺乏參與信托流轉的直接動力,而政府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相關主體的參與度。一方面,農戶對政府的信任讓農戶對“失土”的擔憂大大減小,這也讓土地整合有了可能;另一方面,政府出于對土地流轉指標的考量,也樂意直接代表農戶與信托公司進行談判并直接參與相關細節條款的制定。但這種大包大攬式的參與,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政府失靈的風險。在“湖南益陽模式”中,參與土地經營權信托流轉的信托公司由當地政府全額出資設立,但該信托公司的人員和辦公場所與當地政府趨同,實質已經淪為政府的辦事機構,這些人員是否具備相關專業信托管理能力存疑[10]。在“安徽宿州模式”中,當地政府直接以信托財產委托人的身份與信托公司訂立合同,政府本身甚至單獨作為受益人參與信托收益分配,農戶在實質上已經被排除于信托關系之外。公權力越權現象在個別地區的土地經營權信托實踐中屢見不鮮,而這類行為的合法性有待商榷,但農戶合法權益將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首先,當政府直接扮演委托人的角色時,作為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農戶被排除在信托法律關系之外,撤銷權的行使將完全依賴于政府,救濟權的實現將會受到極大影響。其次,當政府直接扮演委托人的角色時,流轉效率和政府公信力都會受到考驗。在“安徽宿州模式”中,一共有三級政府層層委托,自上而下傳達土地流轉指令,如此一來,農戶真實意愿非常容易受到忽視。最后,當政府直接扮演受托人的角色時,剝奪了其他市場主體參與信托流轉的機會,違反了市場經濟的主體平等和機會平等的要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下,地方政府原則上不能從事經營行為。此類越權現象也構成了事實上的行政壟斷行為,不利于多元化土地經營權流轉主體市場的構建。
(二)土地經營權的信托流轉困境之根源考察土地經營權信托發展的現狀,所出現的信托公司參與意愿低下、農地用途的非農化傾向嚴重以及個別地區公權力越權等問題,其根源在于信托財產的權利歸屬模糊,缺乏適格的權利主體對信托財產進行管控與收益。
其一,在信托財產的權利歸屬問題上,我國《信托法》并未承認“雙重所有權”理論。英美法系國家根據“雙重所有權”理論確定信托財產的歸屬確立,而我國的信托立法對此問題規定較為模糊。縱觀我國《信托法》,涉及信托財產歸屬的條文僅有第2條,即:委托人將財產權“委托”給受托人。立法者對信托財產的權利歸屬采取了極為模糊的態度,“委托”一詞并未直接說明信托關系成立之時信托財產所有權是否轉移,更沒有明確規定“雙重所有權”。換言之,法律移植于域外的我國《信托法》,其最大的立法缺憾在于未明示規定“雙重所有權”,使得信托這一精巧、靈活的法律制度失去了核心與靈魂。
其二,信托財產的權利歸屬不明確,將衍生出一系列不利的法律后果。首先,不符合信托委托人設立信托的財產安全要求。委托人勢必會憂慮信托財產的所有權到底歸屬于誰?若完全屬于受托人所有,信托財產已經于己毫無關涉,委托人還會選擇信托么?其次,假設信托財產完全歸屬于委托人所有,于受托人毫無利益牽涉,那其與代理制度有何差異?在受托人不存在所有權的情形下,交易第三人如何信賴受托人,如何保證雙方的交易安全?再者,假設受益人與信托財產所有權毫無關聯,受益人的正當利益如何保障?在委托人作為法律主體消亡(如死亡)之后,信托仍然存續,既往以委托人為核心的權利架構,又如何持續性延續?最后,在信托財產的所有權歸屬不明的情形下,受益人的權利主要基于債權性質的信托合同。按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信托受托人的受益權不可能是一類物權,而更傾向于債權屬性。受益人其對受托人如何監督,受托人的道德風險如何管控?
其三,信托財產權利歸屬模糊,無法從信托法理出發確定土地經營權的權利屬性,加劇了土地經營權流轉中產權關系的復雜性。首先,傳統財產權理論認為靜態的財產歸屬問題是物權法律制度的重心所在,但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動態的財產利用問題漸趨成為物權法律制度的核心,農村土地權利體系也逐步分離、細化[11]。自從土地承包經營權“三權分置”確立以來,實踐中土地經營權的產權內容較不明確。土地經營權與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以及集體經濟組織的權利邊界也不甚清晰,在個別地區更存在集體經濟組織干預土地流轉,侵犯農民合法權益的現象。此外,土地經營權流轉過程中,部分地區政府公共服務功能缺乏。農村土地流轉中,公權力應當扮演促成者的角色,積極促成土地流轉,但是個別地方政府仍未充分發揮提供公共服務與糾正市場失靈的職能[12]。其次,關于土地經營權的權利屬性,目前學術界尚存在爭議,主要存在“物權說”“債權說”以及“二元說”等學說。這些學說主要基于三農的視角,較少有學者從信托法理出發探究與論證土地經營權的權利屬性問題。“物權說”認為土地經營權是用益物權,是經營權人對集體所有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權利,在“三權分置”的法律實踐中,特別需要將土地經營權依法確定為物權,因為中央政策文件把土地經營權確定為“可轉讓”“可抵押”的權利,只有將這種權利依法確定為物權,才能滿足這樣的要求。“債權說”認為土地經營權的本權是基于土地流轉合同而產生的,為意定本權不是物權,土地經營權產生于土地經營權流轉合同,是一種獨立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債權,具有債權的請求性和相對性。“二元說”認為土地經營權兼具物權性和債權性的二元法律屬性,若經營期限較長(五年或以上)且需要登記公示的將其定性為物權,反之經營期限較短(少于五年)且不需要登記公示的將其定性為債權。最后,從信托法理分析,信托的本質是所有權重置,其將大陸法系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四項所有權權能,分別拆分給了受托人與受益人,以此實現所有權的重置。簡言之,信托具有相當的法律獨立性,信托財產不屬于委托人、不實質屬于受托人、不名義上屬于受益人。信托財產所有權究竟在哪個信托角色手里?一方面,受托人取得名義上信托的“所有權”,信托財產也應登記在受托人名下,這個登記區別于所有權下交易的登記,而是沒有完整所有權下的信托登記。名義上信托財產在受托人,受托人按照信托合同約定和法律規定行使占有、使用和處分的權能。另一方面,把信托財產的控制管理權、交易處分權給了受托人,受托人沒有收益權,不享有受益權;同時信托財產的最重要的財產屬性受益功能給了受益人。實質上信托的收益權能在受益,受益權應當是一類物權,受益人擁有實質的“所有權”,但又不具備完整的“所有權”。總之,信托財產必須與受托人個人財產相隔離,受益人不能任意支配信托財產也是信托運行的內在邏輯。
土地經營權的物債屬性模糊以及我國《信托法》對信托財產歸屬界定不清等問題,產生了信托公司參與意愿低以及信托農地非農化突出的現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權利界定不清以及公權力未能發揮適當職能的問題,又讓土地經營權信托出現了角色越權以及配套制度不完善等弊端。在這一系列的問題中,土地經營權的物債屬性和信托財產的權利歸屬問題至關重要,這直接關涉土地經營權信托的合法性。故而,有必要回溯信托制度的理論源頭,從信托背后的法理出發,為土地經營權的信托流轉尋找合適的紓解對策。
二、信托財產“雙重所有權”理論的本土化
(一)信托財產“雙重所有權”的內涵及其演化
所謂信托財產“雙重所有權”,是指就信托財產的權利歸屬而言,信托財產的具體權能被重置分配,在信托關系的委托人、受托人和收益人三方法律構造中,名義上信托財產“所有權”歸屬于受托人,受托人可以依法或依契約規定行使對信托財產的占有、收益、使用和處分的權能,但是信托財產的收益權能歸屬于收益人;實質上信托的收益核心權能在受益,按照英美法系衡平法的規定,受益權應當是一類債權,擁有實質的“所有權”,但又不具備完整的“所有權”[13]。“雙重所有權”是信托法律制度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是普通法和衡平法分野的必然產物,也是實現信托財產所有權流轉的核心規定。從英美法系的視角來看,它是理解整個信托制度的法理基礎;而從大陸法系角度來看,它更是信托法移植時兩大法系融合的焦點。也正是因為“雙重所有權”如此關鍵,在解決我國的信托業務出現的核心法律障礙時,它也是繞不開的話題。“雙重所有權”具體是指在設立信托時,為保障信托目的實現,委托人將信托財產轉移給受托人使其獲得普通法上的所有權,衡平法院則出于“刮擦當事人良心”的原因承認受益人對信托財產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權。受托人和受益人享有的權利皆稱為“所有權”,在二者發生沖突時,衡平法所有權優于普通法[14]。
美國和英國的信托法都綜合了成文法與判例法。衡平法在信托法的發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信托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各類信托實務的基本規則都是由衡平法所確立的[15]。信托由用益制度發展而來,用益是最初為了規避英國某些封建土地義務而產生的,但是沒有衡平法保護的受益人難以在訴訟中對抗沒有履行義務的受托人。后來衡平法院注意到了用益這種民間廣泛使用的制度,并承認受益人的所有權,信托也因此誕生。可以說,失去衡平法的信托法將寸步難行。包括我國在內的一眾大陸法系國家實行嚴格的“一物一權”的所有權制度,強調所有權是一種對物直接的、排他的、絕對的支配性權利,這與“雙重所有權”理論似乎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立法上的沖突在土地制度中更為明顯,我國實行土地公有制,這與英美國家的土地私有制有著根本性區別,如何在不破壞現有立法的基礎上安排信托農地的歸屬將是土地經營權信托面臨的最大挑戰。縱觀英美法系國家,英國的信托制度恰恰起源于土地信托,從土地信托肇啟的“雙重所有權”理論也是其自身運行的精髓。如此看來,從“雙重所有權”理論入手,探討信托財產在信托當事人之間的具體權能分配,將對解決我國土地經營權的信托流轉問題產生積極作用。
(二)“雙重所有權”本土化的理論證成在部分大陸法系國家試圖移植信托法時,國內外學者就試圖探討“雙重所有權”與“一物一權”的耦合之處,以期在不同國家推廣信托法的適用。英美法系國家“雙重所有權”的運行離不開衡平法,但上文已經提到,“雙重所有權”是普通法與衡平法并存的司法體制下的產物,有著極為特殊的歷史背景,而并非立法直接選擇,這兩種所有權在司法適用時也不是完全平行的。事實上,信托的最典型特征并不是普通法所有權和衡平法所有權的分野,而在于信托財產財產控制權和受益權的分離。因此,即便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中沒有衡平法,也不直接承認“雙重所有權”,并不影響對信托基本理念的繼受,這也是“雙重所有權”本土化的前提。
在明確信托財產“雙重所有權”的核心理念之后,實現本土化就需要找到其與大陸法系的相通之處。“雙重所有權”中的兩大“所有權”都不是大陸法系中所說的所有權,之所以將它們都稱作“所有權”,只是因為它們確實有著大陸法系語境下所有權的某些屬性或特質[16]。將英美法系中的“雙重所有權”理解成大陸法意義上兩個效力完全一致的所有權是一種觀念上的誤解[17]。以大陸法的視角來看,“雙重所有權”中的受托人和受益人只不過都對信托財產享有不同的權益,若能將這些權益在大陸法中找到合適的定位,那么實現“雙重所有權”的本土化也并非不可能。而實現“雙重所有權”的本土化的前提是為信托財產找到合適定位,但是我國立法者面對這一問題時采取了“知難而退”的策略,既沒有采取“雙重所有權”理論,也沒有確定單一所有權的歸屬。誠然,我國不可能為了信托而全盤否定單一所有權的立法傳統,但《信托法》立法已成,也不應讓其成為我國法律體系中的“異物”。換言之,為信托財產“雙重所有權”尋找合適定位時必須以我國單一所有權傳統為背景,突破形式立法的束縛,從信托的核心功能出發,實現具體制度的落實。
在我國單一所有權的體系下,若想實現與“雙重所有權”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必須借助物債二元的運行機制,以物權和債權的角度對受益人和受托人享有的權利進行區分。從《信托法》對受托人權利安排來看,受托人的“所有權”限于對信托財產的處分與管理,受益人的權利則限于財產的收益與救濟[18]。在這里必須明確“收益”與“受益”的區別,從信托運作的具體流程不難得出,收益具體是指受托人直接獲取信托財產獲利的行為,信托受益人最終獲取信托獲利的行為則是受益,因為有信托管理必要費用的存在,收益一般大于受益的部分。同時,受托人的正常信托業務顯然離不開占有、使用與處分。如此看來,受托人享有大陸法系語境下單一所有權的全部權能,即受托人的所有權完全可以定位為符合大陸法特征的、完全的、唯一的所有權。另外,從英美法系“雙重所有權”的視角來看,“用益”發展為信托的關鍵是衡平法介入保護了受益人的受益權。因此,衡平所有權的定位是“雙重所有權”本土化的關鍵環節。
受益人所有權究竟是物權抑或是債權一直是國內外學者探討的問題。有學者從受益人的“受益權”出發提出“物權說”,認為信托財產最終流向受益人,那么也應當把信托財產所有權賦予受益人,即受益人是真正的所有權人[19]。這種學說面臨較大的挑戰:首先,受托人享有大陸法意義上的所有權是確定的,如果再將受益人的權利認定為所有權,事實上又突破了我國單一所有權的體系,這是沒有必要的。其次,“物權說”最大的問題在于沒有理清信托運行的基本規則,即受益人已經失去了對信托財產的直接控制,那么這種失去占有權能的權利也當然不可能是物權。探討信托財產“雙重所有權”的本土化路徑必須堅持從制度功能出發,這也是“物權說”所欠缺的,如果從制度功能的角度出發再進行深入分析,不難得出受益人享有的權利在大陸法中定位為債權是較為合適的:一是請求受益權。受益人的最主要權利表現為根據信托合同向受托人請求相關權利,這種權利屬于債權并無爭議。二是對信托事務的監督權。受益人作為信托利益的享有者,擁有對受托人進行監督的權利,以此保障自身的權益,這種權利又能與收益請求權形成主債權與從債權的關系[20]。三是第三人在明知受托人違反信托目的處分信托財產時,仍然受讓該財產的,受益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撤銷該行為,這種權利也可以歸納為債權人的撤銷權。由此可見,衡平法所有權(受益權)應當在大陸法意義下定義為債權。
“雙重所有權”理論的本土化是建立在傳統物債二分體系之上的。而在物債二分體系內,債權具有相對性,無法作為財產歸屬的客體。質言之,“債權所有權”無法被“處分”所評價,其也失去了作為信托財產的可能性。因此,信托財產“雙重所有權”理論的本土化不僅包括將受托人、受益人的權利類型分別定位至所有權、債權,債權被排除在信托財產之外也是該理論的應有之義。
綜上所述,從信托制度功能出發實現信托財產“雙重所有權”的本土化是完全可行的。信托受托人享有對信托財產的使用、收益、占有以及處分權能,可以作為我國法律體系下的單一所有權人,而信托受益人的權利也可以被債權所定義。如此一來,信托關系當事人的權利配置就可以物債二分為基礎進行設計,如果再輔以具體法律條文以及信托目的對當事人范圍進行明確劃分,那么任何一類信托的流轉優化方案就都能呼之欲出了。
(三)“雙重所有權”與物債二分在制度功能上具有相通性
將“雙重所有權”中的普通法所有權和衡平法所有權分別認定為大陸法語境下的物權和債權,既保留了立法傳統又能實現制度功能的基本一致。下面以信托主體的權利義務情況進一步說明。就委托人而言,在信托關系成立時,其就喪失了對信托財產直接的支配權。而無論是英美法制度設計還是物債二元設計,委托人都保有一定的干預權,這種干預權的大小由信托文件所決定。從受托人出發,英美法的普通法所有權和大陸法的所有權都能讓受托人有足夠的權利進行正常的信托業務。與此同時,衡平法所有權和債法上的義務也都能實現相應的約束,以此保證受托人履行信托義務。再來看受益人,衡平法所有權和債權都實現了受益人在請求支付利益、監督信托實務等方面的權利。最后,無論是何種制度設計,善意第三人應受保護,惡意第三人皆不會受到法院的青睞。綜上所述,以物債二分的制度設計為“雙重所有權”尋找合適的定位完全能夠保障信托核心功能的實現,“雙重所有權”的本土化具有可行性。
三、土地經營權的信托流轉困境之紓解(一)明確農地信托中土地經營權的物權屬性基于“雙重所有權”理論的本土化解決土地信托中信托財產的歸屬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明確土地經營權信托中土地經營權的物權屬性。首先,若將土地經營權界定為債權存在巨大的缺陷,最大的原因在于債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具有不穩定性。農業生產投入大、周期長且風險大,需要長期穩定的農地流轉關系與之相匹配,而在債權關系下的土地經營權則維系于脆弱的信托合同關系。其次,債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容易引發權屬不清晰的問題。債權的任意性導致當事人之間對于土地經營權內容約定不明,而物權法定可以明確其具體權利內容,且需要登記生效產生一定的公信力,債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成立自合同生效開始,缺乏物權公示的公信力。再次,債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將導致其流轉動力不足、市場價值容易被低估,最終損害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益。最后,物權性質的土地經營權滿足信托實踐的需求。根據“雙重所有權”理論,我國傳統的民法體系難以接納債權作為信托財產,以債權為信托財產的債權信托在我國的實踐中也尚處于理論層次的摸索階段,僅有少數金融機構和工商企業是債權信托的委托人;債權信托的運作方式往往是有償折價出售、債轉股和抵債財產變現,土地經營權顯然不是這類運行方式的操作對象;債權信托的信托財產往往表現為定期存款單、票據以及保險證書等等,土地經營權顯然也不在這些范圍內;絕大多數土地經營權信托的信托合同出于實際經營需要,期限大多會超過五年,這也避免了所謂“二元說”中關于登記效力的問題。可見,根據我國信托業的實際和土地經營權信托運作實踐,土地經營權在土地經營權信托中應界定為物權。
步入“三權分置”時代以來,土地經營權是土地權利流轉中最主要的客體,土地經營權信托也不例外。而論及土地權利時,會涉及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四項權能,即受托人的具體權利表現為土地經營權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權能。從表面看,農地集體所有權、經營權人和承包權人都享有上述四大權能,這似乎會產生權能重疊的問題。事實上,雖然農地集體所有權、經營權和承包權享有權能的名稱相同,但是每項權能的具體內涵以及存續期間都有差異,不會有重疊的問題[21]。而我國土地經營權信托中存在的公權力越權現象往往就打破了這一平衡關系。在鄉村振興視閾下,如何劃分適格的信托當事人范圍更是農村土地經營權信托法律構造的焦點問題[22]。“雙重所有權”理論的本土化清晰界定了受托人和受益人的權利,而這些權利內容正是劃分適格主體的關鍵。
(二)主體認定與權能配置1.受托人范圍與具體權利
我國《信托法》第24條規定,受托人必須是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法人。之所以強調受托人必須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主要是因為只有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受托人才有能力去管理信托財產。同時,如果涉及特別的財產,受托人則必須具有管理該種資產的專業知識。常見的信托財產為股票、房產以及現金等,而土地經營權信托的財產是土地經營權,一般的自然人不宜作為受托人。但在排除自然人后,法人的范圍仍然相當廣泛,政府作為機關法人充當受托人似乎又是可行的。其實不然,我國的土地經營權信托尚處初級階段,僅僅實現了土地整合、土地流轉以及土地經營等基本目的。土地經營權信托相較于其他土地流轉形式,最特殊的優勢在于能實現土地生產的資本化以及市場化,這也是未來土地改革的必然方向。同時,實現信托財產的資本化以及市場化更是信托業的內在要求:在《信托法》之外,還存在專門規制營業信托的“兩規”——《信托公司管理辦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管理辦法》。土地信托的信托財產為用益物權,并不是我國《民法典》物權編上的“有體物”,而“兩規”規定信托財產損益獨立,管理信托事務產生的收益、負擔的風險以及債務由信托財產獨立承擔,不得用其他財產墊付。土地經營權這一財產權當然無法直接用來承擔風險以及償還債務等結算業務,為了使土地經營權信托能夠符合“兩規”規定,必須借助一定的金融手段。我國的重慶江津以及南海等地區已經成功開展了土地抵押貸款、土地折價入股等土地證券化實踐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而我國信托業自發展以來便與證券業有著密切的聯系,可見土地證券化是頗為理想的金融化途徑。土地證券化的核心在于面向金融市場發行土地收益憑證,以此籌措資金,并為后續的各種融資業務提供基礎。這些業務顯然是超越政府的能力范圍的,以政府作為受托人的土地經營權信托也難以實現土地經營的市場化與資本化。換言之,土地經營權信托的受托人應當限于專業的商事信托公司,只有專業的信托公司才能在符合受托人身份資格的基礎上不斷吸納社會資本進入農業投資項目,以此實現土地經營權的長期信托目的[23]。
受托人可以作為我國法律語境下的所有權人,并可從物權的四大權能(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出發確定受托人的權利。根據“占有”這一權能,受托人可以在流轉期限內自建農田基礎設施,還可以在同等條件下優先續租。根據“使用”這一權能,受托人可以在流轉期限內從事農業生產、建設基礎設施以及對土壤進行改良。根據“收益”這一權能,受托人可以獲得農業生產、補貼收益(不論實際農業經營人是否是信托公司)。根據“處分”這一權能,受托人可以將承包地再轉租給專業農業生產公司,還可以面向金融市場發行土地收益憑證、發展信托投資、信托基金投資等業務,以此實現土地經營權信托的證券化。
此外,根據信托法的一般原理,為了實現信托的一般目的,信托公司作為土地經營權信托受托人還享有信托事務處理權、給付報酬請求權、優先受償權等基礎性權利[24]。同時,受托人也應當承擔給付信托利益義務、履行忠實和注意義務等,以此實現信托業務的正常運作。另外,作為土地經營權的合法享有主體,信托公司的義務還包括滿足一定的糧食生產指標,在滿足指標之后可以自行安排經濟作物的種植以及發展旅游觀光等高效益業務。
2.委托人與受益人的范圍與權利
我國土地經營權信托存在公權力越權的現象,其中的一個表現在于個別地區的政府成為了事實上的受托人和受益人,意味著政府享有了土地經營權,這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承包法》的角度來看是不合法的。為了保證農戶的合法權益與信托的正常流轉,農戶應當作為委托人參與制定信托合同并作為受益人享有流轉利益。作為委托人,農戶最主要的權利表現在可以自主選擇受托人、隨時了解信托財產的管理情況,并在管理方式不合適時要求受托人作出調整。受益人的“所有權”相當于我國法律語境下的債權,受益權是主債權,對信托事務的監督權是從債權。所以說,農戶可以要求信托公司給付信托利益并對受托事務進行監管。同時,根據債權撤銷權,在信托公司違反信托目的行使處分權時,農戶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撤銷該處分行為。監督權和撤銷權的存在對農戶權益保障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兩權的同時存在能在最大程度上減少農戶“失土”的擔憂,提高農戶參與土地經營權信托的積極性。
3.其他主體權利實現機制
我國的農村土地制度中,集體所有權存在一定程度虛化、弱化的情況。而在土地經營權信托中,集體所有權的存在可以促進規模化流轉。為實現這一目的,可適當動用集體所有權中的處分權能。根據處分權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權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收回承包地、調整承包地以及將承包地轉為集體建設用地等。土地經營權信托的大規模流轉離不開連續的、成片的土地,若一個地區內的大部分農戶簽訂了信托合同,而有少部分農戶愿意自己經營,則會造成非信托土地夾雜在信托農地之間的情況,給規模經營造成障礙。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集體經濟組織可以行使置換權,對已承包的土地進行置換,以達到土地連片的目的[25]。大片土地的集中或連片也會降低信托公司的前期工作成本,吸引信托公司的參與。
另外,政府在土地經營權信托中該扮演何種角色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政府參與程度直接影響了土地信托配套制度的成色。政府不宜作為信托法律關系的直接參與主體,但可以憑借其在農戶中的威信扮演一種促成者和監督者的角色。具體來看,政府可以成立中介機構,為農戶和信托公司提供信息流通的途徑與交流談判的場所,并為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農戶主張更多合法權益,以促成土地經營權信托的成立。此外,政府可以依據其天然的監管職能對信托農地的用途進行監管。政府以促成者和監督者的角色參與土地信托,不僅可以避免越權的問題,還可以為土地經營權信托的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四、結語土地經營權信托在我國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其在實現土地規模化流轉、農業生產資本化等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然而,囿于信托財產法律屬性存在爭議、主體認定與權能配置不清晰等問題,我國目前業已開展的土地經營權信托實踐規模有限,且進一步發展面臨較大的挑戰。土地經營權的信托流轉困境紓解對策,須從信托財產“雙重所有權”理論入手,探求受托人和受益人權利在我國法律語境下的物權屬性,而受托人和受益人的權利分別可以認定為所有權和債權,并以物債二分的內涵為基礎對相關權利進行設計:受托人的“所有權”體現于對信托財產的處分與管理,信托公司可以根據土地經營權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這四大職能實現對信托農地充分的經營管理權,包括但不限于自建基礎設施、從事農業生產、再轉租以及發展金融業務等,受托人享有的土地經營權為物權;受益人的權利則限于財產的收益與救濟,農戶不再直接參與農業生產活動,而享有對信托事務的監督權、信托受益請求權以及撤銷權。同時,根據其他法律規定劃分適格的信托主體范圍:政府無法成為土地經營權的實質享有主體,也不適宜直接從事市場經營活動,應當排除在土地經營權信托的主體范圍之外;根據信托法原理,適格的委托人及受益人應當為農戶,適格的受托人應當為商業信托公司。除了信托法律關系主體之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政府也應在土地經營權信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為信托的高效流轉起到服務保障作用。
參考文獻:
[1]房紹坤,任怡多.新承包法視閾下土地經營權信托的理論證成[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2):33-44.
[2]陳敦.土地信托與農地“三權分置”改革[J].東方法學, 2017(1):79-88.
[3]蔡立東.中國式物權制度的文明刻度[J].中國社會科學, 2022(12):108-119.
[4]胡建.農村土地抵押法律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81.
[5]南光耀,諸培新,王敏.政府背書下土地經營權信托的實踐邏輯與現實困境:基于河南省D市的案例考察[J].農村經濟, 2020(8):83-90.
[6]王方,沈菲,陶啟智.我國農村土地信托流轉模式研究[J].農村經濟, 2017(1):43-47.
[7]陳敦,張航.農村土地信托流轉的現狀分析與未來展望[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2015(5):94-98.
[8]魏曉,張琳,許波,黃宇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化改革研究:以湖南省沅江市草尾鎮為例[J].國土資源導刊, 2013(10):13-16.
[9]李蕊.農地信托的法律障礙及其克服[J].現代法學, 2017(4):54-66.
[10]張占鋒.土地經營權信托實踐中的政府角色:以安徽和湖南省土地經營權信托實踐為例[J].世界農業,2017(1):210-216.
[11]張志坡.權利上的權利:一個法學上的發現[J].法治社會, 2023(4):91-102.
[12]楊璐璐.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現實困境與制度性原因分析[J].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 45(4):64-72.
[13]陳雪萍.信托財產雙重所有權之觀念與繼受[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 36(4):77-84.
[14]方嘉麟.信托法之理論與實務[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4:29.
[15]霍玉芬.信托法要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8.
[16]李群星.信托的法律性質與基本理念[J].法學研究, 2000(3):118-126.
[17]張天民.失去衡平法的信托[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4:4.
[18]甘培忠,馬麗艷.以獨立性為視角再論信托財產的所有權歸屬[J].清華法學, 2021, 15(5):55-68.
[19]溫世揚,馮興俊.論信托財產所有權:兼論我國相關立法的完善[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2):203-209.
[20]于海涌.論英美信托財產雙重所有權在中國的本土化[J].現代法學, 2010(3):159-168.
[21]廖洪樂.農地“兩權”分離和“三權”分置的經濟學與法學邏輯[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20(5):109-118.
[22]王眾,李體欣.鄉村振興視閾下農村土地經營權信托法律構造中的主體適格問題研究[J].金融理論與實踐,2022(10):112-118.
[23]苗繪,王金營.農地信托中土地證券化融資模式借鑒與創新[J].會計之友,2021(23):64-71.
[24]馬建兵,王天雁.農村土地信托法律問題研究:兼談西部特殊性問題[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20:183.
[25]蔣濤.英國土地信托法發展演變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259.
(責任編輯:秦紅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