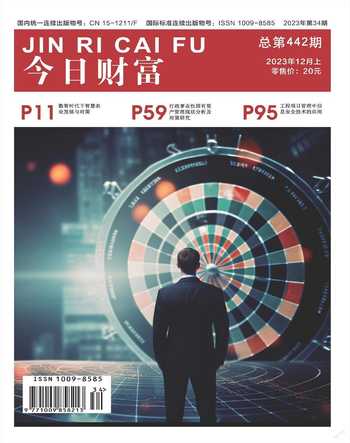城市融入視角下寧夏移民青年就業狀況分析
寧夏生態移民工程極具地方特色且模式多樣,這里不僅有將困難地區居民分散安置到生產生活條件良好、閑置土地、宅基地比較多的村落插花移民,也有把貧困地區群眾整體跨區域搬遷的吊莊移民。寧夏銀川市西夏區興涇鎮就屬于典型的吊莊移民,這里有很多年輕人學歷低,也沒有一技之長,舉家遷移銀川后逐漸習慣城市的生活方式,不愿意像父輩一樣種地吃苦。這些人一方面有意愿融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缺乏獲得這種生活的能力和斗志。
一、相關概念解釋
歸屬感:又稱為隸屬感,它是個體與所屬群體間的一種內在聯系,是指一個個體或集體對一件事物或現象的認同程度,并對這件事物或現象發生關聯的密切程度。對于不同的對象,歸屬感的維度往往是不同的。
吊莊移民:是寧夏經過多年實踐的一種生態移民模式,其特點是在自治區所轄區域內,將貧困人口成批地從一個生態脆弱地區遷至另一個有荒地資源的地區,重建新家園,構建新社區,實現脫貧致富和持續發展。
同輩群體:又稱同齡群體,是由一些年齡、興趣、愛好、態度、價值觀、社會地位等方面較為接近的人所組成的一種非正式初級群體。同輩群體在青少年中普遍存在,他們交往頻繁,時常聚集,彼此間有著很大的影響。
城市融入:“城市融入”是一個社會學概念,是指外來人口進入城市,實現空間地理上的遷移,同時在經濟上和生活方式上適應城市生活,在心理上對城市產生認同。借鑒西方國際移民理論及國內對于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指標設計,主要包含經濟整合、行為適應、文化接納、身份認同四個融入層次。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獻法和訪談法,收集相關文獻資料,訪談熟悉歷史情況的有關人員,掌握興涇鎮吊莊移民的背景、現狀和歷史沿革等基本情況。通過走訪入戶和隨機訪談,對銀川市西夏區興涇鎮興盛村有青年勞動力和就業創業需求的家庭進行訪談,梳理歸納并得出結論。
三、興涇鎮興盛村基本情況
興涇鎮是自治區最早實施“以川濟山、山川共濟”戰略鄉鎮之一,1983年群眾積極響應國家移民政策,從涇源縣遷入興涇鎮,2001年移交銀川市原郊區管理,2002年11月銀川市轄三區重新劃界后,興涇鎮劃歸西夏區管轄。興盛村和其他村一樣,也屬于興涇鎮整村吊莊移民,先輩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由固原市涇源縣各地向現在的興涇鎮整批移居,村里有很多適齡青年勞動力。興盛村位于西夏區興涇鎮南部,轄區占地5.8平方公里,分為5個村民小組,共有村民1180戶3862人,回族人口占比100%。村黨支部現有黨員65名,其中女性10名,35歲以下黨員12名。村“兩委”班子成員5名,其中大專以上學歷2名,平均年齡46歲。全村除在校生和殘疾、高齡等人群外,18~60歲適齡勞動力1900余人,男女性比例基本持平,18~35歲的青年勞動力暫未統計。
四、移民青年城市社會融入影響因素
興盛村移民青年作為本村的“移三代”,同時具備移民和本土的特征,既矛盾又統一,其城市社會融入受以下因素影響。
(一)個人能力的獲得
移民個體是否能融入城市社會與其個人能力情況密切相關,特別是移民青年,在遷入地出生、就學和長大,較其從農村移居而來的父輩而言在個人能力方面有所進步。青年移民比父輩更有勇氣融入城市社會,他們有機會通過求學、技能培訓、婚姻等方式實現遷入地城市社會的“主動融入”,一般來說,個人獲得的能力越大,個人價值實現的程度越大,社會融入度就越高;反之,高度的城市社會融入也會促使個人繼續努力以獲取更大的能力,激勵其實現個人價值最大化。但是移民青年處于吊莊的城市邊緣,往往很難取得較大的個人能力,這就決定了他們實現遷入地城市社會融入的過程并不容易。
(二)社會資源占有
興盛村的移民是整村搬遷的吊莊移民,從遷出地流出到遷入地適應,移民周圍的社會資源有所變化,這給他們的城市社會融入帶來了一定的影響。青年移民在社會資源占有方面比自己的父輩更有優勢。他們自出生以來,遷入地社會交往決定了他們在血緣、地緣、業緣等方面都接觸了更多的社會資源,這些資源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應對各種挑戰,適應移民生活,實現遷入地城市社會的順利融入。但由于移民整體搬遷后,村落中村民的同質性仍然很高,村落的組織結構(村落聚居)和團結方式(機械團結)并未改變,移民青年在傳統吊莊范圍內獲取的社會資源往往是單一的、匱乏的,歷史的吊莊范圍及周邊的高度同質和聚合也使移民青年群體在遷入地的城市社會融入倍加艱難。
(三)傳統價值觀念
通俗地講,“吊莊”是指一家人走出去一兩個勞動力,到外地開荒種植,就地建一個簡陋而僅供暫棲的家,這樣一戶人家分居兩處,一個莊子吊兩個地方,故稱之為“吊莊”,把貧困地區群眾整體跨區域搬遷稱之為“吊莊移民”,有將村莊直接“吊”過來的意味,而追溯歷史,興涇鎮的前身正是移民吊莊。興盛村的移民是自固原市涇源縣遷來的,他們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經過吊莊整體搬遷,移民群體在遷入地同樣聚居,觀察興涇鎮目前所轄的行政村,“興盛”“黃花”這些地名在涇源縣同樣存在,或許一模一樣的村名正是整體搬遷不忘故里的具體表現之一。所以,在移民村內,傳統的價值觀念與搬遷前的舊村別無二致。傳統的價值觀念既奠定了村民之間社會交往的基礎,又影響了居民在遷入地城市社會的融入,青年移民群體同樣面臨這樣的矛盾。
(四)文化接納認同
整村搬遷而來的興盛村在對遷入地的文化接納與認同方面也有所保留,雖然青年移民群體“移三代”的身份決定了他們不會像父輩一樣幾乎對遷入地的文化全盤否定,但從小的耳濡目染也讓他們不得不在“一邊接納、一邊抵觸”的矛盾狀態中反復拉鋸,這體現在很多方面。比如很多村民家中,有些年輕的媳婦往往穿著打扮入時,在個人形象管理方面看不出和城市人有特別大的區別,但仔細聊聊就會發現,她們無論是在生育觀念上,還是在個人生活上都與城市女性相去甚遠。再者,有家長因為孩子出去“喜歡胡吃”(即食用了禁忌食物),不想讓孩子外出務工,詳細了解會發現,有的孩子只是吃了一個龜苓膏,因為其父母并沒有見過和吃過龜苓膏,也不了解龜苓膏的成分,所以形成了對遷入地從文化符號到具體事物的抗拒。青年移民雖相對父輩而言對遷入地文化接納認同度較高,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來自原生家庭和環境的影響,這也給其城市融入帶來挑戰。
五、移民青年就業存在問題
(一)從業條件與就業技能有差距。興盛村的移民青年因“就近入學”政策的影響,大部分都在本地的移民吊莊學校就讀,這些學校師資力量薄弱,生源基礎較差,所以很多個人學業上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未能獲得較高的學歷文憑和從業技能。而當前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他們的自身情況,很難滿足用人單位的用工條件,存在勞動力市場中常見的“供需不匹配”情況,在整個勞動力市場中不具備競爭優勢,無論是學歷還是技能,都與從業準入標準有所差距。
(二)從業愿望與就業現實有落差。按時間來算,目前的興涇鎮興盛村移民青年群體屬于“移三代”,都是在興涇鎮本地出生就學,沒有經歷過移民前的生活,在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上更傾向于過上“都市人”的生活,普遍具有“市民化渴望”,因此更希望自己能找一份較“體面”的工作,不想再像先輩一樣吃種田的苦。但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分層加劇,階層的上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存在青年有“就業夢”和求職愿望,但在現實中受到打擊的情況。這種打擊使移民青年群體產生了從業愿望與就業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也反過來影響了他們的價值觀念。筆者在入戶調查的過程中發現,大部分青年都不愿意照看家里的牛,轉而去城里“混生活”,以便于有機會找一份“體面”的工作,父母也不知道孩子在城里做什么,表示不指望孩子能為家里做什么貢獻,只要可以養活自己就行了。
六、移民青年就業融入對策建議
結合興盛村青年移民在就業和城市融入方面的需求,從以下幾方面提出對策建議,以幫助移民青年群體盡早就業和更快融入城市,緩解移民青年就業難問題。
(一)依托政府平臺提升移民青年融入能力
移民青年就業不能只依靠青年群體自身“單打獨斗”,就業平臺對其而言十分重要。各級政府公共就業服務部門應積極落實公共就業指導、線上線下招聘、職業介紹、勞務等各項就業創業惠民政策,不斷加大政策宣傳力度,積極推薦有求職意愿并符合條件的重點就業群體參加各類招聘活動,移民青年可借助本地公共就業平臺求職就業。近幾年,隨著自治區“三大三強”“兩個帶頭人”工程以及西夏區“六抓六強六促”等行動的開展,西夏區政府有關部門號召“以技能培訓促就業創業”,整合科技、農牧、就業等部門培訓資源,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舉辦各類技能培訓,引導村民就業創業,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力度。興盛村所在的興涇鎮政府對接自治區、銀川市和西夏區各級政府及部門,組織適齡勞動力參加農業技術、養殖技術、家政服務、烹飪、電焊、手工編織等實用技能培訓,為移民青年個人能力提升做出努力,通過個人技能提升推動其實現遷入地城市社會融入。
(二)整合社會資源構建移民青年融入關系
發揮黨組織作用。近幾年,興涇鎮結合市場需求根據自身實際開始積極發展特色產業,按照“支部+村集體+合作社+建檔立卡戶+農戶”的模式,千方百計為村民開辟出勞務輸出、種植養殖、拱棚蔬菜種植3大增收渠道。就“標桿人物”作用發揮來說,興盛村現住人員中有政府部門退休返鄉的公職人員,還有一些是在各行各業有突出表現的優秀代表。這些行業領域內的“領頭羊”,不但自身贏得了財富和榮譽,更積極帶動了本地經濟發展。他們積極利用自己的優勢和資源推動本村問題的解決,吸納待業青年實現本地就業,為許多移民家庭帶來可觀收入的同時,也為青年移民拓展人際交往、構建社會關系網絡和進一步實現遷入地城市社會融入提供了可能。
(三)轉變傳統觀念提升移民青年融入意識
興盛村由于整村搬遷,村內居民的同質性非常強,傳統觀念根深蒂固,傳統思想深入人心。近幾年,隨著村(社區)改造,有一定經濟實力的村民住進了樓房,村民的聚居形態有逐漸分散的趨勢,居民的思想觀念也隨著居住形式和從事生產活動經營的多樣化而發生變化,傳統觀念不斷被新事物、新思想解構,思想觀念的與時俱進大幅提升了移民青年的融入意識。
(四)增強文化認同培養移民青年融入歸屬
興盛村的村民經過整體搬遷,保留了對其故里涇源縣主流文化——秦隴文化的強烈認同,在遷入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體現出濃厚的秦隴文化特色。這種“文化守護”一方面是保守求穩、思戀故土的體現,另一方面也對移民青年的遷入地城市社會融入帶來了一定影響。因為寧夏南北分屬兩種文化類型的緣故,移民自遷移后就深陷“由農村到城市,由秦隴文化到塞上文化”的雙重不適應交織的困惑。隨著在遷入地本土出生的一批移民逐漸長大成年,并在銀川接受教育和結交本地朋輩群體,“文化守護”的現象在年輕人中已不多見,“移二代”“移三代”在遷入地文化認同方面已經與銀川市民趨同,慢慢從思想上、歸屬上都逐漸完成市民化過渡和遷入地城市社會融入,獲得了較強的歸屬感。
(作者單位:寧夏銀川市西夏區就業創業和人才服務中心)
作者簡介:劉宇晶,女,漢族,寧夏大學法學院社會工作碩士,現為寧夏銀川市西夏區就業創業和人才服務中心四級主任科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