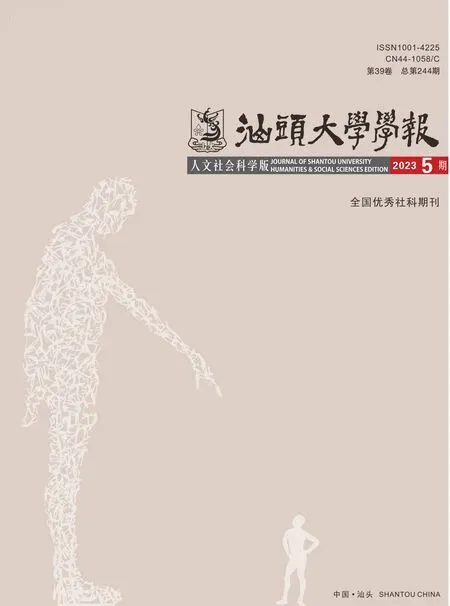論《羚羊與秧雞》中的科技倫理與生態共同體建構
王青璐
(肇慶學院文學院,廣東 肇慶 526000)
《羚羊與秧雞》是加拿大文學女王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創作的一部展現人類未來恐怖走向的小說。其中,絕大多數人類死于喜福多藥片制造的災難,實驗室中誕生的后人類取代了傳統人類。研究者對小說的分析基本圍繞科技發明對人類未來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這個方面展開。在丁林棚看來,小說旨在批判科技無節制發展背后的“技術和消費主義對人性的玷污”[1]114。格魯夫認為小說是對現有科技發展狀況的批判,提出“將倫理融入全球化的方方面面,建立和諧的全球秩序和包容性的星球意識,維持人與自然世界的平衡,人類社團之間的平衡,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平衡”[2]181。阿特伍德也提出關于科技和人類未來發展的疑問:“我們如果繼續按照現在的路走下去會怎樣?這個斜坡有多滑?我們的可取之處是什么?誰又愿意制止我們?”[3]346她在小說中譴責發展至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對當下過度開發自然資源的行為和存有爭議的人類增強實驗進行批判,揭示科學研發實驗中的倫理越位行為對生態共同體和人類自身造成的巨大傷害。小說將人類的未來寄托在科學活動主體的道德取向上,希望科學家能受到科技倫理的約束,在不破壞人同生態共同體關系的情形下,進行科學研究。
一、人類中心主義的局限與倫理越位
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文學“是特定歷史階段社會倫理的表達形式”[4]1。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人類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生物性選擇即自然選擇階段,這個階段人獲得了區分于獸的外形;之后通過教與學,人類進行第二個階段,即倫理選擇階段,人成為倫理意義上的人;最后人類將進入第三階段,即科學選擇階段,“科學選擇解決科學與人的結合問題”[4]251。《羚羊與秧雞》想象了人類從倫理選擇階段向科學選擇階段過渡時可能出現的血腥暴力事件:科學家秧雞發明、推廣喜福多藥片,讓絕大多數人類暴病身亡。所以,不少讀者、研究者為小說中出現的科技力量的負面影響感到擔憂。不過,作者本人卻希望讀者、研究者“不要誤認為《羚羊與秧雞》反科學”[5],聲明“科學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是一種工具”[5]。通過細讀小說可以發現,除了科技帶來的負面影響,作者還對人類發展過程中思想價值與物質、技術發展脫節,科技倫理的失效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局限可能會引發的災難感到焦慮。
秧雞發動的“無水的洪水”災難,可視作是在應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局限性,終止人類中心主義極端化走向的嘗試。人類中心主義“是一種以人為宇宙中心的觀點。它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必然地構成一切價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不具有內在價值而只有工具價值”[6]58。人類中心主義有著悠久的歷史,“西方哲學傳統否認人與自然之間有任何直接的道德關系”[7]105,認為只有人類才有道德身份,在對待人和其他生命的關系時往往以人的利益為價值取向,肯定并提倡人類具有征服者和主宰者的地位。二十世紀以來,不少理論者開始反思人類中心主義的負面作用,提出“非人類中心主義”“去人類中心主義”等理念,嘗試修復人同生態共同體的關系。但是只要人在場,人類中心主義就會一直存在。所以,“去人類中心”的企圖是徒勞。文學倫理學批評始終對人類存有希望,相信“只有人才能建立維護自然秩序的倫理規范,也只有人才能擔負保護自然和解決生態危機的道德責任”[8]24。人類必須發揮理性意志限制自己的行動,積極應對科技發展和文明進程中一系列活動引發的不良后果。小說中的科學家秧雞以喜福多藥片滅人,又讓新型人類秧雞人取代人類生活在世界上,其實是對已暴露出局限并走向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進行修正的嘗試。小說中,整個生態系統在人類的活動下變得千瘡百孔。潘多拉的盒子早已打開,科學家秧雞只是加速了災難的進程,反而讓生態共同體得到重建的機會。
倫理越位是指人類在與大自然的關系中“毫無限度地入侵大自然留給其他生物的領域”,“入侵、破壞或占領不屬于自己的領地”[4]214的行為。小說中出現的倫理越位現象有兩種:分別是人類對外界環境發起的倫理越位行為和人類對生物體內基因、蛋白質等結構、元素發動的倫理越位。作品中,承載人類和萬物生活的生態系統已走向崩潰:“海岸附近的地下畜水層變咸了,北部的永久凍土層開始融化,遼闊的苔原泛出沼氣,大陸中部平原地區的干旱不見結束,中亞地區的大草原變成了沙丘,肉類越來越難弄到了”[9]26。環境惡化也在威脅人類的生存,底層、邊緣人群受到的影響最大。雜市是底層人群聚集的區域。生活在雜市的人們必須佩戴“可以過濾掉微生物,還能去除可吸入顆粒”[9]298的口罩才能正常生活。
科學家還在粗暴地改變生物的原生性,貪婪地從其他生物的性命中攫取利益。科技讓他們“有了上帝的感覺”[9]53,生物通過數億年進化而來的蛋白質、細胞、組織在實驗室被重新組合成新型生命。而這些新的物種都是為滿足人類的需要而設定的,如器官豬。為了增產、節約時間成本,滿足人類換取健康鮮活內臟和器官的私欲,科學家在良種轉基因宿主豬體內培植多種安全可靠的人體組織器官。一只豬體內就同時長著五六只腎。新創造出的攜帶人類基因、長著人類器官的生物也混淆了人與其他生命體的邊界,打破大自然的規律。
小說中的科學家還將研究對象轉至人類自身,進行人類增強(human enhancement)實驗,創造新型人類。人類增強是一項發展不完善且存在爭議的實驗活動,可分為彌補性增強和擴展性增強兩類。彌補性增強就是用移植或者植入人造器官等方式讓具有先天缺陷的人變為“正常人”。擴展性增強則是“本來就沒有缺陷的‘正常人’,希望使自己得到超越正常性的擴展”[10]98的實驗活動。小說呈現了人類增強實驗成為熱銷產品的現象。欣膚公司研發出用“新皮膚替換舊表皮層的方法”[9]57,出售能打破人體正常新陳代謝規律、讓人青春永駐的商品。而誕生于實驗室的后人類秧雞人則是為滿足市場需求而設定的,“具有任何體貌、心智或精神上的特征”,能夠讓“整個人都可以按預先挑選好的特點被創造出來”的“類型齊全的雜交品種”[9]315。阿特伍德的想象也不是天馬行空,現實中的科學實驗也早已觸碰了人類基因池。可避免雙親遺傳缺陷的“三親嬰兒”已于2016 年誕生,“三親嬰兒”除父母雙方的遺傳物質外,還攜帶來自一位健康女性捐贈者的線粒體DNA 的科學嬰兒。2018 年11 月26 日,中國科學家賀建奎宣布了首對能天然抵抗艾滋病病毒的基因編輯雙胞胎露露和娜娜的問世。在《羚羊與秧雞》中,作者則通過人物的命運來表達了對觸碰基因池的科學實驗的警惕和擔憂,認為一些科學活動缺乏未來視野,無視人和其他生物之間輔車相依、唇亡齒寒的關系,會給人類帶來災難。
《羚羊與秧雞》呈現人類和動物在人類倫理越位活動中的悲慘遭遇,批判極端人類中心主義帶來的災害,說明人類不能憑借技術擺脫生態破壞的罪責,更不能從生態共同體的災難中幸免,也指出了人類對其他生命犯下的罪惡,最終也會在人類身上出現報應。吉米、吉米的媽媽、羚羊和阿曼達四人都同基因編輯生物浣鼬有著命運上的聯系。浣鼬是實驗室高手們“業余愛好的產物”[9]53,性格溫順、性情好,長得聰明伶俐且人畜無害。吉米在生日那天得到浣鼬“刺客”作禮物后,就把它帶回學校向他人顯擺。在唐娜·哈拉維看來,這種把寵物當成工具來讓自己獲利的做法,就是一種以人類為中心的“嗜技術的人文主義自戀癥”[11]33。吉米的媽媽不支持主流科學家的倫理越位行為,也反對吉米的做法。她在離家出走時把浣鼬帶走,理由是:它“生活在野生、自由的森林里會更快樂”[9]63。被槍決前,她還提醒吉米:“別忘了‘刺客’。我愛你。不要讓我失望”[9]268。吉米在“天塘”實驗室初見羚羊時,她也“抱著一只年幼的浣鼬”[9]319。羚羊出生在東南亞的村子里,自幼被家人賣給人販子做花童、雛妓,同浣鼬一樣,善良無害,脆弱、不堪一擊。她的結局是被秧雞割開了喉嚨。羚羊生前還從自身經歷中領悟出人類是“極少數幾個在面對資源急劇減少時仍不限制繁殖的物種之一”,絕不會“削減自己的物資供給的”[9]123。小說的尾聲,吉米在森林里見到兩個男人在烤浣鼬吃。前女友阿曼達被俘,是他們的儲備食物和泄欲工具。聞著烤肉味,見到幸存人類的吉米沒有感到振奮,反而對浣鼬產生了同情:“他們一定開槍打死了它。可憐的動物”[9]385。小說以浣鼬串聯起不同的人物在人類倫理越位活動中的悲慘遭遇,在反映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局限會帶來負面影響的同時,也對讀者進行一番警示。
二、科技倫理與科學家的道德取向
小說在批判人類中心主義的局限性和倫理越位行為的同時,也寄希望于科學活動主體能夠樹立正確的道德取向,用科技倫理進行自我約束。小說最重要的科學活動主體秧雞是一個形象復雜、評論不一的科學家。阿特伍德通過秧雞發起的“無水的洪水”人類滅世之災,呈現用科技倫理約束人類倫理越位的必要性,反思科學家道德取向的重要性,認為科學家也應該樹立正確且有利于生態共同體發展的倫理道德觀,為生態共同體和弱勢人群服務。德國哲學家漢斯·約納斯倡議的技術倫理能夠為解決小說中暴露的科技倫理問題提供啟發。約納斯認為“地球的權力是頭等的,人再也不能只想著他自己”[12]28;“技術所固有的無節制傾向使威脅成為迫在眉睫的事”,人類“必須以一定適度的道德從技術本身中獲得治療其疾病的手段,這就是技術倫理學的核心”[12]31。
從研究現狀來看,秧雞是一個評價褒貶不一的人物。丁林棚認為秧雞“不僅沒有實現完美的純粹理性的人性,反而毀滅了整個人類社會,也給自己帶來了滅頂之災”[13]112。鄧寧則在解讀秧雞、羚羊與吉米三人形象時,提出他們之間的關系象征“基督三位一體”,肯定了“秧雞發揮父親的作用,是一切的創始者,戰勝了混亂”[14]95。其實秧雞形象的復雜性和爭議同小說的敘事形式有關。《羚羊與秧雞》采用了故事外的全知敘事者,圍繞秧雞的好友“雪人”吉米的經歷建構雙線敘事模式:一條是現時敘事,聚焦吉米在災難后的生活;另一條是回顧性敘事,以倒敘的形式從吉米的童年家庭生活展開,展現他和秧雞、羚羊間的往事。所以,秧雞形象的建構是以吉米為中介來實現的。吉米本身就不是一個可靠的參照對象,同秧雞等科學家在生活方式和認知層面上有著巨大的差異。他還沉溺于世俗享樂,行事懶散,有過眾多情人。在吉米眼中,少年秧雞是一個書呆子,穿著沒有“著裝標準和視覺效果,平淡得乏善可陳”;是運動低能兒,不會進行“特別需要力氣的那種”運動,“不適合參加那些需要團隊配合的運動”[9]74。秧雞就讀的理工科學校在吉米看來是“孤僻者大學”,那里的學生都是“邋遢相”“不拘小節”“不修邊幅”[9]211。通過庸人吉米的視角來建構秧雞形象,必然會削弱秧雞形象的多樣性和正面性。災難后,吉米帶著后人類秧雞人走出實驗室,來到海邊生活。作為幸存者,他要躲避外界捕食者的威脅,忍受氣候災難,還要解決飲食生計。異常孤獨的吉米陷入了癲狂狀態:“要么他就像那些器官豬一樣嘟噥、尖叫,或如狼犬獸一般嚎著:阿嗷!阿嗷!有時候到了黃昏他就在沙地上跑來跑去,把石頭扔進海里并大吼”[9]11。為排解寂寞,他還時常自言自語,甚至出現了幻聽。讀者、研究者在了解吉米的經歷后,自然會在同情吉米之余,譴責秧雞的科學活動帶來的災難。
事實上,秧雞是一個有正常社交,有七情六欲,獲得過其他人物的支持和贊賞的人。吉米媽媽認為他有“讓人十分欽佩的心智”,“不會欺騙自己”[9]71。羚羊很尊敬他,認為他“生活在一個更高的世界里”,“正在做大事”[9]324。秧雞也有一定的人文素養,曾在聊天時引用過拜倫的話:“如果人們有別的事可做,誰還會去寫作?”[9]172他很重視與吉米的友誼,讀書時會把“自己復習功課的時間騰出來輔導吉米”[9]180,建議吉米“好好讀一讀斯多葛哲學”[9]72,到精英學校沃特森-克里克之后,也會請吉米來做客。秧雞對羚羊有著狂熱的愛情。在吉米眼中,“他簡直是在討好她”,“對她信賴有加,也許超過了對吉米的信賴”[9]325。所以,秧雞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科學怪人。
之外,不同于主流科學界,秧雞對人類中心主義保持清醒、冷靜的批判態度,重視生態共同體的和諧統一,身上體現了正面的科技倫理的約束。他關注生態共同體的健康穩定,對整個生態共同體抱有同情心與責任感,還對其他科學家長期從事的倫理越位行為深惡痛絕。他在“天塘”實驗室中復原了一片“生長著郁郁蔥蔥、可調節氣候的熱帶雜交植物群”[9]308供秧雞人居住,表達了對人與生態共同體和諧關系的重視。秧雞的生態理念同美國科學家及環保主義者奧爾多·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中提出的“土地倫理”趨近。在20 世紀40 年代,利奧波德發現尚未有一種倫理理念能夠處理人和土地以及土地上生長的各類動植物的關系。于是他“擴展了群體概念的外延,把土壤、水、植物、動物囊括其中”,“把這些要素統稱為——土地”,“扭轉人類在‘土地-群體’中的征服者角色,將我們變為‘土地-群體’的一員公民”[15]210。秧雞也會從生態共同體整體利益的角度出發,反思他和其他科學家的科研活動可能引發的后果。
秧雞個人所持有的科學倫理觀念也讓他陷入倫理兩難的局面:要是服從主流科學家團隊的選擇,配合主流的需要進行科學生產活動,就會加劇對生態共同體的破壞;如果選擇以喜福多藥片終止倫理越位,維護生態共同體的利益,就會違背當時主流科學界的共同追求,成為異端。可他義無反顧地站在了主流的對立面上,做出違背極端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選擇。所以,秧雞是在生態共同體徹底崩潰前制止了更多的倫理越位行為,讓生態共同體得到喘息的機會。秧雞以喜福多藥片改變世界的行動看似是非理性行為,實際是對現實世界中技術倫理力量單薄、人類中心主義理念盛行的現象的抗議,也是科學活動主體在科技倫理指導下進行的撥亂反正。從生態共同體發展的角度來看,秧雞起到了重整乾坤的作用,成功扭轉了人與生態系統間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讓生態共同體重歸平衡與穩定。小說借秧雞的倫理選擇強調了科技發展中維持生態共同體的和諧、穩定的重要性,凸顯了科技倫理在場的必要性,指出科學家應對人類和地球的未來負責。
但是,秧雞發動的“無水的洪水”災難和他最后殺害羚羊的行徑,都暴露出其個人道德取向的缺陷。他缺乏對個體生命的尊重,自大地認為可以主宰、安排他人的命運。他認為羚羊能為自己殉情:“要是我不在了,‘羚羊’也不會在。”[9]333最后,他在喜歡羚羊的吉米面前殺死羚羊,再自殺,把吉米留在被喜福多藥片清洗過的世界上。秧雞的行動說明了只依靠科技倫理的約束,是不能確保科學活動真正為人類造福的。科學家必須要完善個人道德價值取向,平等地看待、尊重其他生命,重視生態共同體的和諧、穩定。
三、人類增強與生態共同體修復
文學倫理學批評提出科學選擇是人類文明在經歷倫理選擇之后正在或即將經歷的一個階段。未來人是科學選擇的結果:“是通過技術對處于倫理選擇過程中或完成了倫理選擇過程的人進行科學改造或以科學的方法制造人”[16]70。《羚羊與秧雞》在關于人類未來的暢想中,沒有繪制出科技興盛的圖景,反而呈現了絕大多數人類在被科學家研發的喜福多藥片消滅后,人類文明和科技中斷的可能性。由此,小說以回到過去的思路打斷了通往未來科技神話的進程,對如何降低人類倫理越位的侵害,維護生態共同體的和諧穩定,以適應人類在未來的生存,進行深入思考。阿特伍德在書中發出了人類必須敬畏自然,尊重生態共同體的號召,還探討了人類增強實驗為代表的科學技術能否發揮有效作用,推動人與生態共同體關系的修復等問題。
小說關于人必須敬畏自然的理念是借由吉米在災難發生后的世界中的遭遇來進行展現。阿特伍德戳破了科技發展給人類帶來的有關上帝、征服者身份的幻想,傳達了人類應對大自然保持敬畏的觀點。在德國哲學家漢斯·約納斯看來,“敬畏崇拜”是一種“倫理的義務”。他把敬畏的價值訴諸于“恐懼”的感覺:“我們這些強者和有權力意識的人必須蓄意地并且以自我教育的方式使自己置身于‘開始學習恐懼’的處境中”[12]44。約納斯的觀念同其生活時代有關,20 世紀60、70 年代世界處于美蘇冷戰和核戰爭的威脅中。2003 年問世的《羚羊與秧雞》距離漢斯·約納斯在1979 年的《技術、醫學與倫理學》中談論“敬畏”僅過去24年。在這期間,生物科學的發展突飛猛進。一些學者敏銳地發現了生物技術潛在的破壞力不亞于核武器。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就在《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后果》中指出,生物技術比核武器更難掌握,“能夠在小得多,且經費要遠遠低廉的實驗室進行,全球也沒有達成限制其風險的類似共識”[17]189。
吉米在災后世界受到的威脅中,有一部分來自那些出自基因編輯實驗的新物種。他不得不上樹,躲避大腦皮層植入了人類腦細胞的器官豬、兇猛的狼犬獸、野貓等擁有超常體力和智力的食肉生物。其中,器官豬擁有超越普通豬和其他動物的智商,豬群內部能夠交流協作,能夠采取聲東擊西、使用誘餌等方式捕獲獵物。除了新型物種,吉米還要逃避各類自然災害的傷害。小說中,自然災害“如一只掙脫了束縛的巨獸”[9]246,龍卷風經過時“像一臺龐大的發動機里的齒輪組在運轉”、“一件巨大的物體撞擊了外墻”[9]245。人類的微小、脆弱,在自然面前不堪一擊的形象借吉米的遭遇在小說中建構出來。他的遭遇是對災難前人類的各類狂妄舉動的回應。可見,將自己視作征服者的人類,“最終也敗給了自己的征服”[9]210。《羚羊與秧雞》向世人發出了要對自然和生命保持敬畏的聲音,力圖喚醒人們重新看待人類在自然中的真實力量。
文學藝術為人類暢想未來提供場地,秧雞人也是研究者秧雞為生態共同體自身修復做出的貢獻,反映了阿特伍德持有的“人類一切科技皆為人體與心智的延伸”[18]66的觀念。一些研究者也認為,《羚羊與秧雞》展現了科學技術的正面價值。波爾森認為秧雞利用科學“控制人類的本性”,“生物工程和環境友好的原始人秧雞人”是“人類的替代品”[19]95。卡納萬肯定了秧雞人的正面意義,聲稱自己“將《羚羊與秧雞》《洪水之年》當成一個關于讓我們的世界變成更好的社會而不是重歸自然的聲明來讀,它們寓言了改變社會關系與生活方式的急切必要性”[20]155。后人類秧雞人身上體現了關于用人類增強實驗等科學手段改善日益惡化的生態共同體的思考。
總體而言,秧雞人是環境友好型物種。秧雞人的生活習性符合約納斯在《技術、醫學與倫理學》中提到的“簡樸”價值理念。“簡樸”意味著消費習慣中的節制與適度,“節制與適度在整個悠久的古代西方文化中曾是人人必備的德行”,提倡“簡樸”理念的現實必要性在于“阻止包含在整個過程中的搶劫、物種退化和星球污染”,“預防星球資源的枯竭”,防止“人為造成的世界氣候不可救藥的變化”[12]45。與“簡樸”理念相對應的是無止盡的欲求,秧雞意識到人類有欲壑難填的特點,“人總要追求更多更好的東西,這種欲望之潮會壓倒它們”[9]307,所以設計了欲求低的秧雞人。秧雞人的壽命被限定為無法超過三十歲。因為在設計者秧雞看來,長生不老只是一種概念:“如果你不把‘必死’看成死亡,而當作對它的預知和恐懼,那么‘長生不老’就是指這種恐懼的缺席”[9]314。它們被設定了固定的交配次數和有限的發情次數,“每個女性每三年一次就足夠了”。秧雞借鑒了狒狒和章魚可變換膚色的能力,讓女秧雞人發情時,“臀部和小腹會呈現蔚藍色”[9]169,由此對異性發出信號。另外,每次發情時,女秧雞人會從求愛的男性中挑出四人,與他們輪流發生性關系,直到完成受孕、藍色消退為止。秧雞認為,這種設計可以保證所有人的性需求,人類性需求降低后,就能大大降低犯罪率,“不再有賣淫,沒有對兒童的性虐待”,“沒有拉皮條的,沒有性奴隸”,“不再有強奸”。人類傳統的家庭倫理關系也會發生改變,與之有關的爭執、暴力也會減少,“不再有什么財產需要繼承,不再有戰爭所需要的那種父子間的忠誠”,“也不會再引發自殺或他殺”[9]170。因此,秧雞人能夠過著一種簡單、快樂的低欲求生活。
秧雞人身上還匯聚了其研發者對未來人類日常生活、同生態共同體的關系等多方面問題的期許。秧雞用基因編輯技術賦予秧雞人超強的野外生存能力。秧雞人是人與多種動物、植物基因拼接的產物。在外形上,他們有著不同的膚色,但個個都有“抗紫外線的厚實皮膚”[9]6。他們的身體散發著柑橘類水果味道,能夠驅走蚊蟲,所以秧雞人不用穿衣遮陽御寒、防蚊蟲。秧雞人的尿液中添加了編碼指令序列的化合物,“能有效驅趕狼犬獸和浣鼬,也能在較低的程度上對付野豬和器官豬”。男性秧雞人每天都會舉行晨間儀式——集體撒尿來驅逐會傷害他們的生物,由此避免了同其他生物發生沖突。他們還被賦予自我治療的生理屬性。秧雞發現“貓科動物在發出呼嚕聲時其頻率與用于治療骨折和皮膚損傷的超聲波一致”,就把秧雞人的“舌骨結構加以修改,將自發神經通道連接起來”[9]161。之外,秧雞人還被設計為食素生物,吃草、樹葉和根,因此不需要捕獵。在走出“天塘”實驗室前,他們還被灌輸了所有的生物都是羚羊的孩子的理念,由此相信萬物平等。
阿特伍德筆下有關秧雞人走出天塘實驗室并順利適應大自然的情節,想象了基因編輯技術幫助未來人類突破各種限制,更好地生活的可能。如果《羚羊與秧雞》沒有出現人類滅絕災難,秧雞人就會順利進入消費市場,與人類共處。而喜福多藥片引發的災難則成功規避了人和新型人類相處的問題。可是現實中,該如何面對正在興起的人類增強技術呢?事實上,人類增強技術飽受爭議。沒有人可以預見觸碰人類基因池的后果。支持者認為人類增強實驗只要正確、規范使用就能為人類造福。美國哲學家羅納德·德沃金在《至上的美德》中指出“使未來的人類壽命更長、更有才華、取得更大的成就,這種超然的抱負本身沒有錯”[21]481。英國納菲爾德委員在2018 年發布了有限度支持基因編輯的報告《基因編輯和人類生殖:社會倫理及法律規制》。反對者如斯洛維克則批判了這種科學實驗,認為“人類與動物身體的混合創造了……所謂的‘嵌合體’,使人很容易想起神話中的妖物,自然的怪胎”[22]190,是對自然的褻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就賀建奎宣告基因編輯雙胞胎出世一事,于2018 年11 月27 日發布了《中國科協生命科學學會聯合體聲明》,表示中國科學界現階段對基因編輯技術持審慎態度,反對人類基因編輯實驗,還指出“基因編輯技術作為一項革命性技術正在推動著生命科學研究發展,但其應用安全性尚有待于進一步全面評價,如何審慎使用該技術關系到人類健康和長遠福祉”[23]。福山在人類增強問題上也表現得十分謹慎,指出:“我們試圖保存全部的復雜性、進化而來的稟賦,避免自我修改。我們不希望阻斷人性的統一性或連續性,以及影響基于其上的人的權利”[17]172。福山還提出這項技術必須由“民主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決定是正當使用還是不正當使用,希望人類增強等涉及人類基因的實驗能夠受到管束。
盡管小說肯定了人類增強實驗成果——秧雞人的正面價值,但喜福多藥片引發的“無水的洪水”災難還是指出了科技會帶來巨大危害的可能性,也由此削弱了秧雞人形象中的正面性。這一矛盾同作者阿特伍德在小說虛構中探索科學發展與人類未來時的不確定態度有關。出自實驗室的秧雞人反映了阿特伍德對科學技術能為人類造福的觀念的深信不疑。但阿特伍德同時也認為在極端人類中心主義主導下,倫理越位活動可能為人類帶來災難。她以吉米在災后世界中的獨自闖蕩的情節展現了敬畏自然的必要性。而吉米的所見所聞也削弱了小說中科學力量的正面價值,強調了科技的不適當發展可能會引導人類走向恐怖的未來。
如今,長著獠牙,會合作捕捉人類的器官豬已跨越次元壁,來到現實生活中。科學家已經宣布研究出可供養人類內臟器官的新型生物豬。但它們是否會掙脫束縛,恢復動物天性,傷害、獵食人類,我們還無從知曉。這也讓人們思考,基因編輯與人類未來的聯系是否會變得更為緊密。可以確定,今天回頭來看阿特伍德這部出版于2003 年的作品,其中反映的問題與困境都是很值得思考的。人類在未來能否合理利用科技,進入文學倫理學批評憧憬的科學選擇時代,還是將科技轉變成傷害人類自身的“潘多拉的盒子”,都還是未知之謎。而作者阿特伍德始終強調科學只是工具,關鍵在于使用者的情感和智慧是否足夠成熟。雖然小說中的未來幻想讓人不安,但或許這些驚悚的情節能喚起讀者關注生態共同體的平衡穩定,推動科學家保護生態共同體的行動,及時制止倫理越位對生態的破壞,平等對待其他的生命,審慎地進行人類基因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