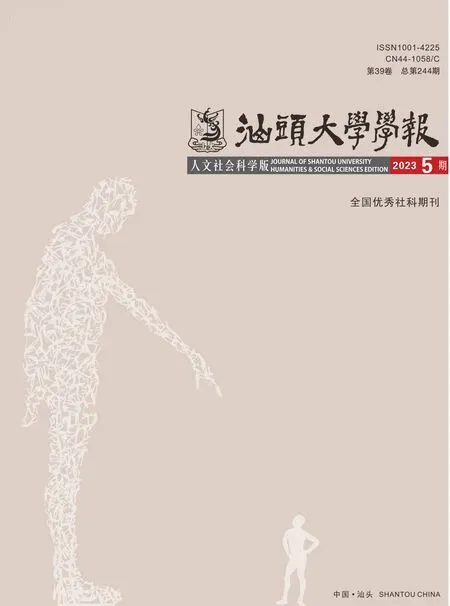杰克·倫敦的亞太敘事與種族倫理意識
王丁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國語學院,北京 100191)
雖然杰克·倫敦因其北疆小說聲名鵲起,但不可否認的是,他“是通過海洋進入文學世界的”[1]。維羅妮卡·瓦申克維奇(Weronika ?aszkiewicz)更是將他譽為“寫作中的水手、航海中的作家”[2]。13 歲時,衣衫襤褸的倫敦攢錢買下了一條舊船,開始在舊金山灣上練習航行技術[3]23-24。由此,貫穿其一生的海洋情結便開始生根發芽。到了1907年,成為暢銷書作家的倫敦才真正擁有了自由航行的經濟實力。于是,他循著約書亞·斯洛克姆(Joshua Slocum)的足跡開始環球航行。盡管環球航行因倫敦身體惡化,最終未能完成。但率先完成的亞太航行成了他人生最后階段的創作源泉。亞太敘事是19 世紀美國文學的傳統母題,自赫曼·麥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將泰比島塑造為“人間天堂”以降,美國作家就追隨著其步伐對亞太地區展開了浪漫的文學想象。到了20 世紀,恰逢美國對外擴張,它將自己的“后湖”擴張到整個亞太地區。作家們對該地區的文學想象與帝國擴張互補互動,倫敦的作品自然也在其中。不少學者都從帝國意識形態的視域解讀倫敦的亞太敘事。羅德·愛德蒙德(Rod Edmond)從疾病與身體入手,探討了殖民入侵對土著文化的破壞。而詹姆斯·倫德奎斯特(James Lundquist)認為,倫敦在種族書寫中表達出了對被壓迫民族同的情感,使他擺脫了種族主義者的標簽。但是,這些非黑即白的解讀都忽視了作家復雜多樣的主體意識和含混雜糅的倫理選擇。亞太敘事是倫敦根據旅行見聞加工而成的,那么,聶珍釗的“腦文本”將會拓展這一過程的闡釋空間。本文將借助“腦文本”的概念,從《麻風病人庫勞》(“Koolau The Leper”)的改寫入手,探討以民族抗爭取代家庭情節,是否真的是種族正義的倫理選擇?那么,為何亞太敘事又對中國疫病化,呈現出種族倫理的悖論呢?文章聚焦于倫敦四次亞太旅行所形成的文本,將其種族倫理意識置于19 世紀初末的歷史語境中,解開文本中的倫理悖論。
一、庫勞故事的改寫與腦文本
如果要試圖闡釋《麻風病人庫勞》的改寫,就要先厘清倫敦亞太旅行的動機與原因,這一動機也促成了他將如何展開亞太世界的文學想象。據倫敦傳記記載,倫敦夫婦是在閱讀了斯洛克姆的《環球獨航》(Sailing Alone Around the World,1900)燃起了冒險的激情,放棄了加州的農場生活,開啟了亞太航行。不過,從倫敦作家身份的角度看,他的航行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為自己的創作找尋更多的靈感與素材。據船上的廚師馬丁(Martin)回憶,“蛇鯊號”就如一座海上的文學寶庫,滿載著杰克寫作用的紙,打字機用的紙,數以百計的紙;還有杰克挑選的五百本書籍,涉及不同的主題[4]。此外,倫敦的亞太旅行也有經濟收益方面的考慮。他在出航前就與《婦女家庭之友》(Woman’s Home Companion)簽定合同,承諾將南海冒險記錄下來呈現給對“遠西之地”充滿好奇的美國讀者,后者為他提供經濟支持。但是對于亞太敘事的創作而言,彼時經濟收益已不是倫敦的主要驅動力,因為他已譽滿國內,技藝也日臻完善。也即說,在創作前期,“他期待寫作的投資能得到回報,他長期約束自己,將時間和精力投入其中”,但“一旦技藝嫻熟,地位穩固,他又信心滿滿地對這項職業表現出幾乎不屑的態度”[5]。于是,他成了自己筆下馬丁·伊登(Martin Eden)的幽靈,內心的真實感受成為其亞太敘事的首要表達目的。那么,倫敦的亞太敘事是如何體現其內心感受與倫理選擇的?
倫敦對庫勞故事的改寫之處就體現了他的倫理選擇。據推測,故事的原版本由“蛇鯊號”的水手伯特·斯托爾茲(Bert Stolz)口述而得[6]。該版本比較可靠,因為斯托爾茲的父親是14 年前被庫勞(Ko’olau)殺死的白人警長。根據他的口述,庫勞是夏威夷島的土著,因為患上麻風病,當地政府要求其去莫洛凱(Molokai)隔離。庫勞同意隔離,但希望和自己的妻兒在隔離區共度余生。因為他的妻兒都沒有感染麻風病,政府拒絕了他的要求。于是,庫勞帶著他的家人逃到了考艾島(Kauai)的山谷中,還殺死了一個前來抓捕他的警長。兩年后,庫勞的兒子因染上麻風病死去,隨后庫勞也死去,妻子派拉妮(Pi’ilani)埋葬了他們后回到家中①Kahikina Kelekona(John G.M.Shelton)在1906 年用夏威夷語將派拉妮的口述記錄下來了,然而并沒有考證表明倫敦懂夏威夷語且讀過Kelekona 的版本,并且這份原住民原始檔案一直被學界忽略。。而在《麻風病人庫勞》中,倫敦刪去了浪漫的愛情與家庭故事情節,代之以夏威夷首領庫勞帶領族人的反殖民抗爭。他筆下的庫勞是一位魅力十足的尼采式少數族裔英雄。
在做出這一改寫時,倫敦其實是把斯托爾茲的口述文本儲存成了腦記憶,再呈現成了書面文本。聶珍釗提出的腦文本概念恰巧為解釋這一過程提供了理論支撐——“當一個人通過聽覺器官接收到另一個人通過發音器官轉化成聲音符號的腦文本時,就轉化成記憶存儲在自己的大腦里,變成又一個腦文本”[7]。構成腦文本的基本單位是腦概念,倫敦借助腦概念進行思維,根據某種倫理規則不斷對腦概念進行組合和修改[8]33,并將其轉化成以文字或符號為載體的書寫文本,倫敦通過修改腦概念加入了自己的倫理選擇。另一方面,聶珍釗將“人的大腦類比于計算機中的中央處理器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腦文本類似計算機中的運行程序”[8]30。而根據喬納森·奧爾巴赫(Jonathan Auerbach)的《男性的呼喚:成為杰克·倫敦》(Male Call: Becoming Jack London,1996)一書所言,20 世紀初自然主義的風行,使得作家們重新審視了從身體(大腦)到機器(打字機)的寫作機制。在提到這一機制時,倫敦使用了輸入/輸出的隱喻,他把打字機想象成作者和文本之間的接口。倫敦聲稱,修改只發生在打字過程中,通過打字定稿后,提交的手稿就會變成印刷品被出版[9]。雖然,此處倫敦試圖強調寫作的機械化生產模型,但是這一隱喻將打字機延伸為腦文本的生產場所、人體的外掛中央處理器,使得腦文本到物質文本的過程更加具象化,進一步證實倫敦的改寫并非靈光乍現,而是有意為之。通過比較庫勞故事的變化,可以看出倫敦腦概念重新編碼的過程中的倫理傾向。
《麻風病人庫勞》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改寫之處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首先,從人物設定上,倫敦放棄了妻子和兒子兩個人物,增加了一群與庫勞共同藏身山洞中的夏威夷麻風病人,淡化了家庭與愛情的因素,構建了一個民族共同體。故事開頭庫勞以“我們”[10]47、“兄弟”[10]52與麻風病人相稱,與“他們”(白種人)劃清界限。因為拒絕被送到莫洛凱,庫勞作為首領,與族人共同建立了一個島外伊甸園,“一個鮮花盛開的峽谷,有著令人生厭的懸崖和峭壁,上面布滿野山羊的糞便。三面墻壁布滿著熱帶植被和洞穴入口——里面是臣民們的巖石巢穴”[10]51。其次,與流傳的口述版本相比,倫敦將大量筆墨用于麻風病人體貌特點的描述。他將他們比作造物主發癲時失手造出的怪物:
他們曾是男人和女人,但現在不再是了。他們是怪物——在面孔和形態上都是人類的怪異漫畫。他們可怕地扭曲著,看起來像是在千年地獄中被折磨過的生物。他們的手就像鷹身女妖的爪子。他們的臉奇形怪狀,猶如發狂的造物主在生命的機器中隨意玩弄的產物,被碾壓、被擦傷。到處都是造物主抹去了一半的痕跡。有一個女人正在流淚,從兩個看不出來是眼睛的可怕的洞里。[10]49
倫敦對病態肌體的細致描寫絕非只是想渲染麻風病的恐怖,而是想借機“揭露殖民體系對當地文化產生的影響”[11]203。這種影響對脆弱、自給自足的南海生態系統往往是毀滅性的。由此,在原故事版本中,未被強調的疾病表征被倫敦刻意放大了,而夏威夷人的病態肌體與巴赫金(Bakhtin)所謂的“怪誕形象”(grotesque image)相呼應。怪誕形象是指在死亡和誕生、成長和形成階段,處于變化、尚未完成的變形狀態的現象特征,猶如一種活死人的狀態[12]29。它是開放的身體,與世界沒有明確的分界線:它與世界、動物、物質相混合[12]32。正是這種閾限性具有顛覆白人權威話語的力量,使得倫敦的版本將敘述重點放置在庫勞帶領其族人的英勇抗爭上。再次,倫敦也將敘述人從原版本中的妻子派拉妮轉化為無名的第三人稱全知敘述者。與《驕傲之屋》(The House of Pride)中其他兩部以白人為主視角的麻風病故事不同,他(她)仿佛站在庫勞的立場,贊美其對前來逮捕他的士兵發出的“我曾生得自由,也將死得自在”的宣言[10]50。故事中,即使山谷家園被炸得稀碎,庫勞也沒有投降,他帶著毛瑟槍躲進叢林中,直到手指潰爛到不能扣下扳機,他將毛瑟槍放在了胸前[10]86,以這種姿態死去。倫敦對庫勞臨死時這一細節的描寫表達了他對夏威夷人至死抗爭的贊賞。
上述改寫塑造出一位尼采式的夏威夷勇士,由此表達出倫敦對夏威夷民族的欣賞與同情,這一內心感受透露出他在腦文本的重組過程中對種族倫理的思考。倫德奎斯特將這一倫理選擇進行了過度地渲染,他認為“倫敦對波利尼西亞人還是西瓦什印第安人公開表達的同情之心,使得他作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者的錯誤的指控被推翻”[13]。誠然,庫勞故事的改寫為分析倫敦的種族倫理傾向提供了文本支持,但是對于倫敦這樣一位身處美國發展關鍵期的文化研究對象來說,非黑即白的絕對判斷未免太過簡單,其思想具有復雜的悖論性,我們需要更加全面地解構他的亞太書寫,從而為其改寫作出更為深刻的倫理注解。
二、亞太敘事與種族倫理悖論
倫敦曾借庫勞之口將麻風病的來源歸咎到在蔗糖種植園中干活的中國苦力身上,這一情節將黃種人妖魔化,顯然與他對夏威夷少數族裔的欣賞相悖。麻風病被稱為“中國疾病”(mai Pake)[11]195的說法顯然缺乏科學依據。1865 年,夏威夷政府在出臺《防止麻風病擴散法案》時,將麻風病的官方名稱改為了“隔離疾病”(mai ho’okawale)。然而,在多數美國作家的夏威夷書寫中仍保留了這一稱呼。“按照瘟疫文化理論的解釋,疾病之前附著種族或者地名。并非無意之舉。它是將疾病歸罪于他者的一種很自然的手段”[14]。將麻風病命名為“中國疾病”,無疑同將肺結核稱為“猶太人疾病”的做法類似,具有妖魔化他者的意識形態目的。
縱觀倫敦的整個亞太敘事可以進一步讀出他對東亞黃種人的歧視與蔑視,從而引發對其種族悖論的深入思考。他一生曾四赴亞太航行,使他得以深入認識東亞的地域環境和東方人的性格特征,因此,他的亞太旅行敘事成為研究其筆下東方形象的重要文獻。他將亞洲人稱作“亞洲佬”(Asiatic),認為黃種人天生精明狡詐,表現出一種仇視與憎惡的態度。與上文中對夏威夷族人英勇坦蕩的贊頌形成對比,使得亞太地區成為其倫理悖論的試煉場。可以說,倫敦的日本之行開啟了他的寫作生涯。17 歲時,他隨“蘇菲·薩瑟蘭號”(Sophia Sutherland)到日本海域獵取海豹,創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說。在母親芙羅拉(Flora)的勸說下,他用《遠離日本海岸的臺風》(Story of a Typhoon off the Coast of Japan,1893)一文參加了《呼聲》雜志舉辦的寫作比賽,并奪得了一等獎[3]40,這件事情堅定了倫敦要靠腦力賺錢的決心。《臺風》一文對風暴進行了生動的記敘,但并未突出故事的發生地。而同時期創作的《夜游江戶灣》(“A Night’s Swim in Yeddo Bay”,1902)則投射出倫敦對貪婪的日本性的厭惡。作品以第一人稱敘述視角展開,講述了一位名叫查理(Charlie)的美國老水手醉酒于橫濱,被日本水手鉗制后,要求以衣物抵船票的故事。該作品只將美國水手的視角單向地傳遞給讀者,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目的性。在查理看來,“日本人通過狡詐的伎倆來奪得西方物質文明”[15],這種急切的渴望則側面表達出作者的種族優越感。1904 年,當倫敦受赫斯特邀請,前往東亞報道日俄戰爭時,他的亞太文學創作出現了轉折點。赫斯特報業政治傾向明顯,一向以煽動民族矛盾著稱。比如,它曾在1896 年煽動美西戰爭,支持美國侵略擴張的行徑。而在麥卡錫主義盛行時,赫斯特報業帶頭呼吁對電影進行嚴厲檢查,美國電影業因為害怕而幾乎癱瘓[16]。鑒于此,倫敦的戰地報道一定程度上與其雇主的傾向同音共律,表達出對白種人的欣賞和對黃種人的貶低。他在報道中將日本比作猴子,把日方的勝利歸功于民族的好斗與狡詐。他寫道:“你有沒有體驗過站在一個籠子面前……那只猴子的表情如此天真、友善,兩只眼睛緊盯著你,毫無惡意,而暗地里卻在挪動著腳,妄想趁你不備向你突然襲擊。所以,要加倍提防籠子里的猴子……當心日本人!”[17]可以看出,他對日本人的態度由厭惡轉為恐懼。日本戰勝沙皇俄國意味著黃種人戰勝了白種人,西方國家此時感受到了來自明治日本的威脅。而倫敦為大和民族貼上“軍事黃禍”的標簽。這些戰地報道成為倫敦日后亞太敘事的前文本(pretext),構成了他的種族倫理與國家身份認同。
倫敦筆下的東亞并非鐵板一塊,其中國形象在“黃禍論”的整體基調下呈現出與“軍事黃禍”不同的民族特性。在1902 和1903 年創作的系列短篇《白與黃》(“White and Yellow”)與《黃手帕》(“Yellow Handkerchief”)中,倫敦首次將中國人塑造成文本的主角。他以青年時期在舊金山灣當牡蠣海盜與漁警的經歷為藍本,復刻了白人漁警與中國捕蝦者的沖突。倫敦借少年漁警之口表達出他心中中國人精明重利的民族特性——他們將網弄成最小的格,“甚至連那些不到0.25 英寸長的新孵化的小魚卵都不放過”[18]。中國性在1904年的《黃禍》(“The Yellow Peril”)一文中被進一步定義。炮聲轟隆下,中國百姓一點也不驚慌,他們仍照常耕作、沿街叫賣。這些日常情景的描述看似是對中國人的欣賞,但倫敦接著表達出的擔憂否認了這一觀點:中國地廣物博加之勤奮的民族特性,若有人喚醒了這頭擁有四萬萬人口的睡獅,一定會威脅西方的安全。西方人永遠不可能喚醒它,而“棕色”的日本人極有可能做到。彼時,聯合的亞洲必定會給美國的經濟與安全都帶來重創。所以,倫敦呼吁西方世界決不能容許“黃禍”發生。“雖然倫敦并非‘黃禍論’的始作俑者,但根據自身經歷對亞太時局的分析和預測與帝國時代需求相吻合,而他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烏托邦敘事也基于同樣的全球性視域”[19]86。在其烏托邦敘事中,倫敦幻想以中國人的種族滅絕消解了“黃禍”的威脅。創作于1907 年的兩部短篇小說《史無前例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和哥利亞(Goliah)主題相似,以科幻的形式對《黃禍》做了進一步的注解。不妨拿《史無前例的入侵》做例子進行解讀。《入侵》將時間推進到1970 年,中國的人口已達5 億,遠遠超過世界上白人人口的總和。西方各國擔心他們很快就會被黃種人的移民浪潮淹沒。一位美國科學家提出用細菌彈對中國進行轟炸,然后進行長達5 年的“衛生消毒”。倫敦顯然關注到了新興的優生學話語,因為他在作品中把孟德爾學說作為解決國際問題的策略。一旦人口增長遠超過可用資源,就在多民族的融合中培育出一個最優秀的種族存活[20]。而這一策略的代價是犧牲不可同化的中國人。勤奮且聰明的中國人在以商業化為主導的現代社會,給美國人帶來了極大的威脅,使得倫敦筆下的中國成為不同于“軍事黃禍”的“經濟黃禍”。
在亞太敘事中,倫敦對同處于東亞的朝鮮雖著墨不多,但通過少量的敘述可知其族人貧窮又怯懦,充滿了奴性,是天生的“仆人”。斯通的倫敦傳記《馬背上的水手》(Sailor on Horseback,1938)記錄了他在日俄前線與朝鮮人的沖突。他的馬夫向軍司令部索取馬料時,一個朝鮮人不肯給他全份。當倫敦指責那個朝鮮人克扣了馬料,對方用刀子做了恐嚇的姿勢,而倫敦則一拳把他打倒在地[3]171。這一小插曲充分展現出他心中朝鮮人的民族特性——他們貪婪但是缺乏力量,這源于被占領幾個世紀后形成的奴性。當日本人經過時,朝鮮的村莊和城鎮都被遺棄了。沒有農田,也沒有人做買賣。幾十個朝鮮青年抽著幾碼長的煙斗,他們精力旺盛、身材健美,但卻習慣了被打、被搶,從不反抗。總得來說,倫敦認為他們的政府很腐敗,人民缺乏主動性。但是,作為役畜,他們卻很完美。所以,倫敦在離開東亞時,給了忠實的朝鮮少年馬仰箕旅費,雇傭馬仰箕到他美國的家中,為他收拾房子、做飯[3]174。由此可鑒,倫敦對朝鮮人的忠誠表示認可和贊賞。但是,又因認為其民族不具有自主性和自強精神,倫敦將朝鮮人視為劣等人,表現出白人的優越感。
倫敦的亞太敘事充滿了矛盾與悖論。在“黃禍論”的整體基調下,東亞三國族人呈現出異質性——他視日本人為“軍事黃禍”、中國人為“經濟黃禍”、朝鮮人為最忠實的仆人人選。這與前文所述的夏威夷話語相對比,呈現出極大的張力。所以,對倫敦的種族倫理觀念不可做單一的決斷。正如里斯曼(J·C·Reesman)所言:“他對亞洲、對種族的看法與態度顯然要復雜得多。雖然倫敦曾認同其所處時代對亞洲人的種族偏見,但他(對種族倫理)的思考遠非止步于此”[21]。那么,我們所要做的不是停留在矛盾觀念的展現上,而是要去挖掘與理解其亞太敘事中種族悖論形成的脈絡。這正符合聶珍釗提出的文學文本批評的本質任務——具有矛盾與沖突的觀點構成了文本的倫理結,“文學倫理學批評的任務就是通過對文學文本的解讀發現倫理線上倫理結的形成過程,或者是對已經形成的倫理結進行解構”[22]13。
三、倫敦的種族倫理意識
如前所述,當倫敦將庫勞故事的口述版和其他亞太旅行所見所聞以文字的方式寫下時,這一過程必然涉及倫理意識的反映。那么,在亞太敘事的腦文本加工成文字文本的過程中,倫敦是受何種倫理規則的支配表現出如此強烈的種族倫理悖論的呢?總得來說,倫敦一生接受的思想學說極為繁雜。斯通將“達爾文、斯賓塞、尼采、馬克思”[3]92歸納為指引其創作的“四駕馬車”。但仔細分析不難發現,斯賓塞、尼采、馬克思都曾受到進化學說的影響。馬克思的《資本論》(Das Kapital,1867)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發表于同一時期。在隨后出版的序言中,馬克思與恩格斯都引用了進化論來加強自己的觀點。他們寫道:整個人類歷史就是一部階級斗爭的歷史,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間的斗爭[23]。斗爭與進化是進化學說的核心觀點。《資本論》把社會看作是一個進化到目前階段的有機體來研究。尼采也是進化論的支持者,因為他認為生命的本質在于生命意志[24],“超人”是進化論發展的最終產物。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ake Zarathustra)的序言中,尼采對進化表達出更加明確的觀點。他說:“人是深淵上的繩索,在動物和超人間拉伸”[25]。我們可以把人看作是動物和超人間進化的某一階段,人類的未來或是返祖、或是永恒超越。由此,達爾文的進化論為馬克思和尼采的學說提出了有力的注解。
而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在達爾文框架上發展出來的,在內戰后傳入美國,彼時正值美國工業迅速發展的時期,資本家將其奉為圭臬,因為它恰巧為商業競爭和適者生存提供了理論依據。據考證,1860 年至1903 年期間,斯賓塞的著作在美國銷售了368 755 冊[26],使他一躍成為19 世紀末美國的文化偶像。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分析了斯賓塞熱的原因,他說“斯賓塞用一種表面上很深刻的語言來表達自己,但實際上完全可以被視為未完成教育的、自學的,甚至是文盲這類群體理解接受”[27]。倫敦就是在自學期間大量閱讀了斯賓塞的著作并將其作為其文學創作的理論依據。《海狼》(The Sea Wolf,1904)中,拉爾森反復強調一種“酵母哲學”——“大吃小才可以維持他們的活動,強食弱才可以保持他們的力量,越蠻橫吃得越多,吃得越多活動得越長久”[28]。“酵母哲學”就是斯賓塞學說的翻版。盡管縱觀倫敦的一生,其思想一直處于波動與流變中,但以斯賓塞哲學為主導的進化學說貫穿于他的創作之中。正如他借“另一個自我”馬丁·伊登之口說:“進化為生命的萬能鑰匙”[29]。那么,亞太敘事中倫敦對夏威夷的同情與對東亞三國的貶低也是與進化學說同音共律的。
倫敦對夏威夷土著的同情并非源于對種族壓迫的反思,而是對斯賓塞倫理的實踐。斯賓塞將道德、幸福、價值等概念融入進化學說,提出“道德是自然進化的產物……所謂行為的善惡,都是由行為能否有利于生命的自我和繁衍決定的”[30]。“自然進化”有著趨利避害、保護自我的傾向,從有助于生存的行為中獲得快樂。這種進化的結果是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而這種幸福是建立在利己主義的基礎上的。在倫敦夫婦開始“蛇鯊號”航行的十年前,也即1898 年,夏威夷已被美國吞并,導致亞太地區的爭奪開始成為美國的戰略重心。在夏威夷作品創作之時,夏威夷與東亞相比已不是“他者”,而是美利堅共同體的一部分。在已確保自己國家“前哨”安全的情況下,倫敦贊美夏威夷土著庫勞的英雄行為,間接為1901年美國頒布的“海島案例”(Insular Cases)對夏威夷不平等的公民權而發聲,這正與斯賓塞所倡導的“最大幸福”相呼應。同時,倫敦還借助作品中對美國和夏威夷政治沖突的淡化和改寫來消除美國吞并夏威夷的不道德感。在去世前最后一次游歷夏威夷時,倫敦創作了短篇小說《我的夏威夷之愛》(“My Hawaii Aloha”,1916)表達出他對夏威夷的歸屬感。他認為,“夏威夷人是任何外來人能得到的最引以為豪的榮譽……總有一天,當我談起我自己,我會說,‘我是一個夏威夷人,我屬于夏威夷’。這便是我的夏威夷之愛了”[31]。
而對于未被納入美利堅共同體的東亞三國,倫敦在其腦文本轉化為文學文本的過程中,受到斯賓塞倫理的無意識影響,采取了打壓與丑化的態度。在親歷了“東亞現場”的倫敦看來,明治維新后的日本進入了帝國主義行列,撼動了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秩序,新的世界史將會開始。若中國這條東方巨龍覺醒,必然使得太平洋成為各國爭奪的中心。那么,基于斯賓塞倫理的第一原則,倫敦將個人和國家幸福置于首位,幻想將東方“他者”消滅。這種幻想在他的科幻烏托邦敘事中達到高潮,他將中國置于病毒滅種的危機下,展現出一種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說的極端應用。倫敦以美利堅民族共同體為核心創造的完美世界不僅用投擲病毒的手段剝奪了東亞人的生命權力,更是剝奪了東亞種族的生育與繁衍后代的權力。他筆下人類發展的終極狀態是讓黃種人永遠留在歷史之中,只有這樣,美國人的幸福才有保證,太平洋地區才不會成為東方的“前哨”。早前國內研究形成了倫敦是一名社會主義作家的刻板印象,而本文得出的種族倫理意識似乎與社會主義的“全人類共同體”相矛盾。其實,倫敦的社會主義思想中始終流露著一種故作姿態,他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者,而是利用社會主義為自己建立一種保護制度,確保自己不會從已登上的白人精英地位跌落。也即說,倫敦的社會主義不是設計出來為全人類謀幸福的理想制度,而是為有著同樣血緣的種族謀幸福的,其目的是使那些擁有特定血緣的“優等種族”更加強大,使他們生存下來,繼承土地,消滅“劣等民族”[19]264。由此可見,《麻風病人庫勞》的改寫與亞太敘事所展現出的種族倫理悖論實則都被斯賓塞倫理所支配與滲透。
現實世界的倫敦處于美國19 世紀向西運動的浪潮中,作為帝國冒險家,他乘著時代的浪花來到遠西之地,試圖循著麥爾維爾的步伐,重拾東方伊甸園的美好想象。而在其亞太敘事的文本世界,遠西之地并非一塊同質化的土地,夏威夷與東亞三國呈現出了巨大的悖論與張力,使得倫敦本人的倫理意識變得更加復雜、難以分析。但是,若參照聶珍釗的觀點,將挖掘作家的倫理意識與剖析文學人物的倫理選擇進行比對,都“回到歷史的倫理現場,站在當時的倫理立場上”[22]4,就能解開這一倫理結了。倫敦受19 世紀末美國社會上斯賓塞風潮的影響,并結合自身感悟與經驗將自己的種族倫理意識投射到亞太敘事的文學影像中去了。在現實與文本的交匯地帶,正如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Criticism and Imperialism,1993)中所強調的“文化與帝國擴張之間的關聯”:我們要把藝術放到全球的現世背景中來考察,所以,帝國主義時期的每一位藝術家都或多或少會受到時代的影響[33]。至此,亞太地區在此被抽象化,不僅成為倫敦種族悖論發生的場域,更是東西方文明沖突與爭奪的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