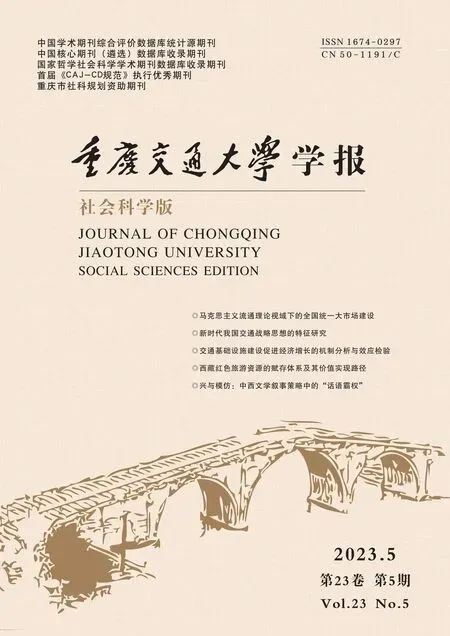疾病與社會排斥
——克萊門斯·J.塞茨小說《英迪格》解析
張 瀟
(安徽大學 外語學院,合肥 230601)
2021年德語文壇最高獎項“畢希納文學獎”頒給奧地利作家克萊門斯·J.塞茨(Clemens J. Setz, 1982—),他成了該獎歷屆得主中除漢德克(Peter Handke)外最年輕的作家。數學與日耳曼語言文學出身的塞茨創作了一系列小說、短篇、詩歌與戲劇,先后獲得不萊梅文學獎、萊比錫圖書展獎、威廉·拉貝文學獎、克萊斯特文學獎等眾多獎項。畢希納獎頒獎辭說道:“他通過驚人的多面性與多元性,百科全書式的知識以及頗具詩意與語言創造性的豐富想象,展現出一種激進的當代性,一次次證明了偉大文學的美麗與特質。他通過長篇和短篇小說反復探索著人的界限。他那令人不安的露骨文辭直戳我們當下生活的核心,因為它遵循著一種深刻的人文主義情感沖動。”[1]此外,作家父親工程師的職業背景與作家本人少年時代對計算機技術的癡迷,使得其語言展現出獨特的科技感、游戲性、鮮活度與廣泛的互文性;母親的醫生身份以及作家本人在殘疾兒童研究所、寄宿學校與老年人護理中心的社會工作經歷,則使其對個人與社會、疾病與健康等重大人生問題有了深刻認識與感悟,促成其從享受獨來獨往到投入社會生活的轉變[2]。
塞茨的代表作《英迪格》(Indigo,2012)獲得當年德國圖書獎短名單與2013年德國經濟文化組文學獎“文本與語言”,引發德語和英語文學屆的廣泛關注與討論。小說以雙線交叉敘事的方式,分別從曾任教于一所患有英迪格疾病兒童隔離中心的老師塞茨和一位曾為該中心患病兒童羅伯特的視角,描述隔離中心兒童的生活狀況,塞茨探尋兒童被轉移真相以及被傳癲狂殺人等一系列事件。作家使用紀錄片與懸疑片的技巧,穿插臨床病歷、研究人員的采訪稿、典型病患的診療記錄與赫比 (J. P. Hebe)小說手稿等真實與虛構的文件插圖,從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教育學與生物學角度探討英迪格病與患病兒童的種種問題。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樂于并長于“用一種十分特殊的方式在文學作品中探討當下與當下現實”[3]。作家本人與一些文學研究者都認為,這部10年前創作的小說于今天仍有極大意義,不僅照應全球新冠疫情,其揭示的“不得不保持距離,以及人在更深層面上的傳染性”問題也使作家扮演了一種“先知”角色[4]。
下面將基于社會排斥的緣起、內涵、類型、成因與后果等理論觀點,探討小說中對患有英迪格疾病兒童實施社會排斥的緣由、手段與結果,思考作家筆下疾病主題的特點、意義與作用,總結作家的思想觀點,并通過探究文學對社會問題的呈現與評價方式,思考當代疾病主題小說的獨特審美價值與社會意義。
一、社會排斥理論簡介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國等西歐國家經歷了經濟與產業結構調整、階級結構與社會利益關系變化,面臨著新型貧困問題。法國學者勒努瓦(René Lenoir)在《被排斥群體:法國的十分之一人口》(1974)一文中首次提出現代意義上的“社會排斥”概念。法文“Les Exclus”原指被保險制度排除在外者,勒努瓦將精神病患者、身體殘疾者、(有)自殺(傾向)者、老年患者、受虐兒童、吸毒與濫用藥物者、越軌犯罪者、多問題家庭、單身父母、邊緣人、反社會者等都納入被排斥者范疇[5]。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歐洲一體化與全球化發展,歐洲社會出現各種形式的邊緣化現象,各國開始從政策層面回應社會排斥這一社會事實;20世紀90年代起,歐洲之外的國家與眾多國際組織普遍關注社會排斥這一重大問題,并用相關理論范式分析本國的相關社會問題[6]。
對“社會排斥”的定義,政策研究者與政府部門和學術界的側重點各有不同。2004年歐洲理事會提出:社會排斥是某些個人由于貧窮、缺乏基本技能和終身學習的機會,或因受到歧視,而不能得到工作、收入和教育的機會,被推到社會邊緣,無法全面參與社區和社會網絡以及各項社會活動,難以觸及權力和決策團體,經常感到沒有權利以及不能控制影響他們自身生活的決策問題[7]。珀西-史密斯(Janie Percy-Smith)總結社會排斥涉及的具體層面,如政治(民主參與與政治權力受限)、經濟(貧窮與失業,不能享受住房、土地、信貸等)、文化(文化歧視、種族或文化中心主義)、公共服務(不能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與資源、醫療健康服務等社會保障)、社會(不能正常參與社會交往與社會生活實踐)、空間環境(較差的居住條件與環境質量、弱勢群體集中化與邊緣化)、社區與鄰里(公共服務減少,鄰里支持網絡喪失)等[8]。布查德特(Tania Burchardt)則突出被排斥者社會公民身份的不完全實現和對社會生活的不完全參與[9],并將其主動參與社會公民正常活動的愿望與需要作為社會排斥形成的前提之一[10]。麥克唐納(G. MacDonald)和利里(M. R. Leary)同樣關注排斥者的歸屬需求,認為社會排斥是指在社會互動中,個體被其想與之建立關系的他人或團體拒絕、分離、排斥或貶低,無法得到渴望的關系或滿足歸屬的需求[11]。個體的關系與歸屬需要無法在群體或他人中實現是社會排斥現象的核心方面[12],可見,社會排斥也涉及人的精神與心理需求。其次,社會排斥是無形的,如地位、權利、自尊、期望等的喪失[13]。此外,社會排斥是一個累積性、連鎖性、循環性的過程;是個人與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各種不利因素累積的結果[14];是一個動態過程,某些劣勢導致某些排斥,后者又導致更多的劣勢和更大的社會排斥;社會成員在某一層面遭受的排斥往往會使其在其他層面也遭受排斥[15]。
促成社會排斥的因素有社會階層、種族、膚色、宗教和政治派別、收入、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地理位置、童年關系、個人習慣和外表等[16]。李斌概括社會排斥的六大生成機制:“自我”生成論,由社會下層人員自身行為與態度造成;社會結構生成論,由社會結構本身的不平等性造成;勞動過程創造論,經濟發展中人員與信息交換強化員工的參與趨勢,對“場外人”產生排斥;社會政策創造論,社會再生產導致群體與個體優劣勢的累積,后者又被社會政策強化;意識形態認可論,由傳統文化意識、現行法律與政府安排造成;社會流動反映論,人們從勞動力市場、貧困與富裕等狀態間的流動性影響群體間的排斥[17]。
關于社會排斥的后果,景曉芬總結了四個方面:導致貧困,這是最直接的后果;不利于社會整合,被排斥群體對社會的認同與凝聚力被削弱,獨立、自由與自我意識的發展促使其通過具體行動表達不滿;造成被排斥者巨大的社會焦慮與心理壓力,產生自卑、失去尊嚴與地位之感,陷入自我封閉狀態;違背社會公正原則,被排斥者的權利與機會被剝奪,其他群體不合理地獲得更多利益,不符合現代社會的發展目標[18]。
就小說《英迪格》而言,疾病是社會排斥的直接誘因,患病兒童是社會排斥的具體對象。下面擬分別闡釋小說中社會排斥現象的緣由、手段與后果,思考社會排斥理論的內涵與應用,以及社會排斥作為文學現象與社會問題的異同。
二、排斥的緣由
《英迪格》具有十分明顯的虛構性,前述社會排斥的六大生成機制與小說情節難以實現一一對應,但仍為讀者提供啟發。首先,被認為具有輻射性的英迪格疾病無疑是患病兒童遭受社會排斥的直接原因。患病兒童遭遇排斥是完全被動的,純真無辜的兒童不僅對自己的疾病及其影響一無所知,他們反而被動地承受著成長環境的影響與塑造,如隔離中心一棵與眾不同的樹那樣:它“分明遵循簡單的原則生長,向上,分叉,如此等等……這根瘋狂的異枝或許是受地下水流、磁場或者光線的影響吧”[19]76。可見,患病兒童對所遭受的社會排斥既無法預料,又不愿其發生,也無法抵抗。相對地,排斥的緣由與出發點則更多是作為大多數的“健康人”對疾病本身的錯誤認知。
小說中的疾病被命名為“Indigo”,該詞源自希臘語“indikón”,在德語中意為“das indische”(印度的),是一種源自印度的植物中提取、現在亦可人工合成的靛藍色,它作為顏料與染料的歷史悠久,并對基礎色彩理論的建立與有機化學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20]。但在數學老師塞茨看來,卻是“最可笑的”“十足荒謬”[19]23的一個指稱,因其無法起到一般命名應當達到的作用,即幫助人們認知某事物并將其范疇化。這體現了正是由于這種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疾病的神秘性。這種神秘性首先體現為怪異的癥狀:患病者無一例外是2000年前后出生的兒童;他們與正常兒童相比沒有任何外在異常;本身也無任何不適,卻會使靠近者“頭暈、腹瀉、發皮疹,重則導致所有內臟的永久性損傷”[19]22,且癥狀隨距離縮小而加重,甚至已故兒童的尸體必須火葬,否則不能埋入公墓,以免繼續傷害健康人。
英迪格疾病的神秘性使人們對其諱莫如深,避之唯恐不及。正如司湯達《阿爾芒斯》中,奧克塔夫的母親拒絕說“結核病”,她怕一旦說出這個詞,兒子的病情就會迅速惡化;人們甚至只能用首字母“I-疾病”“I-兒童”(以下均使用該表述)來談論。如桑塔格所言,疾病“本身喚起的是一種全然古老的恐懼”[19]7;人們會出于認知不足與對疾病傳染性的恐懼,為任何一種病因不明、醫治無效的重大疾病賦予消極意義,“內心最深處所恐懼的各種東西(腐敗、腐化、污染、反常、虛弱)全都與疾病劃上了等號”[19]53。而這種認識層面上的消極賦義與疾病本身是否具有傳染性并不直接相關。小說中對疾病名稱的選擇與確定——人們避免以首例患者姓名“羅徹斯特綜合征”命名或采用類似“艾滋病”等本身具有歧視色彩的指稱,也從側面反映出人們對疾病與患者的消極認知。
對疾病的恐懼與消極賦義根源于對“他者”的界定與敵對。人們會“把那些特別可怕的疾病看做是外來的‘他者’,像現代戰爭中的敵人一樣”[21]88,并且“不合時宜地把邪惡與非我(non-us)、異族等同起來……被判定為邪惡的人總是被視為或至少可能被視為污染源”[21]121-122,疾病最終被等同于邪惡和不潔。小說中,人們對I-疾病與I-兒童污名化與妖魔化的最極端表現,即對I-兒童尸體火葬。因為火在西方宗教與文學傳統中兼具懲罰與凈化的作用,如《圣經》中天火燒滅罪惡之城索多瑪,地獄中不滅之火刑罰異教徒,以及《神曲》中永火折磨罪惡靈魂。
排斥他者意味著與他者保持距離。個體與同類中的其他個體以及與異類之間都會保持一定的空間距離,這是動物在發展進化過程中普遍培養的認知與行為模式。小說中多處出現“proximit?t”(英文proximity)一詞,該詞原指時間或空間的臨近,文中指“安全距離”。“每個人身邊都有自己的封鎖區半徑……一旦人與人之間的封鎖區半徑重合,人們就會陷入恐慌,繼而不斷拉扯、吼叫。”[19]442塞茨老師到隔離中心任教之前,在當地一處“距離意識與學習中心”做研究工作,隔離中心的I-兒童之間也要時刻遵行這一原則,連其中思想最為叛逆與先進的成員也極力鼓吹“安全距離”說。因此,作為一種社會行為的排斥不僅局限于小說中的I-兒童等特殊人群,也是人類發展歷史中的普遍現象,隱而未現,卻無處不見,針對的對象可以是一切相對于排斥主體而言的他者。
與促成社會排斥的一般因素如能力缺乏、貧窮無業、越軌犯罪等相比,小說中I-疾病本身的真實性一開始就被作家懸置。不僅塞茨老師始終質疑其真實性,相關看法也缺乏科學依據,“或許只是一種臆想”,“專業文獻中鮮有提及,提及涉事者時也只給出姓名的首字母,沒人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19]123-124,甚至一位英國母親誤判兒子病情而引發一時轟動。即便如此,出于對未知他者的恐懼與錯誤偏激的認知,人們仍斷然將I-兒童一概送至隔離中心,將其從健康人的活動區域中排除。
此外,Indigo(靛藍)獨特的實際應用場景也賦予其一定的社會隱喻與諷刺意義。一方面,靛藍有醫療保健功能,作為中藥成分,可輔助治療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牛皮癬、喉嚨和喉部感染等疾病[22];另一方面,它在日本傳統醫學中被用作抗炎物質,如武士穿著用靛藍染色的衣服來治療傷口,靛藍染色的毯子和衣服是送給新生兒以保護其免受疾病侵害的傳統禮物[23]等。可見,作家用一種原有醫治功效的元素來命名一種疾病,本身就極具諷刺意味。還需注意的是,Indigo還指一類(通常是兒童)不適合現有社會體系、與眾不同、天賦異稟、象征人類未來與希望的世紀“超人”(1)相關觀點可參見:JAFFE K.Indigo-erwachsene.Wegbereiter einer neuen gesellschaft[M].Hanau:AMRA,2008; HUPPERTZ SV.Indigo-und kristallkinder:Die Kinder des neuen bewusstseins[M].Dürrholz:ausZeit,2010;VAN HELSING J.Die kinder des neuen jahrtausends:mediale kinder ver?ndern die welt[M].Fichtenau: Amadeus-Verlag,2021;MARTENS A.Ein Indigo zu sein ist ein geschenk[M].Norderstedt:BoD,2022等。。小說中也有多處暗示:作為I-兒童代表的羅伯特時常將自己想象為蝙蝠俠,成年后的羅伯特果真成了一位成績斐然的畫家;其他所有“擁有英迪格藍色氣場的孩子們”都擁有“巨大的潛力”,盡管在隔離中心時未能接受正常、充分的教育,但在離開隔離中心后,無一例外地在各個領域取得斐然成就。他們作為一種“精神性的、智性的存在”,標志與引領著一個新時代,“一個魚的時代”,甚至他們“來到這個世界,就是為了拯救它”[19]52-53。將I-兒童與燈泡類比——“他們就像燈泡。未來某個時刻就會油盡燈枯,他們的影響力將消失殆盡。大部分發生在成年階段早期”[19]196-197,則可視為對構成社會主要力量的成年人的諷刺:后者受過教育,心智成熟,自詡健康道德,握有判斷與支配外物的權利,實際上卻平庸無能,不能促進世界與文明進步。這樣看來,作為進步性、革新性力量的I-兒童對原有的社會秩序以及人的既有地位和觀念產生沖擊,必然遭到作為社會大多數的健康人或普通人詆毀、排斥與打壓。這與桑塔格的觀點“疾病意象被用來表達對社會秩序的焦慮”[21]65再次形成呼應。新舊社會秩序的對立與強弱關系也通過I-疾病的一個奇異特點折射出來:患病兒童本身感受不到痛苦,出現各種癥狀的反而是周圍的健康人。這也說明,小說中的I-疾病并非作為一種有醫學可能性的現實狀況,更多是作為一種文學隱喻得以呈現;人們對I-兒童的排斥行為實則基于自我保護與利己主義的集體性錯誤認知,是對社會革新力量的排斥。
三、排斥的手段
就實施社會排斥的施動者而言,學界現有研究中鮮有系統全面的闡發。方長春的定義“(社會排斥即)以某種(人為設置的或潛在的、自發形成的)機制限制一些個體或群體獲取特定資源”中所言的“某種機制”是一種較為靈活寬泛的表述。伏干則指出:“在社會排斥的概念體系中,施動者通常沒有被明確指出,而是通過在概念形成過程中‘誰被排斥’和‘排斥出什么’來建構施動者”,有時“無法將社會排斥的施動者建構在某一特定對象主體上,而是施動者被一個被操作化了的抽象主體所代替”[19]112-113。小說中,作家并未直接提及政府、制度與結構問題在排斥過程中的角色,所涉各方——隔離中心管理與研究人員、教師、醫生、I-兒童的家人,也未通過語言文字等方式直接表露排斥意圖,而是用看似合情合理、符合公共利益的理由掩蓋與美化實際的排斥行為。這說明:第一,社會排斥可以在有限的范圍與層面產生,往往根源于意識、認知與情感的排斥;第二,社會排斥具有累積性與連鎖性,一方發出的排斥會激發其他多方共同排斥,排斥因而總是一種集體行為。此外,實施排斥的個體在與其他實施排斥者的隱秘“合作”中會陷入一種對自身行為的無意識,并將排斥行為常態化、合理化與隱秘化。這一點通過小說中的一個類比映射出來:“比如一家專門生產武器的公司,做著把神經毒氣爆破筒賣給秘密公司等一些毫無人性的黑暗勾當,但工廠里的每個人都是善良、友好的公民,只是為了供孩子上大學……并且會在下班后心滿意足地坐在電腦前,觀看普通電影里善良女人的悲情戲。都是正常的男人、女人,為人和善,很好相處,甚至相當理智。”[19]439
探究社會排斥的手段時,可參照理論部分總結的社會排斥實現的具體層面,即政治、經濟、文化、公共服務、社會、空間環境等。就小說內容而言,I-兒童遭受社會排斥主要體現在公共服務、社會與空間環境方面。
為I-兒童設立的隔離中心是對其進行社會排斥最直接有效的手段。隔離中心位置偏遠隱蔽,人們要經過“一條黑暗的、被詛咒了的林中道路”才會發現它,并且“永遠也不要希望里面關著的精神病人會康復”[19]76;隔離中心內部“空氣黏稠、沉重,寬大的窗戶從不會打開,任何角落里都能聞到刺鼻的油漆味和地板清潔劑那股具有攻擊性的氣味”[19]62。可見,隔離中心的周邊環境與內部居住條件相當惡劣,人們通過將I-兒童邊緣化與集中化實現排斥的第一步。就隔離中心的核心任務而言,I-兒童與外界徹底隔絕,見不到隔離中心之外的任何人,無法與父母和同齡人交流。隔離中心剝奪I-兒童正常參與社會交往和社會生活的權利與機會,并通過一個與眾不同、自我封閉的場所,為嚴格實行紀律創造了必要前提[24]160-161。
嚴格的紀律規定不僅旨在切斷I-兒童與外界人和事物的聯系,而且也為限制I-兒童之間的聯系。I-兒童私下跑出自己房間,與其他孩子交談的行為會受到懲罰;在玩方格游戲時要嚴格遵守獨特的游戲規則,精準地站在五點梅花形的連接點上,“孩子們之間永遠保持著出奇一致的距離,此外,也總是穿著同樣的衣服。沒錯,這正是孩子們的悲劇與勝利所在”[19]197-198。盡管隔離中心負責人魯道夫博士——用德語范圍內已成禁忌的希特勒之名,不乏諷刺意味,認為該游戲“非常有益于康復”[19]215,但其弊端顯而易見:其一,空間上的絕對距離限制I-兒童間的交流,造成其心理疏遠與情感冷漠,更無法促成群體聚合力與團隊精神;其二,同樣的衣服反映出隔離中心對I-兒童個體的高度同質化認識與要求,這一點也體現在中心對I-兒童編號并用絕對數值量化的做法上。
方格游戲體現的同質化管理方式符合福柯所言規訓機制中常見的空間利用法,即“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個位置都有一個人……打破集中布局;分解龐雜的、多變的因素”,以“消除那些含糊不清的分配,不受控制的人員流失,人員的四處流動,無益而有害的人員扎堆”,進而“建立有用的聯系,打斷其他的聯系,以便每時每刻監督每個人的表現”[24]162。因此,可以說隔離中心是為了遏制被排斥兒童中可能存在的不穩定因素并實施高效控制,以規訓與紀律的形式限制甚至剝奪兒童的自由選擇權,不容其逃脫與反抗的監禁場所,相比修道院、軍隊、學校而言,是更為謹慎、隱蔽與有效的實施紀律的機構。
對兒童的終極排斥手段則是作為小說另一高頻關鍵詞與第五章標題詞的“轉移”(relozieren)[19]221。該詞源自拉丁語,部分對應德語中的“versetzen”,即“將……移至或置于某種(消極)境況中”,暗示被轉移至的新環境的惡劣。隔離中心工作人員喬裝打扮被轉移的孩子,像給葬禮上的孩子化妝以使其應對艱難處境,但這只是面對外界與患病兒童的掩飾、欺騙與美化。相關人員對被送去的環境含糊其詞、避重就輕,“合理利用英迪格潛力協會”的會長鮑姆赫爾說道:“孩子們會被善待。至少是相對好地對待。有吃有住,不受酷刑……我也不知道,是有戰略意義的建筑旁的一所學校,還是一間監獄。”[19]323協會將“有吃有住,不受酷刑”當作可以執行的標準,可謂對人道主義與博愛原則的輕視;協會對I-兒童的“利用”則反映出利己主義原則。
這種利己主義的表現十分明顯。在I-疾病為人所知之初,市場上出現一系列相關主題的T恤、杯子等商品;媒體爭相報道與杜撰離奇事件以賺取利潤;美國布魯克林地區的大批年輕母親甚至排隊售賣自己患有I-疾病的孩子,以換取錢財和補給品;甚至連隔離中心的負責人也感嘆道:
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建材市場。貨架、貨架,到處都是貨架,每排貨架上都擺滿了工具,人們可以任意取用,直到將其用壞。您想想動物們吧!只要我們發現了一種新動物,我們首先感興趣的永遠是“我們能不能吃它”這一問題。在我們人當中也是如此。一個小孩出生后,人們便會思考:這小孩有什么用處?對我有什么好處?[19]385
可見,人與人之間盛行著一種工具性對待原則,一種將自我以外的一切存在為我所用的傾向。而這種對人的異化與工具化會進一步發展,造成被利用者的痛苦與損失。比如一群原本單純善良的富家孩子在社會消極環境的熏染下,成了毫無憐憫之心的自私自利者,他們主動接近克里斯托夫,并非為了陪伴安慰,而是以其為工具,進行“勇氣實驗、流汗療養以及鍛煉忍受能力”[19]287。在作家看來,這種損人利己的做法是歐洲人久已有之的通病,貫穿包括殖民掠奪、民族融合、民主制度建立、資本主義發展等階段的歐洲文明發展全歷程,并已深入骨髓、難以革除。作家借布魯塞爾專家費倫茨之口,以看似模糊曖昧,實則辛辣冷峻,并具有一種荒誕美學的語言說道:
我們是歐洲人,我們可以折磨別人,只要這能緩解我們的頭痛。我想,我們出了問題。很可能出在我們的遺傳基因上……可能在于我們經受過的眾多疫病。我們是最先建立城市的……不知何時起,我們就出問題了……我們祖先那更加強健的身體有著一種“硬件缺陷”。思想沿著怪異的軌道展開……比如我們喜歡聽別人哭喊[19]412-413。
作家借此表達對歐洲文明發展的批判性反思,指出排斥是權力博弈與利益爭奪、確立強勢地位與滿足優越感的動力、手段與結果,不僅見于特定社會群體之間,也會產生于種族與文明之間。
最后,在隱秘的施動者中,家人尤其是父母對I-兒童的排斥起到重要作用。塞茨老師初到隔離中心時,希望從I-兒童的家庭環境與成長經歷尋找患病原因。小說第五章記錄了一條令人唏噓的報道:一位疑似患有I-疾病的五歲女孩被父母鎖在家里并遺忘,幾天之后饑渴而死。男孩克里斯托夫兒時,爸爸由于無法承受心理與身體壓力,某次以買煙為借口,徹底離開母子二人,而這種“某次買煙時一去不返”的年輕父親不計其數;克里斯托夫的媽媽同樣持有一種絕望心態,“我不抱任何希望。坦白地講。我是現實主義者”[19]125。父母至親從身體上的遠離與躲避、情感上的拋棄與放棄,都構成對I-兒童極大的傷害。這在作家看來無異于一種隱性暴力,然而“家里的暴力是最常見的。一個人最初接觸到的人際關系即與家人的關系。每個孩子都被交付父母,其生命由此開始。這個初始階段中隱藏著諸多貫穿其一生的極端成分。邪惡、破壞和折磨與健康和安全最接近的地方就是家,二者在家里相輔相成、難以區分”[25]。
四、排斥的結果
社會排斥不僅涉及人的物質需求,也涉及精神與心理需求;不僅導致被排斥者無法(充分)獲得各項權益與服務,也體現為地位、權利、自尊、期望等喪失。小說中,對I-兒童的社會排斥造成如此多的后果,以下扼要列舉兩方面。
(一)社會交際(能力)缺乏,人際關系冷漠
隔離中心I-兒童的整個童年時期到成年階段早期都“在他的I-空間、他的專屬區、輻射區里度過”[19]78,缺乏必要的社會交際生活。住在家中的克里斯托夫同樣被母親“監禁”起來,他認識與參與外面世界的渴望只能通過三臺望遠鏡來實現,人際交往也僅限于與一個同患I-疾病黑人男孩的書信往來。在遭受壞小孩捉弄與欺辱時,克里斯托夫沒有躲避或反抗,反而一再落入前者的圈套。與其說他缺乏社會經歷,不識人的惡意,不如說他情愿遭受惡待,也要與自我和疾病之外的世界建立聯系。長期遭受顯性與隱性排斥的I-兒童,在隔離中心嚴格紀律的約束下早已形成躲避人群的本能性反應機制,“(馬克斯的)后退躲避似乎是無意識的舉動,一種自然反應,就像人們下決定時摩擦雙手,或不耐煩地等待時蹺起二郎腿時那樣”[19]191。此外,塞茨老師就特定人群遭受排斥舉過一個極端實例:登山者們保持距離前行,一位隊友突然身體僵硬、意識模糊,而其他人為了保存體力、節約物資,既未出手相救,也未及時求救。這種排斥行為反映出人際關系之冷漠,根本上出于人類自衛自保、自私自利的本性,如小說中羅伯特所引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那句“人與人之間恰如狼與狼”[19]188。這種排斥、冷漠與殘忍最終導致I-兒童的社交恐懼和社交無能。羅伯特在隔離中心的短暫生活期間變得敏感易怒,甚至有了迫害妄想癥的表現:他因個人畫展偶遇欣賞者的詢問而驚恐不已,久久不能釋懷;與女友分開后疑恨暗生,闖入昔日好友之家大肆破壞;對曾經的數學老師始終抱有恐懼、懷疑、輕蔑與排擠的態度。
而在I-兒童內部,同樣存在這種冷漠與疏離。孩子們盡管處于一種甚至多種形式的共同體關系中——居住在一起者組成的鄰里共同體,或具有一致的思想傾向與(因患同種疾病而可算作)志同道合者組成的友誼共同體[26]中,卻由于嚴守距離原則,缺乏真實有效的交流,彼此間沒有同病相憐的安慰,沒有同甘共苦的盼望,沒有得到保護與理解的安全感,也就無法形成一個情感相系、守望相助的共同體。相反,他們不得不承受“讓人作嘔的那種自己是唯一一個被人們這樣對待之人的感受”[19]78,在困惑、迷茫、絕望與麻木中度日。
(二)話語權與自主權喪失,認知與情感受挫
對I-兒童患病與否及其嚴重程度的判定是除I-兒童外多方外部力量聯合作出的,作為多數的一般群體對作為少數的特殊群體在認知與情感層面的排斥可謂對后者實施排斥的第一步。諷刺的是,關于I-疾病尚無科學可靠的理論依據或檢測手段,一切醫學假設都可能是謬見,一切旁觀者的描述也不可靠,各樣的科學實驗與調查研究非但沒有澄清I-疾病,反而加深人們無理的臆想與固執的偏見。而“當一個醫生把一種人體狀況診斷為疾病時,這一診斷就能夠而且常常改變病人的行為。因此,患病是一種人為創造的狀態,這一狀態和他們對實際情況的理解相一致”[27]。小說中,作為患者的I-兒童始終處于被動地位,對自己是否有病的發言權與決定權被完全剝奪,屬于自己的身體也被他者的認識與論斷異化。處于感知與認識世界、培養認知與判斷能力關鍵階段的I-兒童不得不依附于外界對自己的評判,被動建立模糊甚至錯誤的自我認知。
不僅如此,人們對他者的界定與妖魔化會“不可避免地發生這樣的轉變,即把錯誤歸咎于患者”[21]88。甚至可以認為,前述克里斯托夫甘心接受壞孩子的捉弄,是因為認同他人對自己不潔、有罪的定斷,認為自己不配擁有自尊與希望,甚至理應蒙受偏見與羞辱。這種荒謬且危險的觀點“不僅削弱了患者對可能行之有效的醫療知識的理解力,而且暗中誤導了患者,使其不去接受這種治療”[21]43-44。該問題一方面導致父母、親人對I-兒童身體與情感上的雙重離棄,使其不得不適應孤獨絕望的處境,甚至如同待宰的羔羊,毫無反抗地服從命運安排。羅伯特在生物老師辦公室雜志封面上看到逆來順受的蚯蚓——“鐵絲穿過它們的頭部和大腦……但此處的這種生物不管經受多么殘忍的凌虐,都絲毫不會想到復仇或自衛”[19]207時,甚至得到一種比宗教能帶來的更大的安慰[19]218,旨在赦罪與救贖的宗教似乎已無法為遭受社會排斥的I-兒童提供安慰與出路。另一方面,這也致使社會各方因為對I-疾病與I-兒童的絕望態度而不愿在資金、研究等方面提供支持,隔離中心僅僅致力于對I-兒童的隔離與控制,并未積極探索認識I-疾病并尋找治療方案,診所與各處研究中心進行的動物實驗毋寧說是一種欺騙性的表面工作。
“從詞源上說,患者意味著受難者。”[21]111誠然,I-疾病本身并未給I-兒童帶來痛苦,卻導致社會各方的排斥,從而造成物質與精神、個人與社會層面的一系列消極后果。在魯道夫博士看來:“這個世界對社會權力與機會有限的孩子來說和對我們常人來說是不同的……在這些事上,沒有圓滿的結局,只有公平的結局。”[19]211事實卻是,社會排斥反映出造成的不公平現象客觀存在著,而所謂的公平總是對作為大多數的健康人利益的保護。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既未探討社會排斥的解決手段,也未提供被排斥者獲得慰藉與幫助的有效途徑。這一方面揭示出社會排斥這一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則是發揮了文學作品激發讀者獨立思考與自由闡釋的特長。
五、結語
與《霍亂時期的愛情》《鼠疫》《喪鐘為誰而鳴》等傳統疾病小說相比,奧地利作家克萊門斯·J.塞茨的代表作《英迪格》賦予疾病獨特的樣態與內涵。英迪格并非黑死病、鼠疫等真實歷史事件或已有臨床實例的醫學現象,而是一種結合疾病表現與疾病想象、社會現象與文學創造的詭異可疑的虛構疾病。小說非揭露社會矛盾、呼吁人性美善的戰斗檄文,而是寓荒誕于真實,寓幽默于沉重,隱晦而巧妙地指涉社會排斥問題。作家深入人的天性本能與社會性的合理之處和陰暗方面,表達人道主義情懷與對歐洲文明發展歷程的批判性思考。基于對小說中疾病與社會排斥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認識。
第一,排斥并非基于實證事實,而是人們出于恐懼,基于對他者的界定,以及面對他者的自衛與利己本能作出的反應。這一心理根源表明:排斥是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難以通過文明的進步根除;其對象并不限于特定的弱勢群體,而可以是相對于排斥主體而言的一切他者。小說中“病人”之健康與“健康人”之痛苦的反諷式對比,則拋出了健康與疾病的界限、疾病的判斷標準與判斷者等問題。此外,英迪格兒童的特殊性與康德、歌德、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將天才或超人與疾病聯系,以患有或戰勝疾病來升華生命的理念形成隱秘呼應。可以說,排斥亦可是既有社會規則下的多數人對作為少數的革新力量的敵對。
第二,在排斥的實施問題上,排斥是對特定少數群體的范疇化與邊緣化,有顯性與隱性實現形式。隔離中心剝奪患病兒童參與社會生活的權利,以機械性的同質化管理與嚴苛的紀律要求對其規訓;父母的身體與情感疏離作為隱性暴力加劇社會排斥;陌生人的捉弄、社會各方以病取利的行為更反映出人與人之間的工具性對待原則和極端利己主義。排斥總是多方合作、互相激發的社會性行為,并會在產生集體無意識的過程中被常態化與合理化。排斥是權利博弈與利益爭奪、確立強勢地位與滿足優越感的動力,手段和結果,不僅見于特定社會群體之間,也會產生于種族與文明之間。
第三,就排斥的后果而言,疾病既是兒童個體與社會的聯系紐帶,也導致其社會關系惡化與崩潰。受排斥兒童不僅缺乏必要的社會參與經歷,社會交際無能,形成創傷后自我封閉的自然反應機制,導致群體內部的疏離、冷漠以及共同體意識的淡薄,他們也喪失對自己身體的發言權、決定權與自由發展權,在排斥環境中被動形成模糊、錯誤的自我認知,陷入自卑、孤獨、迷茫、絕望與麻木的處境。
小說《英迪格》的現實意義不限于創作當時與當地,而是能為全球后疫情背景下,甚至各個時代的讀者提供關于人性、社會與文明的思考。讀者可以借此探討一系列現實問題:如何對待對社會大多數有不利影響,卻同時需要保護的少數群體?如何認識家庭與社會各方對病患等弱勢與邊緣群體的責任和負擔?如何為患病兒童等特殊群體提供教育?如何平衡本能情感與社會共識、自由發展需要與紀律規訓機制,以及人的個體性與社會性?如何達到社會平等、認同、接納與融合,促進理解、博愛、守望相助,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文學在其中可以和能夠扮演怎樣的角色?
疾病雖發生于個體,卻總是一個社會性問題,在個體之間、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疾病與邊緣人現象伴隨著人類社會建立與文明發展的全過程,涉及人性與存在等根本問題,不僅是世界文學史中的經典主題,也為當代作家所重視。作家的另一部小說《女人與吉他間的時光》(DieStundezwischenFrauundGitarre,2015)、Peter H?rtling的小說《思維游戲者》(DerGedankenspieler,2018)、Martin Sch?uble的小說《純凈之國》(Cleanland,2020)、Jasmin Schreiber的小說《馬里亞納海溝》(Marianengraben,2021)、Juliane Pickel的小說《駝背的狗》(KrummerHund,2021)等近年來優秀德語文學作品均以疾病與社會為主題。這些新疾病小說通過靈活新異的表現手段與敘述技巧,賦予疾病更加多元多面的意義,在為讀者帶來特殊的審美體驗與情感慰藉的同時,也從文學角度為描述、探討甚至解決社會現實問題提供了寶貴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