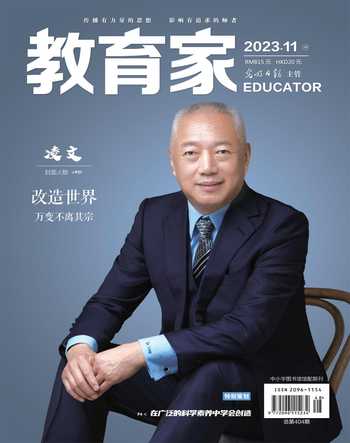黃國勝:科學課要駛向興趣、成長和收獲
鄧曉婷
丹麥皇家科學院,年輕的“奧斯特”們輪流發表演講。從臺下的緊張、局促、不屑一顧,到臺上的嚴肅、認真、侃侃而談,對電與磁的發現,他們每個人都有鮮活的觀點。這所“皇家科學院”,是溫州瑞安市虹橋路小學科學教師黃國勝在講解電與磁時,用PPT中世紀幕布圖片簡單搭建起來的儀式感。他鼓勵孩子們以發現者“奧斯特”自居,暢聊對這個重大發現的感言……
黃國勝的課堂,從不拘泥于形式,他認為一節好的科學課最終要指向三個關鍵詞:興趣、成長和收獲。不僅教課,黃國勝還常年組織跨學科教研,深入中西部地區,為科學師資薄弱的學校做公益培訓。每當看到一所學校、一個地區的科學教師隊伍逐漸壯大起來,他都會覺得自己離夢想更近了一步——“怕什么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我們要試圖去改變現狀”
和很多科學教師一樣,黃國勝一開始并不是教科學的。
但在他身上,從小就有一種樂于創造的天賦。他的童年充滿了各種天馬行空的想象——家里的廢棄豬圈是他的造夢場,黃國勝在這里建造過“軍工廠”“食品廠”“電影院”,對什么感興趣,他就會嘗試著做出來。
黃國勝曾在一篇文章中回憶當年的趣事:“我把尼龍固定在紙的方框上,畫上一些圖案,用手電筒做光源,用力一拉尼龍下端,小兔子就奔跑起來,把我的小伙伴們都看呆了。培養了一批粉絲后,我樂此不疲地當了好幾個月的導演。前幾年老家裝修,我還翻出了兩大盒彈珠,這可都是我當年‘電影院的票房收入。”
長大成人之后,黃國勝念師專期間偶遇恩師,他的音樂天賦一下子被激發了出來。他一度認為自己會成為一名專業的音樂教師。然而在閣巷小學的第一節公開課,就讓黃國勝失去了信心。由于他的聲音條件和小孩的音域差得太遠,再加上當時慣用的收音機教學過于刻板,黃國勝的音樂課上得很失敗,他苦笑:“一周過后,音樂課成了我的噩夢,我成了孩子的噩夢。”
此后,黃國勝被安排接手學校的常識課。常識包羅萬象,十分有趣之余,也面臨不小的挑戰。在當時,這門課并不受家長“待見”。和其他學科相比,常識的地位很低,低到家長看到他一臉冷漠,甚至不會和他打招呼。
更為棘手的問題出現在課堂。黃國勝發現連學生也不喜歡這門課,“因為其中涉及面太廣,歷史、地理、社會知識占了大部頭,剩下的生物、物理內容,教起來要么缺少種植經驗,要么缺乏實驗器材。任課老師基本上由其他學科老師兼任,讀一讀,背一背,填一填,一節課就結束了。”
這樣的教學方法讓他感到毫無生氣,簡直像催眠曲,讓學生呼呼大睡。黃國勝說,一看到孩子們睡覺,就會嚴重打擊他的熱情。于是他在課堂上立下規矩:“你們給我一些時間,先聽我上課,如果真的不喜歡,可以睡覺,但絕對不可以打呼嚕、講夢話。”孩子們哄堂大笑之余,也開啟了新的課堂體驗。
想要改變現狀,就得把學生從睡夢中“拎”出來。他把枯燥沉悶的歷史知識變成了課本劇,讓孩子們在蕩氣回腸的歷史語境中收獲真情實感;地理知識廣博難記,他就教學生如何當導游,帶領同學們“游歷山川”。課外,他帶著學生一起研究沙蟹在淡水里是否能存活、植物的根往哪邊生長、生姜適合在哪種土壤中生存……
“社會不重視、家長不重視、學生不喜歡,但如果我們自己不試圖去改變現狀,整天坐在辦公室抱怨是沒有用的。”一些“課改”的實施,讓學生動起來了。在各類優質課評比中,黃國勝屢獲獎項,經由當地媒體的報道,黃國勝的名氣逐漸響亮。他擔任區科學教研組的組長,帶領100多名成員持續深入科研。于他而言,最重要的是憑借自己的努力,改變了常識課在學生、家長心中的刻板印象。
“只得出結果是不對的”
十多年后,新設的科學課取代了常識課。在常識課上的打磨和經驗給了黃國勝底氣。但科學課更加聚焦,更加專業。對于一堂科學課,黃國勝認為一是要讓學生真正明白現象所反映出的規律,二是要在重探究的同時加強研討。
基于對學生的了解,黃國勝在課前會仔細思考課程內容要如何開展。科學課四年級下冊《運動的物體有能量》,其重點是讓學生理解物體的速度和動能之間的關系。“原本的實驗裝置,是讓斜坡上的一輛小車沖撞約10厘米處停著的小木塊,通過觀察小木塊被撞得有多遠,來判斷小車在不同位置俯沖下來的能量大小。對四年級的學生來說,要測距離,再反過來測時間,太難了。”
得益于從小就愛鉆研的樂趣,黃國勝想到了一款街頭游戲“拳頭力量測量器”,該游戲有一個顯示屏,能夠用數據直接判斷出拳頭砸向機器的力量大小。于是,他花一個星期時間做出了一款能量與速度一體化教具。課堂實驗中,每當小車滑行下來撞到木塊,儀器上立馬就會出現相關數據。
黃國勝還注意到,很多教師在科學課上重探究、輕研討,學生的實驗過程有時會長達20分鐘,再加上整理教具,留給研討的時間幾乎為零。“做實驗只得出結果是不對的,要想盡一切辦法讓學生研討交流。老師要尊重學生,把課堂交給學生。”
一次去臺州上課,在講完奧斯特發現的電與磁原理后,他慷慨激昂地對學生說:“你們現在不是別人,你們就是奧斯特。臺下的同學更要帶著挑剔的眼光,你們是院士,要雞蛋里挑骨頭!”孩子們一個個走上臺,“各位院士,我是某某·奧斯特……我的研究過程是……”歡聲笑語中,每個人都講出了自己的心得。臺下的小院士們也踴躍提問,相互質疑,相互解答。這場融入了科學史、科學家精神的“丹麥皇家科學院成果發布會”舉辦得很成功。
多年來,黃國勝在為他人答疑解惑的同時,也在不斷豐富自己。“尤其是新課標出來之后,廣義的科學還包括工程和技術,很多老師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如果我們自己都不懂,怎么去教學生?”曾有一年黃國勝去臺灣桃米社區交流學習,一位講解兩棲動物的老師讓每一位聽眾都聽得出神,事后黃國勝才得知這位老師并不是生物學專業出身,“她居然是學經濟的,僅僅因為對生物學感興趣,才去社區參加了培訓,這讓我深受啟發。”
回到瑞安,黃國勝決定將教育培訓資源從校園拓展到社區,他開始做跨學段、跨學科、跨專業的教師專業提升培訓。一遍遍梳理團隊需求,再邀請各領域的工程師或學者給老師們開講座,“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學科里,語文老師、數學老師一樣可以參加培訓。學科之間的這種關系已經從單學科到多學科、跨學科,最終的目的是超學科。”
“手動起來,思維才能跟上去”
隨著瑞安的科學教育越辦越好,黃國勝將目光投向了偏遠山區。15年來,黃國勝和多家公益組織持續深入中西部,細水長流,為其量身定做適合當地學校發展的科學教育培訓。
各地情況不一,師資問題最為突出。“比如呼和浩特,15所項目學校的小學科學專職教師曾不超過10人,且參加培訓的機會少之又少。再如曾經汶川地區的汶川一小、龍溪小學、雁門小學,每所學校的科學老師只有2—3名,開展教研難上加難。在了解情況過后,我首先測算了三所學校之間的車程,最遠不超過25分鐘,因此我建議他們形成一個教研共同體。”
黃國勝說,培訓前的調研是重中之重。通常他接到的培訓邀請,都已定好時間、地點、內容,這時他總要反思:這些需求是當地老師提出來的嗎?如果不是,黃國勝則會提前2個月與當地教研員對接,摸清需求,再做1—2年的提升計劃。
“有些地區的老師,連基本的課都上不下來,甚至連常見的科學儀器都不會使用。那么,‘高大上的科學課過程設計培訓未必合適,他們反而聽不懂、不想聽。”黃國勝認為,在開展所謂的教育扶貧之前,大家最容易走入的誤區,就是“想當然”。
2009年,黃國勝到過西部一所小學。該學校是由某結對城市政府在震后援建的新校,造價高昂。寬敞的校園、精美的實驗室讓每一位參觀者都感到驚訝,更加出乎意料的是,各種不同版本的實驗器材擺放得一塵不染,從未開封。“原因其實很簡單,沒人會用”。黃國勝說,這類學校往往需要的,就是最簡單的參與式培訓。如果老師不具備該有的能力,所有的美好愿景都無法落地。
2012年,黃國勝重返當地。經過培訓團隊三年的努力,不僅科學教師的專職數量上去了,實驗課也開起來了,“只有學生動起來了,思維才會跟上去,培養科學素養才能成為可能。”
在青海湟中,黃國勝提議發起并深度參與的“桂馨科學夏令營”營員爆滿。他幽默地說:“就是‘走后門都塞不進去!原來每屆最多只有100個孩子參與,結果人數一年比一年多。今年夏天,營員人數已經達到了260人。”他認為,社會重視、家長支持、學生喜歡,這便是科學教育最好的生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