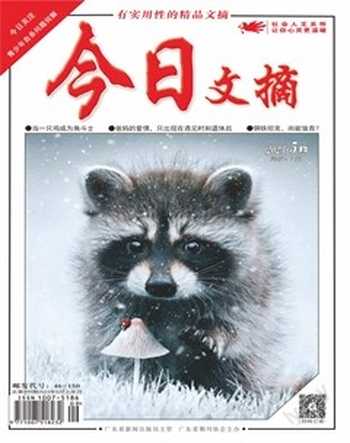像擺脫“冷氣”那樣擺脫“孔乙己文學”

“孔乙己文學”來了。“如果我沒有上過大學,那我一定心安理得地去打螺絲。可是沒有如果。”“學歷不但是敲門磚,也是我下不來的高臺,更是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在這些句子成功引起關注之后,部分網友開始共情,感嘆自己是“現代版孔乙己”。
“孔乙己文學”來得快,但勢必也去得快,因為這個說法本身就是個偽命題。充其量,它更像是一種牢騷或自嘲,是短暫的情緒載體,是當前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心中的一點介懷與感慨。它甚至沒法像“凡爾賽文學”“廢話文學”“發瘋文學”等網絡流行文體那樣,形成具有一定生命周期的創作規模——它的標語化、空洞性,以及缺乏必要論據的支撐,都會使它成為一種短命的網絡文體。
既然短命,何以流行?這與網絡情緒的流動性與寄生性有關。當一個網絡上的“金句”無意中被發掘,往往會被部分網友賦予“不可承受之重”的寓意,進而眾人一哄而上,評論、轉發,在社交媒體上流傳。“孔乙己文學”火的那幾天,正值大學畢業生就業、年輕人求職等話題在網絡上熱議。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落差,面對迫在眉睫的焦慮現狀,一些年輕人只能把調侃、自嘲作為排解壓力的出口,于是“孔乙己的長衫”便被人從歷史的角落打撈出來,等同為貶值的學歷。這樣的情緒轉移,是部分網友的意志體現不假,但由此將“高開低走”的“鍋”甩給學歷,由此對讀書有用進行否定,則不啻為一種簡單粗暴的做法。
魯迅寫的孔乙己,年齡在四五十歲之間,沒有理由成為當代年輕人的共情對象,繼而采取不正視現實、不愿面對困難的逃避態度,更是無稽之談;孔乙己所處的時代,大約為清朝光緒中期,那是個悲哀的年代,是讀書人倍感無力的時代,當下雖然競爭激烈,現實中存在種種困難,但屬于年輕人的上升通道仍然不少。與其對標“孔乙己的長衫”自怨自艾,不如放眼未來,付諸行動,以實踐改變生活,以行動積蓄能量,為機會到來時做足準備。
孔乙己也好,“孔乙己的長衫”也好,都是被借用的符號,并不能起到一面鏡子的作用,如果硬要將之當作鏡子,那么映照出來的景象,也一定是錯位的、模糊的。年輕人可以同情孔乙己,但要拒絕成為孔乙己。而拒絕的首要條件,就是拒絕“孔乙己文學”這一蒼白的心靈按摩手法,要像勇士一樣直面挑戰。
魯迅先生說過,“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無論是過去的年輕人還是現在的年輕人,都應把孔乙己視為“冷氣”的組成部分,把“孔乙己文學”視為“自暴自棄”的話語。用“孔乙己文學”表達一下介懷問題不大,但切忌把一個偽命題當作真命題鄭重其事地看待。
歸根結底,“孔乙己文學”仍然是一種帶有消耗性質的起哄文學。希望在這一輪“孔乙己文學”熱過后,那部分自認為是“現代版孔乙己”的年輕人,可以更勇敢地擁抱現實,拓寬思維與視野,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拼搏之路。
(蕭力薦自《環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