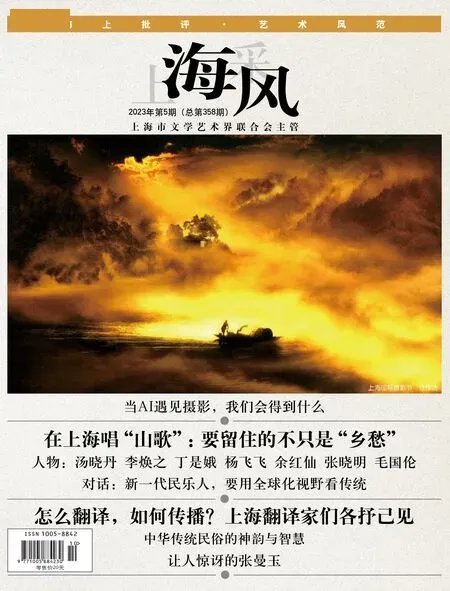那些年,擺攤頭那些事
■ 莊大偉
記憶中老上海的路邊攤、夜排檔、煙紙店、馬路菜場,已經消失很多年了。回想起阿拉小辰光看到過的那些充滿煙火氣的場景,那些擺攤頭的故事,至今心中依然暖意濃濃……
路邊攤
那些年,路邊攤是上海灘上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一清老早,賣早點的攤頭(通常是一輛放著玻璃框的黃魚車)就出現在路邊,給匆匆出門的上班族提供大餅、油條、蔥油餅、蟹殼黃、羌餅之類的早點。
大馬路上人來車往,是看勿到有人擺攤頭的。小攤頭一般都擺在小馬路上,轉彎角落,或者居民進進出出的弄堂口。
阿拉學堂門口的一條小馬路上,就有很多小攤頭。特別是到了放夜學辰光,從小零食攤的到修鋼筆的,排了一長串。
在這些小攤頭里,當然是賣小零食的攤頭最多了。勿少學生仔都是饞癆胚,袋袋里只要有幾分錢,都要把它們用光。小攤頭上的小零食交關便宜,一分二分都可以買,什么桃片、話梅、鹽金棗、粽子糖、九制陳皮、醬油瓜子、奶油五香豆、三北鹽炒豆……小零食多得莫佬佬(很多)。
記得小攤頭里有賣新疆葡萄干的,裝在小盒子里。小盒子只有火柴盒那樣大,里面裝了可憐巴巴的十幾粒葡萄干。這些從遙遠的新疆運過來的葡萄干,那辰光賣得很貴,阿拉小巴辣子一般是勿舍得買的。
老師、家長都反對阿拉學生仔買小攤頭上的小零食。手捏捏,蒼蠅飛飛,多少勿衛生啊!不過阿拉這些學生仔基本上都是一只耳朵進一只耳朵出。每一個學生仔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吃零食吃壞肚皮的記憶,不過從來沒有看到過吃壞肚皮去找小攤頭算賬的,只怪自己嘴饞,自認倒霉。肚皮好了,嘴巴一饞癆又去買那些甜的咸的吃了。所以那辰光面孔上有白印子的小朋友勿少,這是肚皮里長蛔蟲的標志。有辰光吃壞了,肚皮瀉,爹爹就會倒出小半杯自己浸的楊梅酒,吃到肚皮里火辣辣的一陣過后,肚皮馬上勿瀉了,百試百靈。我懷疑自己吃老酒就是那個辰光學會的。
除了賣小零食的攤頭,還有套圈圈、做面人、打氣球的攤頭。在這些攤頭周圍常常圍滿了學生仔。袋袋里沒有鈔票的小朋友也在圍觀,圍著看熱鬧呀。藤條做的圈圈跳跳蹦蹦的,很少看到有圈圈套進獎品上的。不過圍觀的小朋友還是會大呼小叫的。而圍在做面人小攤前的小朋友都不大出聲,大多瞪大著眼睛,看著彩色面團在手藝人指間搓搓捏捏,一歇歇功夫,一個個孫悟空、豬八戒、哪吒、濟公便活靈活現地出現了。偶爾有學生仔買去一個,大家便朝他(她)投去眼癢(眼熱)的目光。打氣球的攤頭前,“乒乒乓乓”的氣槍聲也吸引了勿少看熱鬧的小朋友。記得除了打氣球,也有打麻雀的。麻雀在扁平的鐵籠子里扇動翅膀,逃來逃去,等著挨槍子,也是蠻可憐的。小姑娘喜歡圍在賣蝴蝶結的攤頭,還有電影明星照片、歌片攤頭前,挑挑揀揀。
反正放學辰光,這條小馬路上,全是阿拉小巴辣子們的市面。
有一趟我看到有一個賣鉛筆的攤頭,賣的是赤膊鉛筆(筆桿沒有上漆),是工廠里流出來(很可能是偷出來)的次品,價鈿很便宜,我買了一大把。第二天正好碰到測驗,我的這些赤膊鉛筆常常斷筆芯,石墨筆芯很硬,不時勾破卷面。我心境大亂,自然成績不理想。后來姆媽問我,你的測驗成績不好,跟鉛筆有啥關系?“當然有關系了。”我拿出了這把赤膊鉛筆。于是姆媽講:“要記牢,好貨不便宜,便宜沒好貨。”這句閑話,我一直記得牢牢的,至理名言哪。
偶爾在小攤頭上買的東西,也有救急的。記得有一年六一節,班級里聯歡會,每個同學都要表演一個小節目,原來準備朗誦一首詩或者唱一首歌(大部分同學都這樣),偏偏碰到扁桃腺發炎,一張嘴,發出來的聲音像啞殼蟬。急中生智,我突然想到前一天放學辰光在小攤頭上買過一副魔術撲克。根據里面的說明書,昨天夜里白相過幾趟。只好臨時抱佛腳了,我依葫蘆畫瓢,當場表演了一套魔術撲克,大獲成功。哈,至今記憶猶新。
到了熱天,馬路上賣冷飲的、賣水果的小攤頭最多。阿拉頂喜歡買斷頭棒冰,便宜。削甘蔗皮的小販,動作麻利,三下五除二,一根甘蔗的皮削得干干凈凈。買賣甜蘆黍,小販是勿削皮的,吃的辰光,一不當心就會割開手指。現在西瓜品種改良了,一年四季都吃得到西瓜,而且吃大不到不甜的西瓜。不過那些年,買到不甜的西瓜,是經常碰到的事體。所以經常會為西瓜甜不甜發生吵相罵的事體。后來賣西瓜的小販門檻也精了,只吆喝“包開西瓜”,就是保證開出來的西瓜是熟的,所謂“包熟不包甜”。稱好分量,一刀下去,勿管甜勿甜,只要西瓜是熟的,鈔票付脫,西瓜拎走。熱天還有賣叫蟈蟈的攤頭,常常是阿拉男小囡的聚集地。
到了過年辰光,小馬路一個個賣木刀、木槍、野烏臉(臉譜)、風車、兔子燈的小攤頭就鬧猛起來,像雨后春筍一樣。有一趟我用零用鈿買了把水槍,“啪啪啪”亂飆(射),勿當心把水飆到隔壁人家灶披間(廚房)的熱油鍋里,差點闖窮禍(插一句,小辰光最怕小朋友對你講“大偉,儂闖窮禍了”,因為自己做錯了事常常不知道做錯了事)。
炮仗,也是阿拉男小囡的最愛。有一種“地老蟲”的炮仗,點著后會在地上亂竄,然后爆炸。阿拉買來“地老蟲”,經常會在人多的地方偷偷地放,嚇得小姑娘亂叫,大人亂罵。著勁!有一趟住在阿拉隔壁的“長腳鷺鷥”,在商店里放了一只“地老蟲”,“地老蟲”亂竄,竄到角落頭一堆硬柏紙(馬糞紙)里爆炸,結果差一點引起火災(還好火苗被營業員兩盆水澆滅)。面孔嚇得刷白的“長腳鷺鷥”被營業員送到了派出所。從那以后阿拉再也不玩這種嚇人的“地老蟲”了。
那些年,城管勿叫“城管”,叫“糾察”。他們手臂上戴著印有“糾察”字樣的紅袖章,專管那些在馬路上擺攤頭的小販。如同現在的“貓鼠大戰”一樣,只要遠遠地看到戴紅袖章的來了,小販們就一哄而散。
那些賣外煙的最活絡,只是在路邊放一只破筐,上面蓋著張硬柏紙,紙上寫著“外煙”。那些外煙販子眼烏珠亂轉,看到男人家就上前,“朋友,外煙要伐?外煙要伐?”他們的口袋里(內插袋、外插袋)裝滿了萬寶路、健牌,像裝滿了子彈匣。也難怪,外煙的成本高,要是被糾察捉牢,損失就大了。有一個賣零食的專業戶,一趟也沒有被“糾察”捉牢過,“我的眼睛只要注意那些販外煙的,他們一滑腳我就溜。賣外煙的那批小滑頭,是我的風向標”。
那辰光只要一發現街頭出現糾察,早有準備的小販們,把攤在地上的被單一卷(商品是放在被單上的),立刻就滑腳。不過賣油氽臭豆腐的攤頭最難撤了,儂能拎起一鍋子油逃嗎?只能坐以待斃,別無它法。
當然也有“智斗”的。弄堂隔壁的阿三頭在手帕廠上班,有一段辰光單位里工鈿發勿出,就發絹頭(上海人習慣上把“手帕”叫“絹頭”)給工人。那些年,罐頭廠發罐頭,食品廠發壓縮餅干……并不少見。阿三頭住的是街面房子。糾察來了,要沒收攤在席子上的絹頭。阿三頭勿買賬,吼道:“滑稽伐,我把絹頭拿出來曬一曬可以伐?”說著他又從屋里抱出一床被頭來曬。糾察們只好吃癟,在哄笑聲中沒趣地走了。
要說看到糾察逃得最快的應該是開著卡車來賣西瓜的小販,他們喇叭一響開走了,氣得糾察直跺腳,一點辦法也沒有。還有一點我一直搞勿懂,小販們看到有糾察來全都各自逃散,只有賣梔子花、白蘭花的老太,穩坐釣魚臺,依然篤悠悠地叫賣“梔子花、白蘭花,3分洋鈿買1朵,5分買2朵……”沒有一個糾察會去找她的麻煩。莫非是因為小本買賣,本鈿太小了?
小販們看到糾察來作鳥獸散,阿拉小巴辣子看到小販們兵荒馬亂的樣子,最開心了。記得那辰光還流傳著一句順口溜:“同志們,捉牢伊!投機倒把販賣糖精片。”哈哈。
我從小就喜歡吃茶葉蛋。印象中賣茶葉蛋的基本是老太,跟賣梔子花的老太一樣,糾察是勿來尋她們麻煩的。我吃茶葉蛋,從學堂門口一直吃到證券公司門口,可惜現在賣茶葉蛋的攤頭已經沒有了。
夜排檔
阿拉小辰光也有夜排檔,不過勿叫“夜排檔”。天黑以后弄堂里的路燈亮了,有辰光會聽到“篤篤篤,賣糖粥”的叫賣聲。弄堂里有挑著擔子進來賣糖粥、餛飩、酒釀圓子的。聽到叫賣聲,小攤頭周圍就會陸續出現拿著飯碗、鍋子、飯盒來買夜點心的顧客。他們七嘴八舌,鍋盆叮當,弄堂里立刻熱鬧起來。他們中有家里做夜班要回家的,有幾個人打麻將打到一半感覺肚皮餓的,也有聽到弄堂里的叫賣聲嘴里饞癆的。
我就是屬于這種聽到“篤篤篤,賣糖粥”的叫賣聲,便會饞癆的人。我問姆媽:“要勿要去買點夜點心吃吃?”姆媽經常回答:“今朝儂夜飯沒有吃飽?半夜三更的(其實哪里半夜三更呀?)吃飽了肚皮,會睏勿著的。”我心里說:“其實勿吃才睏勿著呢!”有辰光姆媽會開恩,從絹頭包里抽出幾角洋鈿,“去買兩碗小餛飩”。我立刻拿著鋼精鍋子,飛一般跑出去,加入買夜點心的隊伍。有辰光爹爹單位里加班,回家晚了,姆媽想要出去買點夜點心,都勿曉得到啥地方去買?挑著擔子串街走巷賣夜點心的,他們是來無影去無蹤的,到啥地方找他們去?半夜里肚皮會餓,爹爹最好嘴巴里塞塊蘇打餅干墊墊饑。
后來阿拉弄堂隔壁的小馬路轉彎角子上,到了天暗下來,油布大陽傘下白天擺皮匠攤的地方,出現了一個路邊攤,專賣柴爿餛飩。啥叫柴爿餛飩?百度上說,柴爿餛飩是上海對流動餛飩攤的一種稱法。上海餛飩攤最早可追溯到清末時期,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上海十分常見。攤販于深夜用木柴燒火并打著竹板叫賣,所以稱為“柴爿餛飩”。
我家附近的這家柴爿餛飩,夫妻倆一個燒煮一個收碗擦桌。幾只長條凳,兩只能夠折疊的桌子。油膩膩的桌面上,擺放著醬油、辣醬、醋。燒煮餛飩的大鍋放在一只舊柏油桶上,桶壁上開著通風口,燃燒著的柴爿噴著火焰。遠遠地,就能看到這片煙火氣,所以不用叫賣,完全是一副“姜太公釣魚”的樣子。要曉得夜里是沒有糾察來干預的,所以可以篤篤定定地坐下來,慢慢吃。夫妻倆的吃飯家什一輛黃魚車都可以裝著跑,進退自由,頗為瀟灑。記得乘風涼辰光,爹爹、姆媽帶阿拉吃過幾趟柴爿餛飩,味道還真勿錯!
不過那些年這樣的路邊柴爿餛飩攤,還是寥若晨星,勿大容易看到。到了20世紀80年代,上海灘的夜排檔(后來不局限于夜市)開始逐漸多了起來。據說大排檔本寫作“大牌檔”,興起于二戰后的中國香港。“檔”在粵語中有不固定流動的意思。百廢待興之時有人在街邊賣熟食,提供折疊桌椅,晚上休息時,就用鐵皮把排檔大包廂捆起,置于路邊。到了50年代,香港政府給這些攤檔發牌照進行規管,由于牌照是張大紙,得裱起來放在顯眼處,故為“大牌檔”。但“牌”又與“排”同音,不少人誤以為大排檔是“一大排人食飯”的意思,因而又寫成“大排檔”,也就這么流傳了開來。
大排檔全國各地都有,大多是聚集的小吃攤,沿馬路一溜排開,以燒烤、串串、麻辣燙和簡單小菜為主。后來有些店面固定下來,也開始講究裝潢,雖然衛生情況仍然不佳,但沸騰的人聲配合食材和鐵鍋當街高溫爆炒,吸引路人,生意自然不錯。上海的夜排檔紅極一時的,當數虹口區的乍浦路。當年我家離乍浦路不遠,我經常會聚集三五好友去那里聚餐。那時的乍浦路美食街,店家已經過百,小吃排檔、家常菜、高檔館子一應俱全。
那些年,長寧的玉屏南路、彭浦夜市、浦東的昌里路、壽寧路的“龍蝦街”……不勝枚舉。
我就是偏愛夜排檔,喜歡當街高溫爆炒,吃客們吆五喝六,吵吵嚷嚷的那種氛圍。有辰光,幾個勿認得的朋友,各人在各人的餐桌上吃燒烤,喝啤酒,聊天。聊法聊法,跟鄰桌的朋友聊到一起了,于是幾張小桌子拼成一只大臺子,干脆聚在一起吃起了燒烤,喝起了啤酒,聊起了天。吃到最后,還爭著買單。這樣的事體,我碰到過好幾趟。
要說經常來夜排檔的吃客,嘴巴交關刁,哪一家排檔的味道贊,菜肆好,吃過一趟就曉得了。所以儂去夜排檔,揀人多的地方去“消拼(shopping)”一般是勿會錯咯。啥人家調了廚師,一吃就吃出來了。當然,老板(老板娘)熱情,也會拉住勿少回頭客。我認得一個夜排檔的老板娘,人家叫她“阿慶嫂”,吃到半當中,常常送只把小菜,結賬時抹掉個零頭,常常使儂心里交關適宜。有一趟老板娘說漏了嘴,“其實都是湯里去水里來,蜻蜓尾巴自吃自”,雖然話糙但理不糙。還有,生意好的排檔,流轉得快,食材自然也新鮮,也是吃客們選擇的一個原因。
煙紙店
那些年,星羅棋布地坐落在上海灘的煙紙店,賣的東西跟小攤頭上賣的一樣,都是一些小零小碎的日用品。不過開煙紙店,不能講是擺攤頭。開煙紙店要比擺攤頭檔子高,畢竟有一個固定的門面。當然如果想買只鍋子,買聽餅干,儂肯定會去百貨店、食品店買,勿會去煙紙店的。
不過儂講煙紙店跟擺小攤頭一樣,開煙紙店的小老板肯定勿買賬,“阿拉開的煙紙店,樣樣都有,像爿小百貨店”。當年滑稽戲里有句形容煙紙店里東西多的順口溜:“牙刷牙膏香肥皂,衛生草紙電燈泡,阿司匹林橡皮膏……”記得我家住在復興中路辰光,弄堂口有一家煙紙店。小辰光我吃飽飯沒有事體做,曾經跟鄰居阿六頭分頭到附近的一家小百貨店和家門口的這家煙紙店去“調查”,數一數小百貨店有沒有100樣貨色(貨物)?煙紙店賣的貨色有多少?兩家“小百貨”PK一下。
我去的那家煙紙店,我一邊數一邊問一邊記錄:肥皂、草紙、牙刷、牙膏,針針線線、寬緊帶、橡皮筋,各種紐扣、大小撳鈕,刀片、剪刀、長短鉗子,燈油、蠟燭、自來火,紗繩、麻繩、皮鞋帶、跑鞋帶,木梳、頭繩、生發油……真的多得勿得了,數也數勿過來。
不一會兒阿六頭跑回來,問他“調查”到了多少貨色?他結結巴巴地報了一些“菜名”,報不下去了。他說他被百貨店的營業員趕了出來,罵他“小赤佬,勿買東西搞七念三作死啊”。那些年,百貨店里的不少營業員態度都勿大好,不耐煩。儂買東西,想調換一個看看,他們就不耐煩了。要是儂買回去了,再想來調換,那就麻煩了,吃足排頭,“儂自己哪能勿看看清爽”“看到了嗎,商品售出該不退貨”。柜臺上果然有這樣字樣的牌子。阿六頭勿買東西去七問八問,當然要被人家趕出來了。而阿拉弄堂口煙紙店里的老頭老太,人交關客氣,無論老人小囡,“童叟無欺”。姆媽叫我出去買東西,只要煙紙店里有的,我就買煙紙店里的。主要是煙紙店里的老頭老太態度好,耐煩。
上海的煙紙店一般是夫妻兩人一道經營,又叫夫妻老婆店。之所以叫煙紙店,據說因為上海人經常去這種小店里買香煙和草紙,“煙紙店”由此而來。也有另一種講法是,本來這種小店是賣胭脂、雪花膏的,就叫“胭脂店”。后來店主開始賣點香煙、草紙等日用品,于是“胭脂店”叫法叫法就叫成了“煙紙店”。那些年,香煙、火柴、肥皂、草紙是煙紙店的“四大金剛”,那些貼近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小商品,也逐漸進入煙紙店。
煙紙店里的小商品多,而且常常還可以拆開來買,自來火可以買半包,香煙可以三支五支的買。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在要緊要慢辰光可以“救急”,比如半夜里可以買得到藥(胃藥、退燒藥等),臨時停電了可以去買支蠟燭,甚至半夜被蚊子咬,也可以去敲門買盤蚊香,儂只要向煙紙店老板打招呼,“實在勿好意思,實在是被蚊子叮得睏勿著”,煙紙店老板也會揉著惺忪的眼睛,從小窗口里把蚊香遞給儂。
對了,那些年上海灘上的煙紙店,常常配有公用電話,大大方便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居民半夜三更有發急病要叫救命車(救護車)的,儂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敲開煙紙店的排門板,打電話叫救命車。
阿拉弄堂口的這家煙紙店,也安裝了公用電話。編上號碼的排門板,最后一塊排門板上開著一個小窗口,就是用來半夜三更給人“救急”的。記得有一趟一個賊骨頭(竊賊)半夜里進弄堂來偷東西,被居民發現了,把他堵在一家人家的曬臺上。這個賊骨頭手里拎著一根鐵棒,眼露兇光,弄堂里沒有一個人敢上去抓他。這個辰光煙紙店的老板看到了,一只電話打到派出所,一歇歇辰光民警就趕到了。本來大家眼看這個賊骨頭就要翻墻翻到隔壁弄堂去了,民警一到,賊骨頭立刻癱倒,乖乖就擒。后來大家發現,煙紙店電話機的墻壁上,貼著一張紙,上面密密麻麻記著醫院、藥房、派出所、居委會、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等的電話號碼。老板、老板娘真是個有心人。后來居委會干脆把一只失物招領箱也掛在煙紙店門口了,說是弄堂口人來人往,失主容易看見。
煙紙店的這對老夫妻,膝下無子,就靠開這爿煙紙店維持生計。老頭負責進貨,老太看柜臺。我經常看到老頭推著腳踏車(上面堆滿了貨物)進貨,累得滿頭大汗。老頭悶聲勿響的,老太閑話蠻多。鄰舍隔壁來買東西,臨時忘記帶鈔票或者鈔票不夠,老太都是肯讓人家把東西先拿走,“鈔票有空咯辰光掇來(寧波話:拿來),唔告咯(沒有關系的)”。老太是寧波人,一口石骨鐵硬的寧波閑話,人交關客氣。最讓我感動的是,有一趟家里有客人來,姆媽燒小菜燒到一半,突然發現味之素(味精)用光了,她讓我去煙紙店買一包。我奔出去買,勿曉得啥辰光袋袋里的鈔票落掉了。煙紙店老太雖然看我有點面熟陌生,她還是把一包佛手牌味之素交給我,還是那句閑話:“鈔票有空咯辰光掇來,唔告咯。”
后來老頭生毛病走了,煙紙店就剩下老太一個人照料了。鄰舍隔壁看她孤苦伶仃的,爺叔阿姨買東西,常常勿要她找零頭。有一趟我也學他們的樣,故意不拿零頭就跑了。過了兩天再去買東西,老太就一把拉住我:“上趟儂有五分找頭沒有拿。”我慌忙說:“沒有沒有,是儂搞錯了。”老太拍了拍額頭:“要么我搞錯人了……”一副很懊惱的樣子。
是啊,不少上海人的童年回憶里,總也離不開弄堂口的煙紙店。
馬路菜場
其實,小菜場也都是由一個個賣魚賣肉賣蔬菜賣豆制品的小攤頭組成的。那些年,上海灘的室內菜場(比如三角地小菜場、福州路菜場等)不多,而大多數是馬路菜場。
老底子,上海南市的外咸瓜街(咸黃魚街)、面筋弄、魚行街、火腿弄、殺豬弄、豆市街等地方,是晚清、民國年間制作副食品小作坊的聚集地,前店后作坊,也是上海老百姓買小菜個地方。據史料記載,最早市郊農民和菜販子一早在集市上設攤,或者串街走巷叫賣蔬菜,黃浦江、城隍廟、小東門一帶,這樣的集市貿易比較集中。現在的寧海東路,早先就叫“菜市街”。
我家隔壁有條小弄堂,天還沒有亮,小弄堂兩邊就擺起了賣菜的攤頭。其實也不算是弄堂,只是一條沒有路牌的小馬路,兩頭通往兩條大馬路。這條小馬路不是柏油鋪的,是一條七翹八裂的彈硌路,腳踏車踏在上面顛得屁股痛,黃魚車踏過噪聲震耳。這條馬路菜場是有人管理的,進入馬路菜場擺攤頭的小販,不用擔心戴袖章的糾察來驅趕,擺攤頭的都有固定攤位,要想去買點啥,容易找得到。住在附近的居民都喜歡來這里買小菜。姆媽買小菜也常到那里去,姆媽講,雖然那里的小菜花式品種勿多,主要是路近。不過也有不方便之處,就是必須趕在早上八點鐘前去,超過八點鐘這條馬路菜場就收攤了。
這是為啥呢?后來一打聽,原來這條小馬路上有一所民辦小學,八點鐘一到,小學生們就要出來做早操的。那辰光學堂條件差,像這樣沒有操場的弄堂小學并不少見。開頭擺攤頭的小販不買賬,他們出了管理費,為什么這么早就讓他們收攤?民辦小學的校長也不示弱,八點鐘一到,學堂里的學生仔蜂擁而出,擠滿一條馬路,老師手里的電喇叭亂叫。這副吞頭勢小販們如何賣小菜?后來管菜場的跟小學談判,由于先開學堂,后出現馬路菜場的,馬路菜場方“禮讓”,于是訂出了“八點鐘收攤”這么個條款,雙方才歇鼓收兵。其實明明是一條公共馬路,誰有權利這么處置啊?暈。
我經常跟姆媽去馬路菜場買菜,主要是幫姆媽拎籃頭的,有辰光要拎兩只籃頭。一踏進馬路菜場,就感覺到周圍亂哄哄的一片,討價還價的,吵架的,大呼小叫。賣魚賣肉的小販似乎都有一種優越感,吆喝聲音響亮,而擺蔥姜攤的,刮魚鱗的,則總是默默無聲。魚攤頭前腥氣沖天,地上垃圾滑腳,路邊的泔腳桶更是蒼蠅亂飛。昔日的馬路菜場可以用三個字來高度概括“臟亂差”。
馬路菜場常常會延伸出一段路,也有擺小攤頭的,不納入馬路菜場管理。不過糾察會來趕,會來抓,常常也鬧得雞飛狗跳的。只有賣蔥姜的老太,看到糾察來了,繼續穩坐釣魚臺。而那些糾察對擺蔥姜攤的都一概視而不見,如同看到賣梔子花、白蘭花的老太一樣眼開眼閉。
我跟姆媽曾經在馬路菜場那段延伸區域,上過幾次當,都很搞笑。一趟是阿拉明明買了幾只大閘蟹,看著小販把蟹裝進蒲包里,結果拎回到家,發現被調包了,蒲包里的大閘蟹變成了癩蛤蟆。當然阿拉再追出去,賣蟹的小販早已不見蹤影了。還有一趟姆媽叫我去買幾只皮蛋,我也在這段延伸區域看到有賣皮蛋的攤頭,于是買了幾只。那辰光的皮蛋外面都是包裹著礱糠泥土的,等回家后敲開來一看,發現不是皮蛋是洋山芋。我立刻快步返回“作案現場”,當然不見那個賣假皮蛋的。后來我只要經過此地,只要看到賣皮蛋的,總會先買一個,付好鈔票,當場打開來看看,總是一無所獲。我忽然想起“疑人偷斧”那句的成語。
現在馬路邊能看到擺攤頭的越來越少了。如今外賣送貨業務發達,儂只要手指頭一點,大到空調、洗衣機,小到電蚊香、潤唇膏,快遞小哥都會一一給儂送上門來。雖然今非昔比,不過那些年那些小攤頭的記憶,卻依然縈繞在記憶中,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