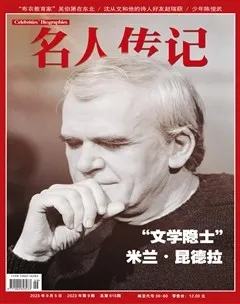我的父親顧冷觀





父親原名顧育仁,曾用名靜銘。顧冷觀起初是其筆名,直到1937年才被用作正名。20世紀30至40年代,父親編輯了三份有影響力的刊物——《上海生活》《小說月報》《茶話》,為中國近代著名編輯家。
年少背井離鄉(xiāng),海上自謀生計
1910年農歷八月初九,父親出生于江蘇崇明城橋鎮(zhèn)一個貧寒之家,由我的祖母和曾祖母撫養(yǎng)長大。祖母原是育嬰堂的棄嬰,由無子嗣的顧家抱回且視為己出,后又被送到私塾讀書。她聰慧貌美,及笄之年,曾祖父因病去世,家道中落,曾祖母不得已為她贅婿。祖父長祖母十五歲,同意入贅又隱瞞了年齡,才“乘虛而入”。婚后祖父終年在英國駐上海領事館(以下簡稱“英領館”)當信差,收入微薄,故祖母一直自謀生計,經(jīng)營一家點心店,兼賣餛飩和酒菜。她每天清晨即起,做餡子、搟皮子、包餛飩,苦撐一家祖孫三代的生計。曾祖母也助她一臂之力:釀崇明老白酒,在天井種菜,還常年養(yǎng)著十多只雞,可做成鮮嫩可口的白斬雞待客。
父親六歲那年,祖母又領回家一個“新妹妹”。 他因為添了一個玩伴驚喜萬分,狂奔至床前,不慎磕倒在踏板上,咬斷了舌頭,滿口是血。祖母東挪西借,張羅了一百元大洋,當夜帶他乘帆船到吳淞,再轉到上海投醫(yī)。舌頭總算接上,但清貧之家從此欠債累累。父親晚年每憶及往事總嘆曰:“母恩浩大,無以言傳也。”
崇明雖屬彈丸之地,但人文薈萃。辛亥革命后,縣城之內取消私塾,辦起不少新校。父親六歲就讀的城南小學就是一所洋學堂,采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科書,設有四年制初小、三年制高小和四年制中學,很注重教育質量。學生字句通順后再習作文,逐步融會貫通。校有良師,家更有嚴母。夜晚昏黃的油燈下,祖母一邊織布,一邊督促他讀書、寫作業(yè),因此父親從小打下了堅實的學業(yè)基礎。因家境貧寒,父親很早就學會了養(yǎng)雞。幼時沒有糖果可吃,蘆根和山芋干就都是可口的零食。每逢天晴,他便要忙著去采集枸杞頭、薺菜、馬蘭頭等野菜,補充食物之不足。小麥登場后,則常以麥粥充饑。
父親十四歲時,祖母去世,生活頓失依靠,學業(yè)中斷。不久,他到上海隨祖父入住英領館,做些零星小事來補貼家用,如為打網(wǎng)球的洋人拾球,得一兩毛賞錢;或照顧領館中的外國孩子。不久他被我祖父送到一家機器廠當學徒,學做鉗工。
該廠地處提籃橋的舟山路,四周皆荒地。父親夏天睡閣樓,臭蟲成堆;冬天則睡在灶下取暖。師父和師兄能上桌吃飯,他只能夾點菜在飯碗里,蹲在門口吃。如此艱難屈辱的生活維持了兩年,工廠倒閉了。父親只得返回英領館。據(jù)父親回憶,當年他常伴英國領事的女兒玩耍,學得一口標準英語。領事離任回英國前曾邀請他同行,因祖父反對而未果。
祖父經(jīng)朋友勸說,終于打消了要求父親白天打工的念頭,送他讀了中學。父親于1926年入讀圣芳濟中學,開始了半工半讀的生涯,1928年肄業(yè)后入讀青年會中學專攻英語,以期日后在英領館謀職。此兩校均系教會所辦,教員大都是外國傳教士和神父,全部用英語上課。青少年時代,他長期生活在洋人多于華人的環(huán)境里,受到了正規(guī)的英文教育,但他也愛好國文,積極探索。高中畢業(yè)后,父親考進南京的金陵大學讀文科,課余喜歡寫作投稿,肄業(yè)后進入英領館工作。因向往做一個自由職業(yè)的文化人 ,他終于辭卻了領事館的差使。
1936年,父親應聘三和出版公司被錄取,擔任校對一職。雖然工資低,父親卻能廣交文友,而且從工作中初步了解了編排格式和印刷程序,為他后來擔任私營雜志編輯積累了經(jīng)驗。半年以后,上海聯(lián)華廣告公司招聘他為廣告文學撰寫人員,同時編輯一本專業(yè)廣告雜志《廣告與推銷》。父親刻苦努力,很快成了內行,受到重用,由公司方面提供吃住。這樣,他的生活才穩(wěn)定了下來。
主編《上海生活》,穩(wěn)步邁入文壇
1937年聯(lián)華廣告公司業(yè)務擴大,父親受聘主編《上海生活》,兼任廣告文學撰寫員。 同年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上海生活》刊發(fā)一卷六期后因戰(zhàn)亂而停刊。其時,上海租界已被日軍包圍,淪為“孤島”。
1938年6月《上海生活》復刊后,增加了不少新欄目,成為滬上一份不可多得的綜合性月刊。它始終遵循創(chuàng)刊宗旨:“嚴守的立場,是要雜而不蕪。”在內容上“不空虛,不無聊,不低級趣味”,文字力求通俗,內容卻力避庸俗。據(jù)父親回憶,它以大量篇幅指導上海市民之衣、食、住、行等方法和門徑,是一本探討如何在上海生活的雜志。淞滬抗戰(zhàn)后,同胞紛紛涌入租界避難,至8月底已多達七十萬人左右,尋找住房十分困難。他為此撰文《談談住的問題》,指導市民如何租房,才能夠不吃虧上當,并刊文探討如何挺過難熬的通貨膨脹,頗受讀者歡迎。
1939年1月,《上海生活》被暢銷上海的《新聞報》看中,隨其夕刊《新聞夜報》附送。報壇巨子、《新聞報》主筆兼副總編輯嚴獨鶴擔任了《上海生活》的名譽主編。自此,刊物的發(fā)行量頓時大增,風靡“孤島”,成名的作家紛紛前來投稿。
《上海生活》連載過不少名作,比如鄭逸梅的《說林掌故錄》和《數(shù)十年前之上海》、張恨水的《到農村去》、包天笑的《恨綺愁羅》等。包天笑小說之離奇曲折、鄭逸梅文史掌故之趣味盎然,以及聞名遐邇的武俠小說家顧明道及章回小說大家張恨水的撰稿,都深受讀者歡迎,雜志因此進一步拓展了銷路,父親的聲望也隨之逐步提高。誠如父親1940年之撰文:“《上海生活》 出版至今,歷史悠久,聲譽良好,內容以透露上海人生活動態(tài)為中心,兼載輕快流利的譯文、掌故,和風趣活潑的短篇創(chuàng)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 日寇侵占租界,上海淪陷。《上海生活》即隨《新聞夜報》停刊。刊行期間,它以文字、廣告、漫畫、攝影等多種藝術形式反映出當時上海這座“孤島”的特種生活環(huán)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在2006年7月將它作為海派文化和昔日上海灘的真實寫照予以精選重版。
在主編《上海生活》的五年間,父親不但組稿、審稿,負責撰寫篇幅浩繁的廣告文字,還親自寫稿一百四十余篇。其筆名除了“冷觀” 外,還有 “育仁”“靜銘”“冷”“觀”“育”“仁”“靜”“銘” 等。每逢周六,父親必在粵餐館美華酒家與文人相聚,約稿加聊天,與老朋友聯(lián)絡感情并結識新朋友,從而鞏固和擴大了他的作家群。他的 “周六聚會”十多年雷打不動,直到他離開文壇。
主持《小說月報》,新老名家云集
1940年10月, 聯(lián)華廣告公司聘請父親創(chuàng)辦抗戰(zhàn)時期上海第一份大型文學刊物《小說月報》,助理編輯有呂白華和丁景唐,名譽顧問是嚴獨鶴。出版在即,父親告知讀者:“……《小說月報》集各體各派之大成,盡合讀者口味,選長篇短篇之佳構,此中一網(wǎng)蒐羅。執(zhí)筆者:包天笑,張恨水,徐卓呆,秦瘦鷗,程小青,徐碧波,范煙橋,王小逸……”果然,創(chuàng)刊號上亮相的幾乎全是名士名家。創(chuàng)刊號很受歡迎,曾再版過一次。
其時,上海前后以《小說月報》為刊名出版的大致有三種:最早的一種,由“競立社”出版;第二種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三種就是我父親主編的。其在培養(yǎng)新晉作家、團結新老文人、保留民族文脈方面,都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1941年底,日寇勒令停辦二十余種報刊,查封商務印書館等五大書局,文學創(chuàng)作空間備受擠壓。通俗名家中除張恨水赴內地外,其他大都選擇了留守:鄭逸梅、顧明道、包天笑、徐卓呆、秦瘦鷗等滯留上海,而周瘦鵑、程小青則固守蘇州。正是父親通過《小說月報》為他們提供了創(chuàng)作平臺,緩解了他們在經(jīng)濟上的種種壓力。
在《創(chuàng)刊的話》一文中,父親寫道:“上海自成為 ‘孤島’以來,文化中心內移,報攤上雖有著不少的東西,但是真正適合胃口的,似乎還嫌得不夠。”父親聲明:《小說月報》以小說為主,散文小品為輔;作者必須在純正的原則下提起筆來寫作品,這絕對優(yōu)勝于那些空虛的、無聊的、低級趣味的文字。在編輯方針上,父親主張三個特點:一是新舊小說并重,沒有門戶之見;二是各種體裁兼?zhèn)洌瑥V泛團結作家;三是注意提攜文學新人。《小說月報》不僅以著名作家為主要作者群,更別開生面地為青年作家乃至大、中學生提供施展才華的舞臺。
父親在編輯《上海生活》時,就與諸位名家如程小青、張恨水、鄭逸梅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小說月報》創(chuàng)刊后,這些文友不僅自己積極投稿,還協(xié)助父親向其他名家約稿。比如,父親仰慕包天笑之名,可與之素不相識,乃托鄭逸梅介紹,征到了長篇小說《換巢鸞鳳》。接著,包天笑又投來了《燕歸來》。如此這般“滾雪球”,為《小說月報》寫稿的名家越來越多。著名出版家、作家陳蝶衣也曾是《小說月報》的作者,他的《媚惑記》就發(fā)表在《小說月報》創(chuàng)刊號上。
自第二期起,父親發(fā)起大中學生征文比賽,第四期起即開辟征文園地,定期給獎。比較隆重的一次是借中法藥房二樓召開的給獎大會。除獲獎者外,參加評獎的人如嚴獨鶴、包天笑、沈禹鐘等前輩也出席了大會。父親以持續(xù)的征文培植新作家,從積案盈箱的征文稿件中,發(fā)掘和培養(yǎng)了施濟美、俞昭明、程育真等后來文學史上的“東吳系女作家”群體,以及徐開壘和沈寂。徐、沈兩位后來分別成為中國著名報人和電影編劇家、小說家。沈寂在《顧冷觀日記》序言中道:“陳汝惠的《死的勝利》《小雨》是抗日愛國的典型作品。我自己也是受這些小說的影響,將我的第一篇小說《暗影》,投寄給《小說月報》,發(fā)表在首篇。顧冷觀先生應該是最早發(fā)現(xiàn)并推崇我作品的恩師。”
《小說月報》也傾力扶持新文學作家,從第六期起,改變辦刊方針,引入新文學作家的作品,促使新舊文學融合。于是,趙景深、魏如晦(錢杏邨)、胡山源、陳汝惠、陳伯吹、周楞伽等人的作品也時見該刊。
在眾多作家中,包天笑先生撰文最多,刊發(fā)于短(中)篇、長篇、筆記這三個《小說月報》最主要的版塊。舊派通俗作家一向被新文學作家們視為落后于時代的封建余孽,所以《小說月報》為他們提供集體復出的平臺肩負著很大壓力。其實這批作家,因日寇入侵,血洗我祖國大好河山,致使生靈涂炭而義憤填膺。他們內心的憤怒和抵抗,不難從《小說月報》刊發(fā)的文章中窺探一二。
由此可見,《小說月報》通過提供創(chuàng)作平臺,推動了通俗文學名作家的集體復出;通過引入和培植新作家,促進了新舊文學的融合;通過文學批評引導讀者,培育了新的閱讀市場。隨后,《小說月報》的作者陳蝶衣和周瘦鵑創(chuàng)辦《萬象》和《樂觀》,推動了抗戰(zhàn)時期上海通俗文學的繁榮。可以說,《小說月報》促成了戰(zhàn)時上海通俗文學的復興。
從1944年起,因物價狂漲,期刊入不敷出,《小說月報》不得不于11月停刊,共出版四十五期,是上海“孤島”和“淪陷”時期辦刊持續(xù)時間最長的文學期刊之一,為失陷遭劫的市民提供了一點新鮮的精神食糧。
編輯《茶話》,婉轉揭露時弊
1946年6月,父親創(chuàng)刊《茶話》,編輯還有呂白華。《茶話》創(chuàng)刊時其經(jīng)銷處已多達八十個,遍及國內各大城市,并遠銷菲律賓等地,后又增銷新加坡等地,其以豐富的內容和壯觀的作家群吸引了眾多讀者。
《茶話》體裁豐富,涵蓋長短篇小說、雜感隨筆、地方游記、人物傳記等,屬綜合性文學刊物。供稿作者大多是《小說月報》曾經(jīng)的撰稿人,如趙景深、陳汝惠、程小青、徐卓呆、范煙橋、錢今昔、周楞伽、包天笑、胡山源、譚正璧等,也有一些是文學新人。
創(chuàng)刊號并無創(chuàng)刊詞,開篇即是陸丹林的《總理大本營時期手札》,匯集孫中山于1923年6月至9月致葉恭綽的四封信函和11月致張作霖之函,并將原件制版刊印,頗為引人注目。辦到第八期時,申小迦接替了呂白華編輯一職。申家與父親交往已久,申小迦的父親即申石伽。
《茶話》的作品中,有描寫家庭婚戀的,有反映市民們在抗戰(zhàn)勝利后對現(xiàn)實失望情緒的,有調侃艱難生活以及諷刺社會丑惡現(xiàn)象的,有通過歷史小說等來借古諷今的。同時還關注民眾并予以指導。譬如面對屋荒,告訴人們“人多屋少怎樣避免爭吵”;對愛美的女性講“如何培養(yǎng)高雅的言談舉止”;對于男女問題,則談“怎樣消除夫婦暗礁”“夫婦同工往往會發(fā)生仳離”,等等。
《茶話》創(chuàng)辦時,正值抗日戰(zhàn)爭勝利不久,因此極為關注戰(zhàn)爭以及由此帶來的苦難,也關注時局。
自1947年4月第十一期起,《茶話》添設由父親主筆的《風雨集》欄目,每期數(shù)十則,反映社會百態(tài),諷刺政局黑暗,文字短小精悍,筆鋒犀利,為解放戰(zhàn)爭時期艱難生存的上海市民提供了一份精神慰藉。
1949年 4月,《茶話》出了最后一期后被迫停刊,共出版三十五期,較為完整地記錄了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上海市民的生活和心態(tài)。縱觀上海20世紀40年代較有影響的文學期刊,出版時間較長且能維持到新中國成立前的寥寥無幾,僅《永安月刊》《春秋》《茶話》三家。
順勢淡出文壇,劫后再會文友
《茶話》停刊后,聯(lián)華廣告公司仍舊聘用父親,也保留他的辦公室,但不再出版刊物,付給父親的工資自然菲薄。為了養(yǎng)活一家五口,父親不得不尋找第二份工作。1951年下半年,父親放棄聯(lián)華廣告公司的工作,淡出他奮斗多年才躋身其中的文壇,從此一直在中學教書。
之后,父親的生活極為低調,從不在我們面前提起他在文壇的往事,來往最多的只有他幾位平凡而善良的同鄉(xiāng)。至于父親的名流朋友,記憶中除了申小迦先生外,我只見過趙景深先生一次。父親去世多年后,我偶然瀏覽網(wǎng)頁,發(fā)現(xiàn)有多篇碩士、博士論文均以研究他主編的期刊為課題,才知道原來父親曾是上海的名編輯。
父親對教育事業(yè)兢兢業(yè)業(yè),一絲不茍,晚上伏案備課的時候居多。然而無論他工作多么努力,“文革”開始后,他仍受到波及,備受折磨,但父親挺了過來。
熬過苦難歲月,粉碎“四人幫”后,社會漸趨安定祥和,陳伯吹等故舊又登門造訪了。 我亦曾奉父之命前去拜訪申小迦先生。父親也恢復了與秦瘦鷗等老朋友的通信,相約整理“鴛鴦蝴蝶派”史料。21世紀初,舍弟在舊書店里看到過一本有關“鴛鴦蝴蝶派”的書,其中有父親所寫的文章。父親仙逝后,我們翻檢他的遺物,發(fā)現(xiàn)一篇《〈小說月報〉憶語》,字跡蒼勁有力,筆調卻相當輕松,想必與此有關吧。
1969年父親退休后,回到了久違的崇明故居。空屋二間,一人一宅,入夜奇趣橫生。雨夜的淅淅雨聲,秋夜的唧唧蟲聲,冬夜的皚皚白雪,使他詩意盎然,易入夢鄉(xiāng)。從此至1986年,每年春夏季節(jié),他必回故居小住,與摯友長談是一樂,回歸自然又是一樂。晨起去海邊踱步,既鍛煉身體,又可養(yǎng)心。回鄉(xiāng)期間,父親必為鄰里的孩子們補習語文和英文。見青年施國敦孜孜不倦習畫,他愛才之心油然而生,乃推薦該生拜現(xiàn)代著名畫家施南池為師。
上海文史館多次派人請父親“出山”,做文史館員,還有人邀他去編《辭海》,他因已慣于閑云野鶴的生活而一概謝絕,但也為文史館寫過一些資料。
2000年農歷二月初八,父親終因心力衰竭在醫(yī)院去世,享年九十歲。
父親的一生,幾乎都是在清貧中度過的。日復一日,他喜歡邊喝紅茶,邊閱讀書報,紅茶必須是滾燙的。在我的記憶里,他常年喝的紅茶里并無茶葉,而是用最廉價的紅茶梗煮的。我曾多次回國探親,見他依然穿著滿是補丁的衣褲,甚是傷感。他卻總是笑著對我說“知足常樂”。 那是他終生信守的座右銘之一。
父親在坎坷之中奮斗了一生,這是他留給我們后代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和無形遺產。而他對文化事業(yè)的貢獻,隨著歲月的流逝,仍將留存在人們的心間,永遠不會被忘卻。
(實習編輯/侯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