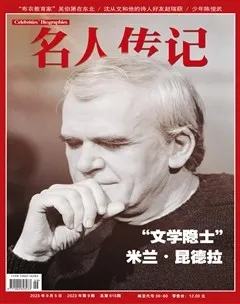流年碎影,美美與共——鄒士方為大師攝影造像









鄒士方有一本厚重的人物攝影集,所有照片均由他親自拍攝,幾乎包括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化界名流。翻動這本影集,寶貴的瞬間、光陰的故事、時代的精神、思想的力量、文藝的趣味都像瀑布一樣,從那座文化的高峰飛流而下。這些流年之中的影像,成為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縮影,見證著那個年代的美學熱和哲學潮。
這是鄒士方的文化寶藏,也是他的青春歲月。他為大師攝影造像的故事,要從他考進北京大學說起。
未名湖畔的學子如魚得水,拍攝20世紀80年代的大師肖像
1977年底,鄒士方參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被北京大學哲學系錄取,成為一名大學生。作為當時的天之驕子,1978年3月,鄒士方正式入學,他張開臂膀熱烈地擁抱未名湖,在中國的文化心臟地帶擁抱浪漫的時代。更令他激動的是,彼時,馮友蘭、宗白華等先生是哲學系的教授,朱光潛是西語系教授,王力是中文系教授,季羨林是副校長,這些光芒璀璨的大師不再遙不可及,而是近在咫尺。
與其他學子不同的是,鄒士方胸前總是掛著一臺照相機。挎著這臺相機,他走進北大名教授們的家中,記錄下大師們的動人影像,也成就了他自己的光影人生。
大學時,鄒士方是文藝骨干,擔任北大五四文學社副社長和校刊《大學生生活》主編。他同時進行文學創作,在《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等報刊上,發表了不少詩文和攝影作品,其中四幅攝影作品入選首都大學生攝影藝術展覽,一幅獲得優秀獎。
負笈北大,鄒士方奔走于朱光潛、宗白華教授的門下,與兩位美學大師朝夕相處,成為他們的私淑弟子。他向語言學大師王力、歷史地理學大師侯仁之及國學大師季羨林求學問道。得益于恩師們的介紹,他又逐步結識了一些校外的名家。
談起這段求學經歷,鄒士方說:“我以為我是趕上了一個好時代。80年代的特殊背景使我不僅能在北大的課堂上學習求知,而且能在課下求教于諸位北大大師的門下,還可以以校友的名義拜訪心儀已久的北大名人。”這些訪問如一盞盞明燈,照亮了鄒士方人生路上的新天地,給他的人生規劃帶來無窮的啟示。
大學畢業后,鄒士方被分配到全國政協,先編政協會刊,后來擔任《人民政協報》副刊專刊部副主任、副刊主編。不久,他受邀兼任《民主》雜志副主編,又被年近九旬的新聞家顧執中邀請協助創辦北京民治新聞專科學校并兼任副校長。出于工作需要,他常向國內的名家們約稿,由此與他們建立了聯系。
鄒士方是20世紀80年代與文化藝術界交往最多的人之一。他與當時四百多位文化藝術名人有過交往,其中密切交往的有六十多人。他收藏有三百余位文藝名家給他的題詞,七百余幅文化藝術名人贈他的書畫,一千余封寫給他的書信,四百余本贈予他的簽名本。他與錢鍾書、沈從文、曹禺等文學大師接觸密切,與美術大師劉海粟、吳作人、李可染、吳冠中,書法大師啟功來往頻繁,為他們撰寫了回憶文章。許德珩、周谷城、楚圖南、王昆侖、錢昌照與他是忘年交。劉開渠、華君武介紹他加入中國美術家協會,冰心、沙汀介紹他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曹辛之為他刻印,梁斌贈他書畫。蔣孔陽、吳祖光、常任俠、管樺為他的著作作序,冰心、季羨林、端木蕻良、趙清閣、蔣星煜、吳小如、張允和、劉章為他寫推介文章。
鄒士方之所以能與眾多的大師、名人結誼,并不完全由于他的編輯、記者身份,更由于他深厚的學養和多方面的才華。他與大師名人之間有共同語言,有對美的共同追求,于是在交往中,他亦逐步成為一名美學家、作家、畫家、攝影家和文藝評論家。
朗潤園中如坐春風,寫下宗白華研究奠基之作
在北大求學時,鄒士方與常在未名湖畔散步的宗白華結緣。鄒士方說,他永遠忘不了走進宗先生家的那一刻。那一刻在他的生命里是原點式的、里程碑式的存在,具有生發的力量,指引他走向了美學研究的道路。
大師聚集之地,總有獨特的風云氣象。宗白華先生家在未名湖畔的朗潤園公寓里。未名湖涵碧,朗潤園涵翠。1980年5月一個晴朗的下午,鄒士方和哲學系1977級的幾位同學來到朗潤園公寓宗白華先生家中。
“宗先生在書房接待了我們。先生白發似雪,面色紅黑,寧靜安詳,豐神瀟灑。屋子不大,室內光影斑駁,窗前盆花吐芳。書架上排排書籍,伴有幾座小型石雕和盆景。東墻上懸掛著油畫《蒙娜麗莎》以及幾幅西洋風景畫、中國山水畫和條幅。”四十多年過去了,鄒士方仍清晰地記得當時宗先生的樣子,連書房里的陳設也記憶猶新。
這次見面,師生對坐,宗白華談話是自由的、跳躍的。學生們懷著虔誠而敬仰的心情,聆聽并了解了先生的過往。宗白華講了自己棄醫學從美學的早年經歷,他說:“我原來是學醫的,但我覺得我終究不適于拿手術刀解剖人的形體,而較適于用理性探索人的內心,就改行鉆進了美學。”鄒士方還了解到,原來是宗白華發現了郭沫若——宗先生把郭沫若的詩文發表在了《學燈》上,并因此與田漢、郭沫若結下深厚的友誼,后來三人一同出版了詩集《三葉集》。
宗白華書桌上一尊雕刻精美的大型佛頭低眉瞑目,神秘微笑,引起了鄒士方的注意。宗白華就講了他和這尊佛像的故事。當得知宗先生因為這尊見證了滄桑國難史的佛頭而得號“佛頭宗”時,大家莞爾一笑。后來,鄒士方在《宗白華評傳》中詳細寫了宗先生與佛首的奇緣。
這次見面,宗白華重點談了中國的美學思想和美學教育,大家如坐春風。一個多小時過去,窗外的屋檐披上了一層柔和的金輝,銀杏樹在余暉中靜默。鄒士方和同學們與宗先生在黃昏里合影留念。
告別之時,宗白華指著墻上的油畫《笛卡兒像》說:“我很喜歡這幅畫。”并為同學們講解這幅畫的妙處。此時,鄒士方內心蕩起一層一層的漣漪,他在宗先生的“眸子里也發現了油畫上笛卡兒的眼睛里蘊含的那種微妙的東西,一種探索真理的心靈之光。探索美的人的身上閃爍著一種美的光芒,這種美是內在的美、知識的美”。
“拿叔本華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經過這次拜訪,鄒士方獲得了宗白華先生的精神真傳,沉醉在美學的新天地。
1981年春節,鄒士方到宗老家中拜年,為他拍攝了一張經典的照片:宗白華與案上朝夕相處的石雕佛頭相伴,他沉思,微笑,安詳,圓融。思想家已然一頭銀發,其思想卻蒼翠青蔥。已入化境的宗白華與石雕佛首,一左一右,一前一后,智慧的光芒與藝術的內蘊,交相輝映。
從1982年開始,鄒士方先后發表《慧眼識才——宗白華對郭沫若的發現和扶植》《美學老人宗白華》《宗白華傳略》《宗白華美學思想初探》《宗白華美學思想再探》《宗白華和他的舊體詩》等一系列文章。冰心對其研究有很高的評價:“他對于宗白華教授的生平和美學思想的研究在國內外尤具有開拓性貢獻。”當時的宗白華被文壇冷落,不似現在如日中天,鄒士方的辛勤工作因此更具有歷史意義。
鄒士方花費心血最多的,是三十萬字的《宗白華評傳》,這是宗白華研究的奠基之作,為后來者提供了豐富的觀點以及詳細的資料和線索,后來林同華主編《宗白華全集》,不少篇章就直接錄自此書,一些篇章由這本書提供的片段或線索而找到了原文。鄒士方查閱了浩如煙海的舊報刊,訪問了近百位宗白華的親屬、同事、朋友。宗白華所從事的每一項工作,所寫的每一篇文章,交往過的每一個人,鄒士方幾乎都進行了調查研究。書中數百幅照片和手跡,大多由鄒士方親自拍攝和收藏。記錄的私人談話、收錄的大師信札,使這本書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可靠性和可讀性。
國學大師梁漱溟曾為鄒士方的《宗白華評傳》題詞,贊之“充實之謂美”。這讓鄒士方喜出望外。鄒士方回憶說:“有一次在全國政協禮堂,梁老同我談美學大師宗白華,說他們相識。我說宗先生是我的老師。由此我與梁老的關系又進了一步。”
1986年,在梁漱溟家中,鄒士方為這位國學大師拍攝了一張黑白照片:梁老臨窗而坐,背后是層層垂拂的吊蘭。他神情嚴肅,目光深邃,雙眉緊鎖,嘴巴緊閉,有種“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般特立獨行的風范。彼時的梁漱溟已是九十三歲高齡,他“猶自帶銅聲”的風骨和強大的精神氣場,都在這張照片上精妙地傳遞出來了。
多次走進三松堂,聆聽馮友蘭的妙論
1978年鄒士方進北大時,馮友蘭已經不再講課。鄒士方有時在未名湖畔遇見馮友蘭先生,眼神就熱烈地追逐著他,直到馮先生在視線中消失。鄒士方時常感到惆悵,如果不能拜訪馮先生,自己在北大的求學生涯就一定會留下遺憾。
機會來了,在同窗好友楊利川的安排下,1980年5月的一個下午,鄒士方一行八名同學到燕南園三松堂拜訪了馮友蘭先生。第一次拜訪,鄒士方就幸運地拍下了馮友蘭罕見的爽朗大笑的照片。2023年2月初,鄒士方接受筆者采訪時說:“馮友蘭是位哲學大師,我看了他所有的全集和選集中的照片,沒有一張是自然而然笑著的,但是我拍到了他大笑的瞬間,很珍貴。”
照片上的馮友蘭身穿中山裝,坐在沙發上,滿頭銀發,尚未蓄須,但白色的胡楂已顯分明。他戴著黑框眼鏡,雙眼微瞇,右手輕托腮,頭稍抬起,臉上開心的笑定格于瞬間。背景中的書櫥里有一尊白瓷仕女像分外奪目,書櫥上掛著一個小巧的葫蘆,喻示著中國哲學的乾坤。鄒士方與馮友蘭就此結下光影的善緣。之后,他多次走進馮友蘭家中,并為馮友蘭留下許多晚年的珍貴照片。
1983年底,聽聞馮先生雙目視力下降,卻仍用口述的方式繼續寫作《中國哲學史新編》,鄒士方深感欽佩,便同友人相約去看望馮先生。1984年1月的一天,他第二次走進馮友蘭家。打開院門,院中三棵挺拔的青松映入眼簾,老先生正埋首于書山之中。四壁全是書,桌上是各種打開的書,椅子上也摞著一堆書,馮先生皓首窮經,坐擁書城。鄒士方回憶,馮先生雖飽經滄桑,須發皆白,但思維清晰,談興甚濃。
這次拜訪不久前,馮友蘭剛過了八十八歲生日,說起自己的年齡,他娓娓道來:“日本人很會利用漢字,他們稱八十八歲為米壽(米字拆開為八十八),稱九十九歲為白壽(百缺一為九十九),稱一百零八歲為茶壽(茶字上為二十,下為八十,中間是八)。我現在是米壽,要向茶壽邁進。”
馮友蘭興致勃勃地向鄒士方介紹了自己撰寫的兩副對聯。一副是在1983年夏天為金岳霖八十八歲壽辰撰寫的賀壽聯:“豈止于米,相期以茶;論高白馬,道超青牛。”金岳霖是研究邏輯學的,并著有《論道》一書,“白馬”用的是“白馬非馬”的典故,而“青牛”指道家的創始人老子,用的是老子騎青牛過函谷關的典故。另一副是前不久在自己八十八歲生辰時自題的賀壽聯:“豈止于米,相期以茶;心懷四化,意寄三松。”“三松”正是馮友蘭的堂號,他當時剛剛完成了回憶錄《三松堂自序》。
1986年1月20日,鄒士方第三次走進三松堂,為馮友蘭留下一張經典的照片:馮先生留著長長的胡須,低著頭,用一管大號毛筆在一方冊頁上題詞。他背后的墻壁上就掛著那副自題賀壽聯。1987年夏天,鄒士方再次拜訪馮友蘭先生,并為這位哲學大師在家里拍下一張低調的照片。氣定神閑的馮友蘭白發白髯,一襲白衣,在深色背景的襯托下,更顯仙風道骨。
鄒士方拍攝的馮友蘭先生的這些晚年照片,雖只記錄了幾個瞬間,但每每翻閱,鄒士方總是感慨萬千。這位心懷使命的哲人畢生致力于中國哲學的薪火相傳,他站在中西方文明的交匯點,遙襟甫暢,逸興遄飛,這番風骨無數次感染了鄒士方的精神世界。
持張允和介紹信拜訪,為沈從文留下最后的相片
1988年1月28日上午10點,崇文門東大街二十二樓六○一號響起了清脆的敲門聲,滿頭銀發的張兆和輕輕地打開門,露出不大的縫隙。門外是一張期待的笑臉,來客胸前掛著一臺照相機,說:“我叫鄒士方,這是張允和老師寫的介紹信……”張兆和接過介紹信快速地看了看,抬起頭。“您是鄒記者啊,快快請進。”張兆和笑意盈盈地說,隨手一推,大門敞開了。鄒士方看著門上貼著“謝絕來訪”的字條,感到能夠登門拜訪沈從文先生,自己實在是幸運。
鄒士方與沈從文先生結緣,源于巴金先生的北京之行。1985年3月28日,巴金從上海到北京開會之際,曾到沈家舊居看望老友。鄒士方跟隨巴金,得以親睹沈從文的風采。當時,沈從文因受中風影響,說話已非常困難。自這次見面始,鄒士方便格外關注這位備受讀者喜愛的文學大師,時刻留意他的消息。
1988年初,鄒士方聽聞沈從文已經康復,就萌生了拜訪的念頭。因聽說沈先生一直閉門謝客,于是鄒士方請沈夫人的姐姐、著名昆曲家張允和寫了一封介紹信:
從文二哥、兆和三妹:
鄒士方同志是朱孟實先生的學生,現在是《人民政協報》的記者。前年他曾陪巴金先生到過你們舊居。
鄒同志曾為我們四姊妹寫過《滋蘭九畹" 姐妹情長》。文筆極好!
他要我介紹來慰問從文二哥,想為二哥拍幾張照片,如能談談話更好。希望三妹好好接待。
季方家我可能去不了,近日患小感冒,不想出門。 祝
全家安康!
二姐 允
1988.1.18
進屋后,鄒士方看到沈從文坐在客廳的藤椅上,安詳,從容,面帶笑容,精神頭很好。沈從文記得1985年巴金來看望他那次,也記得一起來的人。他還是三年前的樣子,只是看上去消瘦了不少。“他過去那一陣子不是真胖,是浮腫,現在臉上、身上的浮腫都消除了,所以看起來瘦了。”張兆和說。
簡單交談之后,鄒士方仔細看了看這間客廳。東墻上掛著沈老寫給夫人的一首宋詩,還有一幅黃永玉的作品。南面的書柜里盡是沈老的著作,花費了沈老后半生心血的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放在最顯著的位置,這本書于1981年9月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客廳里還掛有孫女沈紅為他畫的兩幅速寫像,形神兼備。
鄒士方坐在沈老身邊,與沈老聊天。沈從文知道鄒士方在全國政協工作,便問候起舊雨近況,鄒士方一一回應:“最近徐盈住院了,他的夫人子岡剛過世;賀龍元帥的女兒賀捷生從全國政協調走了;俞平伯的女婿易禮容和哲學家賀麟都很好,易老參加政協各方面的活動很積極。”沈從文告訴鄒士方,他的湖南同鄉唐生智的弟弟故去了。沈從文頗有感慨地說:“都老了!”這聲喟嘆,讓鄒士方不由得想起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中的話:“我和我的讀者,都共同將近老去了……”
鄒士方看著沈老紅潤的面容和頭上的銀發,剎那恍惚:沈先生真的老了嗎?他思維敏捷,記憶力超強,提到某個人某本書,都能對答如流。張兆和說:“許多熟人的名字我記不得了,他會脫口而出。某年某月家里來了幾位客人,他都能回憶起他們的名字。尤其是歷史文物方面,他記得更清楚,他的助手遇到疑難來詢問他,他會給以十分準確的答復,甚至有些資料出自哪部書哪一頁,他都記得十分清楚。”
鄒士方提出為沈從文拍攝幾張照片。沈從文以“這么老,這么丑”為由拒絕。鄒士方說:“您不老,很精神;也不丑,有學人的風度。”并解釋說:“我給您照相,不發表,留作資料。”沈從文風趣地說:“那也是丑的資料。”在鄒士方的再三請求下,沈從文終于允許:“那就照側面吧,側面還好。”
鄒士方連忙選好角度,按動了相機的快門。沈從文坐在陽光里,安穩慈祥,臉上有光芒,眼里有神采。拍完照,有訪客到來,鄒士方就起身告辭了。三個多月后,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去世。
照片沖洗出來,鄒士方發現有一張黑白照頗具神韻。深色的背景里是整齊排列著的沈老的著作和他的藏書,那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清晰可見。幾縷陽光投射在沈老身上、手上、座椅上,黑白交錯,凹凸有致。一束陽光恰好照亮了沈老大部分臉龐,小部分的陰影使照片里的人物有了如同雕塑的立體感。沈老沉靜,淡定,眼神中透露出獨立和自信。鄒士方說,這是他最為滿意的攝影作品之一,也應是沈從文先生在人間的最后留影。此后每當想起沈從文先生,他總會翻看這張照片。
鄒士方的攝影,留下的不只是大師們的珍貴瞬間。這些光影,也承載和記錄著鄒士方求知若渴的青春和生命中那些珍貴的交集。或風云際會,或善緣巧合,或翰墨因緣,鄒士方敲開了一扇又一扇大師家的門,這些交往深深地影響了鄒士方的人生之路。他一生寫作、繪畫、攝影,在美學之路上不斷采擷。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他用對美的理解,用光影的藝術留住了大師們的神采,也留住了一個時代的風韻。“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鄒士方再次翻閱攝影集,流年碎影緩緩移動……
(責任編輯/張靜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