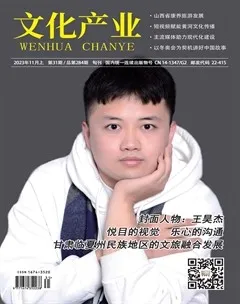二程開創儒學新形態
宋朝統治者在尊孔崇儒的同時還大力提倡信奉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了“儒、釋、道”三教合流的社會思潮。二程(程顥、程頤)的理學思想是以繼承孔子和孟子的儒家道統為己任,在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礎上,批判性地吸收佛、道的某些思想,在隋唐以來儒、釋、道思想融合的形勢下建立起來的一種理論體系。二程的理學思想可以說是先秦孔孟儒學發展的新形態,后人稱其為“新儒學”。現討論二程的理學思想,總結其對儒學發展作出的貢獻。
程顥、程頤是宋明理學的奠基者,也是洛學派的創始人。理學作為一種社會思潮,與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相關聯。然而,程顥、程頤的思想觀念有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程顥主張“心是理,理是心”,而程頤則主張“有理則有氣”。二程的理學思想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是理念基本一致。在政治思想方面,二程認為應當以民為本,保民、重民、愛民,秉持“格君心之非”的思想。在經濟思想方面,二程提出要以農為本,足食備災。在教育思想方面,二程認為應當明理修德,注重崇高道德信念的培養。二程的學說不但對后來的理學、心學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影響了朝鮮和日本的儒學。
二程的生平
程顥,字伯淳,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卒于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被世人稱為“明道先生”。程頤,字正叔,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卒于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世稱伊川先生。根據史料記載,程顥、程頤都出生于其父程珦任黃陂縣(今湖北省黃陂縣)縣尉時。二程童年和少年時期跟隨父親奔波輾轉,在十五六歲的時候,遵從父親的意愿,跟隨周敦頤學習。根據史料記載,宋仁宗慶歷四年(1044),周敦頤任南安軍(今江西大庾縣和南康縣)的司理參軍。宋仁宗慶歷六年(1046),二程的父親程珦(時任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在代理南安軍副職務時認識了周敦頤,“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為學知道者,因與為友”。程頤在《明道先生行狀》中寫道:“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后得之。”張載先生說:“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圣人。”可以看出,程顥、程頤的求學之路十分復雜和曲折。二程在接受孔子、孟子的儒學思想的同時對當時的詞章訓詁之類的學問并不滿意,他們一直在努力尋找新的道路,后來接受了佛、道的某些思想,融會貫通,經過改造創立了新思想體系。之后,程顥、程頤開創伊洛學派,形成理學,最終實現了他們的宏愿。
二程對儒學的新發展
“理”
“理”的本義做名詞,意為玉石中的紋理;做動詞,意為治玉——甄選、拋光玉材。后引申為,做名詞,意為原理、原則;做動詞,意為治理。二程認為不需要過于限定“理”的詞義,而在一些著作中,與二程的“理”較為一致的定義也有許多。朱熹在《大學或問》中寫道:“至于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通過“所以然之故”和“所當然之則”解釋“理”的含義,這與程顥、程頤對“理”的解釋是一致的。《河南程氏遺書》中記載:“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間皆是理。”“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上,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粹言》記載:“窮物理者,窮其所以然也。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顯,必有所以然者。”《論語》寫道:“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作為自然原則的“理”與作為倫理道德原則的“理”之間沒有實質性區別。
“理”通常和“推”或“類”字相聯系。若是將自然的“理”或者倫理道德的“理”適用在某種事物上,我們便可以通過“推類”或者“推理”的方法,將“理”適用在與某種事物同類的其他事物上。由此可以看出,一理可以貫穿萬物,萬理都是一理。《河南程氏遺書》寫道:“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何,窮理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二程的創新之處在于他們認為“萬理歸于一理”。
“命”
二程把“理”升至原來的“天”的位置。“天”和“命”在過去象征著那些被客觀地給定,獨立于人的行為和愿望之外的東西。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對于程頤而言,這只是“理”的一個側面,人們必須遵循的“理”是“自然”之事,不能被隨意編造以適應自身需要。當強調這一側面時,“理”即“天”,由此還得到“理”的輔助術語“命”。《河南程氏遺書》寫道:“曰‘天’者,自然之理也。”“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理”經常被限定為“天理”。程頤闡釋上文所引用的孟子語錄時說:“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
程頤相信若有一物必有一理,若無此理斷無此物。程頤接受“莫非命也”的觀點,抵制張載的“機遇”論。《河南程氏遺書》寫道:“問:‘命與遇何異?’張橫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先生曰:‘人遇不遇,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為相而餓,或先貴后賤,或先賤后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對于程頤來說,“理”既是自然的,又是倫理道德的。一株植物春榮秋衰,很自然地被認為和父慈子孝一樣都在遵循著“理”。這個假定導致了思辨論說上的困難。這一點在程頤探討“命”時表現得較為明顯,他曾說:“行善是循理,而舉止失當也是循理。循理而自毀其族的楊食我,又有何錯?”
“氣”
“氣”以往被認為是自我運動的。二程把形歸于某種精神上的存在,如孟子的“浩然之氣”被認為是有“形體”,以及有“形象”的。《河南程氏遺書》寫道:“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跡,然亦盡有形象。”由于理在一切事物中都一樣,人與人之間的所有差別都是由于他們“氣”的組成不同。風格、風度、神態等都是人的“氣質”之顯示,是氣的外在表象——“氣象”。《河南程氏遺書》記載:“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個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事物相互作用的方式體現在各個層次上,從陰陽二氣到永不停止進行氣聚氣散的“萬物”,都可以用“感”和“應”加以解釋。《河南程氏遺書》寫道:“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易傳》記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陰氣回應陽氣,反過來又刺激陽氣,在天地之間,擴張與收縮、運動與靜止、明亮與黑暗、熱與冷反復交替生生不息。“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于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河南程氏遺書》)
“性”
學者們常常分析“人性”這一思辨難題,寫下許多評論孟子的性善說、荀子的性惡說和楊雄的性善惡混說的文章。人與一切事物一樣,由“氣”組成,循“理”。人的內心存在與生俱來不學即會的五常(仁、義、禮、智、信)之理。與此同時,人生來還具有“天賦之氣”,它決定了天生的人格特點。既然“道德之常”與“天賦之氣”都是與生俱來的,所以“性”一直被毫無區別地用于這兩者之中。“天命之謂性”,指的是“性之本”,當然為善;但是“生之謂性”以及孔子的教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很明顯指的是“氣”,其可能為善,也可能為惡。而二程認為:“‘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概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性”最初“居中”,受外物的作用便釋放出“情”,“情”應該與外部的形勢相協調。“性”是體,“情”是用,兩者的關系如同水與波的關系。《河南程氏遺書》記載:“‘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程頤認為,中是“性”的特點而不是“性”本身。由于缺乏任何描述特性和狀態的術語,這迫使他用了許多筆墨來闡述這個論點,“只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
“心”
“心”通常用來表示心臟,古代學者認為精神活動是在心里而不是在大腦里進行。孟子說有一顆“不動心”時,并沒有在思緒紛亂與實際心悸之間劃出清晰的界限。到了宋代,“心”已經被有意識地賦予了兩個意義:一個是作為身體的器官心臟;另一個是作為存在于心中的某種東西,能控制身體運動,是“知”中的能動者。精神活動被設想為“用”,它隨著外物對內在的“體”的刺激而變化。
二程認為,“性”和“心”是“理”的兩個不同側面。當需要強調道德之“理”與生俱來,此命天授,不論是否喜歡它,它都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時,“理”被稱為“性”;當需要強調“理”控制著身體時,“理”又被稱為“心”。這種“心”與“理”同一的觀點暗示二程并不把“心”視為“知之器官”,這是因為“知”與“心”所知的東西存在區別。
程頤認為歸于“心”的唯一活動是對“理”的直接洞察。對于圣人來說,這種洞察會立即發生;而對于一般人來說,其與思維過程不同,通常是循序漸進的。《河南程氏文集》寫道:“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與思不同,對“理”的洞察并不意味著動,因為一物之理已在心中,“‘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于此也”(《河南程氏遺書》)。慈孝之“理”,在父與子中,也在“心”中。當“心”洞察此“理”時,“心”不須動,因為此“理”已在心中。這是程頤把理氣觀應用于傳統儒家思想時所遇困難的例證。在實際應用中,程頤不得不將情、意、思包含在“心”這個詞內,使它與普通用法一致。程頤用儒家經典《尚書》中的一句話為之辯解,這句話把“人心”與“道心”加以區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體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
程顥、程頤將經學史上宋學的重要內容歸結為以“義”理解“經”的經學思想,這些都對后來經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二程不受制于舊的注疏,大膽創新,站在時代發展前沿,用自己的理解解讀經典,批評漢唐經學,闡發義理,在創新和發展儒家、經學的同時發展了宋代理學。二程的思想在中國經學史和宋明理學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作者單位:中州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