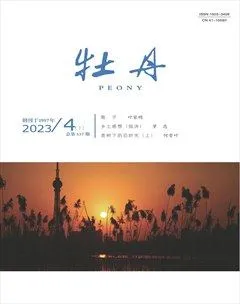論《恨海》中的現代性
吳趼人是晚清小說界的巨子,其小說創作不僅產量豐厚,更是有著極高的藝術價值。《恨海》是吳趼人寫情類小說的開篇之作,建立在“庚子事變”的時代背景下,描寫了當時年輕人情感世界的同時,描摹了一幅晚清政治、社會生活畫卷。本文從《恨海》文本出發,結合時代背景,著重分析小說文本中的人物進而延伸到小說主題及小說創作本身,三個層面層層遞進,探究《恨海》中的現代性,進而描摹作家的創作意圖及其超越時代的思想面貌。
一、緒論
吳趼人生于1866年,卒于辛亥革命爆發的前一年1910年,在其短短四十余年的生命歷程中,可以說他目睹了清朝的整體衰敗過程。同時,吳趼人的先輩大都有過在朝為官的經歷,其曾祖父曾經當過湖南的巡撫及湖廣總督,他的祖父也出任過工部員外郎。之后家族的仕途之路逐漸沒落,其父親只擔任了小小的浙江候補巡檢,但這樣的出生背景也使其能夠切真目睹了晚清的官員階層及富人階層的社會政治生活,再加上家道中落,困苦的少年到青年的經歷,都加深了吳趼人對于窮苦人民生活的體驗與理解。可以說,少年時期的四海漂泊與先輩的為官經歷,讓吳趼人擁有了超出常人的敏銳感知,對于世態炎涼與人情冷暖都有著屬于自己的一套判斷體系。擁有這樣的人生經歷,并且面對著晚清政權的內外風雨交加、搖搖欲墜,以及國家山河破碎、戰亂紛飛,整體社會動蕩不安的時代背景下,吳趼人的小說中體現出現代性既是時代的必然性體現,也是作家融入時代同時超越時代的天才創作的整體顯現。
在此基礎上,吳趼人在小說中自我觀點的抒發,也為研究其小說現代性提供了合理的思路,并具有了一定的闡釋合理性。吳趼人本人生性剛烈,狂放不羈,不愿與權貴相交,這種性格其實與他對于情與倫理道德的復雜關系的理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吳趼人看來,正是“情”才支撐起了人類社會的倫理道德體系,在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其反復闡釋著一種正是當代人鮮廉寡恥、不怕難為情才導致社會道德倫理淪喪的現狀,而正是因其多愁善感,有大部分人不所有的“情”,才能不趨于權貴,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無獨有偶,在小說《恨海》中,吳趼人特意強調了自己對于“情”的獨特理解,而這也體現了吳趼人對于傳統小說中情愛主題的超越。
我說那與生俱來的情,是說先天種在心里,將來長大,沒有一處用不著這個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罷了——對于君國施展起來便是忠,對于父母施展起來便是孝,對于子女施展起來便是慈,對于朋友施展起來便是義。可見忠孝大節,無不是從情字出來的。至于那兒女之情,只可叫做癡。更有那不必用情,不應用情,他卻浪用其情的,那個只可叫做魔。
在作者的自批中,更是直接認為“《紅樓》《西廂》一齊抹盡”,不難看出,單就“情”論而言,《恨海》便擁有相較于傳統小說對情愛主題的超越性,在此之外,《恨海》所體現出來的現代性,更是可以從小說中的人物、主題、創作本身進行綜合討論。
二、現代性的人物
《恨海》中出現了多個人物,而在這些占據小說篇幅或多或少的人物身上,均不同程度體現了《恨海》的現代性特征。張棣華作為小說中占據篇幅最多的女主人公,似乎一直是傳統女性,是遭受封建道德壓抑的代表。縱然吳趼人自己有著對“情”的獨特理解,但吳趼人的“情”理論面對封建禮教系統下的傳統價值觀與道德基準,并不能完全體現出超越性,這是因其本人無法超脫封建社會傳統的忠孝慈義倫理體系,從而使其“情”理論帶有局限性。同樣,從張棣華貫穿整部小說的行為來看,她也確實是被壓迫的傳統女性的代表。
“鶴亭自從搬開之后,棣華便不讀書,只跟著白氏學做女紅,慢慢地便把讀過的《女誡》、《女孝經》都丟荒了,只記得個大意,把詞句都忘了。”這一段文字可以說是張棣華女性命運遭受傳統封建道德壓迫的集中體現。第一,理所當然地便接受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安心于自己的命運。第二,按照古代的習俗,丟掉了文字學習的可能,回歸到“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狀態。第三,更為可悲的是,就算是之前所學習的,也是充滿壓迫意味的《女誡》和《女孝經》。
王棣華同時也展示矛盾性的一面,這種矛盾也正是表現其現代性同時可以輻射《恨海》全書的集中體現。在張伯和和王棣華母女逃出京都的過程中,一方面王棣華囿于傳統觀念,處處掣肘,與此同時,王棣華的內心是早已認定張伯和是自己的丈夫,隱晦地表現出其實自己是想于張伯和共處一室的。可以說,在王棣華身上,既能體現出傳統禮教、儒家思想下的女性受到的壓迫,也展現了女性自我本身對于平權的渴望,以及對于追求愛情欲望的渴求。
《恨海》中的車夫看似是以負面形象存在于小說的進程中,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貪財無義的馬車夫,卻代表著晚清的“理性”形象。原本土生土長的馬車夫,卻在特殊時代的社會環境下,誕生出了與接受過外國文化的上流社會人士一般的形式觀念與道德準則。小說中的馬車夫,一方面對著路費坐地起價,另一方面對自己的命運有著清醒的認知。
“伯和叫套車,忽然兩個車夫之中,有一個說:‘不去了!……大師兄便不怕槍炮,咱們可不行。我不能為了賺幾兩銀子,去陪你們做炮灰。’”馬車夫雖然對大師兄的神功充滿著迷信與誤解,但對于自身的認知卻是十分清晰,他知道自身是為了賺幾兩銀子的勞動人民,而不是擁有神兵神火的大師兄。另一位車夫則更加清醒地認識到,越是在兵荒馬亂的年代,越是要維護自身利益,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坐地起價。馬車夫可以說是吳趼人刻意塑造的丑角,但其實卻是時代的代表,他們既代表著統治階級碾壓下的窮苦人民為了生活市儈逐利的一面,也體現著在時代浪潮下對傳統道德觀念的解構。只有這樣品性的車夫才能夠存活下去,而這正是馬車夫身上的現代性體現。
與之相對應的旅店老者的出場,更是在體現了人民雖置身于狂風暴雨中,但也不乏當代的理性精神。小說第二回:“老者搖頭道:‘這是一班小孩子瞎鬧,怕不鬧出個大亂子出來?”對于現代的理性的人來說,戰爭無論正義與否,給民眾帶來的只有破壞與打擊,這既是老者身上體現的現代性,更是吳趼人借老者之口所要抒發的觀點。
三、現代性的主題與創作
如果說《恨海》中有許多體現著現代性的人物,那么回到小說本身,其主題與創作形式也表現出現代性特質。
其一,關于《恨海》小說的主題,體現了吳趼人小說中具有傳統的一面和現代的一面。首先,《恨海》開宗明義,就預示著其在主題上的創新。在傳統的涉及情愛的小說中,所敘所要表現的情往往都是男歡女愛、醉生夢死的男女之情,至于父女母子、君王人臣乃至兄弟袍澤之情,往往會以孝、忠、義等詞語具象化。而在《恨海》中,吳趼人雖然以“情”為主題,卻擺脫了傳統情愛小說的束縛,不僅僅在定義上解構了“情”,更是在具體的敘述中將“情”在不同語境下的具體表現進行抽象統一,建立了屬于自己的“情觀”。在寫“情”這一主題上,吳趼人更是根據自己對于“情”的獨特理解,豐富了主人公的形象。
在吳趼人看來,張伯和與王棣華的情早已不是單純的男女私情。因為時代社會背景的緣故,他們之間的“情”早已不再是男女之間的兒女私情,而是面對國破家亡時對自身“情”的使用與變形,這種對“情”的變形并將個人情感置于整體社會中的創作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二人的悲劇命運。如果說小說中具有正面形象的王棣華與張伯和代表著“孝女節婦與孝子義夫典型”,那么作者這種以“情”企圖“改良社會風氣,拯救世道人心”的嘗試的必然失敗,既是一種主題的創新,更是理性與自我意愿的矛盾產生的現代性體現。
其二,《恨海》中的大量心理描寫,掙脫了傳統小說的束縛,并且在語言技巧方面體現出革新的一面。相較于對小說人物內心的關注,我國的傳統小說更注重白描,并且擅長使用大量細節描寫來塑造人物,更是通過對主要人物相關的外在形象特點來刻畫人物特點,如孫悟空的尖嘴猴腮、林黛玉的蹙眉、關公的紅臉與長髯。《恨海》在小說創作中,尤其是對王棣華的塑造,運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寫,通過這種心理描寫,結合前文對于王棣華人物現代性的分析,王棣華的人物形象變得更加立體與豐滿,其人物的矛盾性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在小說中,對于王棣華在蓋了伯和被子后的心理描寫,更是將其人物的矛盾性以及其所代表的傳統女性表現了出來。她既被舊秩序傳統道德約束,但同時自身的女性意識覺醒,渴望愛情,直面內心欲望。
這一夜,棣華蓋了伯和的被褥,突然間又犯起了情癡,……只想著今后如何和他相敬如賓,恩愛有加。她想起在村店的伯和如此溫柔體貼,兩人又共同經歷了磨難,奢望著今后得到他的溫存。
除卻心理描寫之外,《恨海》的語言也體現著現代性的一面。晚清時期,面對西方傳教士宣傳思想的外在壓力,以及新聞稿件報道時事的需求,長期從事報刊媒體工作的吳趼人在《恨海》的創作中大膽創新,使用了相當多的白話文技巧,將勞動人民的日常語言運用到了小說創作的過程中。作家對于通俗文字的使用,更是時代變革下文學發展的一種體現,一種現代性的變革蘊藏在小說的語言
之中。
其三,《恨海》中的敘事方式,體現了小說的現代性變革。在小說的敘事視角上,中國的傳統小說敘事往往是全知全能的視角,如《水滸傳》《西游記》中的敘事視角,往往使讀者能夠在閱讀單一故事線條的同時觀察到其余敘事進程的發展。而在《恨海》中,王棣華與張伯和在被毛子兵沖散之后,兩條敘事線就完全分開,從開端之后再也沒有重合,直至最后的悲劇結尾,二人見面才匯合在一起。除此之外,《恨海》的敘事摒棄了傳統小說敘事對于人物點評的過程,一步步走向墮落的張伯和,代表著忠貞美好的王棣華,“守身如玉”的張仲藹,淪為妓女的王娟娟,不同于《紅樓夢》中對各個主要人物的判詞預示,或者《水滸傳》通過穿插在文本中的詩詞對人物進行整體評判,《恨海》對人物的道德評判幾乎沒有,雖然也不乏文本中的“批語”式評論,但總體上來說全書議論性的文字極少,用筆極為克制。
四、結語
總的來說,《恨海》從來都不是一部止于“情”的演繹與書寫的小說,其創作背景的復雜以及時代背景的特質賦予了其廣闊的解讀空間,現代性在其文本上的體現,除卻人物的塑造與小說主題與創作本身外,還有許多方面有待挖掘探究。作者的特殊經歷及其對于時代的洞察,使得《恨海》在表現時代特征的同時,體現出一定的現代性特質。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