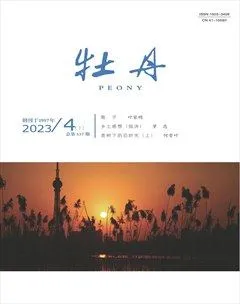論李白身上的貴族精神與俠義精神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存在著以規(guī)則精神、非凡的風(fēng)度、超脫的靈魂、悲憫之心、極高的社會責(zé)任感和進(jìn)取精神為代表的貴族精神。而隨著帝制的出現(xiàn),貴族階級消失,貴族精神逐漸與其分離并獨(dú)立發(fā)展。經(jīng)過周朝的氏族貴族時代、南北朝的門閥貴族時代,現(xiàn)在貴族精神的紐帶傳到了唐代文人的手上,最具代表的便是“繡口一吐,便是半個盛唐”的李白。很多人都會感到疑惑:李白?不就是一浪蕩公子,怎么能夠稱得上貴族?其實(shí)不然,按貴族精神論,李白的詩歌完美體現(xiàn)了超脫的精神、悲憫之心和憂國憂民的社會責(zé)任感。而按貴族論,李白未必就不是一個貴族。
自古關(guān)于李白的身世研究眾說紛紜,但大多數(shù)學(xué)者都是支持宗室說的,其中有一脈的說法筆者覺得很有意思,就是徐本立《李白為李淵五世孫考》一文認(rèn)為李白應(yīng)為涼武昭王十二世孫、太祖李虎七世孫、高祖李淵五世孫、太子建成玄孫。李白曾在《與韓荊州書》中說“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指明自己祖籍在甘肅隴西,而唐太宗李世民的祖籍亦為甘肅隴西,二人同一出身、同一姓氏,為何李白是“布衣”,李世民就是“太宗”?李白族叔李陽冰在《草堂集序》中是這樣記載的:“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jì)人,涼武昭王李暠九世孫。”這前后矛盾的身世,只能說明李白出于某種原因不得不隱瞞自己的身份。而后逢開元盛世天下大赦,李白一家遷入西蜀,即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蓮鎮(zhèn)。所以李白自小接受貴族式教育,其父李客對李白要求尤為嚴(yán)格。為了讓李白重振家族,從小就督促李白學(xué)習(xí)“五經(jīng)”、《論語》,通習(xí)六甲;后來又讓他在大匡山拜師學(xué)藝,向趙蕤學(xué)習(xí)縱橫之術(shù),由此貴族精神在李白的心中逐漸形成并走向成熟。
一、李白的貴族精神
李白的身世為其擁有貴族精神提供了一定依據(jù),即便貴族說最終證明不合事實(shí),也不能否定李白具有貴族精神。自春秋戰(zhàn)國以后,貴族階級被封建帝制壓迫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貴族精神與貴族階級也在這個過程當(dāng)中逐漸分離,貴族精神變得并非貴族出身者所特有,平民也可以培養(yǎng)并擁有貴族精神,權(quán)貴者也未必?fù)碛匈F族精神。下面從三方面簡述李白身上所體現(xiàn)出來的貴族精神。
(一)社會責(zé)任感與規(guī)則意識
貴族作為一個擁有高貴品質(zhì)的階層,但凡國家陷入戰(zhàn)亂,首先受到?jīng)_擊的便是貴族階級。例如《戰(zhàn)爭與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他在國家危難之時挺身而出,參加了俄羅斯抵抗法國拿破侖侵略的戰(zhàn)爭。無論是為了自身還是國家,他們身上都透露出一種責(zé)任感。貴族象征著國家的特權(quán),亦代表著他們?yōu)檫@個國家承擔(dān)著最大、最直接的責(zé)任。隨著貴族階級的消失,這種精神獨(dú)立出來變成了古代文人的思想脊柱之一——憂國憂民的意識。無論是子路“君子死而冠不免”的追求、項(xiàng)羽血灑烏江的氣概,還是被評價為“蠢豬式的仁義道德”的宋襄公,從他們所體現(xiàn)出來的貴族精神中的規(guī)則意識可以看出貴族視榮譽(yù)和尊嚴(yán)高于得失成敗。這樣的規(guī)則意識在后世主要體現(xiàn)為對群體的秩序,即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追求,而憂國憂民又是針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會現(xiàn)象的批判。也就是說,在后世這兩種精神特質(zhì)實(shí)現(xiàn)了融合。
李白的《古風(fēng)》是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為基礎(chǔ)的刺世、諷世之作。例如《古風(fēng)·其三》,“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借批判始皇帝的功過來類比玄宗皇帝,批評玄宗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徐巿載秦女,樓船幾時回?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又寫其沉迷于道教的煉丹長生之法而遲于國政。《資治通鑒》載:“(玄宗)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即言此舉貽害國家。又如《古風(fēng)·其十五》,“奈何青云士,棄我如塵埃”批玄宗不若昔時燕昭王禮遇下士而對其棄之如塵,“珠玉買歌笑,糟糠養(yǎng)賢才”。但是很多人只看到了李白靈氣四溢的游仙詩,沉醉于“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的美好,卻不見李白“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盡冠纓”的憂心,這其實(shí)是對李白的一種誤讀。
(二)悲憫之心與民本情懷
貴族作為社會的精英階層,要對社會提供一種公共服務(wù),能夠“俯身下去”,有關(guān)懷和同情弱者群體并保護(hù)他們的責(zé)任。在李白的詩歌中,這種悲憫之心集中以民本情懷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
李白有對蒼生苦難的無限同情。安史之亂中,生靈涂炭,國家在叛軍的鐵蹄下瀕于覆亡,人民在胡人的屠戮下呻吟掙扎。面對兇殘的豺狼和血腥的現(xiàn)實(shí),李白控訴了不合理的社會現(xiàn)實(shí),如借《扶風(fēng)豪士歌》中的“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嗟嘆戰(zhàn)爭的殘酷,或是借《豫章行》中的“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感慨親人因戰(zhàn)爭而分離的悲痛。
李白有對平民百姓最深刻而真摯的情感。且見那首《宿五松山下荀媼家》,開頭兩句“我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指進(jìn)入荀家后見到凄涼家境陡然產(chǎn)生的憂郁感。祖國的河山是如此美好,按理說,生息在這塊大好河山上的人民應(yīng)該是富足的,實(shí)際上人民的生活十分艱難困頓。這種巨大的反差引起了詩人心靈的震顫。而第三句為什么不言“荀家”而言“田家”,說明詩人此次出訪并非只經(jīng)此處,而是沿途見過很多辛苦勞作的農(nóng)民,“田家”一詞具有深廣的概括性。一年四季中唯秋收是最令人喜悅的,而現(xiàn)在的秋作卻讓人苦不堪言。加之與“鄰女夜舂寒”互文可知,此地男丁恐因戰(zhàn)爭緣故多奔赴戰(zhàn)場,繁雜的農(nóng)活都壓在了女性的身上。“跪進(jìn)雕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餐。”表達(dá)了荀氏老婦對李白誠摯的款待和李白對她真摯的感激之情,以及對自己不能為這些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百姓做些什么的慚愧。
世人皆言李白“當(dāng)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于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系其心膂”,卻不知其亦有杜甫“沉郁頓挫”的“詩史之風(fēng)”以及對百姓無限的同情。
(三)超脫的人生情懷與追求
李白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曾言:“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shù)。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qū)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后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李白將人生分為了兩步走:第一步建功立業(yè),第二步功成身退與自然為伴。李白的身上實(shí)現(xiàn)了匡扶王室的社會責(zé)任感和超越精神的統(tǒng)一。其中第二步最能體現(xiàn)李白超脫的人生情懷與追求。
李白的超脫性與“魏晉風(fēng)度”對人生有系統(tǒng)的反思有關(guān),追求天地之大美(即“道”),以求獲得審美感受的最高境界“超感體驗(yàn)”,主張順應(yīng)自然“無為而無不為”,以“滌蕩玄機(jī)”來把握“道”。以哲理的審美態(tài)度去感悟自然、體悟人生,對李白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如敢于“非湯武而薄周禮”的政治工作態(tài)度,李白在《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中直呼“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又如醉心其中山水,超脫人世情趣和天馬行空的智慧天才在李白《古風(fēng)》中的游仙詩也尚留余韻。例如《古風(fēng)·其五》中“中有綠發(fā)翁,披云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的神秘自在形象,又如《古風(fēng)·其七》中形容安期生“仙人綠云上,自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當(dāng)然也有唯美的女仙人形象,如《古風(fēng)·其十九》中的“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霓裳曳廣帶,飄拂升天行”。
這些逍遙的仙人形象中自然也包括李白他自己,主要以一種努力求仙學(xué)道的形象呈現(xiàn)出來,如《古風(fēng)·其四》中“藥物秘海岳,采鉛青溪濱。時登大樓山,舉首望仙真”。又如《古風(fēng)·其十七》寫李白自己仰慕神仙,后悔沒在盛年時修煉:“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我愿從之游,未去發(fā)已白。”
二、李白的俠義精神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金庸小說中體現(xiàn)出的俠義精神或亦可作為“貴族精神”的分支,這種自在逍遙的俠義精神的形容或許更適合李白。李白生在胡地,身體里原本流淌著胡人的血液,加上他幼年時長居巴蜀,當(dāng)?shù)氐貏萜D險、民風(fēng)豪放,不僅使得他詩風(fēng)雄奇壯美,而且促進(jìn)了他俠義精神的形成。李白的父親平日過著逍遙的生活,與當(dāng)?shù)氐拿撕图澥拷Y(jié)交,除了教李白和其他孩子閱讀,他還花了更多的時間和朋友下棋,比槍和劍,談?wù)撛姼韬蜁@畎鬃孕《δ咳荆罱K也成了日散千金(“曩昔東游維揚(yáng),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jì)之”)、喜好劍術(shù)、武藝高強(qiáng)(“十五好劍術(shù),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的俠士。李白在《古風(fēng)》中也透露了他喜俠的一面,如《古風(fēng)·其十六》將皇上和自己比為干將莫邪:“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沖。”感嘆無人像風(fēng)胡子一般識劍舉薦自己,“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風(fēng)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但是仍抱著與皇上風(fēng)云際會,即“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dāng)逢”的理想。
從李白飲酒時的儀表和舉止也可以看出,李白更像是一位放蕩不羈的俠士。所謂“曾令龍巾拭吐,御手調(diào)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又如杜工部曾如此形容李白:“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種不拘小節(jié)的風(fēng)格,又反過來可以證明李白更符合灑脫自在的俠義精神。
若不論其在儀表上的“不檢點(diǎn)”,李白還有一處很符合俠義精神的特征,那就是好打抱不平和武功高強(qiáng)。李白在《贈從兄襄陽少府皓》中說自己“托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在寫給好朋友陸調(diào)的一首詩中曾經(jīng)談到自己和“黑社會”打架,但寡不敵眾漸漸敗了下風(fēng),最終還是在陸調(diào)的幫助下才成功脫困,即“我昔斗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呵嚇來煎熬。君開萬叢人,鞍馬皆辟易。告急清憲臺,脫余北門厄”。《與韓荊州書中》曾有一句“十五好劍術(shù),遍干諸侯”,李白自小練劍,劍法理應(yīng)不凡,那么他厲害到什么程度呢?《俠客行》中有記載: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人家曹丕七步成詩,我李白比他厲害,我十步可以殺一個人還不留行蹤。這就體現(xiàn)了李白的劍法武藝十分高強(qiáng),甚至勝過了曹子建在文學(xué)上的才能。
李白的友人之愛可不止于此,再看看那首《酬殷明佐見贈五云裘歌》。眾所周知,李白是相當(dāng)喜歡謝朓的,有詩云“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fā)”,以謝朓清新秀發(fā)的詩風(fēng)自比,這首詩更是直言不諱表達(dá)了其對謝朓兄的喜歡,謂之“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fēng)颯颯吹飛雨”,可以說謝朓就是李白的偶像。而李白卻愿意把自己的朋友說成是自己偶像的后繼者,這是很不容易的事。而且李白還大夸特夸朋友贈給自己的衣服,謂其有著“粉圖珍裘五云色,曄如晴天散彩虹”的刺繡,又有“輕如松花落金粉,濃似苔錦含碧滋。遠(yuǎn)山積翠橫海島,殘霞飛丹映江草”的圖案。更夸張的是,如果讓謝靈運(yùn)看到這件衣服,都會誤以為看到了奇山異水而詩興大發(fā),難道李白對朋友還不夠意思嗎?
三、結(jié)語
李白身上的貴族精神主要體現(xiàn)在社會責(zé)任感與規(guī)則意識、悲憫之心與民本情懷和超脫的人生情懷與追求上,且其貴族血統(tǒng)更強(qiáng)化了此說的合理性。但若考慮其性格和行事風(fēng)格,或許將其概括為俠義精神(作為貴族精神的分支)更為合適。
(湘潭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學(xué)院)
作者簡介:林柏豪(2002—),男,福建漳州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yàn)楣糯膶W(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