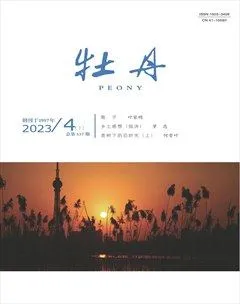沖破生命的桎梏
“我所有的奮斗,我多年來的學習,一直為了讓自己得到這樣一種特權:見證和體驗超越父親所給予我的更多的真理,并用這些真理構建我自己的思想。”美國當代女作家塔拉·韋斯特佛在其自傳體小說《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中這樣講述自己早年遭遇及奮斗歷程。該書作為塔拉的自傳體小說,一上市便熱銷全美。作者在人生的前17年從未上過學,17歲那年通過自學考試考入楊百翰大學,后來通過不斷學習深造取得了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也因其自傳體小說于2019年被《時代周刊》評為“年度影響人物”。本文通過細讀《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并結合波伏娃的女性主義相關觀點、福柯的“監獄”隱喻,進一步探析塔拉的自我救贖和重塑之路,以期啟迪和鼓舞年輕一代。
一、“他者”的桎梏——夫權和父權的枷鎖
出生在一個極度封閉和壓抑的家庭里,塔拉從小面對的是亙古不變的巴克峰、雜亂不堪的廢料廠,以及暴躁陰郁的父親和軟弱無知的母親。在7歲的塔拉心中,自己最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從來不用上學。筆者很難想象,在全球經濟最為發達的美國,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塔拉竟然沒有合法的身份登記,無法接受正規系統的學校教育,甚至從不去醫院治療。這一切旁人看來匪夷所思的事情卻成為小塔拉的生活日常。塔拉的父親吉恩像一個激進偏執的統治者,安排部署著全家人隨時做好與政府戰斗或隨時末日逃亡的準備。在父親吉恩反科學、反現代化的思想浸潤中,一家人都活在對末日的恐懼之中。而吉恩所代表的父權和夫權所營造的恐懼就像一所監獄一般,沉沉地壓在母親法耶和七個孩子身上。在全家人出行遭遇的那次車禍之中,坐在副駕駛的母親法耶頭部受到重創意識模糊,頑固的父親吉恩沒有第一時間將其送進醫院,而是送回家里幽暗的地下室里休養。因為父親吉恩認定醫生無能為力,只有上帝能夠決定母親法耶是生是死。此刻,父親的指令仿佛上帝的旨意,決定著母親的生死。
與其說父親是偏執頑固的信徒,不如說他是傳統夫權和父權的縮影。吉恩是一家之主,他認為妻子和子女就應該按照他的方式去生活。在父親吉恩的認知里,“女人的位置在家里”。“正派的女人”穿衣“永遠不能露出腳踝以上的位置”。塔拉則是父親在廢料廠的好幫手,被廢鐵刺傷后不能去醫院,不能去學校讀書,不能走出山區,日復一日復制母親法耶的生活。諸如此類的父權規訓不僅限制了塔拉的肉體自由,更是滲透至小塔拉的精神世界。
法國女性主義著名作家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一書中提出,男性是“主體”和“絕對”,女性則是被環境所左右的異化的人。在自傳中,塔拉從小成長的環境就是巴克峰上以父親這位獨裁者為首慢慢筑起的一所“監獄”,她從未用自己的思想探索過外面的世界,也無權選擇自己的人生。福柯曾在《規訓與懲罰》中對英國著名哲學家邊沁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設計理念進行了哲學思考,進一步提出了“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他認為,“圓形監獄”不僅具有物質形態的權力意義,更有一種形而上的意義。在福柯全景敞視的比喻中,“監視者”是用無孔不入的監視來控制人的身體的:一方面,個體因身體上的受控進而產生思想上的順服;另一方面,個體通過不斷的自我反思對自身進行控制。“圓形監獄中的監視者不僅控制著知識和真理,他們還制定游戲規則決定著權力的執行。對于囚禁在里的人來說,‘監獄’這個符號的存在就是權力本身。”父親吉恩作為家里的一家之主,便成為規則的制定者和權力的執行者,就像“圓形監獄”瞭望塔上的監視者,即便父親并不是時刻盯著塔拉,塔拉頭頂的恐懼也一刻都不曾消失。在奶奶告訴塔拉要帶她逃離巴克峰去亞利桑那州上學的那晚,小小年紀的塔拉在恐懼籠罩中徹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遠遠在山上看著奶奶的車駛離公路后,塔拉安然走向谷倉開始新一天的勞作。小塔拉對上學、對未知、對冒險的渴望被對這具無形卻沉重的“圓形監獄”的恐懼重重壓碎。即便后來塔拉考入楊百翰大學,她的思想也還囚禁在當年那所幽閉的“監獄”中。
母親法耶本可以支持孩子們刻苦自學逃離這一切,但她慢慢也在那所“監獄”的桎梏和規訓的凝視下成為“他者”,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聲音。母親的沉默直接影響著塔拉,而塔拉作為家里的女性,同樣難逃“他者”的厄運。可以說,塔拉前17年的人生因其“他者”身份在家里沒有任何話語權,默默承受著身體和心理的雙重規訓甚至是摧殘,身陷囹圄,毫無自我可言。
二、主體意識的萌芽——打破絕對權力的決心
“‘我要去……去上大……大學。’他說,面容僵硬。”這是泰勒第一次當著全家人的面說他要離開巴克峰。泰勒是塔拉的哥哥,作為家里的第三個孩子,也是第一個走出大山去讀書上大學的孩子。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本自傳的扉頁上,塔拉寫下了“獻給泰勒”四個字,足以見得泰勒的存在以及泰勒的離家對塔拉來說意義之深遠。泰勒也是筆者在書中十分喜歡的一個人物,他從小患有口吃,不善表達,但在日常父親教條主義的思想禁錮和繁重的機械勞動壓迫下,依然能保持對知識的渴望、對自身生命的探索。泰勒這個人物的魅力就在于,無論外界多么不堪忍受,他始終在內心的平靜中忠于自我。正是這樣一種沉穩而堅定的力量啟發了塔拉的自我意識。
哥哥泰勒與其他人不一樣,當其他幾個兄弟扭打在一起的時候,他會安靜躲在自己的房間給物品分類標記。泰勒會洗干凈一天勞苦后的泥塵坐在書桌前,一邊聽著音樂,一邊看書學習。塔拉則會蹲在他腳邊的地板上,呆呆地聽完一首又一首聽不明白卻穿透心靈的歌。其中有一首塔拉喜歡的音樂,那是一首唱詩班的音樂,也是泰勒離開家留給塔拉的聲音。這種聲音很好代表了泰勒的力量,溫柔但不懦弱,緩緩地在平靜中起身反抗。
福柯認為權力和反抗是共生的,泰勒則是第一個對家中存在的父權壓迫說“不”的人,他默默反抗吉恩一直以來以父親這個身份行使的絕對權力,他是第一個“叛逆者”。他告訴被哥哥肖恩毆打的塔拉“是時候離開了”,告訴她“外面有一個世界,一旦爸爸不再在你耳邊灌輸他的觀點,世界就會看起來大不一樣”。也是在泰勒的多次鼓勵下,塔拉一邊工作一邊攢錢,以備學費之需。即便她起初對自己是否能上大學充滿了懷疑,但是泰勒對教育的向往在她心中埋下的種子激發著她不斷超越恐懼。如果將泰勒和塔拉逃離巴克峰上的“監獄”視為肉體上的反規訓抗爭,那么塔拉在精神上的反抗則是反復曲折歷盡折磨的。
17年來都活在強大的父權話語之下,以至于剛進入楊百翰大學的塔拉很難適應周遭的一切,街道的嘈雜、室友的緊身吊帶背心、歷史書上關于被屠殺猶太人的真實數據,全部都讓她備受沖擊,以致塔拉不斷地在“父親的真理”與學校的經歷中陷入自我懷疑。父親的話語反復在塔拉的腦海浮現,大哥肖恩長期的毆打與辱罵讓塔拉的心理變得病態,無法正視身體的疼痛與心理的痛苦。可見在巴克峰“監獄”里,父親吉恩長期的思想規訓和大哥肖恩的暴力規訓已經成為塔拉自我規訓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進入楊百翰大學初期,塔拉經受著比以往更加激烈的思想斗爭和精神洗禮,面對與舊世界的不完全剝離和與新世界的脫節,塔拉陷入嚴重的自我懷疑,精神世界又一次瀕臨崩潰。在遇到各種課堂上的一次又一次的認知風波,男友查爾斯真切的關懷與鼓勵,大學里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讓塔拉逐漸意識到,只有坦誠面對傷痕累累的自己,才能真正與外界建立連接,擁抱這個新世界里的變化,也更加堅定了塔拉要不斷學習和追求真理的決心。正如塔拉在自傳的第二部分中寫道:“我的一生都活在別人的講述中。他們的聲音鏗鏘有力,專制而絕對。之前我從未意識到,我的聲音也可以與他們的一樣有力。”
三、自我生命的重塑——像鳥飛往自己的山頭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擺脫“他者”的先決條件是消除“他者的內化意識”,實現女性意識的覺醒。塔拉的主體意識在大學求學的過程中逐漸覺醒,但卻依然無法與巴克峰“監獄”里那種久遠而腐朽的凝視抗衡。福柯認為,想要真正意義上展開反規訓斗爭,只能從主體自身入手。而關于主體該如何構建的問題,福柯提出自己的“生存美學”來闡釋這一過程,其核心內容就是“關懷自身”。在《福柯的生存美學》中,高宣揚教授提出,關懷自身是一種由內而外進行反思的方式。由于由外部世界向內心世界觀看的轉化,人們才可以實現對于自身思想進程的觀察和思考。塔拉在學期末沒有回巴克峰的家而是選擇留在猶他州,她搬到城市另一邊的一所新公寓里,想在這個沒人認識她的地方重新開始。然而這個新的開始卻遠非塔拉所想的那樣平靜。當遠在巴克峰上的家人視塔拉為背叛上帝的惡魔并威脅與其斷絕關系時,塔拉飽受精神折磨——仿佛不僅是巴克峰上的家人視她為惡魔,而是整個世界都認為她是拋棄原生家庭的惡魔。她開始懷疑自己選擇接受教育追求真理的代價就是失去巴克峰上的家人。塔拉試圖回到巴克峰修復和挽回這份情感,再次回到巴克峰的家里,看到母親在郵件中描述的像個惡魔的自己,塔拉才意識到父母的荒唐無知早已無法挽救,而塔拉只能挽救自己。“這里沒有什么可拯救的。”
回到學校之后,塔拉決定求助大學心理咨詢服務。面對自己的真實需求以及自己無法提供的東西,塔拉通過一次一次重述自身的經歷,開始真正關注自己內在世界的變化,最終擺脫了一直壓抑在她精神世界的那所“監獄”。而之后塔拉也將這番自我與家庭之間情感拉扯的問題進行反思和深入探究,并寫成了自己博士論文的初稿——《英美合作思想中的家庭、道德和社會科學,1813—1890》。塔拉也在自己27歲生日那天提交了自己的博士論文,通過了答辯,后成為韋斯特弗博士。從17歲到27歲這十年間的掙扎與努力最終還是成就了塔拉的人生。就像塔拉自己在書中說的那樣:“我已經建立了新生活,這是一種幸福的生活。”
四、結語
“這是關于一個廢料廠的小女孩成為劍橋大學博士的故事”或許可能概括出塔拉這本自傳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然而,在筆者看來,塔拉對曾經被“監獄”壓得支離破碎的自己的重新塑造是這個故事最讓人震撼的地方。她通過不斷的求知、思考與自我反省,用自身經歷構建自己的思想,超越并打破父權曾經強加于自己的“真理”。塔拉深知:只有獲得比他們更多的知識,才能擺脫他人知識話語的控制,擁有自己的話語權。不是所有人都有毅力、勇氣,能夠去探索并審視自己內心的真實訴求,不斷打破規訓、追求真理。
在塔拉的故事里,筆者不僅僅看到教育的力量,也看到女性面對傳統父權規訓下堅忍不拔自我重塑的決心和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帶領塔拉走向心靈的自由和平靜,也是這種力量給塔拉插上了翅膀,使她像鳥一樣飛往自己的山頭。
作者簡介:張森(1992—),女,湖北鄖西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跨文化交際、外語教學與外貿人才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