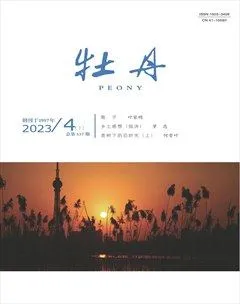無為思想與《復活》中的托爾斯泰主義對比研究
托爾斯泰主義是托爾斯泰宗教思想和宗教觀的代名詞。列夫·托爾斯泰后期世界觀發生激變,一般意義上,認為他的托爾斯泰主義有非常明顯的中國哲學的特點。1877年,列夫·托爾斯泰對中國哲學產生了興趣,這種興趣在1884年達到了高峰。他不僅大量閱讀中國哲學的著作和論文,如研究譯成法語的《道德經》譯本,還親自撰寫、翻譯相關的文章與書籍,如《中國學說述評》《孔子的著作》等。他曾表示,1878—1891年,孔子和孟子對他的影響“很大”,老子則是“巨大”。但他并不是一個悉心崇拜的狂熱信徒。“他對諸子的專門研究未必通透,但從中卻能精準敏銳地抓住和自己的探索相關的精髓,而其思想根基就在托爾斯泰的啟蒙主義的民主思想中。”可以說,列夫·托爾斯泰是以兼收并蓄、取其精華、為我所用的態度來研究中國哲
學的。
托爾斯泰主義是一個東西兼容的思想體系。全人類的博愛精神是其宗旨,道德的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惡、禁欲主義及懺悔意識是其主要內容。老子無為思想與托爾斯泰主義有許多契合之處,也存在許多矛盾沖突之處。列夫·托爾斯泰取其所需、加以引申、為其所用,使無為思想成為托爾斯泰主義的理論支持之一。托爾斯泰主義在總結性巨著《復活》中得到了完美呈現。本文將從個人道德完善、對社會的反思兩個角度入手,對比無為思想與《復活》中展現的托爾斯泰主義,從而進一步分析二者的相似觀點、矛盾沖突及列夫·托爾斯泰對其的糅合運用。
一、道德完善
(一)關于“道”的理解與引申
老子的無為思想是從“道”延伸而來的。在老子看來,“道”是天地萬物都應遵循的總規律,正如《道德經》里所寫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讓老子的另一核心思想“無為”具有實踐性,是其立論基礎。列夫·托爾斯泰十分推崇老子的“道”,不過,在接觸《道德經》之前,列夫·托爾斯泰先接觸的是“福音書”中的“道”,此“道”被界定為“神的話語”、“真理”與“靈”。托爾斯泰主義是列夫·托爾斯泰在“馬太福音”登山寶訓基礎上提出的,是以上帝為核心的。列夫·托爾斯泰認為,人應該完善自我的道德,從肉體生活向靈魂生活轉化。通過這種方式可以與上帝相通,接近真理。
宗教環境培育著列夫·托爾斯泰的博愛精神。在喀山大學就讀期間,列夫·托爾斯泰接觸到了盧梭、伏爾泰等西方啟蒙思想家的作品。他非常認同回歸自然、平等博愛的思想有深深的認同。在列夫·托爾斯泰涉獵中國文化思想之前,其思想就與中國哲學有了許多契合,這些思想“具有歷經宏大時空而栩栩如生的普適性”。1884年,列夫·托爾斯泰研究《道德經》的法譯本,將“道”釋意為“上帝”。1893年,他將《道德經》譯成了俄文,認為受老子影響很大。列夫·托爾斯泰認為老子的“道”也是與“上帝”相關的,“他教導人們從肉體的生活轉化為靈魂的生活。他稱自己的學說為‘道’”。
但事實上,老子的“自然之道”與列夫·托爾斯泰的“上帝之道”并不相同。老子的“道”強調的是自然,是萬物固有的本來規律,是客觀的。“無為”指的是做事要符合自然之道,在為人層面的體現老子認為的完善的道德,即堅守自己善之本性,沒有私心與欲望,遵循自然規律。這使人與人、人與宇宙萬物都能處于和諧統一的狀態。《道德經》第八章寫道:“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在老子看來,社會中存在許多遠離自然、被機心、智巧所束縛的人,老子希望統治者能夠學習水之柔弱不爭的德行,不自為、不自慮,成為至善的化身來引導人民。
列夫·托爾斯泰的“上帝之道”是一個“充滿愛的人格神”,正如“約翰福音”中所寫的“神愛世人”。“福音書”中神將愛作為最高命令,在“約翰福音”第8章,耶穌寬恕行淫女子,并勸誡她“從此不要再犯罪了”,這是耶穌愛的示范。《復活》中也有這樣的體現。瑪絲洛娃作為女犯被押往法庭時,一個賣炭的鄉下人對她畫了一個十字并給了她一個戈比。在小說的最后,列夫·托爾斯泰寫道:“聶赫留朵夫現在才明白,社會和秩序所以能存在,并不是因為有那些合法的罪犯在審判和懲罰別人,卻是因為盡管有這種腐敗現象,然而人們仍舊在相憐相愛。”以愛(饒恕就是愛)處理世間之惡是上帝的方案。
列夫·托爾斯泰的“道”是一個“人格神”,而老子的“道”是客觀自然規律。深受“福音書”影響的列夫·托爾斯泰相信人是可以通過自己選擇悔改而重生的,正如“路加福音”中耶穌身邊那個可以選擇悔改的盜賊。而老子是將希望寄托于統治者,希望統治者能到達至善,引導人民。
(二)禁欲主義
列夫·托爾斯泰認為,人應該從肉體生活轉化到靈魂生活來與上帝接近。在《復活》中,瑪絲洛娃與聶赫留朵夫本始于愛情,卻終變成悲劇。列夫·托爾斯泰主張通過“禁欲主義”和懺悔來完善道德、保持人性的純潔。在《復活》中,聶赫留朵夫的靈魂復活體現在認罪悔改和踐行“福音書”上的教誨上。正如文中他的吶喊:“他感覺到上帝的存在,因此不僅感覺到自由、勇氣和生趣,而且感到善的全部力量。”聶赫留朵夫的態度從關注個人幸福轉變為關注人民命運,實現了“靈魂凈化”之后的他追求對人、對己統一的幸福。瑪絲洛娃的靈魂復活表現在生活觀和行為的改變上,她被苦難折磨得麻木的心也開始蘇醒。在獄中她飽經苦難,卻仍然關心他人。流放期間,她回歸自己的純真善良。聶赫留朵夫和瑪絲洛娃都經歷了肉體生活向靈魂生活的轉化,完善了自我道德,從而實現了“精神覺醒與復活”。
列夫·托爾斯泰對老子提倡的“少私寡欲”頗感興趣,認為這是處理靈肉矛盾的重要途徑之一。他認為:“人就應當學會不為物欲而為精神而生活。這也正是老聃所教導的。”二者都是以禁欲的方式,顯示出精神的重要性,提倡不為物欲而為精神而生活。但是二者卻有不同之處。老子主張的“節欲”是為了“貴生”。“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由于有“身”,所以會擾亂心性。老子認為人首先應該少私寡欲,不能被欲望所驅使,這樣才能保持心性,更好地活在現世。而托爾斯泰主義的“禁欲主義”更偏向于精神的升華,“靈魂凈化”的目的是“把自己的生命和天父的生命熔鑄在一起”。
在道德完善方面,列夫·托爾斯泰將老子思想中客觀的“道”解讀為“人格神”,他們二人都主張節欲與禁欲,但是目的卻并不相同:老子是為了“貴生”,列夫·托爾斯泰是為了“靈魂凈化”。
二、對社會的反思
(一)勿以暴力抗惡與以柔克剛
列夫·托爾斯泰創作《復活》時,俄國社會已處瀕危狀態。列夫·托爾斯泰借男女主人公的“復活之路”踏遍俄國,目睹了百姓的痛苦、社會的黑暗,以瑪絲洛娃為中心,展現了荒唐的監獄景象:因身份證過期就被關押的130名泥水匠、明肖夫母子的冤案。聶赫留朵夫為救瑪絲洛娃四處奔波時,見證了監獄外、城市里人民水深火熱、觸目驚心的生活。“(乞丐)衣衫襤褸,面孔浮腫,帶著孩子們站在街角要飯。”老人、小孩被警察、地主蠻橫對待等。“各種暴力、殘酷行為、獸行在對政府有利的時候,非但不會遭到政府禁止,反而得到政府批準。”殘酷行為被政府默認為合法,那么暴行就會在社會盛行。
受“福音書”登山寶訓和印度甘地“勿以惡制惡”思想的影響,反對暴力是列夫·托爾斯泰一生探索的旨歸。托爾斯泰主義中的“勿以暴力抗惡”是對現行政治制度的批判。列夫·托爾斯泰推崇與“無為”具有相通性的老子的“柔弱勝剛強”觀點。“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列夫·托爾斯泰認為:“沒有阻礙,水流淌;遇到堤壩,水止住;堤壩破了,水便流。在方形的器皿里,水是方的;在圓形的器皿里,水是圓的。正因為這樣,以柔克剛比一切東西都重要,都有力量。”
(二)關于“無為”的理解與引申
列夫·托爾斯泰渴望新的秩序,正如《復活》中所寫:“人類至高無上的幸福——在地上建立天國——也能實現。”為了達到心中構建的理想社會、解決社會罪惡,列夫·托爾斯泰認為應該相信上帝并秉承博愛思想,而不是使用暴力。這與老子政治上的無為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是契合的。老子的“無為之道”是世間萬物的本源,是為人之道,也是老子理想的治理國家的標準。正如《道德經》中所寫:“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他認為治理國家不能違反社會發展的規律,否則就會導致國家的失敗。這是老子對于社會問題所秉持的清靜無為思想。
列夫·托爾斯泰對老子無為思想的推崇與借鑒,是他所堅持的否定社會改革即“為”的思想的發展。他徹底否定了沙皇制度,認識到俄國上層社會信仰、道德的虛偽,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到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社會改良運動。他與貴族、地主階級的傳統觀念決裂,迫切尋找新的信仰來“拯救靈魂”。在1893年5月15日給希爾科夫的信中,列夫·托爾斯泰談到了老子的“無為”。他認同老子的無為思想,并且將其融合為托爾斯泰主義的理論支持之一。在此提出的“無為”是希望統治階級不要為惡。值得注意的是,老子的“無為”是指順應天道,而列夫·托爾斯泰的“無為”批判的是沙皇政府的“為”,比老子的“無為”更具社會批判性。在《復活》中,列夫·托爾斯泰認為一切苦難的根源是沙皇制度和官方教會,官員們搜刮民脂民膏、虐待人民,官方教會愚弄百姓。并且老子的“無為”還要回歸到“無不為”上,而列夫·托爾斯泰主張通過僅靠個人精神的完善來解救人類。
對比列夫·托爾斯泰與老子各自在心中構建的理想社會就可見其中的差別。“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追求的是樸素自然、降低政治干擾的社會生活。而列夫·托爾斯泰的“天國”要求人人都是道德完善的、充滿愛的、不以暴力抗惡的,這是人間無法實現的烏托邦。
在對社會的反思方面,列夫·托爾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惡”與老子的“柔弱勝剛強”是契合的;并且列夫·托爾斯泰對老子的“無為”加以借鑒和推崇,融合自己的哲學觀,形成自己的“無為論”,以支持托爾斯泰主義中的“勿以暴力抗惡”思想。
三、結語
本文從道德完善和對社會的反思兩個角度分析了《復活》中的托爾斯泰主義與《道德經》中的老子無為思想。列夫·托爾斯泰在自己的宗教觀與哲學觀的基礎上,以揚棄的態度吸收了老子的無為思想,將老子的無為思想融合在托爾斯泰主義的建構中。總之,無論是老子還是列夫·托爾斯泰,他們都以獨特的方式深切關注著國之治、民之安。無論是托爾斯泰主義還是老子的無為思想,都充滿憂國傷民之情懷,是對人民的終極關懷。
(天津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