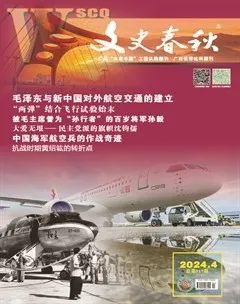“兩彈”結合飛行試驗始末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舉世震驚。但有西方媒體嘲笑中國“有彈無槍”,說的是中國的原子彈只是“子彈”,沒有導彈這支“槍”配套,就算有了原子彈也根本打不到別國的土地上。其實,我國自行研制的“東風二號”導彈于1964年6月29日發射成功,早已初步有了“槍”。然而問題隨之而來:如何將“槍”和“子彈”結合起來呢?緊接著,我國僅用2年時間就成功地進行了“兩彈”結合飛行試驗,成為繼美、蘇、英、法之后,世界上第5個能用導彈發射核武器的國家,徹底打破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核壟斷、核威脅。
確定“兩彈”結合方案
原子彈是一種爆炸裝置,它可以用多種運載工具來運載,而導彈是最有效的運載工具。美國和蘇聯在造出導彈、原子彈后,將二者結合組成具有實戰價值的導彈核武器便成為一種必然。1951年初,美國以飛機空投方式試驗了一種可用作導彈核彈頭的小型原子彈,使他們對導彈裝備核彈頭發生了濃厚興趣,進而實施“宇宙神計劃”,加速導彈和核彈頭的結合。1958年8—9月,美國5次進行“兩彈”結合試驗,并用紅石、X-17等運載火箭帶著核彈頭進行高空核試驗;同年12月,美國將戰略彈道導彈與氫彈頭首次配套組成的導彈核武器——“雷神”中程導彈裝備部隊。蘇聯不甘落后,在20世紀60年代初成功試驗熱核導彈。從此,導彈核武器成為美蘇兩國推行全球核威懾戰略的主要支柱。
為了打破超級大國的核壟斷,我國在研制原子彈的同時就已把導彈核武器作為下一步的發展目標。1962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由7位副總理和7位部長組成的15人專門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專委),以加強對原子彈、導彈等國防尖端武器研制試驗的領導。
鑒于我國原子彈、中近程導彈的研制工作已經取得重要進展,1963年12月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議,作出核武器研究方向以導彈頭為主、核航彈為輔的重大決策;責成有關部門立即開展核彈頭和中近程導彈研制,力爭盡早建立配有核彈的中近程導彈裝備部隊。
1964年5月,我國準備試驗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主管國防尖端武器研制試驗的聶榮臻元帥明確指出:我國裝備部隊的核武器,應該以導彈這種運載工具作為發展方向,并要求抓緊時間,盡快協商擬定“兩彈”結合的方案。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簡稱“國防部五院”)一分院和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設計院(以下簡稱“二機部九院”)的科技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就原子彈與導彈“兩彈”結合問題,進行多次技術論證與協調,并按分工開展初步的研究試驗工作。
在第一枚原子彈成功爆炸前的4個月,我國已經秘密成功試射自行設計制造的中近程導彈“東風二號”,原子彈試驗成功之后,導彈的研制工作加快,開展了可與核彈頭配套的導彈的研究設計。
1964年9月17日,中央專委決定啟動導彈核武器研制計劃,對“兩彈”結合的工作作具體部署,要求二機部和國防部五院(同年年底,國防部五院更名為七機部)共同組織力量,進行早期方案的研究、設計和論證,由五院副院長、科學家錢學森負總責。
當時周恩來詼諧地說,“兩彈”結合,二機部負責原子彈,七機部負責導彈,“二七風暴”要刮起來了!當陳毅、聶榮臻向錢學森詢問研制“兩彈”結合到底需要多長時間時,錢學森表示,大約需要3年,于是,核彈頭與導彈結合試驗正式提上日程。1965年2月,周恩來主持中央專委會第十次會議,討論“兩彈”結合、統一領導、各方協作等問題,明確提出,1965年我國尖端武器研制進入“兩彈”結合試驗年。
為落實周恩來提出的刮起“二七風暴”的要求,二機部幾位主管核裝置總體方案的設計人員和七機部的科研人員一起協商在彈頭內安裝核裝置的要求和基本參數,并組成“兩彈”結合小組。
雙方經反復研究后認為,刮起這場“風暴”需要抓好“小”“槍”“合”“安”4件大事。“小”指的是原子彈要小型化,主要由二機部完成;“槍”指的是由七機部對“東風二號”導彈進行改進,使之成為原子彈的運載工具;“合”指的是“兩彈”結合,為適應原子彈的要求,導彈必須做許多相應的技術改進;“安”指的是安全。
分兩條線進行攻堅克難
4件大事當中首要解決的是“小”和“槍”的問題,由二機部和七機部分兩條線進行攻關。
二機部負責核武器小型化。要想將原子彈裝入狹小的導彈頭錐內,小型化是必須的。沒有小型化,原子彈就難以投送至足夠遠的距離,也就不能夠對遠方的戰略對手實施有效威懾。二機部為此迅速成立專門的核彈頭任務技術委員會,副總工程師張興鈐任主任。
要在第一顆原子彈設計的基礎上,結合導彈對核彈頭的具體戰術技術指標要求,對原子彈進行小型化設計,存在許多棘手問題。安裝在導彈彈頭上的原子彈必須要在體積和重量上大幅減小,外形尺寸和幾何形狀都要符合導彈彈頭的殼體,結構強度和元器件性能必須滿足導彈飛行環境條件,這些都對核武器小型化各部件的設計提出極為苛刻的要求。然而,以中國當時的工業基礎,技術積累嚴重不足,國內不具備精密加工能力,從材料到加工工藝都達不到要求。也就是說,即便部件設計出來,也難以加工出來。
一連串的疑問在張興鈐的腦海里盤桓:難道加工值一定要與設計值完全一致才行嗎?能否允許存在一定的公差呢?部件之間的間隙多大才不影響正常的功能發揮?他經過反復研究,腦子里終于形成一個大致的輪廓。他把自己的想法向研制團隊和盤托出,獲得大家的贊同,經過反復試驗,很快解決了原子彈小型化后的系統最佳公差值問題,既降低了生產工藝的難度,又不影響原子彈效能的正常發揮,解決了核彈頭配裝中近程地地導彈的技術難題。
導彈運載的核彈頭不僅要求小型化,而且要求威力大,還要經受得住彈頭再入環境的考驗。研究團隊提出需要進行原子彈空爆試驗,驗證原子彈在動態下的技術性能,為研制核彈頭提供參考數據。
1965年5月14日,一架裝有原子彈的轟炸機從西北某機場起飛,飛臨試驗場上空,飛行員按照預定程序,將原子彈投擲下去。原子彈在距地面一定高度,準確實現了空爆。根據實驗數據,核武器研究所就核彈頭的體積、重量、環境要求等主要技術問題集中力量攻關,研制出與導彈配套的核彈頭,并于1966年初開始各種地面試驗。
對導彈的改進由七機部負責。我國1960年11月5日成功試射的第一枚導彈“東風一號”,是仿制蘇聯的“P-2”導彈的近程導彈。在此基礎上,七機部開始自主研制新型中近程導彈“東風二號”。在錢學森的帶領下,研制團隊對“東風一號”進行全方位的改進,在提高射程上下苦功夫。他們攻堅克難,歷經多次失敗后,“東風二號”終于在原子彈成功爆炸前的1964年6月29日發射成功,為解決原子彈的運載工具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要用“東風二號”把原子彈送上天,還必須進行方案性的設計修改,做出較大的技術調整。
“東風二號”導彈的控制系統像一條大尾巴,容易暴露目標和受到干擾,而且移動不便,不符合實戰要求。他們改進設計,提出了“割尾巴”方案,改進后的導彈被命名為“東風二號甲”。1965年11月13日,“東風二號甲”進行首次試飛,取得成功,之后進行了10多次飛行試驗,為發射核彈頭準備好了一支“槍”。“東風二號甲”從方案設計到成功進行飛行試驗,僅用了10個月時間,速度之快令人稱奇。
再三研究安全應急措施
在科研人員的不懈努力下,“槍”和“子彈”“合”的諸多問題逐步得到解決后,“兩彈”結合很快轉入試驗飛行階段,但新的問題接踵而來:往哪兒發射?同類試驗,美國射向太平洋,蘇聯射向北極,而當時我國尚無強大的海軍力量,沒有海上測量條件,很難在公海上進行試驗,而且出于保密的考慮,也不宜在公海試驗。經過審慎研究:核彈頭只能朝中國本土發射,發射點在酒泉基地,彈著點定在新疆羅布泊地區。
美蘇的導彈核武器都是朝海上發射,若失敗沒有安全影響。我們在本國國土上進行實驗,如果失敗就相當于在自己頭上扔一顆原子彈。盡管我國西北地區人煙稀少,導彈飛行途經區域仍有人口聚居區,安全問題被擺到了重中之重。
早在1965年5月4日,周恩來在中央專委會第十二次會議上,就對安全問題提出極其苛刻的要求:不僅要做到導彈在飛行中保證不達彈著點絕對不能掉下來,還要做到萬一導彈掉下,原子彈也不能發生核爆。這個嚴苛至極的要求就是要為人民生命安全上“雙保險”。此后,周恩來多次召開中央專委會議,對“兩彈”結合飛行試驗進行研究。在討論中,專家們提出,采用地面各種環境條件模擬試驗和地下核爆試驗,都不能完全模擬飛行過程中的真實狀態,起不到綜合檢驗的作用;采用飛行“冷”試驗(即不配置核彈)方式,也不能綜合檢驗原子彈頭在飛行過程中的真實狀態;只有采用全威力、全射程、正常彈道、低空爆炸的試驗方式進行“熱”試驗(即配置核彈進行核爆炸),才能達到試驗目的,更符合實戰需要。周恩來表態,進行“熱”試驗是必要的,但安全問題絕無退路可言,他責成國防科委會同二機部、七機部多做幾種設想,進行研究比較,然后提出方案供中央專委決策。
國防科委召集二機部、七機部等有關單位負責人和專家開會研究,認真分析試驗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制定應急措施,就導彈核武器試驗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先進行飛行狀態下的“冷”試驗,作為飛行“熱”試驗的練兵;在確保有把握的基礎上,按全威力、全射程再進行飛行“熱”試驗。二機部和七機部緊密配合,將應急措施落到實處。經過改進的導彈有自毀裝置,如在導彈飛行過程中發生故障不能正常飛行時,可由地面發出指令將彈體炸毀;核彈頭有保險開關,如導彈彈體炸毀,因保險開關打不開,不會引起核彈發生核裂變。
1966年3月11日,中央專委召開第十五次會議,周恩來在聽取國防科委關于試驗計劃的匯報后,憂心忡忡地詢問錢學森究竟有多少成功的把握,錢學森很有信心地回答,我們的導彈是安全的。周恩來再次叮囑,“熱”試驗一定要做到萬無一失。這次會議原則同意國防科委提出的試驗計劃,決定先按進行“冷”“熱”試驗的計劃做好準備工作,要求國防科委進一步組織二機部、七機部研究落實各項措施,一定要從多方面設想,分析可能出現的問題,并多做一些試驗,以保證絕對安全。
1966年3月和6月,國防科委先后兩次組織審查保證“兩彈”結合飛行試驗安全可靠的技術方案、發射方案、測量方案及發生意外情況時的應急方案,多次召集有關部門研究檢查“兩彈”結合的研制、試驗工作,及時解決協作中的問題。各方挑選最好的儀器和組件用到“兩彈”結合上。經過多番測試,上萬個零件沒有出現任何問題。
周恩來親赴基地考察
1966年6月30日,周恩來在訪問巴基斯坦等國返回北京途中,特地在酒泉基地停留,實地視察導彈核武器試驗的準備情況。他與正在基地檢查工作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一起檢閱部隊,到發射陣地觀看中近程導彈發射合練,同基地負責人和技術人員親切交談。從火箭組裝到“兩彈”銜接,從發射操作到人員疏散,每一個細小的環節他都追根究底;從氣候到水土,從物質供應到文化生活,他對科技人員和解放軍官兵的生活都詢問得很仔細。周恩來還特地乘飛機專門考察將要進行“兩彈”結合試驗的飛行彈道,從發射區的酒泉基地到彈落區馬蘭基地,當飛越居民點紅柳園時,他再次強調要做好萬全準備方案,指示以防空襲名義進行相應演練,以便在“熱”試驗時,有條不紊地疏散人員。周恩來反復要求“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這16字從此成為國防科研試驗的指導方針。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兩彈”結合飛行試驗的有關部門協同配合,優化方案,對導彈和核彈頭進行各種模擬試驗,確保導彈按預定軌道飛行,在預定彈著點正常核爆,萬一在飛行過程中發生意外,要確保彈體及時炸毀,核彈頭不發生爆炸。
為了加強對試驗工作的領導,1966年9月,成立了由張震寰、栗在山、錢學森等11人組成的“兩彈”結合試驗委員會,張震寰任第一副書記、代理書記。
9月2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原則上同意國防科委的試驗安排,在10月初進行“兩彈”結合自毀試驗,10月中旬進行飛行“冷”試驗,并根據這兩項試驗情況確定進行飛行“熱”試驗的時間;同時責成國防科委會同總參謀部、總后勤部、蘭州軍區、鐵道部、公安部及有關部門組成聯合小組,統一指揮導彈飛行彈道下方紅柳園1.3萬多名居民的臨時疏散工作。為了確保“兩彈”結合飛行“熱”試驗萬無一失,10月7日在酒泉基地進行了一次實際檢驗安全自毀系統的“兩彈”結合飛行試驗。試驗結果證明,導彈工作正常,安全自毀系統可靠。
10月8日下午,周恩來和聶榮臻、葉劍英聽取“兩彈”結合安全自毀試驗結果和“冷”“熱”試驗飛行的準備情況匯報。周恩來明確要求,“冷”“熱”試驗彈都要嚴格檢查,要百分之百地保證不出問題,把各種因素都考慮到,能想到的問題都要檢查到位,一切缺陷都要彌補好;核彈頭要進行撞擊試驗,斜撞、橫撞都要試驗,以保證在各種異常狀態下都不發生核爆炸。周恩來指定這次試驗由張震寰全權負責,并對他說:“10月10日你去試驗基地再檢查一下。‘冷’試驗結束后,你回北京再匯報一次,最后報請毛澤東主席下決心。”
10月13日上午8時33分,第一枚“冷”試驗彈發射成功;16日17時30分,又成功發射第二枚“冷”試驗彈。這兩枚運載模擬核彈頭的導彈飛行正常,引爆控制系統工作可靠,并在彈著區內預定的高度按程序起爆了炸藥部件,進一步檢驗了導彈及引爆控制系統的可靠性。
10月20日,周恩來召集專門會議,聶榮臻、葉劍英、楊成武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及專家與會,聽取張震寰關于檢查“兩彈”結合“熱”試驗最后準備工作情況的詳細匯報,對“熱”試驗準備情況和試驗安全問題再次進行研究,與會人員一致認為經過幾個月的準備工作,“熱”試驗的質量和安全是有保證的。葉劍英高興地說,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用導彈進行核試驗,這在世界上還是一個創舉。周恩來特別強調要精益求精、周到細致,要保證萬無一失。聶榮臻表示要到發射現場主持這次試驗,得到周恩來的同意。
聶榮臻臨行前,于10月24日晚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興奮地說,誰說中國人搞不成核導彈,現在不是搞出來了嘛,同時又指出,這次可能打勝仗,也可能打敗仗,失敗了也不要緊。
聶榮臻坐鎮基地指揮
10月25日,聶榮臻抵達酒泉試驗基地,現場聽取導彈、核彈頭測試情況的匯報,檢查了試驗的各項準備工作,并向基地負責人傳達毛澤東聽取他匯報時所作的重要指示。聶榮臻強調,要深刻領會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充分做好準備,要從壞處著想,不打無準備之仗,把最后的各項準備工作做細做好,力爭成功。
25日下午4時,聶榮臻參加基地黨委對發射區和彈著區未來48小時的氣象研究,現場拍板同意黨委的意見,按27日正式發射來安排發射區、彈著區及場外的各項行動,責成基地黨委當晚將上述安排向北京報告。
導彈與核彈頭對接總裝時,聶榮臻親赴現場督導。人們勸他撤到掩蔽部里,因為1960年蘇聯在進行常規導彈發射準備階段,遇到突發故障,導彈瞬間爆炸,導致在場的涅杰林元帥和160多名科技人員全部遇難。我國這次進行的是核導彈試驗,危險性更大,而“兩彈”對接、通電又是整個試驗最危險的環節。聶榮臻卻拿了一把椅子坐在現場,說:“你們不怕危險,我有什么可怕的!你們什么時候對接、通電完,我就什么時候離開。”有關人員密切配合,順利完成了導彈、核彈頭的最后總裝。
在聶榮臻的指揮下,26日凌晨,裝載導彈、核彈頭的運輸車頂著大風駛往發射陣地。26日上午9時許,張震寰主持召開黨委會,再次研究氣象情況。根據天氣預報,27日氣象條件優良,經報聶榮臻同意,確定27日上午9時為飛行試驗發射時間,并向周恩來、葉劍英、楊成武和國防科委請示批準上述發射時間。周恩來批示同意,指示要沉著打好這一仗。
紅柳園1.3萬多名居民的安全是一個繞不開的大問題。按照理論彈道計算,紅柳園的位置處在導彈飛行96秒至102秒之間,遭遇風險的可能性不大。然而“熱”試驗裝載的是貨真價實的核彈頭,一旦失敗,那里的一切都將不復存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鐵道部調集3列火車將紅柳園萬余名居民臨時疏散到防空洞。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27日凌晨2時,正當“熱”試驗按鈕啟動準備就緒,彈著區突然刮起6—7級大風。核爆炸后的放射性灰塵受大風影響會迅速向大范圍擴散,可能危及正在空爆試驗場區準備氫彈原理試驗的數千名作業人員的安全。彈著區臨時黨委決定,從可能發生的最壞的情況出發,組織彈著區人員做緊急轉移的準備。就在這關鍵時刻,試驗基地的氣象部門判定,這陣大風將以每小時50公里的速度于上午8時移出彈著區,屆時天氣轉好。上午8時許,大風果然移出彈著區。
27日上午9時,發射指揮員下達發射命令,核導彈點火騰空而起,向西飛行,頭體分離后,核彈頭按預定彈道飛向彈著區上空。上午9時9分14秒,核彈頭在靶心上空距地面569米的高度爆炸,生成一個熾熱的火球,一圈彩環隨蘑菇云裊裊上升,爆炸威力初步測定為1.2萬噸梯恩梯當量,試驗取得圓滿成功。
現場所有人都激動萬分,聶榮臻和錢學森緊緊擁抱在一起。聶榮臻激動地跟周恩來通話:“總理,我向您報告,導彈核武器‘兩彈’結合試驗非常成功,請您代我向毛主席報告。”周恩來向全體參加試驗的同志表示熱烈的祝賀。
隨后,聶榮臻在發射現場發表即席講話,在轉達周恩來的祝賀后,他說,國防科學技術在黨的領導下整整搞了10年,這次試驗的成功,是對黨、對人民的獻禮,也是對國防科學技術10年的紀念。二機部、七機部和試驗基地的同志們很努力,感謝大家!他鼓勵大家戒驕戒躁,好好總結經驗,爭取更大的勝利!
10月31日,聶榮臻與錢學森、張震寰等一起來到核試驗基地。他們乘車來到彈著區,察看了爆炸投影點地區被燒成玻璃體的地面。聶榮臻說,我們的中近程地地導彈能達到這樣的準確,核彈頭及引爆控制系統設計得這樣可靠,是很不容易的,真了不起,這說明我們的技術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
新華社就中國成功進行導彈核武器試驗發表了新聞公報,外電驚呼:“中國這種閃電般的進步”,“就好像亞洲上空的一聲巨雷,震撼了世界,對西方來說神話般地不可思議”。確實不可思議: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次導彈核武器發射成功,美國用了13年時間,蘇聯用了6年,而中國僅用了2年。
這次“兩彈”結合飛行試驗的成功,為我國核武器的實戰化打下了堅實基礎,取得了核彈頭研制定型的完整經驗。從那以后,我國的中程、遠程、洲際、潛射等各種彈道導彈核武器相繼研制成功,但再也不用做帶核彈頭的彈道導彈飛行試驗。
這次試驗的成功,也意味著中國拿到了世界核大國的入場券,鑄就了共和國的核盾牌。1967年12月,“東風二號甲”改進型導彈定型,進行小批量生產。1969年改進型導彈正式列裝部隊,我國戰略導彈部隊——第二炮兵部隊(即今天的火箭軍)也隨之建立,奠定了我國國防安全體系的基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