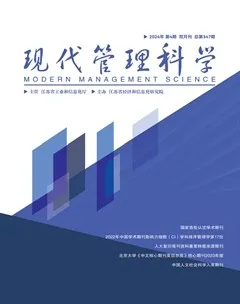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同演化研究













[摘要]借鑒協同學理論,分析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復合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協同作用,探究復合系統耦合協同動態演化過程。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2009—2021年復合系統耦合協調水平,采用Moran’s I指數對其空間相關性進行分析,運用哈肯模型確定了復合系統演化過程中的序參量,并進一步探究復合系統之間的內在機制。研究發現:①2009—2021年高技術產業和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地區差異顯著,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均優于大西北綜合經濟區;②2009—2021年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處于良性耦合低度協調狀態,呈現顯著的空間正向自相關特征,但各綜合經濟區耦合協調程度不一;③高技術產業是復合系統協同演化的快參量,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是起主導作用的序參量,兩者之間存在雙向協同增長效應;④高技術產業可以通過科技成果轉化和和產業集聚機制,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高技術產業;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協同演化;復合系統,哈肯模型
一、 引言
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和保障,對于提升國際競爭力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發展的硬道理,并將“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放在首位1。受制于資源稟賦、金融發展水平等因素,不同區域在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面臨不同的問題和挑戰。高技術產業具有創新驅動、高附加值和高成長性等特點,對于提升區域經濟質效、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及可持續性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同時,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也為高技術產業提供了良好的創新環境和政策支持。立足于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現狀,探究兩者之間的動態演化關系,對于優化兩者之間的協同作用,提高系統結構有序度并實現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于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任保平[1]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了機理分析。部分研究集中在內涵特征[2]、測度評價[3]、發展路徑[4]等方面,還有關于數字金融、數字經濟和數字技術創新助力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與影響效應[5],以及技術創新的空間溢出效應和產業集聚效應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6]。第二,高技術產業。張礦偉等[7]發現數字化轉型對高技術產業創新產出存在正向影響,影響程度隨創新產出的增加而遞減。大多數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高技術產業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效率的測算與提升[8],政產學研用合作如何進一步促進高技術產業技術創新[9],政府研發補貼等政策對高技術產業創新產出的影響[10],高技術產業集聚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11],不同地區科技資源配置對高技術產業TFP的差異作用[12]。第三,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謝會強等[13]探究了高技術產業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非線性影響。Zheng等[14]認為高技術產業是促進區域產業協調發展和區域經濟增長轉型的重要力量。此外,馬昱等[15]分析得出,高技術產業通過增加就業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通過上述文獻梳理,發現現有關于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較多,而對于兩者之間內在機理和動力機制的研究較少,學者們較少涉及兩者之間的復雜動態演化問題。鑒于此,本文更感興趣的是,各地區高技術產業及其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如何?兩者之間的耦合協調程度如何?兩子系統是否存在空間相關性?誰是復合系統中起主導作用的序參量?如何提升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復合系統結構有序度?
為探究上述問題,本文對復合系統耦合協同動態演化進行分析,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2009—2021年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并運用Moran’s I指數對其空間相關性進行分析;最后,根據哈肯模型確定復合系統演化過程中的序參量,檢驗復合系統演化結構有序度的高低及其協同演化的內在機制。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第一,運用協同學理論和自組織理論,對復合系統耦合協同動態演化過程進行分析,從理論上為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協同演化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有助于推動相關領域的研究。第二,測算復合系統的耦合協調程度,并對其進行空間相關性分析,為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協調程度和空間關聯性提供定量分析工具,對于差異化區域協同發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支撐依據。第三,運用哈肯模型確定復合系統中的序參量,從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集聚角度,對復合系統協同演化機制進行檢驗,揭示復合系統演化過程中的內部機制和規律,為理解和評估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協同效應提供新的視角和方法。
二、 復合系統耦合協同演化分析
1. 復合系統耦合協同演化歷程分析
復合系統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子系統構成多主體、多層次、多要素的集合體,可通過各子系統的動態演化、競爭、合作和反饋,使其在時間上、空間上和狀態上形成自組織演化的有序結構[16]。本文借鑒已有研究成果[17],將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復合系統耦合協同演化定義為:在一定時間和范圍內,兩子系統之間相互作用、彼此影響、協同發展,各子系統之間持續交流、合作和共生,從而促進高技術產業技術研發和成果轉化,以創新驅動助力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是高技術產業持續創新和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動態關聯現象。其復合系統結構見圖1。
第一,區域創新。高技術產業注重科技創新,通過技術研發和成果轉化,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持續動力。同時,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創新提升區域經濟質量和效率,包括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等,提供良好的創新環境和政策支持,包括科技創新資金、人才引進政策等,以鼓勵高技術產業創新發展。第二,區域協調。高技術產業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城鄉間搭建技術轉移和應用的橋梁,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優化城鄉資源配置和政策扶持,促進城鄉間的協調,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和全面進步。第三,區域綠色。高技術產業采用先進的技術和工藝,實現生產過程的綠色化和清潔化,推動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產業的發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政策引導和資源管理,促進經濟綠色發展和生態保護,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良性循環。第四,區域開放。高技術產業積極參與國際技術合作和交流,推進新技術新產品的國際化和全球化,推動區域經濟的開放發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和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為高技術產業的國際化提供支持,包括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等。第五,區域共享。高技術產業通過創新創業和技術轉移轉化應用等方式,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政策調控和社會福利保障,促進社會公平和共享發展成果。子系統之間的有效協作和配合,共同推動共享發展、社會進步和人民幸福感的普遍提高,其相互作用和影響共同構成復合系統的復雜性和動態性。
復合系統內部既存在自我強化與穩定的作用機制,也存在不斷適應外界政策環境、市場環境、制度環境等變化的功能機制,這些機制使系統內部各組分間的作用力出現各種微小的隨機漲落,當其出現在復合系統結構突變的臨界點附近時,將使系統偏離穩定的定態解。正是隨機漲落和系統的非線性作用共同形成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復合系統結構演化及其動態路徑,推動系統從無序向有序演化或從低有序度到高有序度演化。其復合系統耦合協同演化機理見圖2。
由圖2可知,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復合系統耦合協同動態演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首先,兩子系統在初始狀態的有序度相對較低,各自處于相對獨立的狀態,相互之間聯系和互動較少。其次,兩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逐漸加強,開始出現協同效應,復合系統處于從無序到低度有序的耦合協同發展階段。再次,兩子系統協同效應逐漸增強,復合系統的有序度逐漸提高,向高度耦合協同方向演化。最后,當兩子系統處于動態有序的平衡狀態時,高技術產業發展通過科技創新帶動產業集聚,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高經濟質效。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優化創新環境和加強政策支持等,提升高技術產業區域競爭力和市場占有率。
2. 系統協同演化機制分析
高技術產業的核心是技術創新,關鍵在于研發和成果轉化,而科技成果轉化的能力和效率可以衡量高技術產業技術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程度。隨著科技成果的不斷轉化,高技術產業發展須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和技術創新的發展趨勢,不斷對技術和產品進行升級換代,區域經濟中的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助力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高技術產業的技術擴散和知識溢出效應,能夠促進企業間進行技術交流和合作,吸引人力資本集聚,產業規模的擴大可以降低部分成本,促進產業鏈上下游分工深化,專業化分工加劇產業集聚。政府通過提供稅收減免、補貼等優惠政策吸引企業入駐,進一步促進產業集聚,提高區域經濟發展水平。
高質量發展的區域通常擁有較高水平的教育和科研機構,這為高技術產業提供了充足的研發人才和前沿的科研成果。較為發達的金融市場和活躍的投資環境使高技術企業更容易獲得風險投資、銀行貸款和其他形式的資金支持,這對于高研發投入和快速擴張的高技術企業至關重要。此外,靈活的政策支持、成熟的供應鏈體系和較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更有助于高技術產業的創新發展。
綜上,高技術產業可以通過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和和產業集聚機制,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可以通過政策激勵與扶持、人才培育與吸引、金融與資本支持、營商環境優化等機制助力高技術產業創新。
三、 研究設計
1. 指標體系構建
基于指標建立的一系列原則,本文高技術產業子系統指標選取參考譚濤等[18]的做法從產業規模效益和產業創新能力方面進行構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選取參考魏敏等[19]的做法從經濟結構優化、區域協調共享、生態文明建設等十個方面進行歸納;趙濤等[20]從產業結構、包容性TFP、技術創新、居民生活和生態環境五個層面進行探討。此外,借鑒馬茹等[3]、李明等[4]的研究,篩選得到初選指標體系。基于數據的可得性原則完善指標體系,并通過專家評閱和探討進一步優化后最終構建了復合系統指標體系,見表1。
2. 指標權重確定
為避免主觀賦權的“絕對經驗性”以及客觀賦權的“絕對客觀性”,本文采用組合賦權法確定權重,確保更加科學合理、可靠準確。
AHP法。層次分析(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是將與決策相關的指標劃分為目標層、準則層、方案層等不同的層次結構,通過對指標進行比較分析,確定指標之間的相對重要程度,進而得出各指標權重[21]。
CRITIC法。CRITIC(Criteria Importance Though Intercrieria Correlation)是由Diakoulaki等提出的一種客觀賦權法[22]。其通過指標的對比強度(波動性)和沖突性來衡量指標權重,并同時考慮指標的信息承載量、差異性和相關性。
3. 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度表示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程度,協調度指系統之間的整體協同水平或貢獻程度,兩者共同決定系統耦合水平。耦合協調度模型如下:
[C=i=1nUi1ni=1nUin1n]" (1)
[D=C×TT=i=1nαiUi] (2)
其中,耦合度C∈[0,1],C值越大,子系統之間離散程度越小,耦合度越高,反之,則越低;n為子系統個數;Ui為各子系統數據標準化值,取值[0,1]。協調度D∈[0,1],D值越大,各子系統間協調程度越高;T為子系統間綜合協調指數;α為貢獻系數且[i=1nαi=1]。
本文參考已有研究成果[23],將耦合度和協調度劃分為若干種類型,劃分標準見表2。
4. 空間相關性檢驗
相鄰區域在地理空間上具有依賴性和互動性,使用莫蘭指數(Moran’s I)可進一步檢驗相鄰區域子系統之間的空間相關性。莫蘭指數分為全局莫蘭指數和局部莫蘭指數。全局Moran’s I和局部Moran’s I的計算公式分別如下:
[I=i=1nj=1nwijzi-zzj-zS2i=1nj=1nwij] (3)
[Ii=zi-zS2?j≠inwijzj-z]" (4)
其中,I為全局Moran’s I,Ii為局部Moran’s I;Igt;0表示呈正相關,數值越大,空間相關性越強;Ilt;0表示呈負相關,數值越小,空間差異越大;I=0表示無空間相關關系。[S2=1n?i=1nzi-z2]為樣本方差;n為區域總個數;[wij]為地理空間權重矩陣;[zi]和[zj]分別為區域i和區域j的屬性值,[z]為其區域均值。
5. 哈肯模型
假設[q1]和[q2]為系統內兩個狀態變量,[q1]是系統中起主導作用的序參量,[q2]是[q1]變化而變化的快參量,則系統演化方程為:
[q1=-λ1q1-aq1q2q2=-λ2q2+bq21] (5)
其中,[q1]和[q2]均為系統內狀態變量對時間的導函數;[λ1]和[λ2]為系統的控制參量;a和b為強度系數,表示[q1]和[q2]之間相互作用強度。
當[λ1]lt;0時,表明[q1]子系統已建立正反饋機制,[λ1]越大,促進系統有序度提高的作用越強,系統有序度越高;當[λ1]gt;0時,表明[q1]子系統已建立負反饋機制,[λ1]越大,抑制作用越強,系統有序度越低。[λ2]的性質與[λ1]類似,[λ2]lt;0和[λ2]gt;0分別表明[q2]子系統已建立正反饋和負反饋機制。當agt;0時,[q2]對[q1]起到阻礙作用,[a]越大,阻礙作用越強;當alt;0時,[q2]對[q1]起到助推作用,[a]越大,助推力越強。當bgt;0時,[q1]對[q2]起促進作用,[b]越大,促進作用越大;當blt;0時,[q1]對[q2]起抑制作用,[b]越大,抑制作用越強。
當系統通過自組織演化達到穩定狀態,滿足[λ2gt;gt;λ1]且[λ2]gt;0的條件時,此系統演化方程符合“絕熱近似”假設,表明[q2]為快參量,而[q1]為序參量。
為了便于哈肯模型在本文研究中的應用,對模型做離散化處理:
[q1t=1-λ1q1t-1-aq1t-1q2t-1q2t=1-λ2q2t-1+bq21t-1] (6)
6. 數據來源
考慮到研究適用性和可用性,選取2009—2021年中國30個省(區、市)(西藏、臺灣、香港和澳門一些關鍵指標值缺失,故不納入研究范圍)的面板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EPS數據庫、各省(區、市)統計年鑒及相關統計公報等,個別年份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補全。
四、 實證分析
1. 子系統分析
2009—2021年30個省(區、市)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子系統的相對均值及排序見表3。從高技術產業子系統來看,2009—2021年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北京和上海等地的高技術產業相對集聚,而青海、寧夏和新疆等地區高技術產業相對較少,產出略顯不足。從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來看,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和浙江等地創新驅動和協調發展能力較強,區域綠色低碳和開放共享水平也均優于貴州、甘肅和青海等地區。可見,2009—2021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和區域經濟發展在部分省份之間均存在明顯的非均衡現象,部分地區高技術產業仍有較大的發展潛力。
為了更清晰地揭示八大綜合經濟區在高技術產業水平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的差異,本文以高技術產業子系統為橫坐標,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子系統為縱坐標,對其復合系統進行分析,見圖3。
由圖3可知,在八大綜合經濟區中,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在高技術產業子系統中均處于中上水平,差距不大,但在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子系統中,東部沿海領先于南部沿海。北部沿海處于中間水平,須充分發揮其人才、知識密集以及信息中心的優勢地位。長江中游、黃河中游、大西南和東北綜合經濟區處于中下水平,這與區域科技資源缺乏、人力資本流失、創新環境不足等因素密切相關。大西北綜合經濟區由于創新人才隊伍不足、科技產出轉化能力不強、產業協調發展較弱等問題,暫時處于復合系統的劣勢水平。由此可見,中國高技術產業和區域經濟發展在空間分布上存在明顯差距,因此,要對其復合系統協調運行機制與區域差異進行量化分析,探究復合系統演化過程,助力區域協調發展。
2. 耦合協調度分析
根據式(1)和式(2)可得,2009—2021年八大綜合經濟區以及各省(區、市)高技術產業與其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度C和協調度D,限于篇幅,僅列出2009年和2021年相關結果及其均值,見表4。
由表4可知,2009—2021年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均值為0.5242,處于良性耦合階段。其中,廣東和江蘇的耦合度最高,均值分別為0.9936和0.9686,說明其復合系統已達到高水平極度耦合狀態;浙江和山東耦合度大于0.80,屬于高水平耦合類型;北京、上海、安徽等均為良性耦合的磨合階段;青海耦合度最低,均值僅為0.0580;新疆、寧夏、內蒙古、海南和甘肅則分別為倒數2至6位,耦合度均在0.30以下。此外,具有高水平耦合度并不代表兩者之間高水平協調發展,絕大多數地區均處于中度協調、低度協調以及輕度失調狀態。從八大綜合經濟區來看,2009—2021年東部沿海耦合度和協調度均值分別為0.8084和0.5407,其復合系統已達到高度耦合中度協調水平,并呈現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態勢。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均為良性耦合的低度協調類型,長江中游雖為良性耦合,但處于中度失調水平。黃河中游、大西南和東北綜合經濟區均為較低水平耦合的嚴重失調狀態,大西北綜合經濟區耦合度和協調度均最弱,處于低水平耦合的極度失調狀態。
3. 空間相關性分析
為了更好地反映復合系統耦合協調度的空間特征,本文對2009—2021年系統的耦合協調度進行分析,結果見表5。
由表5可知,全局Moran’s I均大于零且在1%水平上拒絕原假設,說明復合系統耦合協調度存在顯著的空間正向自相關特征,且空間集聚性較高,整體呈上升態勢。
本文基于全局Moran’s I的空間正相關結果,進一步運用局部Moran’s I探究該空間聚集特征現象出現的具體位置。限于篇幅,在此僅展示部分年份的結果,見表6。
由表6可知,復合系統耦合協調分為4種集聚類型:高-高集聚型,低-高集聚型,高-低集聚型和低-低集聚型。從整體空間分布模式來看,較多省份屬于高-高集聚型和低-低集聚型,這表明大部分區域高技術產業和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都具有顯著空間正相關特征,耦合協調水平相近的區域存在空間相鄰,主要是高值與高值的相鄰、低值與低值的相鄰,集聚層次有待提升。因此,要提升低-低集聚型耦合協調水平,發揮低-高集聚型和高-低集聚型中卓越省份的空間溢出作用,帶動臨近地區的耦合協調發展。
4. 系統演化分析
根據哈肯模型原理,首先,分別假設高技術產業(HT)和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ED)為序參量;其次,驗證演化方程是否成立;再次,通過求解方程檢驗控制參量是否滿足“絕熱近似”假設;最后,根據模型假設是否成立來判定高技術產業(HT)或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ED)是否為系統中的序參量,結果見表7。
當高技術產業(HT)為序參量時,復合系統演化方程不成立,故模型假設不成立。當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ED)為序參量時,復合系統演化方程成立,控制參量[λ1]=0.0333,[λ2]=0.1808,強度系數a=-0.0445,b=0.0294,此時[λ2gt;gt;λ1],且[λ2]gt;0,滿足“絕熱近似”假設。
在研究期間內,a=-0.0445lt;0,表明在復合系統中,高技術產業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推動作用;b=0.0294gt;0,說明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對高技術產業具有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存在雙向的正向協同增長效應。[λ1]=0.0333gt;0,說明高技術產業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正反饋機制并不完善,雖然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可以促進復合系統協同演化,但演化有序度偏低。[λ2]=0.1808gt;0,說明目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高技術產業復合系統協同演化匹配度較低,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系統演化。[λ1]和[λ2]均較小,說明復合系統結構有序狀態水平較低,仍有提升空間。
表8第(1)列是替換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ED)的度量方式,參考王軍等[5]的研究,以區域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替換。第(2)列是更換權重度量方式,采用熵權法進行核算。結果均顯示ED為序參量,HT為快參量,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復合系統中起關鍵性作用,上述結果是穩健的。
6. 進一步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進一步探究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同演化的內在機制。借鑒溫忠麟等[24]的研究,通過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對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集聚機制進行檢驗,結果見表9。
表9第(1)~(2)列為基準回歸結果,第(1)列為僅控制區域和年份效應,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在1%的水平上顯著,第(2)列加入了控制變量后結果依舊顯著。其中,控制變量的選擇參考馬昱等[15]的研究,政府干預程度(GOV)以地方財政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度量,金融發展水平(FD)用金融業增加值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信息化水平(INF)用地區的郵電業務總量與全國之比表示,對外開放程度(OPEN)用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表示。第(3)~(6)列中科技成果轉化(STP)用新產品銷售收入與專利申請量的比值來表示,產業集聚(AGG)采用區位熵指數進行衡量。表9第(3)列至第(4)列、第(5)列至第(6)列分別為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集聚機制的檢驗結果,HT、STP和AGG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高技術產業可以通過科技成果轉化和和產業集聚機制,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五、 結論與政策建議
1. 研究結論
本文從理論上分析了復合系統耦合協同動態演化過程,測算了2009—2021年八大綜合經濟區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程度,運用Moran’s I指數對其進行了空間相關性分析,采用哈肯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確定了復合系統演化過程中反映系統有序程度的序參量,并進一步探究了復合系統耦合協同演化的內在機制。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2009—2021年高技術產業和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從區域相對均值來看,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創新資源集聚,協調和開放共享水平均較高,屬于第一梯隊;長江中游、黃河中游、大西南和東北綜合經濟區屬于第二梯隊;大西北綜合經濟區由于創新人才短缺和成果轉化效率低下等,處于第三梯隊。
第二,從耦合度和協調度來看,2009—2021年復合系統處于良性耦合階段的低度協調狀態。從八大綜合經濟區來看,東部沿海達到高度耦合中度協調水平,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處于良性耦合低度協調水平,長江中游呈現良性耦合狀態,黃河中游、大西南和東北綜合經濟區則處于較低水平耦合嚴重失調水平,大西北綜合經濟區處于低水平耦合極度失調狀態。
第三,從空間相關性來看,2009—2021年復合系統耦合協調度的全局Moran’s I呈現顯著的空間正向自相關特征,空間集聚性呈上升態勢,應進一步提升至更高層次耦合協調水平。局部Moran’s I發現耦合協調發展水平相近的區域存在空間相鄰,整體趨向于高-高集聚型和低-低集聚型。
第四,在樣本期間內,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復合系統協同演化中起主導作用的序參量,高技術產業是快參量,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雙向的正向協同增長效應,復合系統耦合協同演化內部存在科技成果轉化和和產業集聚機制。
2. 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對于區域發展差異問題,應根據各地區的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制定符合當地情境的高技術產業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規劃。此外,加強政策引導,加強區域合作與協調,促進各地區要素流動和資源共享,推動高技術產業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地區間的協調。
第二,在高技術產業和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建立耦合協調機制,促進產業與經濟的相互協同和良性耦合。例如,通過政策引導和市場機制,推動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的深度融合;建立健全協調發展機制,提升高技術產業和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
第三,強化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強政策支持和協同,鼓勵高技術企業加強科技創新和產品研發,促進高技術產業成果轉化,推動高技術產業和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復合系統結構優化和有序度提升。
參考文獻:
[1] 任保平.新發展階段我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實踐路徑與政策轉型[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3):81-90.
[2] 張占斌,畢照卿.經濟高質量發展[J].經濟研究,2022,57(4):21-32.
[3] 馬茹,羅暉,王宏偉,等.中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及測度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9(7):60-67.
[4] 李明,王衛.基于飛地經濟視角的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機理與路徑[J].經濟縱橫,2023(6):90-98.
[5] 王軍,劉小鳳,朱杰.數字經濟能否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J].中國軟科學,2023(1):206-214.
[6] Zhou B,Zeng X Y,Jiang L,et al.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eference in China: A Numerical Simul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 Perspective[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20(54):163-172.
[7] 張礦偉,俞立平,張宏如,等.數字化轉型對高技術產業創新的影響機制與效應研究[J].統計研究, 2023,40(10):96-108.
[8] Liu X, Chen X, Wu Q, et al.Measuring Efficiency of the High-tech Industry Using Uncertain Multi-stage Nonparametric Technologies[J].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2023(216):119490.
[9] Pu G,Zhu X,Dai J,et al.Underst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vestment Performance: Evolu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Lithium-ion Storage Battery in China[J].Journal of Energy Storage,2022(46):103607.
[10] 嚴思屏,郭以恒,于藝楠.政府研發補貼對高技術產業創新產出的影響研究[J].亞太經濟,2023(4):120-129.
[11] 徐丹,于渤.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與多樣化集聚如何影響區域創新能力?——基于我國省際數據的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J].研究與發展管理,2023,35(1):118-132.
[12] 杜寶貴,楊幫興.科技資源配置何以促進高技術產業TFP增長——基于29個省域案例的fsQCA分析[J].科技進步與對策,2022,39(23):65-75.
[13] 謝會強,封海燕,馬昱.空間效應視角下高技術產業集聚、技術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21(4):123-132.
[14] Zheng Y,Cheng Y,Li L.Factors Affecting Regional Economic Synergy in China-based on Research on High-tech Industry[J].IEEE Access,2020(8):14123-14133.
[15] 馬昱,邱菀華,王昕宇.高技術產業集聚、技術創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效應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轉換回歸模型[J].工業技術經濟,2020,39(2):13-20.
[16] Li C, Asif Razzaq, Ilhan Ozturk, et al. Natural Resources, Financial Technologies, and Digitalization: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Human Capital in Selected OECD Economies[J].Resources Policy,2023(81):103362.
[17] Cheng M, Li Q, Wen Z.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alysi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Network and Eco-efficiency in China[J].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2023(99):107008.
[18] 譚濤,李俊龍.我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與區域高技術產業發展水平測度以及耦合協調度研究[J].中國科學基金,2023,37(4):682-691.
[19] 魏敏,李書昊.新時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度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8,35(11):3-20.
[20] 趙濤,張智,梁上坤.數字經濟、創業活躍度與高質量發展——來自中國城市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21] Saaty T L,Kearns K P.Analytical Planning, Chapter 3-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M].Berlin:Pergamon,1985.
[22] Diakoulaki D,Mavrotas G, Papayannakis L.Determining Objective Weights in Multiple Criteria Problems:The Critic Method[J].Computers amp; Operations Research,1995,22(7):763-770.
[23] 張旺,白永秀.數字經濟與鄉村振興耦合的理論構建、實證分析及優化路徑[J].中國軟科學,2022(1):132-146.
[24] 溫忠麟,葉寶娟.中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J].心理科學進展,2014,22(5):731-745.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大數據環境下的評價理論、方法和應用”(項目編號:7163100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戰略性礦產資源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戰略研究(2025-2060)”(項目編號:22XGL003)。
作者簡介:羅婷,女,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科技創新、區域經濟與管理;張永慶,男,博士,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與管理;龔銀銀,女,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技術創新;鄭蘇江,男,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科技管理與創新。
(收稿日期:2024-03-06" 責任編輯:蘇子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