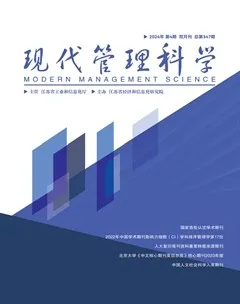供應鏈數字化、全要素生產率與企業綠色創新








[摘要]隨著數字技術深度嵌入供應鏈,供應鏈數字化成為我國加快經濟向綠色轉型的重要著力點,為企業綠色創新提供了重要契機。將供應鏈創新與應用試點政策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以2000—2022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采用雙重差分模型探析供應鏈數字化與企業綠色創新之間的影響關系及其內在作用機制。結果發現:第一,供應鏈數字化可以通過創新賦能和管理賦能促進企業綠色創新,并且該結論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仍成立。第二,基于資源基礎理論、內生增長理論以及動態能力理論的分析發現,供應鏈數字化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企業綠色創新。第三,通過對融資約束、內部控制以及企業污染屬性的異質性分析發現,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效果在融資約束低的企業、內部控制高的企業以及非重污染企業中相對更好。結論明晰了供應鏈數字化與企業綠色創新的關系及內在作用機制,并且為企業通過供應鏈數字化實現綠色創新提供經驗證據,也為我國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實現綠色發展戰略提供重要啟示。
[關鍵詞]供應鏈數字化;企業綠色創新;全要素生產率
一、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1。供應鏈產業鏈的發展關乎國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我國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的重大問題。早在2018年,商務部等八部門就聯合下發《關于開展供應鏈創新與應用試點的通知》2,積極探索現代供應鏈發展的新道路,為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奠定了強勁基礎。近年來,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在供應鏈中的廣泛嵌入使得數字供應鏈作為一種新業態如期而至[1]。強調數字技術嵌入的供應鏈數字化正成為現代供應鏈的表征,備受各界關注。與此同時,全球各地極端天氣事件造成的損失與日俱增。在當前全球環境問題日益凸顯、資源約束日益緊迫的背景下,企業綠色創新成為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2]。然而,由于制度和市場的快速演變以及企業綠色創新復雜性的提升,企業間的競爭已經上升為供應鏈間的競爭,加之綠色創新擁有其他創新沒有的“雙重外部性”特征,決定了綠色創新實踐必須是一個多主體參與的活動,單靠某一個企業無法帶來良好的綠色創新成果。因此,供應鏈網絡便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建立數字化供應鏈,將越來越成為企業保持競爭力的關鍵,那么供應鏈數字化是否對企業綠色創新產生影響?其內在影響機理又是怎樣的?兩者關系的邊界條件又有哪些?這些問題在當前鼓勵建設現代供應鏈以及推進綠色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亟待探討。
基于此,本文借鑒張樹山等[4]的做法,將供應鏈創新與應用試點工作視為企業建設現代數字供應鏈的一項準自然實驗,利用2000—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重點考察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路徑。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體現在如下3個方面:第一,文獻方面。供應鏈數字化尚屬前沿領域,有關研究大多以概念性框架構建為主[5],相關的實證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挖掘,本文為供應鏈數字化的實證研究提供了增量貢獻。此外,關于綠色創新影響因素的研究從供應鏈視角探析的較少,本文從供應鏈與數字化相結合的視角出發,探析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擴展綠色創新前因變量的研究。第二,本文基于資源基礎理論、內生增長理論以及動態能力理論從全要素生產率的角度揭示供應鏈數字化影響企業綠色創新的機制,以往研究多將全要素生產率作為結果變量進行研究,而全要素生產率作為一種綜合指標,會對許多方面產生影響,對其結果變量的研究還有很大的挖掘空間。本文以全要素生產率作為中介探析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路徑,有助于深化對兩者關系的理解。第三,以往研究多將融資約束、內部控制作為中介變量開展相關研究,而本文基于融資約束、內部控制以及企業污染屬性差異,探究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異質性影響,研究結果有助于形成具體的政策靶向。
二、 文獻綜述
供應鏈數字化是一個過程,強調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以及智能軟硬件設備來打造智能互聯技術系統[6],即將數字技術嵌入供應鏈[7],以提升服務價值以及可獲性,使用更具彈性的方式加強鏈上成員的交流互通。本文對供應鏈數字化的內涵界定與此一致。雖然目前國內外對數字化的相關研究已非常豐富,但對于供應鏈數字化的研究還相對較少。有學者研究了其積極的經濟效益,如有助于構建鏈上風險治理機制[8]、增加供應鏈彈性和抵抗力[9]等。此外,也有少部分學者研究了其消極的經濟后果,如帶來巨額的技術成本[10]、技術易被模仿難以形成長期優勢[5]以及破壞組織結構與文化的融洽性[6]等。
企業綠色創新是能夠降低生態環境的壓力、合理配置自然資源、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創新。目前學術界對其研究較為豐富,學者們主要從內外部兩方面來研究影響企業綠色創新的因素。內部主要包括費用投入、高管特征以及組織特征方面,如研發投入的增加會正向促進企業綠色創新[11],高管的環保意識越強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越高[12],組織冗余資源可以減少綠色創新活動開展的阻礙[13]等。外部主要包括政府因素、外部治理等方面,如政府補貼或扶持會有效激勵企業創新行為[14],公眾關注[15]會驅動企業綠色創新。
縱觀現有研究,由于供應鏈數字化尚屬前沿領域,雖直接研究兩者關系的文獻甚少,但近年來相關研究正在蓬勃興起。從數字化角度出發,宋德勇等[16]研究發現企業數字化會提高綠色創新水平;從供應鏈角度出發,有研究指出供應鏈中貯存了企業大部分的碳排放量[17]。另有研究發現,供應鏈上下游資源會影響企業綠色創新[18]。進一步地,供應鏈數字化與企業創新呈現倒“U”形關系[19]。在少數探討供應鏈數字化與綠色創新關系的文獻中,學者主要將目光聚焦于外部綠色供應鏈的集成上,指出綠色供應鏈集成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20]。
通過梳理現有研究發現供應鏈數字化的相關研究近些年正在興起,對于其經濟后果并未形成統一定論;有關企業綠色創新的研究雖已比較豐富,但遺憾的是,從供應鏈數字化視角深入探析綠色創新前因變量的研究還很稀缺。因此,本文從供應鏈與數字化相結合的視角出發,分別從管理層面和創新層面考察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并明晰全要素生產率在其中發揮的作用,為相關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角與思路。
三、 研究假設
1. 供應鏈數字化與企業綠色創新
企業綠色創新是推動綠色發展的重要途徑,而隨著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其與供應鏈的深度融合成為企業綠色創新的重要著力點。供應鏈數字化影響企業綠色創新的機理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層面:
在創新賦能層面,首先,供應鏈數字化的形成必然涉及數字要素的投入,而數字要素的投入能夠實現對企業創新資源配置的重組,尤其能夠提高研發資源配置效率,有針對性地研發、生產符合現代消費者偏好的可再生、綠色產品。其次,供應鏈數字化能夠提高信息傳遞效率以及企業的信息獲取、處理和整合能力[21],打通企業上下游之間的壁壘,增強供應鏈節點中各企業之間的信任,在此基礎上形成技術創新合力、開展協同創新活動、突破綠色技術瓶頸,從而以技術創新賦能綠色創新。最后,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企業融通創新[22],融通創新本質上是企業與其他創新主體間資源深度融合、高度暢通的深層次合作創新范式,而供應鏈數字化本質上是多個創新主體的數字化轉型,這就更加促進企業融通創新,在多創新主體的合作下為企業開展綠色創新活動提供了資源共享與要素供給。
在管理賦能層面,供應鏈數字化是一種“數字驅動供應鏈”的供應鏈管理模式,能夠從管理層面為企業綠色創新賦能,其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數字化能使獨立的企業內部組織結構趨于網絡化和扁平化,而供應鏈數字化能夠改變供應鏈節點的交互結構,加快企業間業務領域的融會貫通,推動供應鏈由線性到網絡再到生態系統的轉變[23],這就促使企業擺脫傳統模式的路徑依賴,以更先進的內部管理模式響應國家綠色發展戰略。其次,供應鏈數字化是以數智技術為支撐,生產技術的迭代升級使得企業生產過程逐漸趨于自動化、智能化,在多個崗位與工作流程中利用“智能機器人”代替傳統的人工作業,如無人車和無人倉等,這幫助企業大大減少了供應鏈管理對象,在人力資本結構方面趨向于使用高技能且具備創新意識的人才,從而為企業開展綠色創新提供了人才基礎。最后,供應鏈數字化打造的智能互聯平臺在環境監督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其可視化和互聯化的特點可以使上下游企業在相互進行環境監督的基礎上開展合作[24],也有利于強化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綠色創新的監督治理效力,減少企業的負外部行為,敦促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增加企業的綠色創新行為。
據此,本文提出假設1:
H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供應鏈數字化會顯著促進企業綠色創新。
2. 供應鏈數字化、全要素生產率與企業綠色創新
企業生產方式綠色化是綠色發展的微觀基礎,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及解決環境問題的核心環節。供應鏈數字化可以通過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促進企業綠色創新、推動綠色發展。
基于資源基礎理論可知,企業實現內部要素的高效配置是企業獲得長足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而數字技術賦能下的供應鏈重構提升了企業在供應鏈流程層面的數字化集成能力,使得企業可以有效整合各種資源、提高企業間要素流動效率、優化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從而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25]。此外,供應鏈數字化可以發揮數字技術連接生產要素的跨組織滲透能力,使企業在資源共享的基礎上獲取自身需要的資源,從而打造核心競爭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基于內生增長理論可知,技術進步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供應鏈數字化能夠形成形成強有力的“關聯效應”[26],在資源共享和協同合作的基礎上合力打破技術壁壘,使各企業在傳統設備改造升級的基礎上實現技術進步與創新,并在減輕企業生產對環境破壞程度的同時,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使企業能夠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進而推動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27]。從動態能力理論來看,供應鏈與智能數字技術的結合為鏈上企業提供了可視化、互聯化的智能聯動平臺,借助該平臺企業可以大大提高應對外界環境的動態能力,根據供應鏈中斷風險及時且高效地作出戰略決策,在采購、生產、銷售等一系列業務流程上表現出靈活性與高效性,從而提高生產效率,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是一個綜合性概念,也可以稱為系統生產率,囊括企業生產過程中各種要素的貢獻,包括人力、物力、財力等[28]。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宏觀上代表著產業的升級與生產力的發展,微觀上意味著企業在相同生產要素投入下能夠獲得更多產出,或者在相同產出情況下減少生產要素的使用,這使得企業具備了高效生產的能力,生產效率的極大提高為企業綠色創新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全要素生產力的提升為企業綠色創新注入了強勁動力,具體如下:其一, 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可以為企業帶來經濟績效,使企業有更充足的資金投入綠色創新活動,從而為企業綠色創新注入資金動力。其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也意味著生產要素資源配置的高效化,企業能夠充分有效利用自有資源去市場獲取企業所需的創新資源或技術,從而為企業綠色創新注入技術動力。其三,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說明企業會減少對低技能勞動者的需求,更多地趨向于引進高技能且具有創新意識的新型人才,從而為企業綠色創新注入人才動力。此外,企業在技術、管理和組織等方面創新能力的提升,直接反映在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上[28]。因此,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是企業綜合能力尤其是創新能力強勁的體現,是企業綠色創新的重要途徑,其與綠色創新的結合可以使企業獲得更持久的市場競爭優勢,進一步推動經濟向綠色轉型。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2:
H2: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供應鏈數字化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企業綠色創新。
四、 研究設計
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年份為2000—2022年的上市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在2000年以前,數字技術發展較遲緩,其與傳統產業的融入也尚處于探索階段。進入21世紀后,中國的大數據、算力等技術迅猛發展,極大地促進了供應鏈和數字化的深入融合。與此同時,國家也在不斷注重綠色創新的發展方向。在本研究中,剔除了統計數據中的ST和*ST等經營不善以及數據不完備的公司,同時也進一步辨識了年度報告中可能存在的錯誤。因此,剔除了如下異常數據:(1)缺少關鍵財務指標的樣本;(2)不滿足會計準則的樣本;(3)數據不全的樣本。經過如上的篩選之后,得到36359個觀測值。企業財務數據的主要來源是CSMAR和WIND數據庫。本文采取縮尾策略來避免極端值導致的檢驗結果誤差。
2. 變量定義和模型構建
(1)被解釋變量:綠色創新(Green)。本文通過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來獲取綠色專利數據,參考王馨等[15]的做法,將綠色發明以及綠色實用新型專利先進行數量加總,并在此基礎上加1后取自然對數。
(2)解釋變量:供應鏈數字化(DID)。本文參考張樹山等[4]的做法,利用2000—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采用雙重差分的方法,考察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試點企業的虛擬變量(Treat):當樣本中的企業屬于供應鏈創新和應用試點企業的時候,賦值為1,反之為0。試點前后的虛擬變量(Time):依照供應鏈創新以及應用試點工作的時間,2018年及以后取值為1,反之為0。理由如下:商務部等部門在2018年4月發布《關于開展供應鏈創新與應用試點的通知》,提到試點工作由兩部分組成,其中之一是試點企業,試點企業主要利用數字技術推動產業鏈、供應鏈轉型升級。經過半年時間的進展,確定55座城市和266家企業為試點對象,因此以2018年作為分界年份。
(3)中介變量:全要素生產率(TFP),考慮到LP法作為一種半參數方法能較好解決內生性和樣本選擇問題,因此本文選用魯曉東等[29]的LP法計算結果。
(4)控制變量:在劉海建等[20]和張樹山等[30]的研究基礎上,本文選擇資產負債率(Lev)、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獨立董事比例(Indep)、董事人數(Board)、兩職合一(Dual)、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管理層持股比例(Mshare)作為控制變量,同時也控制企業與年度影響。變量定義見表1。
3. 模型設定
式(1)中,本文利用雙重差分模型檢驗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根據江艇[31]機制檢驗的研究方法,設定式(2)檢驗全要素生產率的機制效應。
Green[i,t]=[β0]+[β1]Treat[i][×]Time[t]+[β3]Controls[i,t]+[β4][YEARi,t]+[β5]FIRM[i,t]+[εi,t] (1)
TFP[i,t]=[β0]+[β1]Treat[i][×]Time[t]+[β3]Controls[i,t]+[β4][YEARi,t]+[β5]FIRM[i,t]+[εi,t] (2)
綠色創新用Green表示,供應鏈數字化用Treat×Time表示,全要素生產率用TFP表示,Controls為控制變量的集合,FIRM表示個體固定效應,YEAR是年份固定效應,ε為誤差項。
五、 實證分析
1. 描述性統計
表2為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綠色創新的最大值為6.848,最小值為0.000,均值為0.307,中位數為0.000,表明綠色創新在不同企業程度不同。供應鏈數字化的均值為0.006,中位數為0.000,最大值為1.000,最小值為0.000,說明不同企業供應鏈創新意愿強度不同,應用試點也有一定差異。從控制變量相關數值可以看出,進行供應鏈數字化的企業有著較好的企業成長性以及較強的內外部治理能力,且這些數據的均值和中位數都較為接近,說明數據得到較合理的處理,有利于進行接下來的回歸分析和操作。
2. 基準回歸分析
本文使用模型(1)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不考慮相關控制變量且不固定企業和年份效應的時候,系數是0.5775,為1%水平的顯著程度;當控制年份和企業固定效應但不控制變量時,系數變為0.3999,且呈現1%水平顯著程度;當控制相關變量,但不控制年份和企業固定效應時,供應鏈數字化與綠色創新的回歸系數變成0.4588,且仍在1%水平顯著為正;當考慮控制相關變量以及年份和企業固定效應的時候,回歸系數變為0.3102,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是正向的,以上結果均驗證假設1,即供應鏈數字化可以促進企業綠色創新。
3. 機制檢驗
根據江艇等[31]關于機制檢驗的研究,本文利用模型(2)進行機制檢驗。表4列(2)顯示供應鏈數字化與全要素生產率的回歸系數是1.5310,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可知,供應鏈數字化能夠提升供應鏈整體效率以及響應速度、降低企業信息搜尋成本,進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能夠促進企業生產效率的提供,使企業獲得更多經濟效益,進而可以加大對綠色創新的投資研發,促進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即全要素生產率作為供應鏈數字化提升綠色技術創新的機制變量是成立的,假設2得證。
4. 平行趨勢檢驗
以2018年為試點時間,由圖1中的綠色創新平行趨勢圖可見,2000—2004年,實驗組的綠色創新水平和對照組的比較接近,表明早些年供應鏈試點的企業非常少;2004—2022年實驗組的綠色創新水平都高于對照組,特別是在2018年政策實施的時候以及政策實施以后的4年時間,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在實驗組和對照組之間有較為顯著的差異,說明平行趨勢檢驗的假設成立。
5. 安慰劑檢驗
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可能是遺漏變量所致。本文通過安慰劑檢驗的方式將解釋變量在研究樣本中隨機打亂,進行數據匹配。利用匹配好的數據進行回歸,結果見表5。回歸系數已經不再顯著,表明安慰劑檢驗成立。為提升結果的穩定性,對模型(1)按照上述步驟做500次的重復回歸。回歸500次以后的系數如表5所示。圖2是P值和系數的關系圖,可見虛線位置處P值等于0.1,圖中的P值絕大部分都大于0.1,說明估計的系數絕大部分都不顯著,表明供應鏈數字化確實能夠顯著促進企業綠色創新,結論穩健。
六、 進一步檢驗
1. 融資約束
企業融資約束的高低可能會影響企業進行供應鏈數字化轉型的意愿。融資約束越高,企業進行供應鏈數字化轉型的意愿就越弱,這可能削弱企業綠色創新行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基準回歸中加入供應鏈數字化(DID)與融資約束(WW)的交乘項(c.DID×c.WW)。如表6列(1)所示,交乘項(c.DID×c.WW)與企業綠色創新的回歸系數為-1.9066,且呈現1%的顯著性水平。可知在低融資約束的企業中,企業能夠籌集更多資金來促進企業進行供應鏈數字化轉型,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力度更強,符合前文推測。
2. 內部控制
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不同時,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綠色創新行為的促進作用可能存在差異。基于此,在基準回歸中加入供應鏈數字化(DID)與內部控制(IC)的交乘項(c.DID×c.IC)。如表6列(2)所示,交乘項(c.DID×c.WW)與企業綠色創新的回歸系數為正向的0.0006,且呈現5%的顯著性水平。可知在內部控制質量較高的企業中,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力度更強。因為企業內部管控能力越強,企業聲譽越好,越會倒逼企業肩負創新責任,進行供應鏈數字化的意愿就更強,促進綠色創新水平的提升。
3. 污染屬性
企業污染屬性可能影響企業進行綠色創新行為,為進一步探討供應鏈數字化對綠色創新的影響,在基準回歸中加入企業污染屬性(Pollute)和供應鏈數字化(DID)的交乘項(c.DID×c.Pollute)。結果見表6列(3)。交乘項系數為-0.1749,在1%水平顯著為正,表明在重污染企業中,供應鏈數字化提升綠色創新的效應更弱。重污染企業通常生產方式和設備比較老化,導致能源消耗較高,同時產生的廢棄物也較多,對環境造成了嚴重污染,與綠色創新相悖,抑制了供應鏈數字化提升綠色創新的效應。
七、 結論和啟示
供應鏈數字化是驅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企業綠色創新是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核心催化劑。本文選用2000—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深入探析了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及其影響路徑。實證發現:供應鏈數字化可以通過創新賦能和管理賦能促進企業綠色創新,全要素生產率是供應鏈數字化促進企業綠色創新的重要途徑,并且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效果在融資約束低的企業、內部控制高的企業以及非重污染企業中更明顯。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企業應緊抓當下供應鏈數字化轉型機遇,推進數字技術嵌入供應鏈,積極打造高效、敏捷且具有強大抗風險能力的數字供應鏈體系。具體可以從如下方面進行:首先,培育供應鏈數字化意識,積極引進數字技術,使企業內部生產經營全流程向數字化靠攏,以數字促生產;其次,在傳統供應鏈的基礎上升級轉型為數字供應鏈,對企業采購、生產、銷售、物流等業務流程全面優化升級,實現全方位的數字化變革;最后,及時檢測供應鏈數字化轉型成效,如應用供應鏈數字化的智能互聯平臺對企業的采購、生產、銷售等各環節進行實時監控以便及時調整優化,充分發揮供應鏈數字化降本增效的功能,為企業綠色創新奠定堅實基礎。
第二,企業要依托供應鏈數字化加大對創新技術的研發與投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綠色創新提供資金、技術、人才動力。針對此,政府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提供政策扶持:首先,政府可以設立企業綠色創新發展基金,給予企業專項幫扶,鼓勵企業積極深入地與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展開聯合創新,對鏈主企業加大幫扶與監管力度,開辟一批綠色創新試點企業,使其起到示范帶頭作用。其次,在創新人才方面,政府要盤活市場人力資本存量,聯合高校院所為企業引進高素質且具備創新能力人才提供優良條件。最后,政府應著力打造多層次、多元化的涵蓋綠色技術生產、交易、轉化、應用和評估等多方面的綠色技術創新市場體系,比如專利許可制度的進一步豐富、市場準入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等,鼓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引進行為。全方位推動企業的綠色創新。
第三,因企施策、精細推進。一方面,對融資約束低以及內部控制高的企業,政府應鼓勵其承擔國家綠色科技專項和創新項目,加大企業對綠色創新技術的投入;可以與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形成高水平創新平臺,以資源共享、要素聯合供給驅動整個鏈上企業的綠色創新。對于融資約束較高的企業,政府可以通過減免稅收、降低融資門檻等措施幫助該類企業提高資本存量。對于內部控制低的企業,政府要在宏觀上把控內部控制體系建設,并加強內部控制在企業投融資時的門檻作用,培養企業建立完善內部控制的意識。另一方面,對于非重污染企業,要充分利用其具有的優勢條件,有效配置資源,靈活運用數字技術,充分發揮供應鏈數字化的環境效益;對于重污染企業,鼓勵其減少傳統能源的使用改用清潔能源,降低碳排放,擺脫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同時鼓勵企業根據自身企業發展階段與供應鏈上下游企業進行資源的互換或清潔技術的共享,并在引進過程中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以供應鏈的創新合力為企業帶來環境效益。總的來說,要因企業施策,釋放供應鏈數字化紅利,最大程度推動企業綠色創新,助力國家綠色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Yang M Y,Fu M T,Zhang Z H.The 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Supply Chains:Drivers,Process and Impact[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21(169):120795.
[2] 蔣建勛,唐宇晨,李曉靜.雙碳背景下數字金融賦能新能源企業綠色創新:基于融資約束視角[J].當代經濟管理,2022,44(5):81-89.
[3] Junaid M,Zhang Q Y,Syed M W.Effects of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on Green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J].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2022(30):145-157.
[4] 張樹山,胡化廣,孫磊,等.供應鏈數字化與供應鏈安全穩定——一項準自然實驗[J].中國軟科學,2021(12):21-30.
[5] Bhattacharya S, Chatterjee A.Digital Project Driven Supply Chains: A New Paradigm[J].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22,27(2):283?294.
[6] Büyük?zkan G, G??er F.Digital Supply Chain: Literature Review and a Proposed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J].Computers in Industry,2018(97):157?177.
[7] Ishfaq R, Davis‐Sramek B, Gibson B.Digital Supply Chains in Omnichannel Retail: A Conceptual Framework[J].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2022,43(2):169-188.
[8] Rauniyar K,Wu X,Gupta S, et al.Digitizing Global Supply Chains through Blockchain[J].Production Planning and Control,2023(5):1-22.
[9] 史金艷,楊健亨,李延喜,等.牽一發而動全身:供應網絡位置,經營風險與公司績效[J].中國工業經濟,2019(9):136-154.
[10] Dolgui A,Ivanov D.5G in Digital Supply Chai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Fostering Flexibility, End-to-end Connectivity and Real-time Visibility through Internet-of-everyth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2022,60(2):442-451.
[11] 杜金岷,呂寒,張仁壽,等.企業Ramp;D投入的創新產出、約束條件與校正路徑[J].南方經濟,2017(11):18-36.
[12] 席龍勝,趙輝.高管雙元環保認知、綠色創新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績效[J].經濟管理,2022(3):139?158.
[13] 楊靜,劉秋華,施建軍.企業綠色創新戰略的價值研究[J].科研管理,2015(1):18-25.
[14] 章元,程郁,佘國滿.政府補貼能否促進高新技術企業的自主創新?——來自中關村的證據[J].金融研究,2018(10):123-140.
[15] 王馨,王營.環境信息公開的綠色創新效應研究——基于《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準自然實驗[J].金融研究,2021(10):134?152.
[16] 宋德勇,朱文博,丁海.企業數字化能否促進綠色技術創新?——基于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的考察[J]. 財經研究,2022(4):34?48.
[17] Blanco C C.Supply Chain Carbon Footprinting and Climate Change Disclosures of Global Firms[J].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2021,30(9):3143?3160.
[18] Song M X, Yang M X, Zeng K J, et al.Green Knowledge Sharing, Stakeholder Pressure,"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Green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020,29(3):1517?1531.
[19] 吳煒鵬,陳金龍,趙曉陽,等.供應鏈數字化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科技進步與對策,2024,41(11):67-78.
[20] 劉海建,胡化廣,張樹山,等.供應鏈數字化的綠色創新效應[J].財經研究,2023,49(3):4-18.
[21] Cong L W, Xie D, Zhang L.Knowledge Accumulation, Privacy, and Growth in a Data Economy[J].Management Science,2021,67(10):6480-6492.
[22] 李曉翔,雷紹方,張樹含.數字化轉型、融通創新與企業技術效率粘性效應[J].浙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24,52(2):145-156.
[23] Wu C K,Tsang K F,Liu Y,et al.Supply Chain of Things:A Connected Solution to Enhance Supply Chain Productivity[J].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2019,57(8):78-83.
[24] Sarkis J, Kouhizadeh M, Zhu Q S.Digitalization and the Greening of Supply Chains[J]. Industrial Management amp; Data Systems,2021,121(1):65?85.
[25] 羅佳,張蛟蛟,李科.數字技術創新如何驅動制造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來自上市公司專利數據的證據[J].財經研究,2023,49(2):95-109.
[26] 蔡延澤,龔新蜀,趙賢.數字經濟發展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實證檢驗[J].統計與決策,2022(15):98-103.
[27] 武力超,陳韋亨,林瀾,等.創新及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J].數理統計與管理,2021,40(2):319-333.
[28] 李占風,粟文元.數字經濟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J].西安財經大學學報,2023,36(6):58-69.
[29] 魯曉東,連玉君.中國工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估計:1999—2007[J].經濟學,2012(2):541-558.
[30] 張樹山,張佩雯,谷城.企業數字化轉型與供應鏈效率[J].統計與決策,2023,39(18):169-173.
[31] 江艇.因果推斷經驗研究中的中介效應與調節效應[J].中國工業經濟,2022(5):100-120.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數字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項目編號:21amp;ZD113)。
作者簡介:顧巍,男,博士,云南民族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企業管理;孫晴晴,女,云南民族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企業管理;張和平,男,云南民族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內部控制;王滿四,男,博士,廣州大學創新創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創新創業管理。
(收稿日期:2024-04-22" 責任編輯:殷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