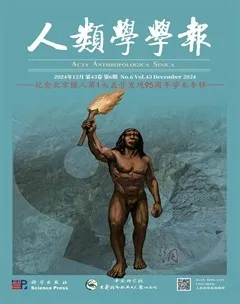中國晚更新世早期現代人內耳迷路的形態變異




關鍵詞:早期現代人;內耳迷路;更新世晚期;歐亞大陸;現代人擴散
1 前言
早期現代人在歐亞大陸出現的最早時間可能在距今10 萬年左右[1-3],而大量現代人化石出現在歐亞大陸上是在距今約5 萬~3 萬年前[4-10]。早期現代人走出非洲的化石證據雖然豐富,但是現代人進入歐亞大陸以后的擴散以及更新世晚期現代人的演化仍然存在許多未知。尤其是東亞地區,由于缺乏5萬~3萬年之間的人類化石,并且許多化石的測年還存在許多不確定性,東亞地區現代人的演化與擴散依然是近些年學者研究的重點。近些年來,東亞地區越來越多新的化石發現表明,時代較晚的現代人化石也常表現出原始與進步特征鑲嵌的模式,例如, 隆林人、馬鹿洞人和獨山洞人[11-13]。對此,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假設,認為這些特征可能來源于局部區域孑遺的特殊的早期現代人類型,或是古老型人類與早期現代人雜交的結果[13]。而隨著關于丹尼索瓦人以及中更新世古人類研究的不斷增加[14-20],許多中更新世古人類可能與丹尼索瓦人之間有著較為密切關系,而且他們在現代人起源與演化中可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研究暗示歐亞大陸上現代人的起源與演化上可能比之前想象的要更加復雜,這個過程不僅涉及到多方向的擴散與傳播[16],許多未知的古人類可能在這一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來,古基因組學研究發展迅速,為我們了解現代人的起源與演化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證據和細節[21-26]。但是古DNA 的提取受到保存狀況的嚴苛限制,因而形態學的研究依然是我們了解人類演化細節的重點。在提取古人類形態特征和重建系統發育信號上,內耳迷路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內耳迷路位于堅硬的顳骨巖部,在人類化石中通常保存較為完整。內耳迷路的形態在個體發育的早期就已經達到成年狀態,并且在系統發育中較為保守,因此經常被用于系統發育分析[27]。內耳迷路的形態在人類演化的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相比于大猿,人類擁有更大的垂直半規管和更小的水平半規管,這種趨勢從直立人開始尤為明顯[28,29]。尼安德特人的內耳迷路具有區別于直立人與現代人的一系列特征[30]。相比于智人,尼安德特人擁有較小的垂直半規管,較大的水平半規管,前半規管的扭轉程度更強,后半規管相對更矮,后半規管相對于水平半規管位置更低,壺腹線的角度更垂直等[27,28]。此外,尼安德特人還具有更長的耳蝸,更短的耳蝸圈數,可能對低頻聲音更加敏感[31]。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通過對世界不同地區人群內耳迷路形態的研究,發現其形態差異與地理距離具有高度的相關性[32],這表明內耳迷路的形態可以反映更短時間尺度上的人類遷移與擴散的歷史。前人基于內耳迷路線性測量的研究顯示,更新世晚期早期現代人的內耳迷路與現生人群基本一致。例如,資陽人的內耳迷路形態落入現生人群的變異范圍之內[33]。柳江人的內耳迷路總體與現生人群一致,但是在某些特征上與中更新世古老型人類以及尼安德特人類似,例如前后半規管的比例較大[34]。隆林人頭骨雖然具有古老性狀,其內耳迷路形態卻未表現出明顯區別于現生人群的特征[35]。
中國更新世晚期的現代人化石對于研究早期現代人在東亞地區的擴散與傳播有著重要的作用。本文擬通過分析柳江人、資陽人、隆林人、招果洞人和奇和洞人的內耳迷路三維形態,并與世界范圍內的現生人群進行比較,以期深入了解這些人類化石內耳迷路形態變異及其與現生人類之間的聯系,提取更多的形態學證據以闡釋現代人在東亞地區擴散的細節。
2 研究材料與方法
2.1 研究材料
本文研究的人類化石材料包括柳江人、資陽人、隆林人、招果洞人和奇和洞人(圖1),數據來源為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Paleoanthropology, IVPP)。其中,柳江人、資陽人和隆林人的內耳迷路在此前也有形態學研究[34,35,33]。柳江人CT 數據的掃描分辨率為56 μm,年代為距今3.3萬~2.3萬年前[36] 或6.8萬年前[37];資陽人的掃描分辨率為160 μm,生存年代為距今3.9萬~3.7萬年前[38];隆林人的掃描分辨率為44 μm,距今約1.15萬年前[11];招果洞人的掃描分辨率為160 um,距今約1萬年前[39];奇和洞人的掃描分辨率為24 μm,距今約9500年前[40]。為保證在相似的樣本量下對比化石人類與現生人類的形態變異,對比標本選擇了來自亞洲、歐洲和非洲的現代人樣本各12 例,男性和女性樣本的數量相等,共計36 例標本。亞洲標本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使用工業CT 掃描,掃描分辨率為160 μm。歐洲和非洲現生人群樣本館藏于金山大學達特標本館(Darts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使用南非金山大學演化研究所(Evolutionary Studie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顯微CT掃描,掃描分辨率在120~130 μm。亞洲人群、非洲人群和歐洲人群的樣本組成及其他細節在之前的研究中也有詳細描述[41,42]。所有標本的內耳迷路均在Mimics 23.0軟件中完成重建并且獲取三維標志點,重建時閾值分割采用半最大高度法(Half maximum height)[43]。在局部保存較差的化石標本中(例如,柳江人)依據前后圖像的連續性使用手動分割,最后重建得到的模型輪廓清晰,關鍵特征保持較好,且已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到驗證,因此我們認為標本的埋藏狀況對分析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前人研究表明,內耳迷路線性測量存在一定的性別差異,但是排除尺寸因素的比例(例如半規管長寬比)在不同人群中卻幾乎沒有表現出性別間的差異[44],幾何形態測量的關注重點是排除尺寸因素的形狀差異,因此本研究中性別不會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此外,先前的研究表明,內耳迷路的左右側存在一定不對稱性,例如,在21 項線性測量中有10 項具有顯著的左右側差異[45]。但是這種兩側的差異與個體間的差異相比僅占很小的一部分(0.22%),并不會對研究結果產生較大的影響[46]。人類化石標本很難同時保存左右兩側的數據,因此本研究中所有標本均選擇左側內耳迷路進行分析,部分僅保留右側內耳迷路數據的人類化石(柳江人、隆林人和招果洞人)通過相對矢狀面鏡像的方式獲取對應的左側模型。
2.2 幾何形態測量
本研究根據內耳迷路的形態,在內耳迷路三維模型的表面確定了148 個標志點與半標志點(圖2)。該標志點方案主要參考Beaudet 等[47] 的研究并增加了耳蝸半標志點的數量以匹配半規管半標志點的間距,該方案在先前的研究中也有過應用[20]。在本研究中,耳蝸使用2個標志點與48個曲線半標志點,總腳使用2個標志點與8個曲線半標志點,前半規管、外半規管和后半規管均使用2個標志點與28個曲線半標志點。其中前半規管、后半規管和總腳相交處為同一個標志點。
關于標志點的具體定義為:標志點1,蝸頂,耳蝸朝向前外側的尖端;標志點2,耳蝸向前庭的入口與圓窗下緣相交的一點;標志點3,前半規管、后半規管與總腳相交的一點;標志點4,總腳到前庭的入口;標志點5、6、7,三個半規管壺腹分別與前庭相接處(前半規管、外半規管和后半規管);標志點8,外半規管到前庭的入口。曲線1(48 個半標志點),耳蝸最外側的輪廓,在標志點1 和2之間均勻等分48 個點;曲線2(8個半標志點),總腳的外部輪廓,在標志點3和4之間均勻等分8個點;曲線3(28個半標志點),前半規管的外部輪廓,在標志點3和5之間等分28個點;曲線4(28個半標志點),外半規管的外部輪廓,在標志點6和8之間等分28個點;曲線5(28個半標志點),后半規管的外部輪廓,在標志點3和8之間等分28個點。
在獲取標志點與半標志點后,通過geomorph 包中的gpagen 函數進行廣義普氏分析(Generalized Procrustes" Analysis, GPA)獲取標準化的坐標以消除標本間非形狀因素(大小、位置以及旋轉)的影響,在此過程中保留所有標本的中心大小以進行后續的內耳迷路尺寸對比。標準化后的現生人群坐標通過交叉驗證的組間主成分分析[48] 確定其主要形態變異以及人群間差異(Morpho 包中的groupPCA 函數),隨后將化石人類標本的坐標帶入并計算其組間主成分得分。組間主成分所代表的形狀變化通過內耳迷路三維形狀疊加的方式進行展示。最后,通過典型概率[49] 計算所有化石人類標本屬于每個現生人群的概率(Morpho包中的typprobClass 函數)。典型概率通過馬氏距離將樣本的分布標準化,以獲取單個觀測值屬于某個多元正態分布的概率。上述所有數據分析與繪圖均在R 軟件[50] 中完成。
3研究結果
3.1 中心大小
箱線圖顯示(圖3),亞洲人群與歐洲人群的內耳迷路擁有相似的尺寸,而非洲人群的內耳迷路則明顯小于前兩者。晚更新世的人類化石中,兩件時代較早的化石標本,即柳江人和資陽人的內耳迷路尺寸明顯小于其他人類化石,并且也明顯小于亞洲人群和歐洲人群,落入非洲人群變異范圍的下限。隆林人、奇和洞人和招果洞人的時代較晚且相近,他們的內耳迷路尺寸也較為相似,且位于亞洲人群與歐洲人群的變異范圍之內,明顯大于非洲人群的尺寸。
3.2 組間主成分分析
第一組間主成分(bgPC1)代表的變異最多(圖4),將亞洲人群與非洲人群和歐洲人群分開,后兩組人群具有相似的第一組間主成分得分。除資陽和柳江的更新世晚期的現代人化石與亞洲現代人群表現出相似的內耳迷路形狀,其形狀與bgPC1最大值處的形狀(青色)類似。例如,耳蝸的圈數較少,耳蝸基底部的位置更加靠近外側,即耳蝸與半規管之間的橫向距離增加,耳蝸頂端較矮,這可能也與耳蝸圈數更少相關。耳蝸基底部位置靠外以及頂端內收綜合體現為耳蝸從頂部到底部的厚度較小;前半規管的扭轉程度較小且向前傾斜角度較大。大部分歐洲人和非洲人的內耳迷路形狀更加趨近于bgPC1最小值處的形狀,表現為與上述描述的狀態相反的趨勢。隆林人、招果洞人和奇和洞人位于亞洲現生人群變異范圍之內,柳江人和資陽人的內耳迷路形態則位于歐洲和亞洲現生人群之間。
第二組間主成分(bgPC2)代表的變異較少,將非洲人群與歐洲和亞洲人群分開。非洲人群的內耳迷路形狀與bgPC2 最大值處(青色)類似,其耳蝸從底部到頂部收縮的趨勢較緩,具有較強的前半規管扭轉,外半規管的相對尺寸較大且頂部有向下彎曲的趨勢。歐洲人群內耳迷路的形態更多的位于bgPC2 最小值處,而亞洲人群內耳迷路形態則位于非洲人群和歐洲人群之間。所有化石人類的內耳迷路形態都與亞洲現生人群更加接近,但也同時落入現生歐洲人群變異范圍之內。
綜合兩個組間主成分,隆林人、招果洞人和奇和洞人內耳迷路的形狀位于亞洲現代人群變異范圍之內,與歐洲和非洲人群的距離較遠,因此他們也具有上述亞洲人內耳迷路的典型特點。資陽人與柳江人的半規管形態位于所有現代人變異的中心位置,距離歐洲和亞洲現代人群都較近,而與非洲現代人群相對較遠。
將人類化石內耳迷路的坐標帶入到組間主成分中計算得到的典型概率顯示(表1),隆林人、奇和洞人和招果洞人的標本屬于亞洲人群的概率最高,資陽人屬于歐洲人群的概率最高,柳江人屬于歐洲人群的概率較高。這一結果與組間主成分分析的結果基本一致。
4 討論
本研究基于小樣本量的分析表明,三大地區現生人群的內耳迷路形態具有較為顯著的差異。其中,歐洲人群與非洲人群在總體形態上更加相似,亞洲人群與前兩者相比則表現出更多的差異,更確切的證據還需要基于大樣本量的研究。此外,本文研究結果與前人的研究基本一致[32],即不同人群間內耳迷路形態差異的大小可能反映了人類走出非洲的地理距離。從組間主成分得分的變異范圍上看,非洲人群的內耳迷路形態變異范圍較小,歐洲和亞洲人群的變異范圍較大。而在傳統的認知中,無論是形態學還是遺傳學的證據都表明,作為現代人的發源地,非洲地區的現代人具有更高的表型和遺傳學變異[51,52]。如果排除樣本量與取樣誤差等因素,本文的研究結果可能暗示內耳迷路的形態變異在現代人走出非洲后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例如語言、運動能力、環境適應以及基因交流等,因此導致了非洲以外地區現生人群的內耳迷路擁有更多的形態變異。
本文所分析的5 件更新世晚期現代人化石標本,其中3 件標本的所屬時代都在距今1萬年左右,即隆林人、奇和洞人和招果洞人的內耳迷路形態與尺寸都位于亞洲現生現代人的變異范圍之內。而時代更早的2件化石標本,柳江人和資陽人的內耳迷路形態相似,且與亞洲和歐洲現生人群的形態均較為接近,與非洲現代人表現出一定的差異。遺傳學證據表明,歐洲與亞洲現代人的分離時間在距今8萬~4萬年[26]。根據現有的測年數據,在本文的研究中,柳江人和資陽人距離歐亞大陸上早期現代人分化為歐洲人群和亞洲人群的時間最為接近,這可能是這兩件標本內耳迷路形態特征與現生歐洲人群和亞洲人群相似的原因。相比于時代較晚的早期現代人,柳江人和資陽人的內耳迷路形態可能也更加接近歐亞大陸上早期現代人分化初期的形態。
奇和洞人的內耳迷路形態與亞洲人群一致,明顯區別于歐洲以及非洲人群,這一點與古基因組學的研究一致,即奇和洞人所代表的古老人群是中國南方新石器時代人群的共同祖先[53,54]。招果洞人的內耳迷路形態與亞洲人的相似性最高,基于頭骨的形態學研究也表明招果洞人已經表現出典型的中國南方新石器時代人群的特征[55]。雖然隆林人的內耳迷路與招果洞人相似,但不同于招果洞人,隆林人的頭骨仍保留有許多古老特征,表現出古老與進步特征鑲嵌的特點[11]。從內耳迷路的三維形態來看,隆林人的內耳迷路并沒有表現出與現代人群較大的差異,這一點與頭骨形態學的研究不同[11],而與內耳迷路的形態學研究一致[35]。此前基于頭骨形態學的研究,學者們認為隆林和馬鹿洞人類化石可能屬于古老人群的孑遺,或者非洲早期現代人多次遷移中的一支,可能是走出非洲前早期現代人內部分化的結果。然而基因組學的研究表明,隆林人的基因組的尼安德特人或丹尼索瓦人的含量不高于其他現代人[53],且其對現代人沒有基因貢獻,可能屬于未知的古人類。結合本文的研究結果,我們認為隆林人可能代表現生人群分化后更加接近亞洲人群的階段,此時現代人的內耳迷路形態已經表現出較為明顯的人群間差異,但是由于其長時間處于隔絕分化的狀態,頭骨形態仍保留了較多的原始特征。本文基于內耳迷路的分析所提供的證據可能并不全面,更加準確的結論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支持。歐洲的早期現代人不乏與古老型人類交流的證據。生活在歐洲的最早的一批現代人化石中許多都保留了短時間內與尼安德特人交流的基因證據。例如,Pestera cu Oase 1含有9% 的尼人基因,估計在第4~6代以前就有一個尼人的直系祖先[56]。時代更晚的Zlaty k?ň 保留有更長的尼人片段,暗示這種人群與現代人的分離時間在早期歐洲與亞洲人群分離的基部[57,18]。雖然在東亞地區沒有尼安德特人的分布,但是可能生存著丹尼索瓦人以及其他未知的古人類,而且現代人的擴散也有可能是多頻次以及多方向的[16]。歐洲早期現代人經歷的基因交流、隔離與滅絕,很有可能也發生在亞洲早期現代人中。本文研究沒有發現隆林人內耳迷路明顯區別于現生人群的特征,但是鑒于隆林人頭骨以及古DNA 的獨特性,不能排除其屬于一個未知古人類物種并獨立演化的可能性。
綜上,內耳迷路作為古人類化石中比較容易保留下來的結構,能夠較為真實地反映人類演化歷史和人群遷移過程,可以為系統發育分析提供寶貴的信息。本文研究表明,大部分時代較晚的、中國更新世晚期的、早期現代人的內耳迷路形態,與亞洲現生人群具有較高的相似度。時代較早的早期現代人擁有與歐洲人群和亞洲人群相似的內耳迷路形狀,可能反映了現代人分化初期的形態。在未來的研究中,通過對更多人類化石標本內耳迷路形態的分析,我們將會更加深刻地理解現代人在歐亞大陸擴散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