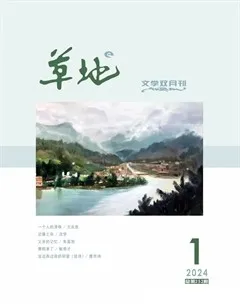母親的稻田
一
小滿過后,天氣就熱了。栽下的秧苗開始泛青,家家戶戶忙著種化肥,我家自不例外。
這天后半夜,我和母親就起床了,拖著架子車向田間拉化肥。來來回回好幾趟,我又累又困,被母親趕回家,又睡了一覺。
母親是什么時(shí)候拉完化肥,又是什么時(shí)候回來帶飯帶水的,我一點(diǎn)都不知道。等我醒過來,天已經(jīng)大亮了。
走進(jìn)廚房,父親正站在灶臺前,拄著拐杖半吊著左腿,向碗里舀稀粥。看著父親咬著牙吃力的樣子,我不禁鼻子陣陣發(fā)酸,真后悔沒有早些起床來。
“大妹。”父親喊我,“快吃早飯吧,你娘都下田去了。一會跟你娘說,天氣熱,早點(diǎn)回來。”
我點(diǎn)了點(diǎn)頭,就著咸菜吃早飯。家里條件不好,下飯菜就只有咸菜,要不就是豆瓣,喝了兩大碗稀粥,仍覺肚子里空落落的。但我不敢奢望什么,起身從墻上摘下草帽,出門往村口走。等我走到田間,左鄰右舍已經(jīng)種完化肥往家里走了。母親將化肥分幾處放好,正準(zhǔn)備下田。種化肥是家鄉(xiāng)俗語,有首兒歌是這樣唱的:“種化肥,一早忙,種得一年稻花香。”意思是天氣熱,向田間施肥,得趁一早。施化肥很似向田里播撒種子,因此又叫種化肥。
我抬頭望了望天空,還不到8點(diǎn)鐘,太陽的光芒已刺得人睜不開眼睛,田間彌漫著一股熱騰騰的霧氣,蒸得人臉上脖子上全是汗水。放眼空曠的田野,就只剩下我和母親兩個(gè)人了。
我走過去抱住母親的肩膀,耍賴似的說:“娘,爸也不叫醒我。不然這會,我們也可以回家乘涼了。”
母親滿是汗?jié)n的臉上蘊(yùn)含著幾絲苦澀,說:“我們家有六畝田,你以為是小孩子過家家啊。唉,說來種化肥都有些晚了,要不是你爸受了傷,哪輪到你細(xì)妹子來干這種體力活……”
農(nóng)村孩子自小都得干體力活,倒也習(xí)慣了。聽著母親的嘆息,我蹲下身去,向兩個(gè)鐵盆里裝化肥。
二
兩個(gè)月前父親在外村攬工,不小心從房上摔下來,將左小腿骨摔斷了。那時(shí)我還在鎮(zhèn)上中學(xué)念書,備戰(zhàn)高考,班主任老師忽然來通知,要我趕快回去,家里出事了。當(dāng)我借老師的自行車趕回家,父親已經(jīng)被抬回來了,放在院壩里,腫起的小腿上只綁著兩塊木板。
村頭大伯比我后到一步,他捂著胸口邊咳嗽邊義憤填膺地說:“怎么躺這啦?就該直接往鎮(zhèn)醫(yī)院送,天王老子耶,這是要人命啦!吭吭吭……”
父親半仰在地上,痛得額頭直冒汗珠,他邊呻吟邊喊:“我真是倒了八輩子的霉啊,我咋這樣不小心啦!早曉得要出事,我掙啥化肥錢……”
母親這時(shí)已失了主張。她從村頭走到村尾,借了一圈錢空著雙手回來,蹲在父親的腳邊,無聲地淌著眼淚。
大伯問:“弟妹,沒借到錢?”
母親背過身直揩眼睛,搖頭。
大伯苦苦一笑,卻說:“去醫(yī)院,肯定花很多錢!再說離家遠(yuǎn),地里的活誰照顧?送回來,也好。”
母親說:“哥耶,再不怎么地,總不可能不看呀!”
大伯說:“看,咋不看?還得包醫(yī)好,我去找王神醫(yī)。”
母親怔了怔,問:“是不是后山那個(gè)能治跌打損傷的老中醫(yī)王先生,以前是個(gè)赤腳醫(yī)生?”
大伯說:“就是他,這個(gè)人牛火(有本事),十里八鄉(xiāng)誰不知道他的名號,那才叫得一個(gè)響。”
大伯話里話外贊不絕口,也不知道這赤腳醫(yī)生是否真“牛火”,但母親顯然是相信的,說:“王神醫(yī)是好,可那……那也得好幾千啦。哥耶,家里情況你也知道的,買化肥的錢還欠著啦。”
“弟妹,錢的事不急,我擔(dān)保,還欠著。家里不是還有五六畝水田,等收了秋糧,再補(bǔ)上。”大伯比出兩根指頭,“我想,至多也就這個(gè)數(shù)。”
“兩千?”
“上次丁老五嚴(yán)重得多,也就這個(gè)數(shù),估計(jì)還能談。”
“你這一說,我倒還記起那個(gè)丁老五來了,是有這么回事。”這個(gè)丁老五像顆定心丸,母親生怕請不來王神醫(yī)了,“兩千就兩千吧,別談了。也不一定非得秋收,我……我再去借。”
“借?你去哪里借?”大伯忽然想起點(diǎn)什么,抬頭四下尋找送父親回來的工頭,但沒看見人,說:“弟妹,這不對啊。好歹幫人做工,出了事,咋就都沒人影了呢?不行,醫(yī)藥費(fèi),得有人出。”
父親痛得直齜牙,說:“不怨別人,不怨別人!”
母親摟著父親的肩膀,嘆著氣說:“是不怨別人,但也不能全怨你呀!你是在工地上出的事,再怎么著,也不能你一個(gè)人負(fù)責(zé)呀。”
父親強(qiáng)忍著痛說:“我們是幾個(gè)人一起攬工,掙到的錢也是平分。人家好心幫咱攬工,家里都不寬裕,出了事,哪有錢賠?就算人家要賠,咱又好意思要不?”
父親這樣一說,母親和大伯咽著喉嚨,無話可說了。
我過去扶父親起來。父親一把拽住我的手,說:“大妹,都是你爸不小心,事情出也出了,怪誰都沒用。你二弟三弟在鎮(zhèn)上念書,回去也別講,你可記住了?”
我邊點(diǎn)頭,邊說道:“記住了。”
“你也快高考了,千萬別分心。”
我又點(diǎn)頭,眼淚就流出來了。
就這樣,我和母親將父親扶進(jìn)屋,大伯走路去請王神醫(yī)接骨。
三
轉(zhuǎn)眼間,太陽已升起一竿子高,田間就更熱了。濕熱的天氣引來大群大群的黑蚊蟲,在稻田里飄蕩,一股股黑煙似的。我學(xué)著母親,打赤腳挽起衣袖褲腿正要下田,但給母親拉住了。母親揚(yáng)起草帽,用力揮散黑蚊,在我挽起的手臂和腿上涂了一層稀泥,又替我戴好草帽,臉上蒙了紗巾,這才允許我下到田里。
我家一共有六畝水田,隔著一條田埂呈階梯分成三塊,下面一塊四畝大田和上面兩塊一畝小田。雖然田有這么多,但家鄉(xiāng)缺水,秋收打完稻谷田里便得蓄水,不然翻年栽不下秧。也正因此,一年收成只有一季,家里所有開銷全指望著秋收的稻谷,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我最先下到田里,又黏又稠的稀泥立刻沒過了膝蓋,手里端著肥料,哪還挪得動步子。可這塊田太大了,總得有人要走到中間去。我漲紅著臉費(fèi)力地向外拔腿,暗暗責(zé)怪自己平時(shí)農(nóng)活干得太少了,就遇上這么一點(diǎn)小小的挫折,竟弄得如此狼狽不堪。
母親見我東一腳西一腳地踩倒好幾蓬秧苗,迅速跳下來,從我手里接過化肥放好,推我上田埂,又小心翼翼地將秧苗扶正。
“大妹,你站在田埂上撒,我撒中間,你先去撒小田。小田窄,你從兩邊撒。”母親端起化肥,向我示范了幾遍。“你別東一坨西一坨的,要撒均勻。秧苗跟人一樣,若是有人吃飽有人餓著,那就不成了。”
我點(diǎn)點(diǎn)頭,端起一盆化肥向上面小田走去。我本想洗干凈稀泥放下袖口和褲腿,可一看田中間一群群黑蚊追著母親旋轉(zhuǎn)飛撲的光景,心就揪緊了。我想,我年輕身上血多,倒可以讓黑蚊過來追攆我,我在田埂上總可以跑得快些。可是,黑蚊依然圍著母親打旋,而母親卻渾然無視,已經(jīng)動作麻利地種起化肥來了。
種化肥,是個(gè)簡單體力活,撒幾遍,也就駕輕就熟。但麻煩卻在于:懷里端著一大盆,一只手向腰腹緊緊箍著,還得騰出只手向外使力。腦子也得活泛,掌握拋撒的密度,記住每一次拋撒的畦壟,據(jù)說像大伯那樣的老農(nóng),只需瞄上一眼,自己田里幾畦幾壟,要種幾斤幾兩化肥,就像心里擺了一架算盤,早打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圍著小田種化肥一圈,日頭已經(jīng)升在了半空。摟著的鐵盆愈來愈重,直往下滑。我站在田埂上喘著粗氣,旁邊的機(jī)耕道一層一層向上閃動著熱浪,像著火似的。我看見母親在田里緩慢地移動,襯衣貼著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了。我既心疼她又無法幫她,田中間還有好大一片沒種完。
我喊:“娘,你上來歇會吧,喝口水,太熱了。”
母親回頭望了我一眼,又順著拋撒的方向轉(zhuǎn)過去。她每轉(zhuǎn)一次方向,便聽見化肥“沙沙”撒落的聲音。母親說:“得快些把田中間種完,到中午更熱。大妹,要不你給娘遞化肥吧,我這一來一去的,費(fèi)時(shí)間。”
于是我便幫著母親遞化肥。母親明顯地加快了速度,她幾乎是掐算著時(shí)間,每當(dāng)我將化肥送到田中間,她手里的盆子正好空下來。也許是熟能生巧,一來二去的,我學(xué)了不少,不僅能夠在田間空畦里行走自如,與秧苗秋毫不犯,還能趁著間隙也似母親那樣,向著田中間種化肥了。
只是,田里比埂上更熱。沒有風(fēng)熱氣散不開,我和母親仿佛緩慢穿行在一個(gè)露天蒸籠里,秧苗葉割得手上腿上全是細(xì)細(xì)的血痕,火辣辣地疼。更麻煩的是黑蚊,總是尋著裂開的泥縫向里叮咬,又騰不出手去抓去拍。我緊咬著牙齒,強(qiáng)迫自己堅(jiān)持,后來索性不去管了,多咬幾次也就疼麻了,一門心思只想著,如何快些將化肥種完好回家。
父親拄著拐杖,站在村口的柳樹下望了好幾次,每次望時(shí)都要向著大田喊幾嗓,聽不清在喊什么,聽得我心揪著一團(tuán)。時(shí)間過去兩個(gè)月了,他的腿明顯地好轉(zhuǎn)了。也幸虧是這赤腳醫(yī)生,起初我還不大相信。他治傷不開刀不手術(shù),靠一雙手捏合接骨,然后在傷處上夾板包藥。上個(gè)星期換藥,傷口愈合得很好,完全消腫了。王神醫(yī)說只要感覺不到脹痛,允許單腳下地來走一走,只是還不能取夾板。父親真下地來走了,還可以做些家務(wù),全家人似乎躲過一劫,歡天喜地像過節(jié)一樣。
四
好不容易將田中間的化肥撒完,時(shí)間就近中午了。我感覺又累又餓,拉住母親坐在田埂樹下躲蔭。這時(shí)候父親又出現(xiàn)了,他不能走太多路,不敢到田間來,只能站在柳樹下喊。
母親說:“大妹,天氣很熱,快叫你爹回去。知道他已經(jīng)把飯煮好了,等種完化肥咱就回去。”
我甩了一把脖頸上的汗水,摘下草帽給她扇風(fēng),說:“娘,要不等明天一早來吧,太熱了。”
母親說:“七九河開,八九雁來,節(jié)令不等人啊,上個(gè)星期就該種化肥了。再說明天……”她頓了頓,嘆口氣,“明天我得拉你爸去換藥,王神醫(yī)帶信說有病人來不了。你呢,你二弟三弟還等著送米,時(shí)間照應(yīng)不過來嘛。”
二弟和三弟都在鎮(zhèn)上讀書,一個(gè)讀初中,一個(gè)讀小學(xué)。最近幾年,大量青壯年外出務(wù)工,讀書的孩子愈來愈少,十里八鄉(xiāng)的小學(xué)合并了,讀書都得去鎮(zhèn)上。來回三四十里路走不下來,全都住校,自己帶碗帶糧食,學(xué)校統(tǒng)一蒸飯。我高中三年也是在鎮(zhèn)上讀的,為了省車費(fèi),星期六下午我一個(gè)人回來,星期天下午回校,有時(shí)沒錢趕車,不管背得有多重,那就只能是步行了。
“娘,就算明天不行,今天傍晚不行嗎?傍晚涼快些。”我還在堅(jiān)持,努力想讓母親改變主意。
“不行,哪有干活做一半留一半的。”母親斷然拒絕,“你不知道,干著活一歇下來,誰還想動。咱娘兒倆動作麻利些,最多再有一個(gè)小時(shí),就撒完了。”
這時(shí)候,又聽見喊。我和母親抬起頭,卻看見大伯提著裝飯的竹籃走到田間里來。
“你爸走不得,我把飯送過來。”大伯看見我,笑呵呵地,“不是在上學(xué)嗎?啥時(shí)候去?細(xì)妹子家的,看累成啥。”
“考完了,不去了,謝謝大伯。”我慌忙跑過去,雙手接住竹籃。
“大學(xué)生就是不一樣,說話做事都講禮。”天氣熱,他不怎么咳嗽了,“二小子和三小子呢?也考?”
我抿嘴直笑。母親接話說:“大哥,看天氣熱得,還辛苦您跑一趟。先前我和大妹還在說這兩小子呢。下個(gè)月才放假,明天得讓大妹送米到學(xué)校,就是沒有油葷,但家里有豆瓣和咸菜。”
“呦,那也行。眼下看著是苦了點(diǎn),不過都是這樣過來的。”大伯安慰似的,“就快熬出頭了,等三個(gè)孩子都考上大學(xué),你和弟就享福了。”
母親輕輕點(diǎn)頭。
母親捧著碗喝著稀粥,眼睛凝視著某個(gè)看不見的地方,漸漸就蒙上了一層薄薄的光澤。
五
母親說最多一個(gè)小時(shí),其實(shí)我們用了整整兩個(gè)小時(shí),種完最后一粒化肥,已經(jīng)是下午兩點(diǎn)鐘,田間最熱的時(shí)候。我都快累癱了,臉上火燒火燎似的,回到家后,向床上一倒,就動也不想動了。
迷迷糊糊睡了一覺,但沒多久又給熱醒了。屋里面既潮濕又悶熱,簡直讓人透不過氣來。天際隱隱傳來雷聲,似乎要變天。母親從地里割了一背簍豬草,回來時(shí)眉眼皺成一團(tuán),坐在墻角不出聲地切豬食。
父親明顯地覺察到了,拄著拐杖一高一低地走到大門邊,向著天空望了一陣,又回頭不安地看著我母親說:“要下雨?”
母親手上一抖,菜刀差點(diǎn)切到了手指。
我走出來喝水,邊走邊用蒲扇扇著風(fēng)說:“爸,下雨好呢,下雨就涼快了。”
父親“哼”了一聲,不滿意地撇著嘴巴說:“你個(gè)細(xì)妹子懂啥!才種完化肥就下雨,那不白種了?保不定還得買化肥,一千多塊錢啦。”
我有些委屈地說:“爸,我也只是說說,未必就真下雨了。好了好了,別生氣了,你女兒又不是雷公電母。”
我以為我的話能將父親母親逗樂,可兩人只是相對長聲嘆氣。于是我不敢說話了,吐了吐舌頭,趕忙溜到廚房煮飯去了。
天黑的時(shí)候,三個(gè)人正圍著桌子吃晚飯,忽然一陣電閃雷鳴,雨真下起來了。雨點(diǎn)“噼噼啪啪”打在房頂上,仿佛下冰雹似的,只一會工夫,屋檐就開始淌水了。
我不敢說話,只顧埋頭吃飯。
母親一直埋怨說:“怪我啊!我要是聽大妹一句話,再怎么著,也得省好幾袋化肥。”
父親嘆著氣說:“吃飯,興許就下一會呢。”
三個(gè)人在桌前悶頭吃飯,雨越下越大,完全就沒有停的跡象。劇烈的閃電帶著滾滾雷聲,仿佛要把房頂揭開來,而院子里,都快流成河了。
“不行,我得去田里一趟。”母親忽然站起來,尋出電筒,從墻上取下雨衣。
“你去干嗎?”父親瞪著眼睛,“你去了,能把化肥撈起來?”
“你別管……”母親聲音帶著哭腔,“就怪我,我要是聽大妹一句……”她的人影一閃,踩著水沖出去了。
父親直推我:“快去把你娘追回來,追回來!”
我看見墻上還掛著一件雨衣,趕忙取下穿上,冒著大雨向院外沖去。
六
我循著黑暗尋到田間時(shí),除了聽見震耳欲聾的雷聲,還有四周“嘩嘩”的水流聲。順著機(jī)耕道一路走過去,很多田缺口都在向外淌水,機(jī)耕道兩邊溝渠里的水不斷地上漲,就快漫上路面了。
我喊:“娘——”
隱隱約約有回應(yīng)。我奔跑著尋到大田邊,才看見母親將電筒放在田埂上,自己蹲在田里堵缺口。我家大田一共有三處缺口,為了保證水不稀釋肥料,也為了太陽烤曬消滅蟲害,缺口放得很低,最多不會超過五厘米。但這會,因?yàn)橥话l(fā)的暴雨,每家的田里都漲水了,都在向外面放水。照理,我家也應(yīng)該這樣的,可母親卻在向上堵缺口。
“大妹,那邊還有一處缺口,快去堵。”母親將電筒光一掃,向著一個(gè)方向指。
我飛快地向缺口跑去。我懂母親的心思,興許一會兒雨就停了,堵住缺口就等于堵住了化肥。
很快,三處缺口都堵上了。
“娘,上面還有兩塊小田呢。”我著急地說。
“先別管,守住大田。”
母親站在田里,焦急不安地看著水慢慢漲上缺口。我和母親早已全身濕透,衣服上、脖子上、臉上、手上全是渾水和稀泥,一股一股向下直淌。可為了堵住缺口,我們什么都顧不得了。
雨還在下,停不下來了。上面兩塊小田缺口完全沖開,水“嘩嘩”地流進(jìn)大田。母親舉著電筒順著田埂照過去,有段矮下的田埂竟也開始向外漫水了。母親將電筒往我手里一塞,瘋了似的跳過去,雙手撈起泥巴將田埂扎高。可是,扎高一處,水卻向另一處漫上來,扎高另一處,水又從別處漫上去。眼看著水已經(jīng)淹沒了秧苗,整條田埂都在向外漫水了。
這時(shí)候,大伯照看秧田正好路過。他看著我和母親仿佛兩個(gè)泥猴子一樣,直顧嘆氣地說:“弟妹,不能這樣啊,再不放水,大田就垮了。”
“垮了?可是才種的化肥……”
“每家都這樣,不放不行啊。”
母親忽然清醒了,著急地又去刨缺口。
母親說:“大半夜就起來,累了一天,太陽烤了一天……”
大伯說:“眼前保住田才是最重要的。”
“我要是聽大妹一句話,也不成這樣啊。就怪我……就怪我……”
我?guī)椭赣H去刨缺口。
我刨著缺口,感覺一把一把的化肥就像晶瑩飽滿的米粒從指縫間溜走,可是我抓不住,握不住。我心里一陣陣刀絞似的疼痛,不知不覺中,淚水就落下來了。但我沒敢哭出聲,我知道母親的心里更苦更痛,可是,憑著農(nóng)村婦女孱弱的肩膀,她還在支撐著一個(gè)家呢。
七
雨下了整整一夜,到第二天早上才停。
大伯來報(bào)信,邊說話邊咳嗽。
他說:“昨晚雨太大了,好幾家田埂都垮了,你家算好的。對了,鄉(xiāng)上派人下來統(tǒng)計(jì)損失,說是每畝田要補(bǔ)貼一百斤化肥,還得重新種上去。”
我起床后,大伯已經(jīng)離開了,也不知他說的話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再種化肥是否會錯(cuò)過節(jié)氣。父親拄著拐杖扶著墻壁走路,一步一挪的;母親則在廚房煮早飯,眼睛又紅又腫。我看著墻角放著一只背籮,里面裝滿稻谷,稻谷里塞著幾個(gè)洗干凈的黃瓜,還有兩個(gè)不大不小的玻璃瓶。一個(gè)玻璃瓶里面裝著咸菜,一個(gè)玻璃瓶里面裝著豆瓣,是要給弟弟送到學(xué)校去的。
吃過早飯后,母親幫我背上背籮。
我試了試,不算太重,我背得動。
“大妹,打完米把糠賣了,你坐車。”母親說。
我“嗯”了一聲,就背著背籮上路了。